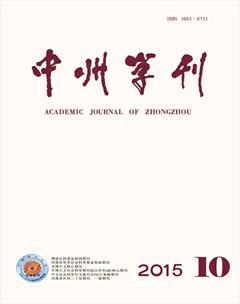孙奇逢与清初社会伦理秩序重建
张佐良
摘要:明清鼎革之后,明朝遗民在清初的社会伦理秩序重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明末清初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孙奇逢,贡献尤其突出。在清朝统治日渐巩固的情况下,他始终恪守民族气节,倡导经世致用,著述明道,化民成俗,通过大量著述来重建和维护儒学正统,并在日常生活中躬行实践,力图以儒家传统模式恢复和重建中国社会秩序。孙奇逢以其深厚的学术素养和高尚的品格德行,对清初社会伦理秩序的恢复和重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孙奇逢;理学;伦理秩序
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5)10-0116-06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易代之际,便会出现因眷恋先朝而不仕新朝的遗民。受“华夷之辨”的影响,这种情况在少数民族建立的新朝尤为突出。明清鼎革,满洲入主中原,时遗民数量之多,可谓一大历史奇观。在激烈的满汉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中,明遗民深感“天崩地解”、中原陆沉之痛。他们或以身殉国,或隐匿山林,或遁迹空门,或云游四方,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当时,在满洲贵族“家法祖制”政治文化重压下,世衰道丧,礼乐尽废,明遗民产生了“以夷灭夏”的强烈文化危机感。在此民族文化绝续存亡的紧要关头,以孙奇逢为代表的理学名儒隐居授徒,著述明道,“继绝学为世用”①,为清初社会伦理秩序重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隐不在山,亦不在水,隐于举人”:
终隐夏峰孙奇逢,字启泰,号钟元,生于万历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1585年1月14日),卒于康熙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1675年5月15日),直隶容城(今河北省容城)人。曾坚辞明清两朝征聘十三次,世称孙征君。晚年讲学河南辉县夏峰村,学者尊称夏峰先生。孙奇逢与浙江黄宗羲、关中李颙并称清初“三大儒”②,而“气魄独大,北方学者奉为泰山北斗。”③
燕赵一地,自古多慷慨豪侠之士。孙奇逢“少倜傥,好奇节,而内行笃修。负经世之学”④,“常欲赫然著功烈”⑤。他事亲至孝,曾为父母庐墓六年,孝行感动乡里,广为世人赞誉。天启年间,孙奇逢不避祸患,毅然挺身而出,与鹿正、张果中等营救遭阉党迫害的东林党友人,其“置身家性命于度外”的侠义之举,深受世人敬佩。时“海内高其义”,称孙奇逢、鹿正、张果中为“范阳三烈士”。⑥黄宗羲对孙奇逢的义行也极为赞赏,称“燕、赵悲歌慷慨之风久湮,人谓自先生而再见”⑦。孙奇逢亦有军事才干,崇祯十一年(1638)秋,孙奇逢率亲友至易州五峰山双峰村结寨自保,并制定规约,将众人团结起来。如《山居约》要求大家严同心、戒胜气、备器具、肃行止、储米豆,⑧以合力抗敌;《严樵牧约》禁止“戕伐人树株,践踏人种蓄”⑨,以与当地人和睦相处。在此期间,孙奇逢及同人修武兴文,备战之余诗歌唱和,使得双峰村在“干戈扰攘之时,有礼乐弦诵之风”。时南京兵部尚书范景文在征聘檄书中称赞孙奇逢:“孝子可作忠臣,文事能兼武备。”⑩这正是孙奇逢极具人格魅力和济世之才的真实写照。
遗民之义,在隐与不仕。孙奇逢17岁中举,一生隐而未仕。明崇祯年间,孙奇逢即以孝行、节义与理学名闻燕赵南北。作为“真孝真廉,有体有用”的地方人才,孙奇逢曾多次被举荐征召,但他均坚辞不赴。考其缘由,大致有三:一是父母见背,不乐仕进。孙奇逢曾称自己“幼读书,妄意青紫”。说明他年轻时颇有致身庙堂、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后因父母相继亡故,孙奇逢“痛未伸一日之养”,“形枯而神伤”,“自觉生气绝,耻事名利场”,“遂于仁(仕)进颇淡”;二是尊父遗训,不求他途。孙奇逢中举后,其父曾告诫说,“国朝重制科,不举南宫者,谓之半截功名,未免降志”,孙奇逢先后12次参加会试,终未成进士。是以“当路累荐举,先生每引此言,坚谢不出”。并表示“愿老死公车,不敢借途求用”;三是天下将亡,不可强仕。明末社会政治腐败,内忧外患交困。天启初年,友人茅元仪曾告诉孙奇逢,“天下大物,将有所属”,预言明朝行将灭亡。后人亦以为,孙奇逢“知天下将亡,而不可强以仕,此固其所以为明且哲也”。
清朝定鼎之初,需才孔急,诏举“怀才抱德,堪为时用”的山林隐逸之士。作为在京畿地区享有盛誉的乡贤,孙奇逢曾多次受到清廷官员举荐。如“国子监祭酒薛所蕴,以让贤荐;兵部左侍郎刘馀佑,以举知荐;顺天巡按御史柳寅东,以地方人才荐;陈棐以山林隐逸荐”。面对“新朝德意”,孙奇逢态度坚决,对所有举荐均以病辞。在辞疏中,孙奇逢称自己是“麋鹿之性,素不喜作官”,“五十余年老贤书,未尝就一官,迹似于隐,然实非隐也,病也。平生多病,兼短于才”,止愿“终老烟霞”而已。
“天下有隐居求志之人,方有行义达道之人。”孙奇逢认为,“贤者辟世,圣人遁世”,“辟世必隐,遁世不必隐。辟则入山唯恐不深,古人所以有不留姓字于天壤者是已。”他称自己是“树遁世之藩蓠(篱),差慰藏拙之门户”。孙奇逢指出,“遁非身隐乃心潜也,敛之则退藏于密,有暗然不显之意”。他认为,“遁则如天山之两相望而不相亲”,暗示着自己与清朝当局的关系,正如“天山之望”。时明遗民死节者颇多,孙奇逢认为,“学问以了达生死为极诣,然世之所谓了达生死者轻生轻死,非真能达生达死也。真能达生死者则生不徒生,而生足取重于世,死不徒死,而死足取重于世”。他说:“圣人无必欲死节之心”,“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断不至进退失据”。但“如其至此”,便当如孔子所言,“杀身以成仁,无求全以害仁。”对于此中大义,孙奇逢以宋元之际的文天祥为例加以说明,“文山以箕子自处,便不亟亟求毕旦夕之命。此身一日不死,便是大宋一日不灭。生贵乎顺,不以生自嫌;死贵乎安,不以死塞责”。这既是孙奇逢对先贤景仰的一种表达,更是在当时境况下对自己的某种期勉。
清军入关之初,即在京畿推行残酷的圈地政策。顺治六年(1649)十一月,孙奇逢因故园被满洲贵族圈占,“无田可耕,居乏屋”,决意南迁。次年五月,在河南友人的热情相邀下,孙奇逢留居河南辉县苏门。此处山水清幽,历来为君子高隐之地。晋之孙登、嵇康,宋之邵雍,元之姚枢、许衡等人均曾隐居于此。孙奇逢认为,“苏门山水佳胜,可堪终隐”。后友人马光裕以辉县夏峰村田庐相赠,孙奇逢遂率子弟耕读于此,终“以燕人而成豫籍”,开始了他在河南长达二十余年的隐居生活。
二、“学术之废兴,系世运之升降”:
经世致用明清鼎革后,社会伦理秩序重建成为当务之急。在清初独特的政治文化生态下,理学获得政府认同,担负起指导社会伦理秩序重建的重任。随着清朝统治的日渐巩固,明朝遗民中的一些理学家在现实中放弃了反清立场,通过倡扬主敬,崇尚躬行,致力于重建社会伦理秩序。
孙奇逢坚持理学主敬论,并从兴复礼教的高度进行阐发。他提出,“圣人以敬为传心之法”,“内圣外王,始终之要,只在一敬”,“千圣相传只是一敬”。孙奇逢将程颐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视为生平体认功课,认为“君子所以居敬,而收放心,学问之道在是矣。礼教之兴”,实有赖于此。孙奇逢提倡主敬,对臣子而言,就是要“事君之礼,无一事无一处不是诚敬之心”;对帝王而言,“则为忧勤惕厉”。主敬是孙奇逢重建和维护社会伦理秩序的重要理论基点。在实际生活中,孙奇逢提倡躬行实践,认为“学非口耳之学,其为躬行之学”,“学非躬行,说精说一,有何裨益?”“学问要从躬上得”。顺治七年,友人谓“此时诗文俱不中用,只宜著书立言,以发明理学为事。”孙奇逢答道:“莫把理学看的太板了。诗文岂遂妨于理学?若欲做诗人、做文人,终身亦不见有到家之日。若欲做学者,诗文寄兴,自不可少。但理学亦非口头讲说。古人知一分,行一分。今人知十分,行不得一分。全要在躬行上理会。”就清初社会而言,躬行的真义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按儒家纲常伦理尽忠尽孝”。孙奇逢为学,主张经世致用。他认为,“以经术经世务,正有用实学也”,“诵诗读书所以经世致用,嘘古人已陈之迹,起今日方新之绪,方是有用之学。乃有诵诗三百而诎于言,所谓儒生俗士不达时务者耳”。对于学术的社会作用,孙奇逢有言:“学问之事,要得趣于日用饮食,而有裨于纲常名教。”由此可见,孙奇逢倡导经世致用,实际上就是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严格遵循儒家纲常准则,进而恢复和重建传统社会伦理秩序。
孙奇逢非常重视学术发展与社会兴衰的联系,认为“世无治乱,总一学术”。他潜心理学,躬行之余,发为文章,试图从经世致用的角度阐明学术,救正人心。孙奇逢认为,“学之有宗,犹国之有统,家之有系也,系之宗有大有小,国之统有正有闰,而学之宗有天有心。今欲稽国之运数,当必分正统焉”。他一生致力于重建儒学正统,著述颇丰。时人称,孙奇逢“《读易大旨》成,而羲、文、周、孔之道传;《尚书近指》成,而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传;《四书近指》成,而孔孟之道传;《理学宗传》成,而后世诸儒之道亦无不传”。孙奇逢所辑《理学宗传》,“叙列从古名儒修德讲学之事”,以明道统,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陆九渊、薛瑄、王守仁、罗洪先、顾宪成等11人列为理学正宗,构建起合同朱陆的儒学道统。孙奇逢注重修史,意在总结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为社会治乱提供借鉴。所著《两大案录》“叙列从古君臣开创守成之事”,以明治统;《中州人物考》《畿辅人物考》叙列两地之“名公巨卿”,分理学、经济、忠节、清直、方正、武功、隐逸七科,“微显阐幽,大有功于世教”;《甲申大难录》叙列明崇祯帝及诸臣死事,“辑得此编明士气”;《取节录》叙列“名公硕辅,以暨农夫妇女”之贤者,以“兴豪杰而范世俗”。清人论其文章著述有云:“无一不关人心世道,脱非躬行心得者,乌能与于斯。”允为至论。
三、“教化行而习俗美”:化民成俗
晚明时期因其“专制统治的松弛化,市民社会的繁荣,反正统思潮的流行”以及长期的灾荒战乱,社会严重失序。“少凌长,小加大;淫破义,贱害贵。礼教尽失,人心陷溺又何可问?”重建社会伦理道德秩序,成为清初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
孙奇逢主张以儒家纲常重建当时的社会伦理道德秩序。他认为,“内圣之学,舍三纲五常无学术。外王之道,舍三纲五常无道术”,尧舜之道、文武之道、周孔之道,“似各不同”,“总之一归于三纲五常而已”;圣人之道、帝王之道、天地之道,皆“三纲五常而已”;“六经廿一史,皆三纲五常之事。离此,则旁门别派,其不流于异类者几希”,直视儒家纲常为世间最高法则。孙奇逢曾说:“纲纪二字,千古治乱攸关。家有家之纲纪,国有国之纲纪。无纲纪,则家非其家,而国非其国矣。”他明确指出,正人心维风俗,“只是令纲纪不坠”,“世而治,纲常在朝廷。世而乱,纲常留岩谷”,而当此之时,激扬纲常,维持世运,“端有望于岩谷之士”,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面对清初“人心之浇也日甚一日,风俗之薄也日甚一日”的社会状况,孙奇逢指出,“从来言治统道统,莫不骇为神奇高远之事。不知总只在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上。盖天下最神远之事,正从最平易中做出。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此治统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道统也”。他将治统、道统请下神坛,落实于平常生活,使人人皆知奋发而有所为。孙奇逢说,“道莫大于兴孝兴悌,事莫重于养生送死”,“风俗之厚,士君子与有责焉”,表示要以元代大儒姚枢、许衡在苏门化民成俗之心,“兴孝、兴悌、兴仁、兴让”,倡扬和躬行儒家伦理道德,以重塑社会风尚。
忠孝节义是儒家重要的伦理规范。孙奇逢在《中州人物考》中特设“忠节”一门,以表彰“仗节徇义之臣”。书中记杞县刘理顺甲申殉节,称其“理学节义,统体一身”,“不惭形影,不愧屋漏,数百年来,大有关于气运也”。孙奇逢认为,“气不激不烈,节不烈不扬”。他说:“予平生无他嗜好,独喜与人谈节义事,自壮至老不倦。”孝是人伦道德的根基。孙奇逢认为,“吾儒为世道计,自当阐幽以诏后世,或式其闾里、或闻诸有司、或书诸史册、或纪之文集”。此种事“一经拈出,人人有兴孝之思”。时杨村孝子赵廷桂家贫,不惜割股以疗母。孙奇逢赞道:“廷桂不读书之人,乃无愧于为人子”,遂作《助婚赵孝子文》以记其事,倡议众人“各省一餐之费,共成孝子之缘”,并筑孝子庐以居之。妇女节烈亦为孙奇逢所推重。他曾指出,“节无论士女,均不可一日去身者也。以今观之,居孀矢志,临难捐躯,女每有士行,而素好读书深明义理者,仓卒决择,反让妇人女子一筹”。孙奇逢认为,“守节之义,自古难之。第守于上成下赞之时,此节之难而易也;守于左倾右危之际,此节之难而难也”。士人之于气节,亦可作如是观。孙奇逢之所以对妇女节烈行为大力表彰,非徒以显其身后名,而是要以此激扬纲常伦理,进而“挽风之浇漓”,所谓“表行所以励俗也”。其诗有云:“衰残历阅九十一,生平最爱节义风。撑天柱地三纲立,巾帼冠裳功用同。”
针对清初社会伦理道德严重失范问题,孙奇逢从家庭、家教和家风入手,提出了立家规家训以教戒子弟,修家乘家谱以讲明仁孝的主张。他认为,人心淳于孝悌,风俗厚于兴孝兴悌。在孙奇逢看来,“一家之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健妇顺、和气薰蒸,吉祥莫大焉”,“一家之中,老老幼幼、夫夫妇妇,各无惭德,便是羲皇世界”。有鉴于“迩来士大夫,绝不讲家规身范,故子若孙鲜克有礼,不旋踵而坏名灾己,辱身丧家”,孙奇逢亲撰《孝友堂家规》,内云:“安贫以存士节;寡营以养廉耻;洁室以妥先灵;斋躬以承祭祀;既翕以协兄弟;好合以乐妻孥;择德以结婚姻;敦睦以联宗党;隆师以教子孙;勿斯(欺)以交朋友;正色以对贤豪;含洪以容横逆;守分以远衅隙;谨言以杜风波;暗修以淡声闻;好古以择趋避;克勤以绝耽乐之蠹己;克俭以辨饥渴之害心。”家规从个人道德修养等多方面对宗族提出了严格要求。在其《孝友堂家训》中,孙奇逢强调以修身为重,愿子弟“为端人,为正士,在家则家重,在国则国重,所谓添一个丧元气进士,不如添一个守本分平民”。孙奇逢以孝友堂家规、家训教育子孙,使得孙氏一门五世同堂,而“家无逆颜,人人尽让无争辩”。时人称“其家门雍穆,有礼有法”。国有牒,家有谱。孙奇逢认为,修谱乃“仁人孝子之所务”,“家家记述其祖父,人人叙录其子孙,仁孝同心,古今一也”。“谱之义,事关仁孝,自道丧教衰,斯义不明,而兴孝兴悌,所以难耳。”因此他大力提倡士人修谱,“每于亲知语次,多及修谱事”,“唯欲以一家之仁孝,兴一乡、兴一国、兴天下”。其弟子耿介认为,“夏峰先生酌家礼而极重族谱,示人知所本也”,“谱修则亲疏、厚薄、小大有等,尊卑、贵贱伦序有纪”,充分肯定了修谱对于维护社会伦理道德秩序的重要作用。
风俗多为地方山川钟毓,习尚渐磨所致。孙奇逢注重移易风俗,力图依据儒家传统礼法重塑地方社会习俗。在日常生活中,孙奇逢注意对“以行礼而反失礼之意”的社会习俗进行斟酌损益。辉县清初极重婚丧之礼,士大夫为流俗所困,往往“宁甘破家”。孙奇逢认为,自“大道凌夷,婚姻之礼似存而实废也”。他提出,婚嫁行礼勿论财,“从来凶终隙末,总皆起于论财。甚至琴瑟不调,亦皆由此。只不论财,彼此相体,久而益亲,便是真骨肉、便是好风俗”。孙奇逢以身作则,抵挡流俗,力挽颓风。为子奏雅完婚时,“四季衣服,两家共办。一切用物,随分酌量”;嫁女则“为布衣一件,嘱之归宁著此服,勿失吾家布素之意”。孙奇逢认为,“风俗之淳,人心之厚,必自慎终追远始”。顺治八年,孙奇逢之妻亡于苏门,友人劝他节哀以养身。孙奇逢说:“圣贤礼仪,天王律令,身形家范,到底不容屑越。”表示要恪守儒家丧葬之礼。孙奇逢移风易俗的努力,不仅是出于其士人身份的责任感,更是来自于对重建和维护社会伦理道德的使命感。
四、“被其教者,出为名臣,处为醇儒”:泽被后世
自孙奇逢倡道苏门,“读《易》百泉,韬光敛耀,静悟渊思,德益劭而学益邃”,广为世人所景仰,“上自公卿大臣以及儒生隐士,近自畿辅河洛以及齐鲁晋楚吴越之间,有志斯道者,无不负笈从游”。“于是苏门一席地,遂为海内理学渊薮。”
孙奇逢以诚意待人,对前来问学者往往因人训造,循循善诱。时“远迩负笈求学者甚众”,甚至“田氓野老”亦来“相质”,孙奇逢均一视同仁,不作歧观,皆“披衷相告,无所吝”。他“与臣言忠,与子言孝,鲑菜苦茗,常至更阑灯灺,犹娓娓弗倦。或千里书札问难,为之条分缕析,无不人人各得其所求”。因其学识渊博,阅历丰富,“有初接者,才品高下即衡量不爽,与之言论辄中隐微;若久与处,洞悉其生平者,即秦越人之视病,不是过也”。孙奇逢“乐易近人,见者皆服其诚信”,不以讲学自居,“不绳人以难行之事”,故人“聆其绪论,无不信圣贤之可为”,“即悍夫武弁,闻之倾心悦服,自勉于善”,由此而产生的教化影响广泛而深远。
孙奇逢一生门人众多。“《夏峰年谱》详载及门诸人”,仅列名者就有近二百人,而“在附案之外者甚众”。时人称,孙奇逢“亲炙之以成其德者,指不胜屈”,“被其教者,出为名臣,处为醇儒”。汤斌、魏一鳌、耿介、费密等人即为其中之佼佼者,“皆负重望于儒林”。汤斌,睢州(今河南睢县)人,是清初著名的理学名臣,仕至工部尚书。其学“大旨主于刻励,讲求实用,无王学杳冥放荡之弊”,深得夏峰真谛,被其视为衣钵传人。《清儒学案》称汤斌“承师法,而兼宗程、朱”。毛奇龄则以汤斌为“圣朝儒术之冠”。著有《洛学编》《汤子遗书》等。魏一鳌,字莲陆,直隶新安(今河北正定)人。曾任山西忻州知州,师从夏峰近三十年,“受性命之学,兢兢以存养省察为要”,著有《北学编》《雪亭梦语》《四书偶录》等。耿介,字介石,河南登封人,其学“以仁为主宰,而握其要于孝,专其功于敬”。兴复嵩阳书院,著有《中州道学编》《孝经易知》《理学要旨》等。费密,字此度,新繁(今四川成都)人,奉父命受业夏峰,为学力戒清谈,主张经世致用。康熙十二年(1673),孙奇逢作《怀友诗》云:“端亮曰潜庵(汤斌),当仁不肯避。明达莲陆氏(魏一鳌),到手无棘事”,“廉干推逸庵(耿介),此度博综备(费密)”,“诗中所举凡二十九人,皆及门高第也”。黄宗羲云:“北方之学者,大概出于其门。”康熙年间汪晋征说:“征君(孙奇逢)倡道于夏峰,潜庵(汤斌)嗣音于睢水,而登封逸庵耿(耿介)先生又同时后先颉颃于潜庵者也。厥后柘城窦敏修(窦克勤)氏、中牟冉永光(冉觐祖)氏,又皆砥砺躬修,精心著述,其所造已足为天下后世所信从。”“儒硕迭起,文献相望”。夏峰之学泽被后世,流衍极远。“大河南北代有其人,而其最著者,则禹州马平泉(时芳)、新郑王淡泉(轸)、河内李文清(棠阶)也。”
孙奇逢不但门人弟子众多,而且交游极为广泛。友人曾问孙奇逢:“先生五十余年老贤书,仕进之心,梦想不到,何不向深山穷谷避迹息影、鹿游石居?而尚寄托风尘之内,幽士为与,通人不拒,此于遁世之旨何如?”孙奇逢答道:“昔人结木巢楼、塞户窦伏、资身卖卜,傭工灌园,甚至为卒市门毁形易面。予高其谊,怜其情,然非予心之所乐也。”其所乐者何?孙奇逢云:“余少秉痴心,以友朋为性命,老更婆心,谓满街皆圣人,故于人之贫贱贤愚,凡有意于我而惠然肯来者,则不谆复而告语之,至于通人,尤是贤者,所当尽力,渠果肯来虚心,我辈何妨实心帮助,宽一分,民受一分之赐。”当时的著名学者傅山对此感悟颇深。康熙二年九月,傅山过访夏峰,归后记云:“顷过共城,见孙钟元先生,真诚谦和,令人诸意全消也。”“吾敬之爱之。不知者以为世法模棱之意居多,其中实有一大把柄。人以隐称之,非也。理学家法一味版拗,先生则不然,专讲作用。”傅山善于识人,眼光独到,深刻地指出了孙奇逢绝非隐者,其处世有原则,而为学重实用。
孙奇逢还和魏裔介、魏象枢等一些当朝理学名臣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魏象枢称曾“间尝驰书,请质所疑,荷先生手教还答,千里如侍几席”。孙奇逢在给魏象枢的复信中说:“窃思真儒名世,代不乏人。”“清明之际,道久矣,有所属矣。先生与柏乡公(魏裔介)莫逆,此事不任,还教谁任?”从上可见,孙奇逢之所以和诸多理学官僚联系密切,一是出于学者之间正常的人际和学术交往需要;二是孙奇逢以遗民之身兴学传道,拒绝与清政府合作,认为出则道不尊;三是孙奇逢充分认识到理学官僚的重要性,对他们寄予厚望。所谓“其为尊官也,方可以行道救民”,且“今天子宰相,皆有好学之意”,若“以二三君子,启沃于其间,则学之典也,在指顾间矣”。总的来看,孙奇逢是希望借助于身居高位的理学官僚来“正君心”,以推动清朝政权的儒学化,恢复理学在意识形态中的正统地位,进而按照儒家传统模式重建清朝社会秩序。
五、“天下望之如泰山乔岳”:道在夏峰
17世纪,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也是一个英贤挺生的时代。孙奇逢“生于燕,终于豫”,一生经历坎坷无数。但他意志坚定,始终砥砺前行。少好奇节,常“以砥柱中流自任,浩然之气百折不回”;老而好学,“念圣学久湮,慨然以绍往继来为己任”。时人谓其“始于豪杰,终以圣贤”。这既是对孙奇逢人生历程的经典总结,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孙奇逢在清初知识界的崇高地位”。
当明清鼎革之际,孙奇逢作为“硕果独存”的理学大儒,虽然“不偶于时”,然能不降其志,高洁自守,占据着民族气节和传统学术的时代制高点,“天下望之如泰山乔岳”。康熙十四年,门人戴明说指出:“夫子肆力潜心攻苦八十年,周规折矩,不失尺寸,故其生平出处常变,辞受取予有金元诸大儒所不及者。”此论极有见地。孙奇逢在清初的政治立场和学术活动,正是以元初诸儒为历史镜鉴的。孙奇逢曾说,“窃思宋元之际,道在许子(许衡)”,“许子兴学,诸儒蔚起,指不胜屈”,读《元史》,“不独识宋元之际,且以见清明之际也”。孙奇逢“蚤年潜心濂洛之学,以孝亲敬长为根基,以存诚去伪,戒惧慎独为持要”,后“以躬行为法程,以时习为工夫,以复性为宗旨”。其为学“旷览百家,独存正解,不求异不尚同,惟求合于圣贤之初意”,会通程朱陆王,一以孔子为旨归。夏峰之学,“专务躬行实践,不讲玄妙,不立崖岸,宽和平易悃愊无华”;夏峰之教,“达于朝,而上为道揆;施于野,而下为善俗”。汤斌称,“吾师夏峰先生平生大节伟然,其气力足以砥柱两间,而细行必矜,小物克谨,所谓豪杰而圣贤者也”。“当草昧初辟,干戈未戢,人心几如重寐,赖先生履道坦坦,贞不绝俗,使人知正心诚意之学,所以立天经,定民彝,不因运会为迁移,振三百年儒者之绪,而为兴朝理学之大宗。”
爱因斯坦认为:“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这一论断在孙奇逢身上得到了充分验证。梁启超指出,孙奇逢“非直其学之高,抑其节行又足以砥所学也”,“是一位有肝胆有气骨有才略的人。晚年加以学养,越发形成他的人格之尊严,所以感化力极大,屹然成为北学重镇”。孙奇逢关注国家与民族命运,一生致力于儒学道统传承和社会伦理秩序重建,不仅当时在学术界具有崇高地位,在社会上具有很大感召力,对后世影响也极为深远。按其时代贡献,大者有三:一是在明清易代之际,始终恪守遗民身份,显示和维护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与尊严;二是在满汉政治文化冲突中,致力于儒学正统重建,赓续和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与文化;三是在清初社会伦理秩序重建的历史进程中,始终高擎理学大旗,引领和推动了社会伦理秩序的恢复与重建。总之,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孙奇逢以其高尚的品行、深厚的学养、坚韧的意志,在清初社会伦理秩序重建中发挥了自己独特的历史作用。
注释
①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下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173、1243、1300、1300、886、795、821、370—371、126、771—772、338、1374、47、1084、288、1388、462、462、415、594、532、537、514、532、624、124、1349、208、1349、1388、1026、221、1361、1238、221、788、767、1053、1192、767、154、164、1243、1351、338、1168页。②“当是时,北方则孙先生夏峰,南方则黄先生梨洲,西方则先生(李颙),时论以为三大儒。”见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37页。③徐世昌著,陈祖武点校:《清儒学案》第一册,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5、2、391、34、48页。④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43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13100页。⑤方苞著,苏惇元编:《方望溪全集》卷八,《孙征君传》,国学整理社,1936年,第105页。⑥⑧⑨⑩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327、849—850、850、1394、1391、1437、1380、1391、1376、1329、878、695、719、15、617、717、1444、516、952、994、534、1427、1316、1313、1393、1342、857、1053、726、108、111、110、919、1053、882、880、880、854、854、1062—1063、1055、1053、1063、1333、1346、938—939、1333、731、1305、1333、1285、1321、1352页。⑦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修订本),中华书局,2008年,第1371、1371页。《清世祖实录》卷九,顺治元年十月甲子,中华书局,1985年,第95页。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上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84、136—137、310、452、136、471页。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188页。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7页。高翔:《在历史的深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63页。朱璘纂修:《南阳府志》卷一,《舆地志·风俗》,康熙三十六年刊本。河北省容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容城县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第630页。傅山:《霜红龛集》卷三十八,《杂记》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68、1068页。耿介撰,梁玉玮、孙红强、陈亚校点:《敬恕堂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25、170、538页。汤斌著,范志亭、范哲辑校:《汤斌集》上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18、260、287、118、1711、1921、118、118、147、118、112页。周际华修,戴铭等纂:《辉县志》,卷首,《桂良序》,光绪二十一年刊本。魏裔介著,魏连科点校:《兼济堂文集》下册,中华书局,2007年,第296、295—296页。汪晋征:《耿逸庵先生敬恕堂集叙》,《敬恕堂文集》,柘城窦氏藏板。魏象枢撰,陈金陵点校:《寒松堂全集》,中华书局,1996年,第570页。佚名:《皇明遗民传》卷三,《孙奇逢》,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2002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第180页。申涵煜,申涵盼辑:《申凫盟先生年谱》,中华书局,1991年,第16页。朱诚如主编:《清朝通史(康熙朝分卷)》下册,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第418页。赵御众等编:《征君孙先生年谱》,《戴明说序》,光绪间增刻《孙夏峰全集》本。嵇文甫:《嵇文甫文集》中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39页。爱因斯坦著,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75页。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5页。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8页。
责任编辑:王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