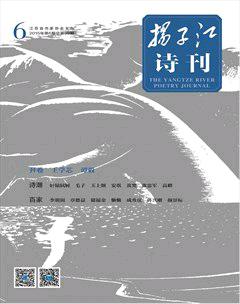(叙利亚)阿多尼斯的诗
欧阳昱译
阿多尼斯,原名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阿斯巴(1930年-),叙利亚著名诗人、思想家、文学理论家、翻译家、画家。迄今共发表《风中的树叶》《大马士革的米赫亚尔之歌》《这是我的名字》等22部诗集,并著有文化、文学论著近20种及部分译著。其旨在重写阿拉伯思想史、文学史的巨著《稳定与变化》分4卷出版后在整个阿拉伯文化界引起震动。近年来,他还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2009年3月作品首部中译本《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纽约墓地(节选)
1
到此为止,
地球画成了一只梨——
我的意思是说一只乳——
但是,乳和墓碑之间什么也没有
除了一个工程技术的诡计:
纽约
一个长着四条腿的文明,每个方向都是谋杀
都是通向谋杀之路,
从远处
传来那些即将淹死者的呻吟。
纽约
一个女人——一个女人的塑像,
一只手举着破布,被一张张纸
称作自由,而我们称那些纸为历史,
另一只手正勒死
孩子,他名叫地球。
纽约
呈沥青色的一具肉体。腰间系着
一根潮湿的皮带,面孔是一扇关闭的窗户……我说:瓦尔特
惠特曼会把窗打开——我说出了原初的口令——
但没人听,除了不在原地的一个神衹。那些
囚犯、奴隶、穷人、盗贼和那些
病人,从他喉中流出,没有开口,没有路。而我说:
布鲁克林桥!但这是把惠特曼连上
华尔街的桥,把草叶连上钞票的桥……
纽约——哈莱姆
身穿丝绸断头台走近的这人是谁?
埋在哈德森河一样长的坟墓离开的这人是谁?
爆炸吧,泪水的礼仪!交织吧,疲倦的事物!蓝色、黄色,
玫瑰、茉莉花;
光线在磨快它的针,而在针扎中
太阳诞生了。伤口啊,藏在大腿和大腿
之间,你射出烈焰了吗?死亡的鸟探看
你了吗?你听见了最后的阵痛了吗?一根绳子,以及
脖子缠住了郁闷,
而在血中,是时辰的忧郁。
纽约——麦迪逊公园大道——哈莱姆
懒惰像工作,工作像懒惰。复数的心塞
满了海绵,手吹着芦苇。
从一堆堆尘土、从帝国大厦的面具上,
升起了历史,一面面旗帜晃荡着臭气:
视觉不盲,盲的是头,
文字不秃,秃的是舌。
纽约——华尔街——第25街——第五大街
美杜莎的幽灵在肩与肩之间升起。
所有种族奴隶的一个市场。人们活得
像玻璃园中的植物。可怜的、不可见的动物
尘土般穿透空间的质地——螺旋的牺牲品。
太阳是葬礼的守灵
日光是一面黑鼓。
2
这儿,
在世界这块岩石发霉的这边,
没人看见我,只有一个就要被谋杀的
黑人,一只就要死的鸟;
我想:
一株寓于红花瓶中的植物,正在变形
而我,从门槛离开;而我读到
贝鲁特和别地的老鼠正大摇大摆
身着白宫的丝绸,以纸张武装起来
啃啮着人们;
读到字母表果园中的猪的余部
正在践踏诗歌。
而我看见:
无论我在哪里——
匹兹堡(国际诗歌论坛),
约翰·霍普金斯(华盛顿),哈佛
(坎布里奇——波士顿),安阿伯(密歇根——
底特律),外国记者俱乐部,联合国(纽约)的
阿拉伯俱乐部,普林斯顿,
坦普尔(费城),
阿拉伯地图是一匹马,拖曳着步子,而时光
松松地晃荡着,像一个马鞍,朝向坟墓
或朝向最黑暗的阴影,朝向死火
或朝向要死的火,揭示出卡库克市
阿尔达兰市和阿拉伯——非洲——亚洲其他这类堡垒另一维度的
化学反应。而这儿就是世界
在我们手中成熟。嘿!我们准备了第三世界、确立了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局,为的是确信:
1——在那一边,开一个爵士乐派对,
2——在这幢房里,有一个人,他除了墨水什么都不拥有
3——在这株树里,有一只鸟在歌唱;
而且也是为了宣布:
1——空间可以笼子或墙壁来量度,
2——时间可以绳子或鞭子来量度,
3——构建世界的制度始于谋杀兄弟,
4——月亮和太阳是两枚硬币,在苏丹的御座下熠熠闪光。
而我看见
阿拉伯的名字越过地球的全宽,比眼睛
更温柔,闪光,但闪的是失落星星的光,
没有祖先的星星,而它的根子在
他脚步里……
这儿,
在世界这块岩石发霉的这边我知道,我承认。
我记起一株植物,我叫它生命或我的国,死亡
或我的国——一股风,冻结得像一件斗篷,一张脸
谋杀了玩耍,一只眼,解雇了光明;
而我发明了你的相反,啊,我的国,
我下行进入你的地狱、我喊叫:
我为你提取了一种毒性的炼金药、我
复活你。
而我坦承:纽约,在我的国,石柱廊是你的
以及床、椅和头。而一切都
可以拿去卖:日光和夜,麦加的石头和底格里斯河
的水。而我宣布:尽管如此,你气喘吁吁地
赛跑,在巴勒斯坦、在河内、在北方和南方,
东方和西方,逆着那些没有历史但有火的形体。
而我说:自从施洗者约翰以来,我们每人都在大浅盘上
托着他切断的头,等待重生。
3
崩塌吧,自由神像,啊,钉在胸脯的钉子
以一种模仿玫瑰智慧的智慧。
风又一次从东方吹来,把帐篷、摩天大楼
连根拔起。还有两只翅膀在题献:
另一张字母表在西方的
地形学中崛起,
而太阳是耶路撒冷果园中
一株树的女儿。
就这样,我点燃我的火焰。我重新开始,构想、
定义:
纽约
一个草做的女人,而床从空虚晃荡到空虚
而这儿是正在腐烂的天花板:
每一个字都是正在堕落的标志;每一个运动
都是斧头或铁锨。而在右边和左边是肉体
它们渴望改变爱情视觉听觉嗅觉触觉
改变改变本身—把时光打开,像一扇门,它们打碎
并即兴地表演剩余的时辰
性爱诗歌道德饥渴言说沉默
并且否定所有的锁。我说:我要诱惑贝鲁特,
——寻找行动。文字死了,别的人说。
文字死了,因为你的舌头已经放弃了
为咕咕哝哝说话的习惯代言的习惯。
文字?你想揭示它的火吗?那么,写吧。我说:写吧。
我不说:咕咕哝哝。也不说:照抄吧。写吧——从
海湾到海洋,我听不见舌头,我读不到文字。我听见
复数的噪声。这就是为什么我瞥见不到任何人投掷火。
行动是一个方向和一个运动,但文字是所有方向
和所有时间。文字——手、手——梦:
我发现了你,啊,火,
你,我的首都
我发现了你,啊,诗歌。
而我诱惑贝鲁特。她穿我,我穿她。我们漫游
像一道光,问:谁看书?谁看见?幽
影为的是达扬,而毛没说错:武器就是战争中的
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人,而非武器,才是
决定性的因素;没有最终的胜利,也没有最终的失败。
我复述这些谚语和警句,就像阿拉伯人做的那样,
在各种颜色的黄金河流从源头流动的
华尔街。在它们中,我看见
阿拉伯的河流载着几百万卸下的四肢
成为献给偶像大师的献祭和供品。而在每一种
献祭和下一种献祭之间,水手咯咯地笑着,滚出了
克莱斯勒大厦,回到源头。
就这样,我点燃我的火焰。
我们住在黑色的怒火之中
这样,我们的肺部就能充满
历史的气息。
我们在黑色的眼睛中崛起,眼睛像被墓地围起
为的是打败遮蔽。
我们在黑色的头中旅行,为的是与
正在接近的太阳
并肩而行。
4
纽约
啊,蹲伏在风的拱门中的女人,
比原子还要遥远的一种形式,
在数字空间中小跑的一个斑点,
一条大腿在空中,另一条在水中,
说你的星在哪儿。战斗正在接近
草和电子脑之间。全部的生命都挂
在墙上,而这儿在流血。在顶端,一只头颅正把
一极接往另一极,中间是亚洲
底部是一具不可见肉体的脚。
我认识你,啊,罂粟花麝香中游泳的尸体,
我认识你,啊,乳房和乳房的游戏。我凝视
你、梦想雪、凝视你,等待秋季。
你的雪载着夜;你的夜载着人们
就像要死的蝙蝠。你内里的每一堵墙都是墓地,每一天
都是黑色的掘墓人
载着一块黑色的面包一只黑色的大浅盘,
还跟它们一起密谋白宫的
历史。
A-
有狗们像手铐一样连着。猫们
生出头盔和铁链。而在老鼠背上潜行的
小巷里,白人警卫像蘑菇一样
生育。
B-
一个女人在她的狗后面漫步;他备了鞍,像
一匹马,大步而行像国王;他周围
城市像泪水的大军在爬行。而在孩子
和老人被黑色皮肤堆覆盖的地方,子弹的
天真像草一样成长、恐怖击打着城市的胸脯。
C-
哈莱姆——贝德福·斯图维桑:人沙凝结成
一座座塔楼。复数的脸编织时代。垃圾是孩子的
筵席,孩子是老鼠的筵席……另一个三位一体
的永恒节庆:收税人、警察、
法官。吞噬之权威、灭绝之剑。
D-
哈莱姆(黑人厌恶犹太人)。
哈莱姆(黑人不喜欢阿拉伯人,他们还记得
奴隶贸易),
哈莱姆——百老汇(人们进入,像酒精和毒品蒸馏器中的软体动物)。
百老汇——哈莱姆,一座铁链和棍棒的集市,而且警察
是时光的幼芽。一颗子弹,十只鸽子。眼睛是盒子
与红雪起伏,而时光是一只跛着的拐杖。致倦怠,啊,古老的黑人,
啊,婴幼的黑人。一次又一次地致倦怠。
5
哈莱姆
我不是从外面来的:我知道你的积怨,知道
它有味的面包。饥馑什么也没有,只有突然的雷,监狱
什么也没有,只有暴力的雷霆。我瞥见你的火
在水管、面具、一堆堆垃圾的沥青下面
递进,冷空气的御座拥抱了它们
踏着流浪者的步子,穿着
风的历史,像鞋。
哈莱姆
时间在死亡的阵痛中,而你是时辰:
我听见泪水像火山一样怒吼。
我瞥见嘴巴狼吞人,就像它们狼吞面包。
你是抹去者,抹去纽约的脸。
你是暴风雨,抓住它,像叶子,把它扔出去。
纽约IBM+地铁来自泥,而犯罪从泥旅行到泥和
犯罪。
纽约=地壳上的一个洞,疯狂
从里面,一条条河地涌出。
哈莱姆
纽约是死亡的阵痛而你是时辰。
6
哈莱姆和林肯中心之间,
我在移动,一个在沙漠中失落的数字
沙漠被黑色黎明的牙齿覆盖。
没有雪,没有风。
我像跟着幽灵的某人(脸不是脸
而是一道伤口或复数的泪水;形体不是形体,而是一朵干玫瑰)
一个幽灵——(是女人吗?男人?女男人?)载着弓
在它的胸口,伏击空间。一头鹿
走过,它称之为地球。一只鸟出现了,而他
称它为月亮。而我得知,他在跑,为的是
见证红印第安人的复活……在巴勒斯坦
而它的姐妹中,
空间是一条子弹的绶带,
而地球是一面被谋杀的屏风。
而我觉得,我是一个在块体中涟漪着的原子
涟漪着去地平线、地平线、地平线。
而我下行进入谷地,拉长、平行地奔跑。
而我突然想起,要怀疑地球的圆形……
而在房里是雅拉,
雅拉是第二个地球的终结
而尼那尔
是另一个终结。
我把纽约放进括弧并在平行的城市散步。
我的脚重重的都是大街,天空是一座湖,里面
游着眼睛的鱼、猜想和云的
动物。哈德森河在鼓翼,像头母牛,穿着夜莺的
肉体。黎明接近了我,一个孩子在呻吟并
指着它的伤口。我呼唤夜,但夜不回答。
夜载着它的床并向人行道投降。这时
我看见它用风把自己覆盖,没有什么比它
更温柔,除了复数的墙和柱子……一声尖叫,两声
尖叫,三声……而纽约开始,像一只冻得半死的
青蛙跳进无水的塘里。
林肯,
那是纽约:倚着老年的拐杖
在记忆的花园里徜徉,而所有的事物都倾向于
人工花朵。而当我盯着看你,在华盛顿的
大理石中,并看见你的复体在哈莱姆,我
想:你即将到来的革命时刻何时到来?
我的声音响起:把林肯从大理石的白色中解放出来吧,
从尼克松解放出来吧,从警卫狗和猎狗中解放出来吧。让他用新的眼睛
阅读黑人之地“真吉”的领袖:阿里·b·穆罕穆德。让他
阅读马克思、毛泽东和阿尔尼法里读过的地平线,阿尔尼法里这个神圣的疯子
他把地球变得如此苗条,让地球寓于文字和
影射之间。让他阅读胡志明想读的东西,乌尔瓦·b·阿尔——瓦德:
我把我的肉体分成许多肉体……,乌尔瓦不知道
巴格达,而他很可能会拒绝到访大马士革。他待在
沙漠是另一只肩膀,扛着他,死亡的重担的
地方。他去找那些喜欢未来的人,太阳的一部分浸泡在一只鹿的
血中,他曾叫道:我亲爱的!他
与地平线作出安排,令其成为他最后的居所。
林肯
那是纽约:一面照不出任何东西,只照出华盛顿的镜子。
而这是华盛顿:一面照出两张脸的镜子——
尼克松和世界的哭泣。进入哭泣的
舞蹈吧。起来,还有一个地方,还有一个角色……我喜欢哭泣的舞蹈
它成为鸽子,鸽子又成为洪水。地球需要洪水。
我说哭泣,但我意思是愤怒。我的意思还是问题:
我怎么能说服阿尔——马拉接受阿布·阿尔——阿拉;幼发拉底河的平原
幼发拉底?我怎样才能用玉米穗
替代头盔?(必须敢于把其他问题向先知和圣书掷去),
我边说,边瞥见一片云以火的项链装饰自己:
我边说,边看见人们像泪水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