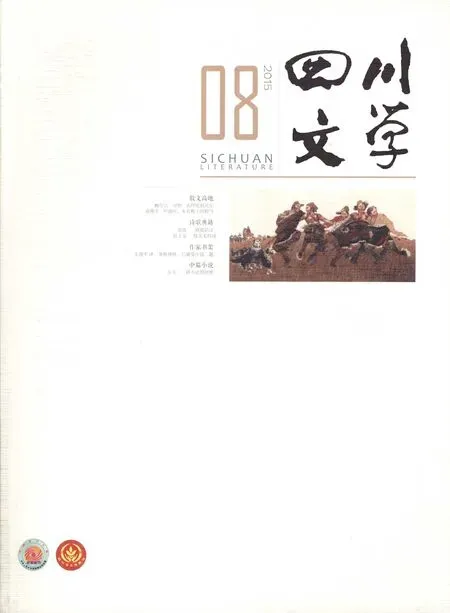英格博格·巴赫曼小说二题
○ 毛燕平/译
斯芬克斯的微笑
曾经有段时间,统治者们都深感岌岌可危——要讲清楚险从何来,简直就是白费力气,因为危险的根源总是林林总总不尽相同——让一国之君忧心忡忡的,正是所谓的动荡与夜不成眠。国王感受到的危险并不来自下层的臣民们,而是由上而来,来自那些无以言说的要求和指示,他对此并不明了,但深信必须遵从。
有人报告国王,宫殿的大道旁出现了幽灵。国王也不由得相信,要制服这个可能会带来危险的幽灵,就必须召唤他让他现身。随即不久,国王便偶然撞见幽灵。因其过于高大没办法一眼看完,故而无从推断他的身形相貌,幽灵让国王先行。起初,国王眼里看见的只是一只庞然大物,只见他拖着脚步蹒跚而行,之后才在姑且认为是脑袋的地方看见一张扁平宽阔的脸,这是一张某种生物的脸,这种生物随时可能开口提问,几百年来都没有人回答好他的问题,无人能针锋相对,回答亦徒劳无益:国王终于认出,这就是令人毛骨悚然古怪异常的斯芬克斯,他必须在她面前为自己的江山和子民的长存竭力争取。幽灵先开口说话,要求国王反驳自己。
“我们的眼睛看不透地球的内在,”她开始说道,“但你们也该去研究研究,跟我讲讲地球内在隐含的事情,谈谈地球的激情和坚韧。”
国王笑了,吩咐他的学者下属们着手研究,凿穿地球,揭开地球的奥秘,进行测量,并把测量所得用最精确的公式表达出来,精确度必须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记录结果的表格无比庞杂,书也越累越厚,国王通过这些资料密切关注着研究进展。
很久后的一天,国王终于可以要求随从们呈交研究成果。斯芬克斯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次完全经受得住考验的不同寻常的研究。只是在很多人看来,斯芬克斯并没有太在意研究的最后结果,不过倒也没有人在背地里埋怨她的这种态度。
一些人担心的是,很明显,斯芬克斯只是让国王误以为自己已经脱离险境,然后再利用谜样的表述让国王掉进圈套。这种顾虑马上就烟消云散了。第二个问题也明白无误、言辞清楚。这个不再神秘的庞然大物泰然自若地提出要求,要求国王查明地球表面的一切,包括环绕地球的其他天体。这一次,科学家们带着自己的团队各自进行研究,对宇宙展开闻所未闻巨细无遗的调查,研究了所有的行星轨道,所有的天体,以及物质的历史和未来,偷偷地有点幸灾乐祸地自以为把斯芬克斯能提的第三个问题先想到了。
连国王都觉得不可能还有什么能问的了,带着成功喜悦的心情将结果交予斯芬克斯。斯芬克斯闭上了双眼又或是她对此视若无睹?国王小心翼翼地揣测着她的心情。
花了很长时间,斯芬克斯才提出第三个问题,以至于所有的人都开始相信,由于过度地回答了第二个问题,他们似乎觉得自己已经铁定赢得了这场死亡游戏。注意到斯芬克斯略微抽搐了一下嘴唇,他们全都愣在原地,没办法开口问,为什么。
“你统治下的人内心是怎么样的呢?”在国王沉思的时候,她问道。国王兴趣盎然,想要有点戏谑地回答这个问题来拯救自己,不过立刻放弃了这个想法,转而寻求别人的意见。他让他的臣民们回答这个问题,转眼又因为要他来下令而勃然大怒。他们开始着手试验,脱掉人们的衣服;强迫众人丢掉羞耻心,督促他们忏悔暴露生活的点滴,剥离内心的想法,用各式各样的数字排列和字母排列整齐排列。
此事何时结束尚难预料,众人也有意不提,国王来到实验室,看起来并没有赢得大家最低限度的信任,国王似乎在思考更快更合理的做法。这一猜想在某天得到了证实,国王召来最知名的学者和最有能力的官员,召开秘密会议,命令他们立即终止这项工作,国王陈述了自己的想法,会议内容不得泄露,然而没过多久,这次会议的影响就波及到了每一个人。
不久之后,一纸号令传到各地,命令专门修建断头台,再挨个点名命令前往,这些人最终命丧断头台。
这一做法带来的觉悟是如此的惊心动魄,远远超出了国王的期望;尽管如此,为了此事能完美解决,国王依然毫不犹豫,为了不影响问题的解答,命令剩下的那些组织修建断头台的男人们在断头台上自行了结。
国王满心期待,一言不发地躬身来到斯芬克斯面前。他看着她的影子就像一张罩子一样盖在死去的人身上,因为影子将他们罩住,这些死去的人现在没法开口说话,。
国王喘不过气来,请求斯芬克斯接受答案离开此地,斯芬克斯做了一个手势,示意并不想要答案,这意味着国王也找到了第三个问题的答案,他自由了,可以支配自己的生命和他的国家的命运。
神秘之海翻起波浪,冲过她的脸庞。她笑着远去,国王还在回想发生的一切,她已越过边界离开了他的王国。
死亡将至
我们的祖母安娜和伊丽莎白已经去世好几年了,祖父弗兰茨和莱奥波德也已不在人世,表兄妹堂兄弟们都是知道的。我们是一个大家庭,不得不历数生与死,甚至也经历了住在司特腾的吉尔伯医生的去世,记住了在豪森死于谋杀的拜恩忒哈尔博士。我们逝去的亲人们分散地埋葬在不同的墓地,万圣节和祷告日,已经被有的人遗忘了,而另一些人却仍还能记起,比如莉泽表妹,又比如阿尔文娜表姐[ 原文为Cousine, 并未注明是堂姐妹还是表姐妹。]。在乡下的农庄,在城里的房子里都还放着贴满照片的相片簿,那里面仍有死去的亲人的照片,甚至还有他们在襁褓里的照片,比如恩斯特表弟,又比如莫特尔表姐夫,一个才二十岁,另一个三十二岁,这样的年纪就已死去,在战场上,又或者在山楂树旁,散步时被一只飞来的球砸中,详细的情况也不是很清楚。我们的悲痛也是不一样的,有些死去的亲人已经被我们忘却,比如米茨姨妈有天肯定也会想起,出生于我们家族的一个旁支的玛丽婶婶也已不在人世好些年了,米茨姨妈怕是早就忘记了这码事或者从来就没真正注意到,虽然她总是非常善于把事情记在本子上,尤其是生死大事。在这类事情上健忘的还有薇拉和安吉拉,尤其健忘的是欧根,他们脱离我们的大家庭独自生活,几乎不和其他家庭成员交换圣诞卡片,时常旅行或者身在国外,建立新的家庭,关于他们的消息我们只能从别人口中听说。
我们家庭的存在——这是唯一明显的法则——是因为死去的亲人,因为那些小菊花,是为了婚礼上的全套婚礼餐具、利口酒杯或者成套餐具,是为了衷心祝福,在特定的日子寄信送出的祝福,祝福新生命的诞生,祝福洗礼,还有生日的祝福和母亲节的祝福。死亡,疾病侵袭着我们的家族,也让我们永远无从理解死亡和疾病。
恩斯特的死笼罩着我们的家族,因担保造假他上吊自杀;四岁孩童瑞奇的死攫住我们的心,他卷进电动饲料切碎机的皮带,重伤致死。 我们的家族不是我们所有的人在一起,不是其中一个分支或一部分人,而是一块巨大的海绵,是记忆,汲取所有的故事而借此创造自己的历史。在海绵的最下层,在它的水分里,在它体内膨胀的记忆里,有我们每一个人,匿名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默默无名。
当死亡以一种在我们看来非常清晰的形象出现,当死神带走我们家庭的一员,我们就会熟悉死亡。躺在信箱里的白色信封,露出以前用剩下的带黑框的信纸,一封日常的信的最后一句带来这样的消息:“PS: 你知道吗,卡尔叔叔十天前因胃癌去世了,他受尽了折磨,这样也算是解脱了。”接下来,全家要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利,变戏法似的用几句话就说尽了卡尔叔叔的一辈子:曾在德国工作,然后娶了蕾西婶婶,喜欢扯自己的耳垂,晚上总在酒馆里打牌,周期性发作酒瘾,没有参加爷爷的葬礼,总是和汉斯叔叔起争执,为了花园为了水果吵个不停,卡尔叔叔天生一副好嗓音,喜欢弹琉特[ 琉特,一种形似琵琶的拨弦乐器。],还有,还有,还有卡尔叔叔现在已与世长辞,长眠于菊花束下,三十年前送的一套利口酒杯,如今只剩下一分钟的默哀,在两件事之间,两封从别处寄来的信,离世两相忘。
我们的家族,没有标准,没有限制,在生活中树立自己的准则,有人成就非凡,有人寂寂无闻,有人让家族蒙受耻辱,有人则成为累赘,还有那些私下流传的消息和背地里的议论,还有……死亡将至,了无尽头。人的记忆够不着的地方,有家族的记忆,密切而又狭隘,但是长久一些,可靠一些。匮乏中的可靠,为了小小的永生,半个世纪之后,也会忘记给最早死去的亲人捎去菊花,也会忘记照料那棵黄杨树。某种程度上,家族也会守护那个名字,只是没办法确切地说清楚,为何我们的家族只保留特定的名字,而没有别的名字。连通过结婚进来的亲人们也是如此,叫特鲁德,彼得,弗兰茨,很多伊丽莎白,很多蒂凡尼,约瑟芬,特雷泽,他们这些名字可都是在官方通过郑重的仪式取的。常见的名字,一直在用的名字,莉西和丽莎,斯特飞,芬妮和蕾西,安妮,罗西,艾迪,总是搅在一起。曾经有一次,我们的姓氏遭遇危机,彼得叔叔和一位自称叫玛丽的小姐相爱,那是在1925年,而恩斯特表弟在他死前的最后一次休假中带回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想娶一位叫卡琳的姑娘,这个姑娘来自汉诺威附近的于耳岑。这位卡琳姑娘在1957年来看望她死去的未婚夫的亲人们,逗留期间爱上一个从莱茵兰来的德国客人,最后和这个叫沃尔夫迪特尔的家伙一道回到了他们的地方,她的名字在那地方比起在我们这儿兴许更兴旺些。
我们家族至少出过两个谋杀犯,两个小偷和三个妓女,尽管没有人看出这些来,我们的家族依然为了历史和政治付出了自己的代价,这个家族,并没有事先约定,却在每一个党派里都有一个自己的成员,甚至多个。我们家族内部持有所有的思想,虽然不是用自己最擅长的表达方式,而是用一种最普通的方式,挑剔这些主张,熟悉这些观点,然后某一天,就有了自己的君主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然后出现了这样一个时期,在那个时期我们的家族出现了纳粹和反犹太主义者,出现了没主见的人,抢劫犯和谋杀犯,同时也有了牺牲者,有时有些人两者皆是,就像泽普叔叔,是国内的老党员之一,战争期间和党内的其他人因为一车木头闹翻,死在了集中营,他是什么的牺牲者,没有人知道……
然而我们的家族——终结了自己的魔法——对那些在他们的帮助、怂恿、助长下形成的思想毫无概念。我们的家族是一个没有头脑的巨人,蹒跚走过那些年代,砍掉的部分又重新生长出来。她是一个没有头脑的庞然大物,管辖政府各部,主管宗教、道德准则和法典,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令人敬仰的家族,经常被人挂在嘴边,看起来神圣无可指摘,这一切的一切,仅仅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有着许多分支的家族,因为有人在盖尔河边的灌木丛交配,因为艾迪叔叔和芬妮婶婶在特伦克造了个孩子出来。这一切给予了我们家族这样的权利,提出合法要求,拥有这个世界,没有旁人胆敢提出异议。我们的不神圣的神圣家族正所谓是不知者不罪,她不是单个的人们,而是所有人的整体,高高在上,得意洋洋地承载着我的名字。的确,我们是她的一份子,她比我们更优越,她不仅仅是一个构想,而是降入尘世的化身。
莉西姨妈要被送进一家养老院。罗西表姐生下一对双胞胎,异卵双胞胎,两个女孩,埃娜和阿尔文娜。谢天谢地。泽普叔叔今年已经第三次住进医院。有人住进医院,我们就会唉声叹气,整个家族都在叹息。疾病困扰着我们。疾病,如果不是如此令人悲叹哀痛的话,想必人们就会接受,好奇地去等待下一个人生病。因为罗西病重,埃娜婶婶不得不立即前往K市照顾孩子们。她写信告诉所有人,要去接替丽莎姨妈,还有大表姐范妮,最后是她把孩子们接到身边照看她们,直到罗西病愈。要是范妮病了,来帮忙的就只有麦扎姨妈,噢,这是不成文的规矩。一个家族里面,总有那么几个女性负责照看所有的孩子,撑过所有的病痛,负责施以援手,而其他在这方面不怎么帮忙的人,需要操心别的事情。比如表姐麦扎和维妮表妹负责的是不断制造禁忌和放荡的话题。整个家族总是坚持不渝地对这两个表姐妹的新老故事感到出离愤怒。麦扎离了婚,追求过牧师,和半个村子的人都上过床,还有,听丽莎姨妈说“没人再要她了”,从此以后她总是去勾搭那些途经山谷借道经过的意大利建筑工人和旅行者。维妮是最小的妹妹,已经第三次当一个已婚男人的情妇了。这个家族总是听到关于她的流言蜚语,也认清了她那让人诅咒的真实生活状态,全家只透露了一部分的真相,但是,家族内部越是冷酷无情地审判她,她就越沉迷其中。有人要接受家族内部的审判,总有控诉者和辩护人,还有观众,每个人在每次案例中的身份都不同,辩护人有时也会成为观众,控诉者有时也是辩护人。
控诉麦扎的人,对维妮漠不关心,只有年纪大的家族成员才会对所有人都十分严厉,只有死去的人才会被神化成模范。祖父们被神化了,而祖母们则完全不提曾祖辈们,他们被加以美化,成为一道远处来的光照进黑暗。
有时,年复一年,家族的一部分人因为其他人而感到羞愧。艾迪叔叔总在他妻子面前抬不起头来,埃娜婶婶为整个家庭而感到害臊,而艾迪表兄总是为艾迪叔叔、埃娜婶婶还有他们的孩子们感到羞愧,他们总是对陌生人,对县长、区法官还有避暑度假的人感到不好意思,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艾迪叔叔羞愧难当,是因为娜娜姑妈偷了地里的南瓜,那是埃娜婶婶的一个亲戚种的,他感到惭愧,还因为弗雷迪是共产党人,还翻过篱笆和避暑的客人大谈“正派的政府”,在退休的人和领工资的人当中注意到了靠养老金过活的泽普叔叔,只要弗雷迪一想起泽普叔叔的存在,他就羞愧得满脸通红,泽普叔叔曾经是纳粹冲锋队队员,在南斯拉夫参加过天晓得什么样的“行动”;泽普叔叔总爱谈起那个行动,总是滔滔不绝地提起那些导致战争失败的军官和犹太人,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给孩子们讲:奥地利是我们的故乡,但德国才是我们的祖国。他送孩子们参加了一个被禁的协会,他们又学着唱歌,打开旗帜,点燃营火,泽普叔叔之后也学了一遍这些,蕾西婶婶知道了这些事,摇了摇头,整个家族也都知道了,在严守秘密的条件下大家都知道:这事不会有好结果。他至少应该让孩子们远离此事。孩子们。埃娜婶婶说,这事已经变得有点严重了,她接着往下讲。所有的人都在说,伊尔克一直相信希特勒还活着,如今的报纸上天天都是连篇的谎话,说谎话的还有彼得,汉西说自己不想和政治扯上关系,伊尔克说,如果是跟俄国人对着干的话,立马又会扯上政治,他了解俄国人,他到过高加索山。我们家族里有五个人在俄国呆过,他们都了解俄国人,有两个去过法国,他们了解法国人,有两个到过挪威和希腊,他们知道有关挪威人和希腊人的一切。所有的人都不信任他们了解的那个国家,最终,我们的亲人们死在俄国,希腊,波兰和法国,我们再也没听到过一点关于他们的消息,库尔特和泽丕曾去过一次意大利,在阿普利亚巨大的墓地里在汉斯的陵前献了花,他们讲了这件事,大家再传言开去,那个墓地保存得不错,照管得也很好,真是无比地巨大,是一片宽阔的陵地,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宽广,保存也完好。
对于这种宽广[ 原文为das Grobe,对应上段中描写墓地宽广的grob,以及下句伟大的时代原文为grobe Zeit,均为同一词,在语义上有前后对应的意思,但是中文词汇中并不存在单个词能表达如此多的含义,故译文做了相应处理。],对于伟大的时代和一切巨大的事物,我们的家族有自己的理解。
说起我们家族的语言,如果不了解我们的语言,又怎么能理解我们呢?我们的语言古老原始,使用至今,有时已不能适应如今的话题,有时却又精准详尽成为诗的源泉。
我们家族的语言是:
弗雷迪一文不值。
埃娜一无所有。
汉斯说的话完全没有道理。
我们自以为聪明,我相信,有什么在召唤我,还有玛利亚和约瑟夫,他轻易就娶了她,婊子就是婊子,感谢上帝,还真是困厄之中饥不择食。我们的家族喋喋不休,整日滔滔不绝,在厨房,在地下室,在花园里,在田间地头说个不停,完全弄不明白,哪有那么多可说的。他们用他们的(……)[ 本篇作品创作于1965年前后,作者去世之后才发表问世,副标题标注未完,因而文中有几处不完整的地方。]充斥着世界。埃娜婶婶又和邻居站在篱笆边上嘀嘀咕咕,泽普叔叔在艾迪叔叔的酒馆里喝着大瓶的烧酒,他们聊个不停,聊干草料,聊发烫的线轴,聊天气,谈杀猪,谈镇上的事情,讨论租金,提起合作社。我们的家族总是设法谈起这世上的一切,对所有的事都要发表自己的评价,绝不失去自我,只偶尔有那么一小段时间,七年左右,禁止发表自己的某些看法,接着又开始继续喋喋不休,我们的家族怀有这世上所有的成见,哪怕本来没有,也要捏造出来,臆想出这世间一切的暴行,在我们的家族里,这意味着:她或者他要么应该被绞死,要么被指控,要么就是活该如此。我们的家族也有宽厚的一面,他们的眼泪,啜泣抽噎着诉说这世间的卑劣,为一头惨死的奶牛流下眼泪,为玛利亚婶婶,为麦扎的不幸,我们的家族最爱为自己哭泣,为他们自己的遭遇痛苦,几乎从不为别人的遭遇流泪,他们也有恐惧,并且享受着这种恐惧:你们听说了吗,他们在那个塔勒的肚子里缝了三针,就在奥伯塔尔。我们的家族享受着坏消息,曾经一座小城被炸,死亡人数不多,在他们嘴里死亡人数不断上升,从一百变成将近一千,恐惧渐增,他们在不幸中舒展四肢、津津乐道。为了不让别人错怪他们,他们自己的不幸也在增加,他们所受的苦痛……
在我们家族里,每个人都一定得长得像某人,这是规矩,从孩提时代就有人对他说,你长得像谁,长得像诺拉或者像葬在阿普利亚的汉斯叔叔,又或者长得像安娜姨妈。最大的荣幸是被告知长得像诺拉祖母。一提起她,到现在都还让人毛骨悚然,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家族大部分的秘密都在她身上。时不时就会有人提起,诺拉祖母是多么的冷酷无情,从来不会给孙子们哪怕一块糖,讲她是多么的孤僻,比别人聪明,总是读很多书,知道历史上发生的所有事情,知道哈布斯堡的鲁道夫、马克西米立安皇帝还有尤金王子的故事,她总是接连几个小时在她的卧室里大声清楚地读历史书,谁也不准去打扰她,没有人敢用du[ 德语中的人称分为非尊称du,用于关系亲密的人之间,还有尊称Sie,用于非亲非友的成人的称呼或尊称。]称呼她。到最后她觉得所有的人都想毒死她,总认为有人密谋害她。那段时间,埃娜婶婶总是哭个不停,因为她自己都快要相信,别的人也这么认为,想要毒死诺拉祖母的就是她,彼得叔叔再也不回家来,因为他不能忍受被自己的母亲当成是杀人犯……。
倘若我泄露出家族里的杀人犯,站出来指控他们中的小偷,我还能称得上是家族的一员吗?去指责别家的罪责和缺陷,倒是真有可能,可是对于自己的家族,绝对不会揭开他们已经溃烂的疖子,我绝不背叛我的家族。比起任何别的家族,我可以更好地观察他们。我睁大双眼看我的家族,打开耳朵听他们的语言,对许多被隐瞒的事情保持沉默。
我们沉默。我们的家族,散落在世间,如同夹杂在陌生生物中的人类,我们的家族拯救不了这世界。
我和我们。我所指的有时难道不是只是我们?我们女人和我们男人,我们的灵魂,被诅咒的我们,我们船员,我们眼瞎,我们眼瞎的船员,我们无所不知的人。我们留着眼泪,沾沾自喜,我们许下愿望,怀着希望,我们深感绝望。
我们不可分离,又各自分隔开来,我们还是我们。
我指的难道不是我们?向着死亡行进的我们,我们,死亡相随的我们,我们倒毙的人,我们无谓的人。
我们无时不在。在所有的思想里,我已不再能独立思考,在泪水中,不再为我一个人而哭泣。
我们祝贺新年。我们许下愿望,希望罗西病情好转,希望埃娜婶婶安详离世。我们害怕艾迪叔叔,我们时常忆起娜娜。
娜娜,一闪而过穿过房门的娜娜,搅着水的娜娜,赶牲口去水井的娜娜。娜娜,开口便是:啊,天啊,啊我的天哪。娜娜,精神错乱被绑在床上的娜娜。被送进精神病院,害怕饿死的娜娜,没人给她面包偷邻居地里南瓜的娜娜。这是不多的一点关于娜娜的记忆,也是记忆里有关娜娜的全部,她是谁,她是我们死去的亲人吗?
请不要惩罚她。请无论如何不要惩罚我们。被纵容的我们,被选中的我们,这就是我们,是想要践踏别人的人,是想要变得强大的人。一直是我们,我希望被我们所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