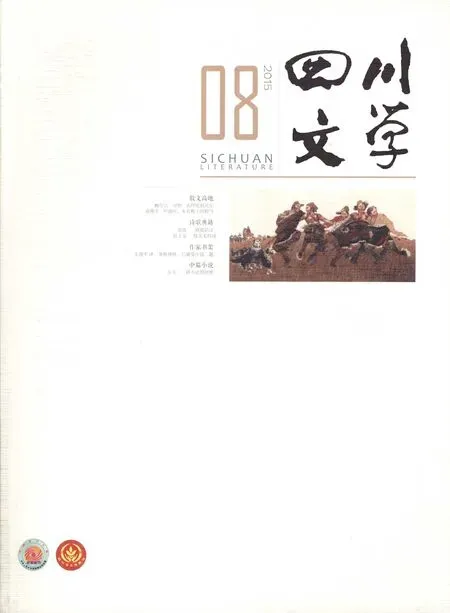看得见的河流(外一篇)
○ 李天斌
一
一个族群、一个家族的源头,往往都会伴随着一个神异的传说。或者是一匹孤独的老马,或者是一匹孑然的苍狼,或者是某只美丽的豹子和温驯的老虎,再或者是其它,这些灵异的动物,总是在最危难的时刻,将他们引向一个平安的处所。一直多年之后,这样的精神虚构仍然能成为心灵温暖的加持。在我家族所能追溯的初始,同样生长着类似的传说。只是在传说中出现的却是一条河流。据我的祖父说,当年他的曾祖父为了躲避仇家的追杀,凄惶之中前路难辨,只能沿着一条河流胡撞乱行,在穿越莽莽山林和荆棘后就落脚在了这黔地山野。从那时起,一条河流似乎便成了我们这个家族的图腾,在看得见河流的地方,似乎便是我们从肉体到灵魂的皈依之所。
“河流的方向,便是家的方向。沿着一条河流行走,你就会看到村子,就会看到家。”这又是我的祖父在多年之后告诫我的。祖父说这话的时候,关于一个家族的传说,已然显得有些缥缈。但一个可以凸显河流存在价值的现实是,整个黔地山野里还是地广人稀,山川阻隔。一个人在荒寂野地里行走,往往百十里路上还遇不到人家。但祖父却从不会迷路,祖父眼里始终有一条河流作他的指南针,沿着河流的方向行走,在那些孤独的白昼或是夜晚,在陌生的路上,祖父往往便找到了歇脚的人家。一条河流的方向,其实就是祖父内心的自我照亮。
祖父一生都没有走出过黔地山野,甚至只是其中一隅便是他全部的世界。但就只在那极小的版图上,他却已经精准地发现了蕴藏在大地深处的生命密码,并凭借着这密码,顺顺当当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我也曾不止一次地猜想,当祖父始终沿着一条河流行走时,当他将自己的心魂紧紧地贴着一条河流时,他或许便找到了生命最慰贴的部分,人生的一切便在一条河流的方向里显得温润起来。
仿佛家族的遗传密码似的,多年之后,每当我看到任何一条河流,我都会在某个瞬间涌起无限的温情和暖意,并想起关于河流与生命互相纠结的话题。
这样的冲动可以追溯到一首诗歌的源头。记得在读师范时,第一次读到唐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当“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的诗句在那花簇缠绕、水月共生中跌落眼底,一条孕育生命最初的宁静的江河,就在第一时间伴随着我家族遗传的密码,深深地击中了我。从此我更加笃信,一条河流的源头,一定就是生命的源头,——不单是我们这个家族,就连所有的族群,其实都完全可以在一条河流里寻找到自己的来去。在色彩缤纷的宁静之下,一条寂静无声的河流,早在默默中说出了生命的一切。
记得我还一边捧着一首关于河流的意识形态的诗歌,一边仔细地注目流过黔地山野的一条物质形态上的河流。我不得不承认,尽管我的家族来自远方,但当流淌到我这里的时候,我已经把这里当成了我的故乡,甚至是一缕浓浓的情结已经融入了我骨血的深处。但因为一份对于生命源头的好奇,在一缕关于河流的形而上的诗意里,我仍然会忍不住地抬起一双多少还显得幼稚的眼睛,一次次望向一条河流的苍茫遥远之处。但我看到了什么呢?一条从远处流过来,流过我们所居住的村子后,又向远处流去的河流,无论是其源头还是最终的归宿地,我其实都看不到。也或许是刚走到半路,一条河流便走失了,便失踪在了命运为它设计的陷阱里,并从此沉沦不知所终?那样我就更看不到了。在强大的时间面前,我们肉眼的可视范围毕竟有限得可怜。但我依然不甘失败地一次次固执地抬起我后来就跟着变得苍茫遥远的双眼,一次次把自己带进一条河流的深处,一次次在那里把自己的心灵交给一条河流。
好在我很快发现了一个秘密,或者说有效佐证了祖父言说的某个方面。我发现,在一条河流流过的地方,总是有一个个的村子像植物一样在沿河两岸不断长起来,先是一株,再又是一株,再下去便长成了一簇簇一片片郁郁葱葱的丛林,跟一条河流相互映衬。族群因为河流而生,在一条河流的滋润之下,族群最终也流淌成了一条河流,彼此都生生不息。就像爷爷的曾祖走了,爷爷却来了,就像爷爷多年之后也走了,而我也来了,沧桑变化的是时间和岁月,不变的是一条始终生生不息的河流,以及河流之上始终安放的家。
二
在读完《春江花月夜》之后,我还继续翻开了整整一卷诗歌的源头——《诗经》,在那里,我再一次看到了一条河流的源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又“苍苍蒹葭,白露为霜;有位伊人,在水一方”,在一条河流开始流淌的时候,我真切地看到了一个尘世的风吹水动——从一场美轮美奂的爱情开始,尘世便从一条河流里获得了它所应该有的颜色和质地,尘世在一条河流里,从此被赋予了生命的灵动和诗意。
也正是从一首诗歌开始,多年来我对一条河流的源头始终心怀神祗似的敬意,总想看一看蕴藏在那源头里的秘密,也终于怀着朝圣一般的虔诚,几乎走遍了黔地山野里的所有河流,但我终于是失望了。每一次,我都只看到了一条河流的一小部分,或者说我只看到了河流所呈现给这个尘世的一朵浪花,任何一条河流,都是以其博大和深邃映衬出了我作为一个窥视者的渺小和微不足道。直到2013年秋天,我才有幸亲眼目睹了一条河流的源头。只是,那条河流很小,还没有名字,唯一可以进入谈资的,就是在它流经的地方,却是黔地山野里生长起来的一座古镇,古镇的名字叫“旧州”。单是从名字上,就涂染了极为厚重的时间的颜色,透过干净清爽的阳光,甚至能嗅得到时间在古镇发酵的味道。还有更重要的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古镇,据说还曾经孕育了若干朝代的军界及政要人物,以及许多被时光淹没却又被记忆传颂的才子佳人,曾经明艳的风尘流光一度照亮了一座古镇以及流过古镇的这一条河流。朋友信誓旦旦地指着一堵山崖下的出水口说,这就是河流的源头,虽然肉眼看去没有惊涛骇浪没有波涛汹涌的气势,甚至只像山野乡间随处可见的一口山泉或是水井之类,但它的确就是一座古镇武运绵延和文采风流的滥觞。就在那一瞬间,我竟然有些莫名的激动,尽管这样的源头似乎“小”了,尽管这样的源头跟一首诗歌里的“源头”相去甚远,但作为第一次看到一条河流最初始的部分,我还是很愿意将其视为我生命中的一次奇遇。
只是我很快就觉得了沮丧。关于一条河流,我们真的能看到它的源头吗?或许一条河流真正的源头,其实还藏在那地底深处,藏在那千山万峰深处,一条河流的源头,或许终其一生,我们其实都无缘窥见其真正的秘密?黑人诗人兰斯顿·休斯在写到对一条河流的窥望时这样说:“我了解河流,我了解像世界一样古老的河流,比人类血管中流动的血液更古老的河流”,——其实,我一直怀疑诗人是将自己的洞察力夸大了。一条比血管还要古老的河流,一条比人类血脉都要丰厚和神秘得多的河流,又岂是我们的一双肉眼能看清的吗?
一条不可得见的河流的源头,使得一条河流从尘世和生命里流过的时候,确乎就被赋予了神祗般的地位。在此,我不得不再一次提到一条河流在我们家族传代中的重要位置。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在我还只有七八岁的时候,爷爷便迫不及待地把我引进了一条河流,一边是清波荡漾流淌不息的河流,一边是一枚红彤彤的夕阳对整个山野的照耀,一边是爷爷为一头刚耕完田土的黄牛清洗身子,再一边就是我站在河流里的耳濡目染,——时间流淌到这里,一条河流的图腾早已经跟泥土和庄稼密不可分,早已经将一条河流的原初意义推向了日常;这样的场景一直被爷爷认为是我们家族传代中走进一条河流的最早的洗礼,也携带着某人成年的标志。顺带说一声,在走进一条河流的生命旅途上,我们家族的“成年礼”总是在七八岁时就已经开始,比一般约定俗成的“成年礼”要提前了许多,许多年后我总会想,除了生活艰辛的原因外,或许还来源于对一条河流的宜早不宜迟的深情崇拜?在所谓家族的遗传密码上,及早地对一条河流的认识和亲近,显然已经成了一个明显的精神标签。从一条河流开始,我们的家族便这样一代又一代地走了过来,家族里的每一个人,便也这样获得了对生命的认知和诠释。不单是我们的家族,其实那些所有像植物一样在沿河两岸生长起来的家族,又何尝不是在这样的物质和精神的地理里寻觅到自己的位置呢?
只是,我们就真的因此而懂得了一条河流么?一条河流,当它在山川大地里波汹浪涌、翻云卷雾时,当它以其博大和深邃让一切都相形见绌时,一条河流在我们的心里,终究是一个不可知的秘密。
三
赫拉克利特说:“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孔子指着一条河流说:“逝者如斯夫。”两个国籍不同、种族不同的先贤,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河岸上却说出了相同的话,同时说出了一条河流所蕴藏的时间的本质和属性。
一条河流,它从时间里流淌而来,又向时间深处流淌而去。当我们站在河岸,试图要读懂一条河流时,除了那大面积的空茫的时间的逝痕之外,我们两手所能抓住的,连风的影子也早已空空如也。
不过,时间本身就是一部厚厚的历史。尽管在时间的所过之处,一切都将变得空茫,甚至是一切都将如流水一样了无踪影,但站在时间的面前,我们仍然能清晰并隆重地感觉到时间所呈现给我们的某种训诫。我跟我的祖父一样,虽然我曾经有幸走出过黔地山野,但毕竟也只是缘于某种偶然,而且这样的“走出”也只是绝无仅有的两三次,也还没有亲眼目睹到真正的大江大河,对隐藏在一条河流里的历史,我至今为止还只是停留在祖父的层面上,还不可能有像黑人诗人兰斯顿·休斯“当林肯去新奥尔良时,我听到密西西比河的歌声,我瞧见它那浑浊的胸膛,在夕阳下闪耀的金光”一样的铿锵的感受。但我不得不说,我却有幸地在黔地山野里遇到了这样一条河,河的名字叫“格凸”,它就流淌在那崇山峻岭、绿树环绕之中,它其实也不过是一条普通的河流,但我敢说,正是这样的一条河流,却让我在初见的刹那就已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关于河流与时间与历史的厚实绵密的气息。
现在,请允许我来具体说一说这条名叫“格凸”的河流。在这条河流的两岸,至今仍然居住着某个族群,跟我的家族相似的是,这个族群亦是因为某种逃避,在前路难辨的情况下一路凄惶地沿着一条河流的指引来到了这里。只是跟我们家族不同的是,当我们的家族在一条河流上定居下来后,我们便没想着再走了,一个明显的特征是,从爷爷的曾祖开始,大凡死去之后,都无一例外地埋进了泥土,一条河流之上的泥土,就已经是我们永远的家园。但格凸河上的族群却不一样,他们虽然在格凸河上定居了,但他们世世代代都想着要重返故里,他们的人死之后,绝不会埋进泥土,只在河流的某一段,寻了某个人迹罕至的山洞,然后将棺材放进去,总盼望着有一天能重返故里的时候,还带着这些死去的人一起沿着这条河流回去。千百年来,代代如此,人人如此,一具具不曾入土的棺材,一个个未曾安息的亡魂,一份沉沉的乡愁始终萦绕在一条河流的上空……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沉重并且无限悲情的故事;我更相信,在这样的故事里,一条河流的历史,已经将流淌在其间的时间涂染到了苍凉。而一条河流,它真的能安放我们的家么?在一条河流之上,我们真的能找到那回家的路么?
不过,作为一条河流,真正让我为之激情难抑的,还是后来我无意中所窥到的流淌在那时间与历史里的家国情怀和生死大义。后来,在我寻觅一条河流的旅途上,同样是在这黔地山野里,我竟然就遇到了这样的一条河流。河流的名字叫“灞陵河”,但 “此灞陵”却非“彼灞陵”,“此灞陵”所吸引我的,亦不是来自“彼灞陵”上“年年柳色,灞陵伤别”的诗情画意。此灞陵河吸引我的缘由是从刻在河流上的一副对联开始的,对联是:“以死勤事,如史阁部遗爱长存,抔土葬衣冠,二分明月扬州路;对宇望衡,此关将军大名不朽,河山留姓氏,千秋风雨灞陵河”。无需去追问曾在一条河流里发生过的是哪场战争,是什么朝代什么时间,也无需追问在一条河流里马革裹尸的是哪一位将军,甚至无需去追问这一场战事的真实性,只需看一眼那关山峻岭以及千秋风雨,就足以让我对一条河流心怀敬重、豪情顿生。我甚至想,较之于我的祖父,我其实是幸运的,在一条河流的时间和历史叙事里,我的祖父毕竟只看到了泥土和庄稼,只看到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常,我虽也没有比他太多的人生阅历,但至少从一首诗歌出发,我已然看到了他所不曾看到过的关于一条河流的别样的精神质地。记得去灞陵河是比2013年还要晚一些的秋天的黄昏,两岸山寒水瘦,芦荻萧萧,唯有一河的水依然奔涌不息,唯有一轮从古至今的月亮早早就挂在了那河水之上,暮色渐起中,我独自站在灞陵河上,尽管同去的朋友紧紧催促,但我就是不愿离去,一颗心,总随着那一河的水风起云涌,我总是想,日常之外,我们是不是确乎地还需要一些铿锵的叙事呢?从日常到精神的攀援,是不是就是肉体与灵魂的诗意飞升呢?……就在那一瞬间,我第一次觉得在原来,我以及我们的家族对一条河流的理解毕竟是浅了,也局促了。也就是在那一瞬间,我再一次想起了我的祖父,再一次想起我们家族的那一句遗传密码,只是若有可能的话,我想稍稍修改一下,我会对我的孩子说:“河流的方向,不仅仅是家的方向,还是精神的方向,它跟我们头顶的星空一样,时常照耀着我们。沿着它行走,就可以寻觅到尘世和生命的真正的秘密……”
残剩的古道
一匹瘦马,一簇枯藤,一株老树,还有一只黄昏的乌鸦,以及一卷瘦瘦的诗歌,在西风中一起向着天涯踽踽独行,这便是一条古道留给人们最深的印象了。此外,还有比如“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嘶”,“客情知古道,秋梦知长亭”等一条古道的意象,都让人忍不住向往。但我说的并不是这样的古道,我要说起的古道,它并不在一首诗歌里,它只在乡野山间,它似乎并不知道这尘世之外,还有离愁别恨,还有缱绻缠绵;尤其是现在,它就只在落日荒山、荒草萋萋里,一切只是剩下,一切只是最后的狼藉。
它甚至没有时间的概念。也许是从唐朝,也许是从宋朝,再近一些,或许便是从明清两代,一条古道便铺展在那山岭上了。它并不知道自己的前生,更无从知道自己的后世。时间在这里只是永远的模糊不清,风霜不断飘过,雨雪不断落下,一年比一年荒芜的草和芦荻不断长出来,虫鸣和鸟吟都更像历经了几世几劫似的,加之又没有什么遗迹可以佐证,虽然偶尔也会有一棵古树或是某座残存的寺庙似乎想要证明什么,但也由于没有充分的证据而作罢,时间在这里终究成了一个永远的疑问。
古道似乎还没有名字,倒也不是被风吹落了,也不是被时间丢弃了,而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名字的,或许是时间知道一条古道要遗失的宿命,所以就没想着要给它取名,一个注定要遗失的事物,倒不如让它自生自灭、寂寂无闻还要好些。我相信时间是睿智的,时间总能恰到好处地安排一切事物所处的位置。
古道一直就落脚在那里,没有抱怨,更没有跻身于繁华的奢想。当然,如果真的有繁华从那里照落,我想它亦不会拒绝,但亦不会欣喜,只默默地看一朵花落花开。包括多年后,当一切都只剩下了蔓草荒烟,当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寂寞地伫立时,我看到的,似乎也还是一条古道的宠辱不惊和去留无意。
时间已经大把大把地滑落,即使是曾经温润饱满的手掌,现在也是十指漏风,山寒水瘦。一条古道,尽管它再淡定,再如何地怀抱一颗出世之心,在这满目的破碎里,终究明显在一寸寸地坍塌,甚至在以分以秒为单位快速沉沦。这不,先前一条在山岭间绵延起伏的古道,如今竟然只剩下了中间这一截,而这一座山岭,显然也早在多年前就被遗弃了,早就已经没有人迹了,时间在这里,更像某种荒芜的存在。
古道前面隔着一条河流,河流上面原本有桥的,但后来桥断了,不知是焚于战火,还是原本那桥,因为不堪于那人世的承载而自己坍塌了,总之就这样把一条古道,生生地斩断了。古道后面,则是被一座新生的城市堵住了,说不定有一天,这中间剩下的,亦要被城市所占据,所谓鲸吞蚕食,正越来越成为时间君临万物的方式。
古道很险峻。尤其是连接着河流的那一面,一级级的石阶从山顶上垂直地坠落下去,河流那边便又是高耸入云的群山耸立出来,似乎除了河流能从谷底穿越而去外,就连飞鸟,亦会因此生怯的。古道四周,林木森森,遮天蔽日,想那些曾经的森森岁月,也一定会有声声猿啼,一直在映衬出一条古道的幽深和遥远。但这并不意味着古道就是与世隔绝的,相反,就在对面群山的半坡上,一直就散落着星星点点的村寨,一直就有人的气息在这里出没,——一边是荒野,另一边却又是人世的中心,两种背道而驰的景致,很奇异地在此相依相融,相生相息。
只是后来路终于还是荒了。后来,当一条古道不再具备作为路所应有的优势后,人们还是将其彻底地抛弃了。一份曾经想要的生死相依,终于在时间里显出了它的脆弱甚至荒诞。四周的林木开始汹涌起来,曾经被一双双脚掌踩踏得光滑圆润的石头,也被青苔和野草覆盖,一切终于都停在了从前,一切都显得旧迹斑斑,即使是某颗一直固执地要在往事中坚持的内心,也终于都像那些生锈的颜色,在对一条古道的凝望里而满目愁郁了。
这样的古道,从本质上说,它更像山野里的一枚叶,风起风落,始终都是阒无声息,始终都是顾影自怜。即使不说穷愁潦倒,即使不说美人迟暮,但一定都是芳华自开自谢,堪堪一份人世的被抛弃和被辜负。
有意思的是,就是这样的一条古道,却被后世的人们编出了无数传说,其中还不乏金戈铁马、英雄美人之类,最铿锵的,竟然还跟某个朝代的某个帝王扯上了关系,譬如说某个帝王在知道这一条古道的险峻之后,就欣然在京城里(其实是想当然)挥毫为其命名等,但真要拿出只言片语的证据,却又无从寻觅。好在人世懂得并能宽容这一切,一切日常中的生命,在骨子深处,其实一直都向往着一份壮怀激烈。尤其是,当一切都成为过往,当传说更像传说,一切是是非非的愿望,就更加有理由给予原谅了,并且,那生命的热度,毕竟也还能在一次次的传说中让人涌起无限的温情和暖意。
这样的古道,它还注定要成为某种荣耀的表达。不管传说是不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件,也不管一条古道现在的命运如何地零落,当时间的帷幕落下,尤其是,在除了一条古道之外,再也寻不出其它稍稍可以指点的风物时,一条古道显然就成了人们精神的坐标。只是这样的内心景致却也透出了人世的悖论——一方面,人们似乎是珍惜古道的,另一方面,却又是对其不断的忽略和破坏,终于使得一条古道,只以残剩的面目在时间里独自斑驳沧桑。生命的真相在这里就像时间模糊的面孔一样,清浊难辨、黑白交织,直至引人惶恐,引人迷失。
当然,在这样的古道上,也一定会有一匹马的身影在那里定格。但那马,一定不会是西风劲吹、夕阳映照天涯的那匹瘦马,也肯定不会是长安古道上马蹄迟迟的那一匹,最多就是一群赶着生活与日子不断上路的一队马帮,在他们的额头上,更多的还是来自地面与尘埃的凝视与抚摸。一队队马帮从山岭下的深谷一步步爬上来,不断地从这里翻山越岭,它们哒哒的马蹄声,一声声敲打在古道上,人们一次次目睹它们越过白天黑夜,然后在一阵阵的烟尘里绝尘而去,——说到底,一条古道所给予他们的最多就是有关日子与生活的某个梦境而已,如果真要说起诗意,最多是在多年后,当我一个人寂寂地在此伫立时,会恍惚觉得它们一定是从梦里走过的,——它们从梦里来,转身又回到梦里去,它们把一个时代、一群人的生活烙印在古道之上,就消失了,就像眼前,风吹尘走,芦荻苍苍间我始终无法握住一缕飘过的轻烟。还有就是,我可能会深入一点地觉得正是这样的梦境,让一条古道,不论世事如何变迁,都能恰到好处地寻觅到灵与肉在记忆中的最美好的位置,我想,这已经是对一条残剩的古道最大限度的精神虚构了。
不过,在这样的古道上,有一种生活却一定是不用怀疑的。虽然往事已远,虽然时间之痕迹已经模糊重重。但我始终相信,在那些曾经的岁月深处,一定有一群群的贩夫走卒和山民不断地从这里走过。只不过他们无论是跟诗意还是梦境都无关,他们或负重前行,或且行且歌,虽然他们也渴望一份人世的精彩,但我相信,当那个念头还没有完全明朗清晰时,就已经被这古道上的日升日落给湮没了。他们从这里走过,头顶上的日子便是那一步步的拾级而上和拾级而下,稍稍有点精神质地的,便是站在古道的至高点上,清干净嗓子猛猛地摔上几句,但那也仅是关于肉体、关于生活与日子的宣泄而已,诗意永远不会向他们靠近,至于秋月春风与是非成败之类的铿锵,那就真的更是传说般的遥远了。只是我又深切地相信,在这里,作为一条古道,它似乎更贴紧了地面与尘埃,似乎更能让我们看清时间与生命的某种真相,因为,能让肉身觉得真切的时时的疼痛,毕竟便是人世的真实与妥帖。我还想,或许也只有这样的场景,才是我们的顿悟,就好比那拈花一笑,就好比菩提树下笑看滚滚红尘的美好一刻。不过,如今这一切都被风吹散了,“风往尘香花已尽,物是人非事事休”,一条残剩的古道,秋草落黄之间,万叶秋声里,只寂寂地落寞于时间的深处,一切的悲欢离合都已隐入蔓草荒烟,一切的不甘或者从容都只交给风去诉说,一切的对于生死的了悟都已经彻底坠入虚无。只是在另一方面,我却又似乎相信,那些曾经活泛的气息一经荡漾,便一定契入了古道的深处。譬如一个深深地凹进石头里的马蹄印,我就固执地觉得它一定是一条古道有意地留在灵魂深处的记忆;又譬如一块石头上青苍的颜色,一定就是一条古道醒着的眼睛,——这样想的时候,眼眶便忍不住有些潮湿了,一切残剩的事物,或许它们真的都有着自己的坚持?只是在面目全非的时间里,他们已经没有任何想要表达的冲动?只是在熟视无睹的日常里,我们已经习惯了对一切事物的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