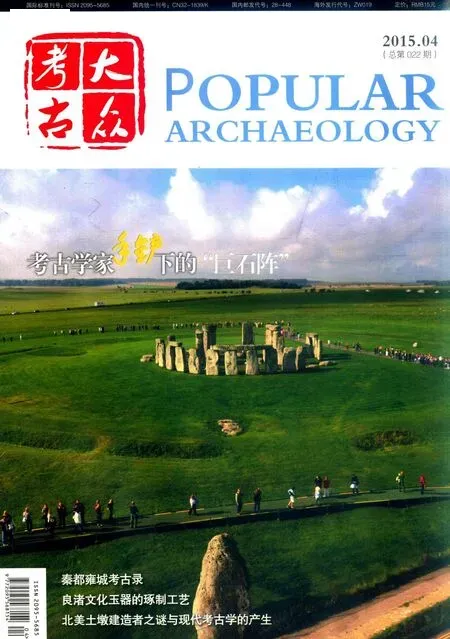沂南汉画像石墓“神人拔树”辨
文 图/王趁意
(作者为河南省收藏家协会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副会长)
沂南汉画像石墓M1 中室八角立柱南面中部绘有一“神人”形象,考古发掘报告对此描述如下:“其下一神人,赤上身,着短裙,佩长刀,赤足,力拔一棵大的上边有果的树”。从画像图案细节上看,所谓神人,一副西域胡人的特征,因此也可称为胡神人。乍一看,以上的描述和报告中拓片基本上是吻合的,但仔细看仍有几处不同:首先,胡神人直立,双手下伸合掌执物,而不是双臂环抱、弓腰低首要“拔树”的姿态;其次,胡神人脸颊上仰,双手下伸所执之物,竟然能够从手掌中穿过,由此看来它至多是个单株的“枝”或“柄”,不可能是大“树”;最后,细看“树”上的“果”,看不出到底是何种“果”,倒像是某种花。我带着这些疑惑,于2013 年3 月到实地考察时,专门对这一图像进行了观测、研究,发现原考古报告的描述和实际情况并不相符。
沂南汉画像石墓,亦称“北寨墓群”,位于山东沂南北寨村,时代为东汉晚期。1954 年华东文物工作队与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进行发掘。墓葬为石质多室墓,包括3 个主室、4 个耳室、1 个东后侧室。墓室中装饰有大量画像。门楣及横额上有胡汉战争、祭祀吊唁、车马出行、宴饮百戏等图像。主室四壁绘有历史故事画,还有大量神仙人物、奇禽异兽等图画。墓内画像多为减地平面线刻,艺术水平较高。1956 年出版由曾昭燏、蒋宝庚、黎忠义主编的《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
“拔树”还是“执莲”?
考古报告中描述的“一棵大的上边有果的树”,我们在画像原图上可以看到“果树”最下面部分延伸到胡神人的双手执握之后,仅露出端头的极少一部分。也就是说,这棵“果树”的下端到神人腰部可能就嘎然而止,并没有入土的根,因此可以初步判断,这不是一棵需要用力“拔”的树,而极有可能是一柄花枝。此神人双臂赤裸,双手平行往前下方伸出呈紧握状,没有丝毫双臂抱树躬腰弯背“拔树”的姿态和神情,而是一幅全神贯注向上托举“花柄”的神情画面。依照考古报告拓片,胡神人大腿部一侧,确实有类似“柄”的连接部分,但从画像原图可以清楚看出这个“柄”的连接部分是不存在的。客观地讲,这个所谓的连接部分应为工作人员拓印图片后没清净的墨渍;双腿右后触地的连接部分,实为身后裙子的飘带。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知八角立柱南面中部石刻为一幅胡神人全神贯注向上举托花柄的画面。
另外,还要解决“一棵大的上边有果的树”的“果”的问题。因为这幅纹饰是减地平面线刻,经历千年岁月的侵蚀,纹饰已有些漶漫不清,加上沂南汉画像石墓处于半地下状态,尚没有找到清晰的图片资料,只能用多幅现场拍摄的照片,从不同角度来说明这一问题。
从画像中可以看出,此神人双手呈握持状,双手之间是一花柄,此花柄向上超过神人头部后,开始一分为三,最左端的支柄为一枝双蒂花苞,中间为主柄,直达上端神人脚下,右端支柄有长条形苇叶状花叶。再经仔细观察,左边并蒂一枝最末端为一花蕊,有三重下垂花瓣,有莲芯,似为莲花。短株花苞纹饰有些模糊,但它和主枝是并蒂关系,也应为莲花才符合情理。中间一枝花柄为主柄,一直伸触到其上面另一图像的脚足部,呈支撑状。花柄最上端是一梯形莲芯,上有三支小花柄,末端有花蕊。最右边支柄上长有长条形苇叶状花叶。最关键的是,这株莲花上面的图像,正是那幅名闻遐迩的带背光的所谓“童子佛像”!我们把这两幅画面联系起来看,“童子佛像”恰好就站在这株莲花上,它明确清楚地说明“童子佛像”的佛饰内容,决不是孤立的,它和胡人、莲花之间是有机联系的整体,加深了其佛饰内容的内涵。
这种莲花造形并非完全写实之物,它是佛教初入中国时,工匠艺人对和佛有关联的莲花一种异化过程后的再创造。这种再创造后的造型一般不出现在常见的汉画像主题上,却往往和有浮图意义的胡神人结合在一起。例如,连云港孔望山X76 号与X65 号造像单手执莲的胡神人形象,二者同为孔望山造像,但两株莲花造型并不一致,莲花均有异化,异化的部位也不一致。以上二例,或许能对沂南汉画像石墓石刻图案中关于“异化莲花”的描述做一注脚。
更有说服力的案例是远在上千公里外四川出土东汉末期、三国时期的摇钱树。这种摇钱树是由枝叶和树干两部组成的,树干上往往有佛像。例如四川安县出土树干佛像与两侧的胡神人;四川梓潼出土树干佛像与右则的胡神人执莲图,值得注意的是异化的莲花和莲叶。另外,有些摇钱树枝叶纹饰上也出现有佛像。
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些枝叶纹饰上经常有莲花纹饰与佛像相伴,有单独出现的,也有和神像(佛像)一起出现的;有单株的,也有多柄的。这些莲花造型和远在千里之外的沂南汉画像石的莲花在造型上有很多类同之处:
一方面是莲叶的造型。莲叶呈大阔叶状是常识,而摇钱树上的荷叶却是长条形的苇叶状,请注意这些苇叶状莲叶和沂南汉画像石墓胡神人执莲的苇叶状莲叶相比较是何等的相似。摇钱树上的这些图案已被相关学者确认是莲花纹饰。二者远隔千里,它们的关系很难用“巧合”来做结论。另一方面是以上图像凡是执莲者大都为胡神人,且都为恭奉姿态。最典型的是城固和安县两个地方各有出土的“枝叶佛像”,左、右两侧手执长柄三蒂莲的胡神人形象,这和我们前面讨论的沂南汉画像墓手执三蒂莲的胡神人形象如出一辙。二者的主题类型也几乎雷同——胡神人侍佛图。胡神人手持莲花由下朝上,或力撑、或高举莲花,向佛像呈仰视恭俸状。
佛教造像还是道教造像?
四川出土的摇钱树神像和沂南汉画像石墓中室八角立柱画像南面最上端的“童子佛像”的性质尚有争论,有学者认为这都是佛教造像,但也有观点认为此二主题是道教造像。为了探究此类造像究竟是道或是佛,我们不妨先来了解一下相关的背景。
孔望山摩崖造像,位于江苏连云港南孔望山南麓西端。一般认为镌刻于东汉时期。有摩崖石刻人物100 余个。造像内容分为佛教故事、本生故事以及世俗生活故事。另外还有与道教有关的人物像。为现存时代最早的摩崖造像石刻,是研究早期佛教图像的重要资料。
摇钱树(或称“钱树”)是汉代墓葬中的一种明器,因其树枝上挂满古代流通的方孔圆钱,所以被人称为摇钱树。主要出土于四川、重庆地区,在贵州、云南、湖北、陕西等地区也有少量发现,时代可延至三国时期。摇钱树由陶质(亦有石质)树座和青铜树干及枝叶组合而成。其树座、树干和枝叶上都有许多图像,主要为钱币、神仙、神兽和仙境等内容。
山东沂南是太平道教长期流行的地区,与其几乎同地、同时的连云港孔望山,均是东汉晚期太平道教派的核心区域。孔望山摩崖造像性质为佛教或道教造像也长期争讼不下,近期出版的《连云港孔望山》一书,已把孔望山造像群定性为表现老子化胡过程中的道教人物造像:“孔望山崖面造像虽然存在目前尚不能解释的图像,但主题上应是以‘老子化胡’的形式来尊崇老子的艺术表现”。虽然该书仅是一家之见,但是我是赞成这一观点的。
我曾撰文指出沂南汉画像石墓中的“童子佛像”长有胡须,很可能是“老子化胡”,即兼具道佛因素的人物(见本刊2014 年8 月刊《沂南汉画像石墓“童子佛像”辨》)。类似于沂南汉画像石墓中的胡神人执莲图却又偏偏出现在千里之外的川、陕、贵、滇等地的摇钱树上。而上述地区是东汉晚期两大道教之一的五斗米教的核心区域,二者在同一主题的表现手法上如此相似,其内在有没有什么联系呢?我认为最少有几点是可以讨论的:其一,二者的流行时期都在东汉晚期至三国以降,这就为二者或相互传播、或相互影响创造了客观条件;其二,二者都和道教的流行有着密切的关系,山东沂南是太平道的中心流行区域,四川、陕南是五斗米道的中心流行区域;其三,史料记载五斗米教教主张陵就是江苏丰县人,离沂南北寨村仅百余公里,他在汉顺帝(126~144)时入蜀,于四川鹤鸣山创立了“五斗米教”,之后祖孙三代(张衡、张鲁)嫡续相传。张陵就是后来被称为“张天师”的张道陵,是西汉开国名将张良之后裔。如果说家乡的道佛文化对张陵祖孙三代一点影响都没有,是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的。美术史家巫鸿教授就认为道教是从东部沿海地区传入四川的。他还更明确指出:“五斗米道所奉经典来自东部,其创教人张陵亦来自汉代画像最发达的山东西南部。”
现在已有不少学者主张四川摇钱树佛像的研究和身份的确认,应和四川道教流行的大背景相联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霍巍教授提出,对于四川摇钱树佛像“有必要突破过去只从佛教传入的单一思路去加以认识的固有模式,而应当联系四川地区的早期佛道关系,早期道教造像的起源等多方面的因素加一综合研究,或许才能取得新的进展”。
结合以上早期道教在四川流行的大背景,巫鸿更是言之凿凿地说:“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四川所发现的公元2~3世纪的‘佛像’,实际上是当地道教美术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其把它们叫做早期佛教图像不如把它们称为早期道教图像。”根据我所掌握的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上述观点我是赞同的,并在以后的研究过程会逐步深入发表这些实物,并结合实物阐述、论证这一观点。
沂南汉画像石墓中室八角立柱南面中部石刻上“有佛背光的童子立像”具有浓郁的老子化胡的道、佛色彩,与四川摇钱树佛像二者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有雷同之处。现在,我们通过实地考察把沂南汉画像石墓考古报告中,对胡神人形象的不当描述匡正过来,并且把沂南汉画像石墓胡神人执莲图和四川摇钱树佛像和胡神人执莲图有机地联系起来,对于研究早期道、佛二教在东部和西南的传播,打开一扇明亮通透的学术之窗、信息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