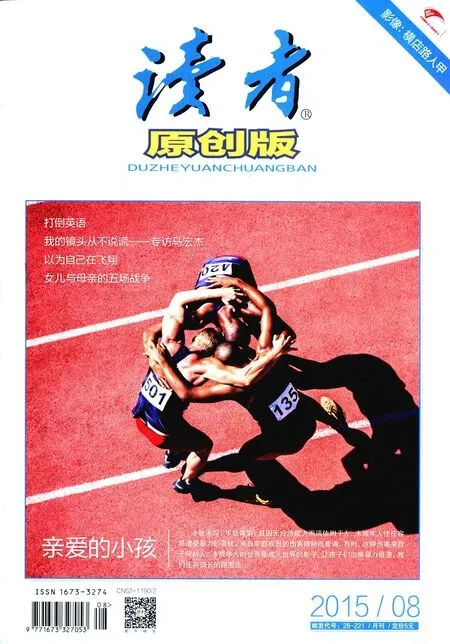石头记
文/图 陈蔚文
石头记
文/图 陈蔚文
1
许多年前,我读过三毛的不少书,其中有一本书叫《我的宝贝》,专写她的一堆物件,手工刺绣、陶器……写她行走世间与它们结的缘。对彼时人生逼仄的我来说,真是些奇妙的体验!一个黄皮肤的女子讲述“物”的故事,同时也指认更辽阔的世界给我们看。

那些对物件的描写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写石头。有一次,她以为跟自己隔阂很深的父母竟捡了两块石头回来给她,在那洗刷半天。
“‘你以前不是喜欢画石头吗?我们知道你没有时间去捡,就代你去了,你看看可不可以画?’妈妈说着。我只是看着比我还要瘦的爸爸发呆又发呆。一时里,我想骂他们太痴心,可是开不了口,只怕一讲话声音马上哽住。这两块最最朴素的石头没有任何颜色可以配得上它们,是父母在今生送给我最深最广的礼物。”
我和三毛一样喜欢石头,不知是否与我在江边度过的童年,以及那个古老的童话有关。那个童话是这样的:三个从战场上活着回来的士兵对村子里的人说,他们用三块石头就能做出一锅鲜美的汤。不过,要是加点儿盐和芹菜,味道会更好……就这样,加进锅里的东西越来越多,直至三块石头真的煮出了一锅好汤。
直到现在,我仍相信除了食物以外,锅内的石头也有某种魔力。
2
十几年前的炎夏,有一回路过花鸟市场,路旁有卡车装了车石头在卖。卖石头的人面上风霜沉重,蹲在车旁吸烟,像穿越了大漠荒原,误入这城市腹地。那些灰白的石头,有层次丰富的纹理,形如山高千仞,它们应当可以做出好盆景,却无人问津。等待这些石头的,似乎只能是静静地在烈日下被炙烤的命运—和将它们运来的人的命运一样。
我挑了七八块买下,最重的一块有十几斤。在家里阳台上安了几排木架,想着用来搁石头,挑了几块小的石头摆上,又在石头上面摆放了微型钓鱼翁、小青蛙……石头活过来了!你看,渔翁正在江畔礁石独钓寒江雪,蛙在田垄间欢快吟唱—任何“工艺品”都不如这些石头活泼、有生命力。
去年夏天去了加拿大的一座小城,那里有几家专售石头饰物的店,鹅卵石粘的台灯、石头拼贴画、小石头做的杯垫……打磨机哗哗响着,边角料被切割抛光,制成不同形状的挂坠。那些石头,竟比宝石更迷人可爱。而在一家博物馆外,我看见大堆淡紫色的石头,蹲在那儿看了半天,极想带走几块,无奈行李已满。由此也明白,石头是以自身的重量系牢与故乡的关系,轻易不愿被带往异乡。
3
参加一次山中笔会,捡了几块溪涧中的石头,同团的朋友J也帮我捡了几块,不想他自此萌生兴趣,成为爱好者,回去还在当地成立了一个爱石协会,有空就领着石友们四处捡石,乐在其中。
有一次开会他带了些石头来,有一块据说是某位画家盛情给画的,石上柳绿花红。我想起多年前看的三毛的《石头记》中她画的那些石头—“夜来了,荷西睡了,我仍然盘膝坐在地上,对着石头一动不动地看着—我要看出它的灵魂来,要它自己告诉我,藏在它里面的是什么样的形象。”
我也想画石。不是柳绿花红,是三毛笔下的那些石头。
正午,拉上朋友去江边捡石头,一堆堆石头看上去乏味。这些石头能画成什么样呢?
捡了一堆回去,细细观察。有块椭圆形的,颇似鱼,再打量,石上有小块鼓起似鳍,前端有道裂缝正似鱼嘴。用白色颜料勾了鱼眼与几片鱼鳞,一条史前的鱼现身了!如庄子《逍遥游》中说的“北溟有鱼”。
另一块土黄色的石头上有几条杂色凸起,择两条做莲茎,绘了高低两朵白莲,莲茎上略描几点金,一幅苍朴的莲图。
“我们希冀透过人的面孔得到的秘密和狂喜,也可以从石头那儿知道。”加缪在某篇文章中写道。
正是这样,慢下来,看石头开出花。这种“相认”和人与人的缘分一样—有些遇见一片混沌,对视再久也是枉然;有些遇见,则让人心生温暖。
画好的石头被朋友要去一些,包括本想自留的一块。有不舍,知道再不会有相同的第二块,那些凸痕、苔迹……每道纹理都是造化予以。这哪里只是石头呢?物里倾注了情,便有了灵性。一旦失散,也同与人失散一样,有无以言表的失落。
4
读白居易的诗,才知这份“痴”香山先生早有体会。
“苍然两片石,厥状怪且丑。”诗人拾到两块石,洗刷掉泥垢,当作从天而落的宝贝,并赋诗《双石》一首:“人皆有所好,物各求其偶。渐恐少年场,不容垂白叟。回头问双石,能伴老夫否。石虽不能言,许我为三友。”
万物有灵,石亦然。它们于山川育化,听凭各自下落。运气好的,遇上诗人这样的“三友”,人石相伴,暮晚有情。更多的石头,栖身荒野滩涂,或成为建筑物的一部分。
愈加珍惜与我有缘之石。万古洪荒,它们能落于我的柜中案头,是要涉过多少缘分的山水?它们沉默不语,见证的世相却以千百年计。
面对一块石头,你知道了守口如瓶是最高的美德,知道了伟力往往栖身于卑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