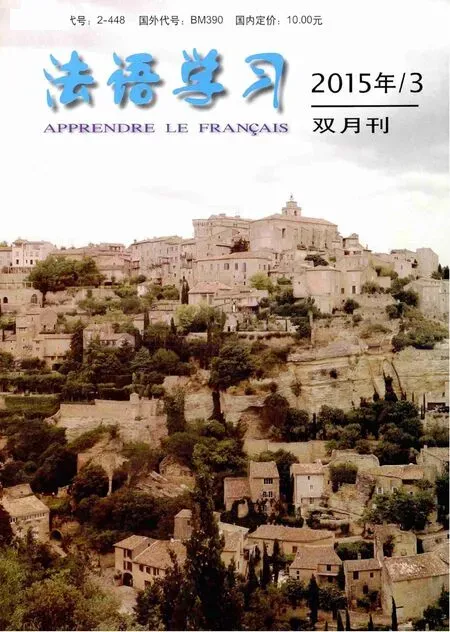解读罗兰·巴尔特的《作家索莱尔斯》
●北京语言大学 刘宇宁
解读罗兰·巴尔特的《作家索莱尔斯》
●北京语言大学 刘宇宁
《作家索莱尔斯》收录了罗兰·巴尔特在1965-1978年间评论菲利普·索莱尔斯作品的6篇文章。巴尔特不顾当时法国文学界对索莱尔斯的一片质疑之声,坚定地为索莱尔斯的先锋文学创作进行辩护,并借此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文本观。而另一方面,索莱尔斯对文学语言的探索也在不断实践着巴尔特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理论。
巴尔特,索莱尔斯,文本
引言
罗兰·巴尔特 (Roland Barthes,1915—1980)是法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和符号学家,其著作对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法国当代思想界的先锋人物,巴尔特的文艺理论已为广大学者所熟知。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1936—)其实也是法国当代文坛的中心人物之一,著作等身。1957年,索莱尔斯以其短篇小说《挑战》1(Le Défi)在法国文坛初露锋芒,获得费内翁(Fénéon)奖,翌年,小说《奇怪的孤独》(Une curieuse solitude)得到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çois Mauriac)和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的高度评价,1961年的《园》(Le Parc)获得梅迪西(Médicis)奖。索莱尔斯迄今共创作出版了小说和文艺随笔60余部,其中影响较大的还有《戏》(Drame,1965)、《数》(Nombres,1968)、《法》(Lois,1972)、《H》(1973)、《天堂》(Paradis,1981)、《女人们》(Femmes,1983)、《恒定的激情》(Passion fixe,2000)和 《时光旅者》(Les Voyageurs du Temps,2009)等。
1960年,索莱尔斯等人创办了《原样》2(Tel Quel)杂志,关注边缘作家并刊登了许多先锋文学评论。巴尔特、拉康、福柯、德里达和克里斯特瓦等著名学者都与该杂志有着密切合作。索莱尔斯较早开始关注中国,其作品中融入了大量的中国元素:汉字、诗歌、绘画、道家思想、《周易》等,涵盖了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前后,索莱尔斯及“原样派”中的亲华派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十分推崇毛泽东思想。
《作家索莱尔斯》(Sollersécrivain)出版于1979年,收录了巴尔特在1965-1978年间评论索莱尔斯作品的6篇文章:《对话》(Dialogue,1979)、《戏、诗、小说》(Drame,poème,roman,1965-1968)、《拒绝承袭》(Le Refus d'hériter,1968)、《视而不见》(Par-dessus l'épaule,1973)、《境遇》(Situation,1974)、《波动》(L'Oscillation,1978)。本文旨在分析和梳理巴尔特在《作家索莱尔斯》中表述的主要观点,借助巴尔特的视角,重新审视索莱尔斯在这一重要时期的作品内涵,以期能够管窥当时法国文学界的主流话题和理论深度。
一、为索莱尔斯写作风格转变的辩护
《挑战》和《奇怪的孤独》奠定了索莱尔斯文坛新秀的地位,读者从这两部作品中不难发现对普鲁斯特和超现实主义的借鉴。然而在20世纪60-70年代,索莱尔斯却偏离了初期的创作道路,转而挑战传统的叙事文学,大胆尝试全新的写作方式。这期间的主要作品有《戏》、《数》、《法》、《H》和《天堂》,并且每一部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中国元素。《戏》和《周易》相似的结构,《数》和《法》中赫然嵌入的汉字,《H》和《天堂》中标点符号和大写字母的遁形,无一不让已然光怪陆离的法国文坛为之瞠目结舌。索莱尔斯文风的转变和《原样》杂志在巴黎文学舞台上的高调,使其身处各种冷嘲热讽的风口浪尖之上,诸如“伪创新”、“附庸风雅”、“不知所云”等各种批评纷至沓来,他也因“出尔反尔”和对自己文学创作的不断否定而受到孤立。
巴尔特在《对话》和《波动》两篇文章中,旗帜鲜明地为索莱尔斯写作风格的转变进行了辩护。他援引了卡夫卡的话:“我没有任何确定的东西”(Barthes,1995:963),并提出自己对索莱尔斯的两点看法:首先是索莱尔斯通过其“波动”,质疑了知识分子的传统角色。自德雷弗斯事件3以来,知识分子已被看作是正义的代言人。索莱尔斯恰恰要解构知识分子的传统“使命”,打破知识分子作为“良知”和“道德”化身的固有形象。他尝试进行着一种“生命写作”(écriture de vie),这种标新立异的实验性创作必然曲高和寡。其次,巴尔特认为,索莱尔斯文风虽有“波动”,但他其实一直坚守着一个永恒的主题,即对写作的坚持和虔诚。他的写作并非为了实践诸如“为艺术而艺术”或是“介入文学”之类的理论,其创新之处在于质疑文学中的固有意象,打破各种习见和定论。
不可否认,索莱尔斯是一位不断探索文学本真、诘问自身写作方式的作家,其勇气和执著是无可厚非的。研究索莱尔斯的学者让-米歇尔·卢(Jean-Michel Lou)甚至认为“伟大的书有它们自身就够了;索莱尔斯的(作品)完全不需要与之相关的评价”(Lou,2012:10)。
二、对索莱尔斯叙事方式的探讨——以《戏》为例
《戏、诗、小说》是针对索莱尔斯出版于1965年的《戏》一书所作的评论,也是《作家索莱尔斯》的核心篇章。索莱尔斯曾宣称:“我的‘书’开始于《戏》(Sollers,1981:161)”,以之为自己先锋文学实践的开山之作。这部作品分为64个段落,没有连贯完整的故事情节,“他/它”(il)和“我”(je)作为叙述者交替出现,每当文中出现“他/它写道”(Ilécrit)时,叙述人称就转换成“我”,这部分文字也被置于引号之中。
关于小说的人称问题,巴尔特在文中做出了详细的分析:“《戏》讲述的故事主体(以下均指该词的结构意义)就是它的叙述者。”(Barthes,1995:934)他指出,经典的第一人称“我”实际是一分为二的,在不同的时间里进行两种不同的活动:一个在行动(经历、体验),另一个在讲述。这种人称叙述带有一定的欺骗性,即行动者(actant)和叙述者由一个模棱两可的“我”结合在一起。在有人称的小说中,叙述活动是隐蔽、不易察觉的。索莱尔斯的实验便是只构建一个行动者,叙述者完全融入“叙述”这个唯一的行为之中。在此类无人称小说当中,叙述活动不再是“透明人”,而是清晰可见的了,其造成的结果就是“叙述”本身在言说。传统叙事方式通常是作者以“我”(je)来谈自己或别人(il),而《戏》中的人称“我”(je)和“它”(il)4却如同回旋镖,投掷时是无人称的“它”,飞出去之后变成“我”,而回到原点时“我”又变回“它”。所以准确地说,这并非两个不同的人称,而是处于不同时间的同一人称,这就是《戏》的主体,一个纯粹的叙述者。
至于《戏》的情节,大部分读者会感到不知所云,很难复述其中的内容。正如索莱尔斯自己所言:这是一个“寻找尽可能‘空’的叙述的尝试”(Sollers,1991:75)。“空”的概念来自于索莱尔斯对道家思想的借鉴,“不过,索莱尔斯感兴趣的似乎并不是‘空’的辩证意义,而只是其概念本身”(车琳,2014:74)。
巴尔特对《戏》的情节做出了如下解释:《戏》中没有小说意义上的“故事”(histoire),而从写作角度而言,却有很多“故事”。故事其实占据了《戏》中非常重要的地位,以至于它成为了探寻的对象,换言之,“故事就是对故事的欲望”(Barthes,1995:936)。如果读者只关注故事中的行动者而忽视故事的叙述者,就永远不可能读到真正的故事。他认为“真正的故事只是对我们讲述的寻找过程”(Barthes,1995:937)。为了阐明这个重言式的论断,巴尔特又援引了塞万提斯和普鲁斯特为例:两位文坛巨擘都认为写作的核心并不是写故事,而是确立一种写作模式,这样才更有可能讲述整个世界。
巴尔特还从符号学角度剖析了《戏》的语言特点。他指出,符号学细致地区别了能指、所指和事物(所指对象)5,而现代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阐明所指并非事物。索莱尔斯的写作实践极力扩大了所指和所指对象之间的距离,正如《戏》中所揭示的:“这里所说的是词语的意义,并非词语中的事物。”(Sollers,1990:99)索莱尔斯以“火”(feu)为例解释道,“火”就是“火焰”(flamme),它本身是什么与我们所看到的词语毫无关系。他甚至认为词语先于事物产生:词语看见、感受并引发了存在的事物。
所指和事物之间的分离,必然导致文本不再具备反映现实的合法性,文学便自然失去了其表现功能。同时,“世界”也不再是事物的集合,而是一个所指场。如此说来,书和世界便是同质性的了,词语和事物可以在同一介质中会通。我们不妨通过追溯汉语中“文”的词源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巴尔特的文本理论。《周易·系辞下》载:“物相杂,故曰文。”《说文》道:“文,错画也。”可见,“文”最初指的是世间万物的纹理、纹路。既然书中的文字(词语)源自于“文”,世间万物也由“文”描摹而成,那么书和世界便是由相同质素构成的。
巴尔特还分析了《戏》中两种语言之间的对立:一种是代表传统文学的“敌对语言”(langage ennemi),它表述过度,充斥着各种制度化、社会化的符号,一直被滥用于编造的故事中。索莱尔斯也称敌对语言是“外在的、借用的,伪造的”(Sollers,1990:81),它认为真正的故事具有欺骗性,其“字母表今后对我们而言是过时的”(Sollers,1968:35)。
索莱尔斯通过《戏》所探求的语言,是一种“天生的,先于任何意识,无可挑剔地符合语法规则的语言”(Barthes,1995:938)。它与敌对语言相反,巴尔特称之为“同盟语言”(langage allié)。“小说就是朝着这种语言前行的:这种反常的语言打破了所有日常语言约定俗成的惯例,它虽然不会得势,但却勾勒出一种决裂和剥离的可能性,一种摆脱重复和异化圈禁的可能性。”(Forest,1992:139)。“同盟语言”虽然能够辅助叙述,却不能动摇“敌对语言”的主导地位,它只能是暂时和迂回的。“寻觅中的主人公、被找寻的故事、敌对语言、同盟语言,这些基本功能构成了《戏》的意义(因此也是其‘戏剧性的’张力)。”(Barthes,1995:941)索莱尔斯讲述了“一种语言自我寻找,自我创造”(Sollers,1990:127)的过程,精确地展现了词语在纸上的轨迹。《戏》无疑是一部奇书,它打破了传统小说以故事情节和人物为基础的叙事方式,将语言作为主题,拒绝文学的表现功能,引导文本讲述其不断生成的机械运动,即意义的出现和消失。
三、发现索莱尔斯文本中的阅读空间
巴尔特通过对《天堂》和《H》的评论分享了他对阅读索莱尔斯作品的一些建议。这两部作品通篇没有标点符号,也没有大写字母,使读者无所适从,不知该怎么断句,被认为是无法读懂的作品。而巴尔特却认为《天堂》不仅可以读懂,而且“奇特、引人入胜、(内容)丰富,从各个方向将一大堆事物搅拌在一起——这正是文学所独有的特性”(Barthes,1995:929)。标点符号对巴尔特而言像个卡住的节拍器,破坏了文本原有的节奏,只有抛开这种束缚,文字的意义才会喷薄而出;他还建议读者放慢速度,依自己的心意来断句、停顿。巴尔特还称《H》将人带到了评论的极限,其形式让阅读有了更大的自由空间。他建议在阅读《H》时,不要局限在作品已有的文本当中,应对作者视而不见,就像和他同时在写作一样。
在1970年出版的《S/Z》中,巴尔特提出了可读性文本与可写性文本的分类(Barthes,1970:10):意义确定,符合现实世界的文本为可读性文本,读者只能被动接受,大多数传统经典作品属于可读性文本;可写性文本的意义不确定,语言不符合常规,有很多情节留白,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积极思考,大部分现代和后现代文学作品属于可写性文本。在巴氏文本观中,《H》就是一种可写的开放文本,其开放性在于阅读过程可以赋予文本以意义,读者能量在文本中进行投注,使得文本在不同读者那里呈现出不同的样貌。为强调阅读对于文本的生成作用,巴尔特总结了阅读的三种空间:
第一种是个人(身体)的,巴尔特在这部分总结了他阅读《H》的五种方式:1)“俯冲”式,即阅读过程中凭直觉或随机地选取一个意群来品读;2)“鉴赏”式,即仔细地玩味一整页的内容;3)“铺陈”式,即像阅读小说那样从头读到尾,并不因为自己的好恶而改变节奏;4)“低空”式,即逐字逐句地推敲,像为书作注那般细致;5)“漫天”式,即与作品拉开一定距离,将它置于历史背景中来分析。
第二种阅读空间是社会学层面的。他反对将《H》及其相关评论割裂开来,认为应将社会反响看作是文本的一部分,因为只有被阅读的作品才是文本。可写文本的开放性使得多元解读成为了可能,而不同读者的多样化理解也同时丰富了文本自身,写作和阅读之间得以交流和贯通。
第三种阅读空间是历史层面的,即文本也面向那些并不生活在阅读时代的读者。巴尔特指出,有些人想把《H》当作未来的文本来阅读,而事实上,一个文本之所以前卫,并不一定因为新奇,而是出于复古:一位但丁或拉伯雷的读者可能要比一位马尔罗(Malraux)的读者更加接近《H》,更加容易理解它。
结语
《作家索莱尔斯》的题目本身就使人感觉巴尔特在着力强调索莱尔斯的作家身份。另外,题目中用的是“作家”而不是“作者”。巴尔特的“作者已死”理论与索莱尔斯的创作实践彼此呼应:索莱尔斯这一时期的文本写作是无人称的,既没有作者的肉身,也没有现实素材,尤其当作家不为人所理解,甚至是不为人知的时候,这种“无人称”作品就更加纯粹。巴尔特所阐释的索莱尔斯是一个“反作者”的作家形象,“只强调符号的作用,而忽视使用符号的人,这正是那个年代的主流话题。”(张智庭,2012:209)
巴尔特与索莱尔斯都拒绝被限制在任何思想的条条框框之中。巴尔特在解读索莱尔斯的过程中也在阐释和印证自己的文本理论。在索莱尔斯、克里斯特瓦和德里达等思想家的共同影响下,巴尔特也在酝酿着自己“由符号学历程的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转变”(黄晞耘,2004:40),即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过渡。

☉注释☉
1.本文所涉及的法文文献题名及引文均为笔者自译。
2.亦称为《如是》或《泰凯尔》,该杂志于1983年结束与瑟伊出版社(Seuil)的合作,更名为《无限》(L'Infini),现由伽利玛出版社(Gallimard)发行。
3.德雷弗斯(Alfred Dreyfus,1859—1935)法国犹太军官,1894年被指控向德国出卖情报而入狱,数年后经证实为冤案。以左拉为首的一批作家撰文声援德雷福斯,该事件对法国知识界和政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4.法语中的第三人称“il”既可表示人称主语“他”也可表示无人称主语“它”,在这里笔者建议选取后一种理解。
5.原文中的这4个词分别对应的是signifiant,signifié,la chose(le référent)(Barthes,1995:940)。
☉
车琳,20世纪60-70年代法国“原样派”知识分子的中国观——以菲利普·索莱尔斯和罗兰·巴尔特为例 [J],中国比较文学,2014(2):68-80.
黄晞耘,罗兰·巴特思想的转捩点[J],世界哲学,2004(1):29-42.
张智庭,符号学论集 [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
Barthes,R.,S/Z[M].Paris:Seuil,1970.
Barthes,R.,Sollersécrivain[M].//Œuvres complètes,tome III 1974-1980,éditionétablie et présentée par Éric Marty,Paris:Seuil,1995.
Forest,Ph.,Philippe Sollers[M].Paris:Seuil,coll.«Les contemporains»,1992.
Lou,J.-M.,Corps d'enfance corps chinois:Sollers et la Chine[M].Paris:Gallimard,coll.«L'Infini»,2012.
Sollers,Ph.,Nombres[M].Paris:Seuil,1968.
Sollers,Ph.,VisionàNew York:entretiens avec David Hayman[M].Paris:Grasset et Fasquelle,1981.
Sollers,Ph.,Drame[M].Paris:Seuil,coll.« Tel Quel»,1965.;rééd.,Paris:Gallimard,coll.«L'Imaginaire»,1990.
Sollers,Ph.,Improvisations[M].Paris:Gallimard,1991.
☉
本文属北京语言大学校级科研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13YBG01)的部分成果,并受北京语言大学青年英才培养计划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