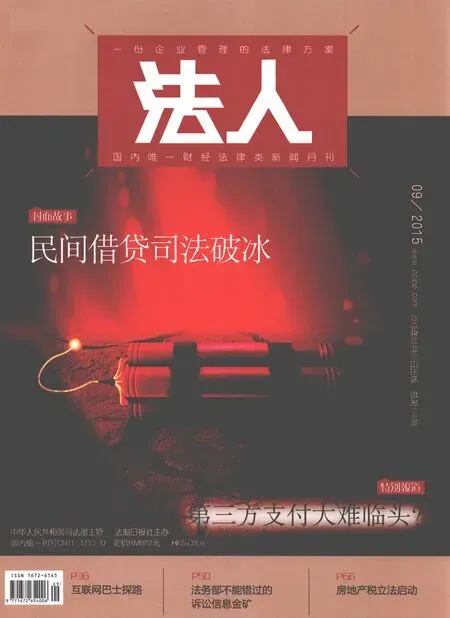一个法律人的近代“闲逛”
◎ 文 《法人》特约撰稿 林海
百年以降,传统文化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有人说近代性损害传统,也有人认为近代性帮助传统发扬光大。
近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人博所著新书《中国的近代性》面世,书中内容很好地诠释了近代性和传统的关系。记者针对书里提及的这些问题对他进行了专访。
传统对于近代性的价值
《法人》:关于传统对于近代性的价值,你说“近代性在损害传统”,也说“丢不掉的儒家传统”在影响着近代化的选择。在您的近代图景里,传统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它对于近代性,对于近代人,甚至对于今天的我们和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制度,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王人博:在我的阅读思考中,“近代”之于中国,一般来说是个不太好的词。它意味着中国旧伤未愈又有了新痛。在这书的序言中,我已经讲明了这种态度:“近代性”是西方对中国扩张与征服的一个结果。中国的近代性是在“先进—落后”这样一个西方与中国的二元结构关系中展开的。用“挑战—回应”这样的表述结构也可以,只是“回应”二字显得轻浅了一点,隐没了“落后”的沉重。进一步讲,对中国近代的“中国中心主义”的分析框架,我没有亲近感。其中的原因甚是简单,我一直没弄明白:如果没有西方的扩张给中国带来的冲击,中国由汉唐洎明清会不会有自己类似于西方的“现代性”?
《法人》:这个问题也困扰着我。中国在面对近代性时总有一种尴尬。那么,假如没有发生外敌入侵,中国的近代性是不是还能发生?或者会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
王人博:这个问题实际是在问,为什么中国的朝代更迭缺少了西方意义上的“中世纪”与“启蒙时代”这样的传统与现代的决然二分?实际上,近代的中国与西方咄咄逼人的现代性相比,咱们处处表现的是落后,这种落后是极端的。因为极端落后,所以中国近代性表现的不是“顺从”,而是“抵抗”。
这种抵抗的姿态产生于:当所有通向西方的“进步”之路被封闭之后,中国的近代性就是通过不断革命而进行的抵抗,在内在层面则表现为“因为无路可走所以必须前行”这样一种精神状态。这样一种精神在个体身上渗出来的人格便是鲁迅。鲁迅一生反抗绝望,中国的近代性也在不断的革命中反抗这种“极端落后性”。
在这样的话语结构里,“传统”一词就显得有点暧昧。在这里使用它,意指的是能否接纳西方“进步”概念的中国所有旧物。当然,“近代”与“传统”这样的对应关系也存在这样一种逻辑结构:近代代表的是新的中国主体性,而这种新主体性与传统肯定存在着内在关联,寻找能够支持这种新主体性的内在资源,便成了中国现代性理论的使命。
而实际上,中国的近代性是在不断革命进而不断否定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传统一直被看作中国落后的代指。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政治家比某些中国学者更为清醒:“反封建”是中国革命最为重要的内容。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更大程度上就是“封建主义”。中国的现代政治构建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不断清除封建专制余毒,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几代政治家最为理性的决断。当然,封建主义的彻底消除对中国而言,是一个稍显漫长的过程,不能指望对一个存在了几千年的遗传基因在几代人身上就能拔除干净。鲁迅“我也吃过人”的惊呼当使我们每个现代中国人警醒。
看待历史的两种态度
《法人》:那么,假如你生活在近代,对你来说,是启蒙更重要,还是救亡更重要?或者,是自由更重要,还是革命更重要?如果在孙中山和胡适的年代,作为一位大学教授,也有生存与安全压力,也有同侪同辈的影响,你会作何选择?
王人博:“启蒙”与“救亡”,“自由”与“革命”,的确是个“假设”的问题。对待历史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站在历史之外看历史。这种方法因为抽身于历史,并跳出历史的圈外站在一个“适当”的高地观测历史,并自身带着一种优越性:客观、公正,而且还有满腔的理性。其缺陷与其优越性一样明显:缺少同情心,即便也掉一滴眼泪,也不过是历史“应当如何如何”。另一种是潜入历史、进入历史的态度。这种方法因为与历史融为一体,有一定的“主观任性”,自身带有“扼住历史的火焰”“火中取栗”的烧灼感。
譬如,同样对待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个二战结束30年后出生的人,与一个从战场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二战老兵”的视角自然不同,前者也许会更公正,但也会公正地消除“身临其境”的亲受性和亲验性。
如果我们采用第二种方法观看中国“近代”,那些“事后”进行的合理解释所使用的模式实际并不存在。“启蒙”在中国近代并不只是“喊”,“救亡”也不只是“干”。所谓启蒙,它本身就是中国救亡的一部分,启蒙首先唤起的是“亡”的意识,并询唤出救亡的途径与意义;而救亡的过程也伴随着启蒙,即“活过来应活出什么样”这样的意识并存于同一时间与空间。
同样,中国近代并不存在“自由”这样的东西和可能性。如果存在,那么历史就成了一个“缺心眼儿”的人。因为它舍弃了自由,往革命走,只能证明自身的悖谬。任何革命都不是从容的选择,而是被逼出来的。除非有路可走。否则,鲁迅也绝不会孤身走入荒野;而胡适之先生固执于自己心造的“自由”于历史,自然带有几分悲怆的况味。这是我的认知。
在我的阅读思考中,
“近代”之于中国,一般来说是个不太好的词。它意味着中国旧伤未愈又有了新痛。
在这书的序言中,
我已经讲明了这种态度:
“近代性”是西方对中国扩张与征服的一个结果。
《法人》:从《法的中国性》到《中国的近代性》,我们注意到你的视野逾越了“法”这个相对狭隘的范围。你觉得在那个时代,具体的法律在近代性、中国性的视野中,能占多大的分量?虽然,在那个时代,用你引用的俄国哲学家赫尔岑的话说,即使是理性也“抵抗不住拳头”,更不用说文化地位远不及理性的法律了。
王人博:不能正确地界定自己,这是我的不幸。“闲逛者”是我对自己一个临时性的称呼。这还是有几分真实:我习惯东看看,西瞧瞧,不会在一个问题上呆得太久,持之以恒对我而言是个反语。
法学是我的饭碗,但我不习惯用法学的眼光看问题。正因为此,一生都错过了法学对我的奖赏。近代之于中国,“法律”问题,只是个芝麻大的事,这个认知算是法学的惩罚。只要还执拗于“近代性”这个问题,我暂时还没有“归队”法学的打算。自己劝服自己的话:“人一辈子要做点不靠谱的事。”所以,这些年还是想了一些问题,譬如“如何认知中国?”这里边有4个问题一直在思考:东方主义、民族主义、进化主义、近代主义;“共和在中国:意义的翻转与再生”写了个头就放在那儿了;最近在读“江湖文化”的东西,又对中国近代的鸦片种植与贸易感兴趣……当然,啥时候能写出来,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不是卖关子,是自己对自己放话以示要做的决心,这也印证“闲逛者”这个头衔不是虚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