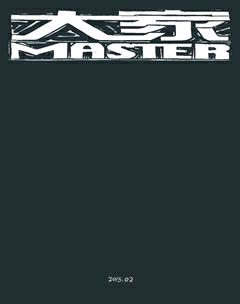旺角
周洁茹

黑夜已经来到了你说怎么办
我们因此相爱了你说怎么办
——艾吕雅
他是死都不肯说爱她的,她又总是迫着他说,于是就分了无数次的手,连他们自己都算不清楚了。
若不是已经十一月中了,她的朋友格蕾丝仍然每天天黑了以后都要去旺角转一圈,影几张相。若不是她的朋友格蕾丝约她在旺角食饭,她突然是去了。她是见不到他的了,在旺角。
她总是半夜接到格蕾丝的电话,有时候叫她出来喝一杯,有时候叫她一起去金钟坐坐,有时候叫她吃鸡煲,就在楼下。她总是不去的,挂了电话,她也睡不着的了,坐着坐着,天就亮了。可是她总是不去的。
你们要待她好,她的朋友格蕾丝对她们所有的朋友说,她抑郁的,你们都不要怪她。格蕾丝说着这样的话,还哭了。
她笑啊笑啊,眼泪都充满了眼眶。她说谢谢你啊格蕾丝,可是我一滴眼泪都不会流出来的。
可是她有什么好抑郁的,什么都有的。
教授丈夫,名校的儿女,工人不偷东西又很会做菜,她不知道她还有什么好抑郁的。
格蕾丝像往常那样打电话给她,格蕾丝说她在旺角坐着,月亮太圆了。
你怎么不去金钟坐着,你在旺角坐着。她说,报上说有黑社会。
格蕾丝说金钟远啊,旺角坐完回家近。
可是你为什么要去坐呢,你不出家门去坐就不用再回家啊,她说。
格蕾丝在电话那头响亮地笑,格蕾丝说旺角的警察好帅。
她突然想起已经分了手的他,是个警察。
因为她总是迫着他说他爱她,他却是死都不肯说的,他说什么都给了你了,她说这一个爱字都不肯给我,他只是抱住她,很用力地亲吻。然后他们就分手了。
她跟一个日日早晨都同她讲我爱你的男人上床,这个男人做得比警察好,她也喜欢那样,没有情的,只有性,做到快乐死,快乐死了。
直到有一天,她突然厌倦。
其实他也对她厌倦。
这三个月,他们上太多次床了,有时候一句话都没有,各自脱各自的衣服,她只记得那些床,连酒店的门,前门或者后门,她都记不得的了。你也知道的,高潮过去了就会特别厌倦。
又没有爱,做爱都没做出爱来。
只是维持着,到底还有点高潮。
她听说毒品的快感超过性交的,她又不敢去试,到底还有家庭。她去问格蕾丝哪里买得到大麻,淘宝吗?
格蕾丝说我拍个照我就应该知道哪里有大麻吗?格蕾丝说大麻就不会上瘾了?你出个轨还上瘾呢。
她说格蕾丝你倒是张口就来啊,我出轨?
格蕾丝说好吧好吧,你出不出轨偷不偷情我完全不关心,我只关心你会不会被伤害。
她说格蕾丝你都没有爱的。
格蕾丝说爱是错觉,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没有爱的。
天天说我爱你的男人约她去卡拉OK,她挺惊讶,以为他是想进一步,有了情,又觉得是负担。
她听说任何话语和行为持续了三个月就会变成习惯,她计算了一下,他们也真是说了三个月的我爱你上了三个月的床了,出轨也真是出成了习惯。
可是她又不爱他的。
她也是不爱丈夫的。
教授丈夫智商太高,结婚的那一天就说她笨,说了十年的笨,她到死都是笨的了,幸好儿女遗传了他的智商,不是她的。
她笑着低了头,低到灰尘里去。
年轻的时候相貌好,中年了相貌的好倒不那么紧要了,丈夫只是享用了她的青春。
格蕾丝说如果有下一辈子,她也要好看一回。她说好看的女人也不是个个幸福的,如果真有下一辈子,她不想好看,她想会点什么,能够拍拍照也好。
格蕾丝说人人都是摄影家,人人心里面有故事。
不要专业的吗?她问。
不要,格蕾丝说。
他们果然是只唱唱卡拉OK,把我爱你说得顺口的男人唱起K来也是拿手,一首又一首,他真是喜欢唱歌,她以前都不知道的。只熟悉身体的男人,也不知道他还会什么。她想去抱他,他推开了她。
又说家里催,走了。
她诧异,去问他们都认识的一个女性朋友,那个朋友住在美国,说没什么好诧异的,他唱K前同她微信做了爱,推开她是当然,又硬不起来。
她一个人坐在卡拉OK的小包房,疲惫又厌倦。镜子里的脸是好看的吧,她自己是觉得一丁点儿也不好看了。突然想起来听说的一句话,每一个女神的背后都有一个操她操到恶心的男人。她竟然笑了。
他们的美国朋友说,他同她传照片的时候误传过私照,她即时知道他是同时与多个女人的了。
太恶心了,她说。
为什么恶心呢?他们的美国朋友说,这个世界不就是这样的吗?
她很快找到了第三个女人,他在回家的路上同她传简讯,盛赞她的鞋美,说去屯门找她。
她建了一个微信组,放他的那些女人,直到第四个女人也加入。五个女人,连同她自己,她们开始讨论约他出来,同时出现,一定开心死了。
她没有参与讨论。太恶心了,她是觉得,这些女人们也是太恶心了。
没有情的出轨,背叛也是残忍的。
她发了一条简讯给警察,分手了一年,头一回发给他,只说了四个字,太恶心了。警察回过来一个问号。她又说了一遍,恶心。警察打了电话过来,她听到他的声音,眼泪就滚下来了。
警察沉默了一下,叫她好好生活。
我怎么会好呢?她说,我这个样子。
警察沉默,背景是嘈杂人声。
你在哪里?她问。
当值,警察说。
我去看看你好吗?endprint
不要来,警察说。
不要,警察又说了一遍。
她在隔天的报上见到了他的相片,职务竟然很高。在一起的时候,只知道他的名字,只有一个名字,她一直疑心那个名字也不是真的,每次他也只穿便服,更没有见过他的枪,她当他是假的。
名字却是真的。
报上讲他在旺角,她想起格蕾丝,每天天黑了就去旺角转个圈,拍拍照片的格蕾丝。
她打电话给她,都是她打给她,好像还是头一回,她先打给她。
格蕾丝约她在金钟,她本不愿意去,又要格蕾丝做晚上出去的由头。只好在金钟。
格蕾丝只挂了一只小相机,她还以为她会拎一只像枪一样的相机。香港的冬天都不是那么冷的,格蕾丝倒穿了一双皮靴,及地长裙,配那双皮靴。她给她看她的相机,塞在她手里,她横竖看不懂,笑着说相机不是越大越好的吗?格蕾丝笑笑。
港铁到铜锣湾,格蕾丝说下车。
她说不是要去金钟吗?格蕾丝说不去金钟,习惯了的,要来铜锣湾看一下。
她跟着她。铜锣湾,她只去过一次?两次?三次?却是在香港住了七年了的。格蕾丝说她抑郁大概也是对的,一个哪儿都不去的女人。
她跟着她,过马路,红绿灯,格蕾丝的长裙皮靴。
我都不知道这儿还有一片呢。她说,报上只说金钟和旺角。
现在知道了?格蕾丝说。
她跟着她,格蕾丝走来走去,拍得却很少。她只是会停在哪里,只是停在那里。她看不出来她在看什么,也不知晓她在想什么。
格蕾丝走来走去的时候,她找到一个帐篷前面的胶凳坐了一下,帐篷里的人正在吃面,互相看了一眼。
她对警察的思念从来没有这么浓烈过。
回到旺角真是黑夜了。这么大,她都不知道他会在哪里。
哪里会有警察?她去问格蕾丝。
这儿有一排,那儿也会有一排,格蕾丝说。
只有这两个地方?她说,他们只是站在那儿,也不动的?
他们只是站在那儿,不动的,格蕾丝说。
她走过去,每个警察的脸都看了一遍,并没有他。警察们并不看她,青年的警察,中年的警察,深色衣服的警察,浅色衣服的警察,天黑得快,她看不分明他们的表情,他们互相也不说话,靠着墙的一排,她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在这里。
要不要去另外一边?格蕾丝说,那儿也有一些警察。
好,她说。
格蕾丝走在左边,她走在右边,她去旺角的次数更是少,路都是不认得的。
我走在你的哪边好?她问。
哪边都行,格蕾丝说,不过很少人走在我的右边。
为什么?
我抽烟啊,烟灰飞到右边的人的脸上。
现在不抽了?
格蕾丝说到了香港就不抽了,没有什么是不会上瘾的,酒精更会上瘾。
人就是这么弱,对什么都上瘾,格蕾丝又说。
可是你不抽了。她说,你倒挺狠的。
格蕾丝几乎没有再拍,如果有一堆人,她就挤进去看一下,很快又挤出来。格蕾丝来来回回的时候,她站在最外围,看一眼格蕾丝,再去看旺角的天空,有一些瞬间是迷茫的,她不知道她为什么在这里。
另外一排警察里也没有他。她竟然松了口气。她竟是不知道真见了他会怎样,上过床又分了手的两个人,她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她也没有准备好。
婚外情已经是不伦,再加上这个时候的旺角。
若是他奉命丢出催泪弹,而她就站在他的对面。她听说一个示威的女孩亲吻了防暴警察的透明面罩,然后他们开始约会,好多年前了,只是听说,还有配图,爱是一切的源头又是一切的终止。她竟然笑了,她只是笨,若是会点什么,亲历了这样的故事,倒可以拍下来,也可以写下来。她只是什么都不会,若有来世,她一定不要活成现在的样子。
格蕾丝说吃煲仔饭,她说好。
路边摊,一碟菜,两个人分,什么都好吃。
格蕾丝说能够去遍全世界,也能够坐在旺角的角落,吃这么一口煲仔饭,做这样的女人。
她没有回应她。左手无名指的钻石戒指,黑夜里闪闪发光。身上男人的每次抽射,无论哪个男人,她总会扭头去看自己的戒指,那枚戒指也没能叫她停下来。
她说半夜的旺角也不是听说的这么危险啊,你看,旁桌都是游客。
暗涌,格蕾丝说。
格蕾丝的手指上没有戒指,格蕾丝吃得也很少。她只知道她不睡觉也不吃饭,她不知道她结过婚没有,有没有小孩,她对格蕾丝竟然是一无所知的。她们的朋友说过的关于她的话,也都不像是真的。
你为什么要找那样的丈夫呢?格蕾丝突然说,你不是活得绝望,你是活得太痛苦了。
我有一个矮小的小学同学。她说,其实也没有人嘲笑过她矮,二十年以后同学聚会的时候她带去她的丈夫,高得过分,我才留意到她有多矮。我的同学说你们这种大女生是不明白的,就是因为我从小矮,我偏要找高的,我缺什么就弥补什么。
我的学业折磨我。她说,每天去学校都是羞辱,我偏要找个教授。
格蕾丝说活该。
她没有想到她会说这样的话。
我付出了代价,她说。
格蕾丝说谁不是付出了代价呢?
格蕾丝送她去地铁站。
不一起走吗?她问。
我还不想回家。格蕾丝说,我想再去那边走一走。
那我也等一下吧。她说,我跟着你。
她每次去时钟酒店,出来都是快的、心急的,也不是怕撞见什么人,只是厌倦。空了的人,走得总是飞快。
即使跟警察,也不是那么留恋。
她从不回头,于是也不知道他留不留恋。
可是她对格蕾丝说,我跟着你。
她一转身就看见了他。他和他的同事,可是她只看见他。就那么,扑面而来。endprint
眼神对接的瞬时,她只有一句,我要死了。
这已经是一年以后了。
如果她会拍点什么,她该是拍下这样的镜头,流动人潮,静止的她,他的擦身而过。如果相机可以拍得出电光石火的瞬间,如果笔可以写得出一毫米的距离,却远过了一亿光年。
格蕾丝说,我刚才数了一下他肩上的星星。
什么?她说,什么。
格蕾丝笑笑。
她扭头望去,只看见他的背,他真是不能与她相认,偷情的男女,旺角的街头,陌生人一样地错过。
阿Sir,阿Sir,格蕾丝追过去。
她惊呆,只是跟住她。
阿Sir呀。格蕾丝的普通话讲得怪异,两位阿Sir,请问朗豪坊在哪里呀?
他的同事说,最高的那幢啊,就是。
她低着头,只望见他的腰身、手铐、枪袋。
她有试过叫他铐住她,他不肯,说根本就不可以带出来的。
他不肯说爱她,他也不肯同她玩,即使在床上。
怎么过去啊,阿Sir?格蕾丝笑得清脆,像一颗豆子。
走过去啊。他的同事说,就这么,走过去。他的手一指,这个世界从来没有这么滑稽过。
格蕾丝又笑,身体都在动。
她竟然不知道格蕾丝也是会勾引人的,而且是街上的警察。
谢谢阿Sir呀。格蕾丝笑得妖娆,我们头一次来香港,香港真是太好玩了。
她低着头,只望见他的脚移开去。
她抬头,只看见他的侧面,真的是陌生的。他的脸时常在她的上面,他的身体总是盖住她的。可是他从来没有这么陌生过。
那你爱不爱她呀?格蕾丝突然说,脸对着她,眼睛却是看他的。
她的心都要静止了。
不爱,她说。
他的同事往后退了一步,这样的情景,他们巡街当是经常地遇到,习惯了的。
他是早已经退进暗影里了,旺角的夜,真的很黑。
格蕾丝送她到地铁口,她没有回家,去了湾仔,C出口,转右行三分钟,就是他们常去的一间酒吧。湾仔,她只认得那一个出口,也只认得那一间酒吧,他带她去的。其实是很吵的一间酒吧,他们说不上一句话,他们也不说话,只是对面坐着,握住对方的手,那些时刻,她以为是执子之手的,涌出来许多悲凉。
她要了一杯白酒,前后卡座都是年轻男女,声浪中舌吻。酒叫她记起来他们做过的爱,他们竟然从来没有一起到过,他甚至很少要,他总是给她,望着她高潮,退去,然后是第二次,很冷静,很冷静。有时候叫她求他,面孔都是清醒的。
他说你到了我就到了,她以为是爱,他只要她快乐,她快乐他就快乐。
或者他只是征服了她,从掌控她里面获取快感,性交给不了的快感,于是说不出来一个爱字。偷情的人又哪里配说爱,出轨上了瘾,也是习惯,出了一次就有二次、三次,所以最好不要有那么一个第一次。出轨的人,都是上了瘾的。就是这么残忍。
他打来电话,她没有接。手机在桌上闪啊闪啊,她的手握住了酒杯。
过了一会,她打电话给格蕾丝,第二次?却是格蕾丝第一次拒绝了她。
格蕾丝说,你自己走回家。
她站起来,走到街上,灯火通明的街,香港真正就是一个不夜城。
格蕾丝说你得自己走回家,格蕾丝说我只有一句是错的,我说你为什么要找那样的丈夫呢?我要说的是,你为什么要找丈夫呢?
她说格蕾丝你为什么又要找丈夫呢?听说你的丈夫家暴你,你也没有能力争到你的女儿因为你没有工作你都证明不了你养得起你自己。格蕾丝挂断了电话。
她想起新到香港的时候,去旺角办什么事情,傍晚六七点。
很旧的街,她迷了路。
她只知道去问警察,她就拦住了对面走过来的一个警察。他指给她路,还陪伴她走了一段,他只是正好也要走那么一段。
他转身离开了以后,她想起来,他的普通话怎么这么好呢,他又这么高大。格蕾丝打电话来,她说她在旺角,遇见一个很帅的警察。格蕾丝说,摸他。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