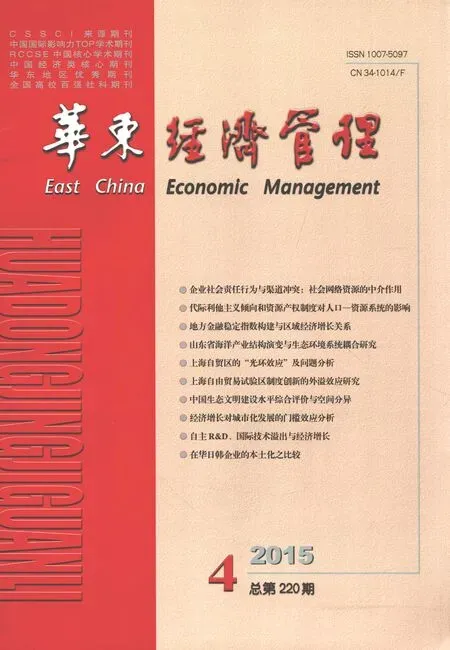职场隔离对服务质量与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情感承诺的中介效应
苏方国,赵 朋,赵曙明
(1.深圳大学 管理学院,广东 深圳518060;2.南京大学 商学院,江苏 南京210093)
一、引 言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职场破坏性行为,如职场暴力(Workplace violence)(Piquero,Piquero,Craig,Clipper,2013)[1]、职 场 侵 犯(Workplace aggression)(Neumanamp;Baron,1998[2];Hills,Catherine Joyce,2013[3])、职场排斥(Workplace ostracism)(Leung,Wu,Chen,Young,2011[4];Zhao,Peng,Sheard,2013[5])、职场隔离(Workplace isolation)(Marshall,Michaelsamp;Mulki,2007[6];Mulki,et.al.,2008[7];Mulki,Jaramillo,2011[8])。据一项调查显示,“七成职场人士曾遭遇职场冷暴力,而其中七成又由上司施加”(子强,2009)[9]。越来越多的职场人士反映:在公司被上司架空、被长期出差、被边缘化、被调离擅长的岗位等类似断绝发展机会的显性“动硬”的职场隔离;还有一种隐性“玩阴”的职场隔离,表面工作岗位等都没有改变,但实质上在工作上得不到正常的支持与发展机会,在人际关系方面被孤立和冷落,被上司视为空气,拒绝交流。国外职场的破坏性行为更多表现为直接的面对面的肢体冲突,而国内职场更多地表现为隐性的非面对面的精神虐待。遗憾的是,国内对于职场隔离的现有研究仅集中在性别隔离、户籍隔离等比较显性的现象上,如王红芳(2005)[10]发现市场竞争直接引发的大量职业性别隔离,所以现有研究还缺乏对职场中广泛存在的架空、边缘化、孤立等精神虐待型隐性职场隔离的研究。
职场隔离(Workplace isolation)包含了职场排斥(Workplace ostracism),可能比职场排斥更隐性、更无形,职场隔离是一种冷暴力,是一种惩罚,是对不遵守群体规范人员的故意冷落、孤立和施加社会压力。对个体而言,职场隔离可能会给员工造成压力、焦虑、失眠等生理与心理问题(迈尔斯,2006)[11];对组织而言,职场隔离可能影响组织成员之间的有效协作(巴纳德,1938)[12];对社会而言,被隔离感的员工可能导致群体性反生产行为与极端的群体性事件。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
(一)概念界定
(1)职场隔离是指“描述员工感知的组织隔离和同事隔离的心理构念,缺乏同事和上司的支持,缺乏与团队成员的社会和情感互动的机会”(Marshall,Michaelsamp;Mulki,2007)[6]。员工在工作场所不能获得相应的社会支持和指导,找不到归属感,进不了公司事务的圈子或者同事的非正式组织。除了工作事务的商业联系,员工与同事之间没有多少感情联系,员工很难获得身份认同和群体归属。本文将职场隔离界定为在职场中不是由于自身心理与性格因素引发同事和上司的排斥,而是由于与公司或同事之间情感缺乏和机会缺乏的一种阻隔员工平等全面参与组织活动的社会性行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首先,本文认为职场隔离界定不包括在职场中因为自身心理与性格因素引发阻隔,这种自我隔离局限于个体分析,表现上是个体主动排斥与同事和上司的人际互动,应对的方法主要是心理的辅导或者工作方式的重新安排等,是个体心理问题,而非普遍性的组织问题;其次,职场隔离的本质是与公司或同事之间情感缺乏和机会缺乏,表现在个体被同事及其人际关系网络所排斥,周围可能都是同事,不孤单但是很孤独;另一方面,个体被公司的网络所排斥,无法接触核心任务、核心人员和核心技术;第三,职场隔离的后果是员工之间的不平等,具体可能是发展机会的不平等、薪酬待遇的不平等、晋升的不平等,等等;最后,本文探讨在职场中个体被动的职场隔离,被阻隔在情感与机会之外。
(2)服务质量。因为服务具有无形性、异质性、生产与消费的同步性(Parasuraman,Zeithaml,Berry,1985)[13],所以员工对服务质量有很强的控制权和决定权。顾客感知中的服务质量是顾客对服务的卓越性或优异性的整体判断(Parasuraman,Zeithamlamp;Berry,1988)[14]。服务质量有众多衡量标准,其中最有影响的应该算Parasuraman,Zeithamlamp;Berry(1988)[14]提出了服务质量的标准SERVQUAL方法。他们提出顾客感知到的服务质量是由以下五类属性决定的:有形性(Tangibles)、可靠性(Reliability)、回应性(Responsiveness)、安全性(Assurance)、移情性(Empathy)。
(3)工作满意度(Job satisfaction)是预期与实际收益之间的差异,描述是个体在工作中对于工作的性质、人际关系、薪酬与晋升、工作环境等等感受到满足的心理状态。
(二)职场隔离对服务质量与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巴纳德(1938)[12]指出企业实质上是一个协作社会系统,协作的效率与效能决定了企业的竞争力与业绩。很难想象,当我们把某些人隔离某些圈子之后,还希望全部人员之间能够有效协作。职场隔离会导致较低的工作绩效与服务质量(Marshall,Michaels,Mulki,2007[6];Mulki,et.al.,2008[7];Mulki,Jaramillo,2011[8];Kamasak,2010[15])。对服务企业而言,职场隔离也可能导致员工对工作热情和士气的降低,而服务工作又需要员工积极与顾客互动,如笑脸相迎、同理心的倾听、周到服务等,所以遭受职场隔离的服务员工很难调动与保持热情的服务状态,最后往往导致较低水平的服务质量。职场隔离不仅降低服务质量等工作角色内行为的绩效,还会降低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等职外行为。如,吴隆增、刘军和许浚(2010)[16]实证结果显示,职场排斥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李锐(2010)[17]研究支持职场排斥与员工职外绩效的工作奉献和人际促进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另外,职场隔离也可能削弱团队或者群体协作,从而导致较低的服务质量。基于上述研究,提出以下假设1a。
假设1a:职场隔离对服务质量存在显著负向影响。
对个体而言,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亲密关系有利于促进个体健康状况和提升个体幸福感,而孤独隔离的人更容易体验到压力、焦虑、失眠等健康问题(迈尔斯,2006)[11]。首先,感觉到隔离的员工更容易在工作中体验到挫败感、无力感,看不到职业发展机会和未来,失去进取心,减低工作满意度与工作绩效,程苏(2011)[18]实证支持了职场排斥对员工的抑郁程度存在显著的影响;其次,被隔离员工可能还存在消极归因而引发的“自我挫败的社会认知和社会行动的恶性循环”(迈尔斯,2006)[11],如果在职场之外没有倾诉对象或亲密关系网络,很容易产生自杀等极端自虐和自残行为;再次,隔离感可能会在员工之间相互传染相互影响,导致群体性反生产行为。服务人员的工作是一种情绪劳动,如果与顾客“面对面”互动的一线员工感知到职场隔离,会导致工作满意度与工作绩效的降低,那么顾客的满意也很难实现。因此,提出假设1b。
假设1b:职场隔离对工作满意度存在显著负向影响。
(三)中介机制
Allenamp;Meyer(1990,1996)[19-20]将组织承诺分为三个维度:情感承诺、持续承诺和规范承诺(Affective,Continuance,and Normative Commitment)。相对于是否继续维持与企业关系的持续承诺和遵守社会规范的规范承诺,情感承诺更强调组织承诺的核心与本质,即员工对组织的忠诚感与归属感。情感承诺是员工对组织目标和价值观的心理认同、信仰和支持的程度,具体表现为员工对组织形象和声誉主动维护、向其他人宣传组织、愿意为组织的发展付出努力、因自己是组织的成员而骄傲和自豪。职场隔离减少了组织承诺(Kirkman et.al.,2002[21];Wiesenfeld,Raghuramamp;Garud,2001[22]),而元分析也表明情感承诺与员工绩效呈正相关关系(Riketta,2002)[23]。因此,我们推测,员工感知到上司或者同事的职场隔离可能会降低其对公司的情感承诺,而发生“踢猫效应”(受到不公待遇后寻找无辜者发泄,如小猫),可能会转向无辜的顾客发泄不良情绪,结果只能为顾客提供低水平的服务质量。例如,Parasuraman,Zeithamlamp;Berry(1988)[14]所指出顾客感觉中的服务质量之一就是移情性,即销售人员在服务过程中体察到顾客的个性化需求并让顾客能够在体验到良好的情绪,感知到职场隔离的员工因为对公司的情感承诺比较低,所以可能在销售过程不愿意考虑顾客的个性化需求并积极给予回应,结果就会导致较低的服务质量。因此,基于上述研究,提出假设2a。
假设2a:情感承诺对职场隔离与服务质量的关系存在中介效应。
因为职场排斥更多的是故意主动有意识地远离目标对象、阻隔、打压目标对象,而职场隔离不仅包括公司、主管和同事在主观上进行的故意隔离,还包括信息技术、交流互动等客观因素缺乏而导致的无意隔离,所以职场隔离包含了职场排斥。现有国内研究虽然缺乏职场隔离的研究,但是已有学者探索职场排斥的结果与中介机制。例如,国内有学者从组织认同角度,分析职场排斥对工作绩效、职外绩效与进谏行为的影响,吴隆增、刘军和许浚(2010)[16]发现职场排斥与员工组织认同之间的负向相关关系;李锐(2010)[17]实证发现在中国组织情境下职场排斥与员工的职外绩效存在负向相关关系,组织认同对职场排斥与工作奉献的关系具有完全中介作用,而组织认同对职场排斥与人际促进的关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方志斌和林志扬(2011)[24]实证也支持,员工组织认同对职场排斥与员工进谏的关系具有完全中介作用。职场隔离减少组织承诺,并会导致较低的工作满意度(Kirkman et.al.,2002[21];Wiesenfeld,Raghuramamp;Garud,2001[22]),因为组织认同与情感承诺都包含了对组织的接受、内化、依恋等心理感知,所以我们推测情感承诺是职场隔离与服务质量和工作满意度之间非常重要的中介机制。因此,基于上述研究,提出假设2b。
假设2b:情感承诺对职场隔离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存在中介效应。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样本为广东省某市一家电器公司的一线销售员工,共发放181份匿名填写调查问卷,问卷是由研究人员直接发放和回收的,回收138份,问卷回收率76.2%;有效问卷116份,有效回收率64.1%。样本主要特征为,女性占66.4%(77人),25到34岁占54.3%(63人),高中或中专占71.6%(83人),工作年限中3年到10年占46.6%(54人),11年到20年占24.1%(28人),可以看出企业中员工的参加工作时间大部分较长,工作经验比较丰富。
职场隔离问卷采用的是Marshall,Michaels,Mulki(2007)[6]等编制的职场隔离测量量表,共10个反向测项,采用利克特5点计分进行评价,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为0.750。职场隔离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拟合优度指数GFI为0.919,比较拟合指数CFI为0.918,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为0.091。
情感承诺量表来源Allenamp;Meyer(1990)[19]与李超平、李晓轩、时勘和陈雪峰(2006)[25],采用利克特5点计分进行评价,共6个测项。情感承诺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为0.775。情感承诺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拟合优度指数GFI为0.988,比较拟合指数CFI为1.000,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为0.001。
服务质量来源于Johnston(1995)[26]与凌茜等(2009)[27]从员工帮助顾客的意愿、敬业精神、服务的主动性等六个方面计量员工的服务质量,共6个测项,采用利克特5点计分进行评价。服务质量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为0.743。服务质量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拟合优度指数GFI为0.968,比较拟合指数CFI为0.967,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为0.076。
工作满意度来源于坎曼等[28]编制的整体工作满意度问卷,共3个测项,采用利克特5点计分进行评价。工作满意度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为0.868。工作满意度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拟合优度指数GFI为1.000,比较拟合指数CFI为1.000,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为0.001。
控制变量主要采用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如性别、年龄、学历与工作年限。
四、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如表1所示,职场隔离与服务质量的相关系数为-0.442(P<0.001),情感承诺与服务质量的相关系数为0.488(P<0.001)。职场隔离与工作满意度的相关系数为-0.426(P<0.001),情感承诺与工作满意度的相关系数为0.609(P<0.001)。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二)职场隔离对工作满意度与服务质量的影响——情感承诺的中介效应
职场隔离对情感承诺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584(P<0.001,表2),表明职场隔离对情感承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员工感知的职场隔离会显著降低员工对组织的情感承诺。职场隔离与服务质量之间的回归系数是-0.468(P<0.001),显示二者之间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表明职场隔离情况越严重,对服务质量的负面影响越大,所以假设1a得到支持。引入情感承诺,回归结果显示,职场隔离与服务质量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291(P<0.01),回归系数减少了0.177,显著性也大大降低了;情感承诺与服务质量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304(P<0.01),表明情感承诺对服务质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Sobel检验的结果表明,职场隔离与服务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间接效应,Z值为-2.831(P<0.01),故情感承诺对职场隔离与服务质量之间关系起到了显著的中介效应。依据Baronamp;Kenny(1986)[29]对于直接效应的判断标准,情感承诺对职场隔离与服务质量的关系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所以情感承诺有利于减弱职场隔离对服务质量的负面影响。因此,假设2a得到了支持。

表2 职场隔离对工作满意度与服务质量的影响——情感承诺的中介效应
职场隔离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回归系数 是-0.418(P<0.001),显示二者之间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表明职场隔离情况越严重,对工作满意度的负面影响越大,所以假设1b得到支持。引入情感承诺,回归结果显示,职场隔离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107,回归系数大大降低了,而且不再显著了;情感承诺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532(P<0.001),表明情感承诺对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Sobel检验的结果表明,职场隔离与工作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的间接效应,Z值为-4.507(P<0.001),故情感承诺对职场隔离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起到了显著的中介效应。依据Baronamp;Kenny(1986)[29]对直接效应的判断标准,情感承诺对职场隔离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即情感承诺有利于阻断职场隔离对工作满意度的负面影响。因此,假设2b得到了支持。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职场隔离常常是上司或者同事等个人采取的阻隔行为,情感承诺更多的是公司制度特别是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塑造的。我们实证结果显示,情感承诺对职场隔离与服务质量的关系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所以情感承诺有利于减弱职场隔离对服务质量的负面影响。这一研究结果意味着,上司或者同事等个人在职场隔离行为会降低一线员工的服务质量,但是如果公司有完善的人性化制度有利于建立员工情感承诺,那么情感承诺可以减弱职场隔离对服务质量的负面影响。
我们实证还发现,职场隔离与工作满意度负相关,情感承诺对职场隔离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所以情感承诺有利于消除职场隔离对工作满意度的负面影响。上司或者同事等个人的职场隔离行为会显著降低员工的满意度,但是公司如果有良好的制度则可以增加员工情感承诺,而情感承诺可以完全消除职场隔离对工作满意度的负面影响。
职场隔离普遍存在至少具有以下深层次的中国文化情境因素:
(1)当今中国是依然是一个身份社会[30](陈刚,2005),很容易因为各种社会身份导致职场隔离。例如:女性职业晋升中的“天花板效应”、针对农民工的公务员招聘,另外,临时工与正式工、外派人员与自雇人员等。这类人为的依据社会身份进行人员分类容易产生基于身份的职场隔离,不利于唯才是举,选贤任能,而更可能以身份用人,导致管理效率的降低与同事之间的不信任。
(2)黄囇莉(2007)指出,“中国人最根深蒂固的愿望乃是追求和谐,在《易经》中,‘冲突’是一种恶或不吉”[31]。因此,在职场中即使有对立与对抗,中国人也常常不会采取可能导致冲突的公开正式面谈方式解决,而是进行无形的职场隔离进行精神虐待。
(二)理论贡献与管理意义
(1)中国文化情境因素导致职场隔离的普遍性,然而职场隔离的国内研究尚属空白,所以本研究弥补了一点国内职场隔离的研究缺口;本研究揭示了职场隔离对服务绩效与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机制,发现了中介变量,即情感承诺可以削弱职场隔离对服务绩效的负面影响,能够完全消除职场隔离对工作满意度的负面影响。
(2)本研究的管理意义在于:①管理层可以采取规范的管理制度、门户开放的管理政策、申诉制度等来尽可能的减弱甚至消除职场隔离的现象;②管理层可以通过人性化的雇佣关系制度、多渠道的沟通机制、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政策来提升员工的情感承诺,员工较高水平的情感承诺可以削弱职场隔离对服务绩效的负面影响,完全消除职场隔离对工作满意度的负面影响。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建议
(1)职场隔离的量表是基于西方组织情境开发的,可能在中国情境下存在一定的偏差,未来研究可以开发基于中国情境的本土化职场隔离量表。
(2)所有量表都是由一线员工填写,可能导致共同方法变异(Common Method Variance)的影响(Podsakoff,MacKenzie,Leeamp;Podsakoff,2003)[32],我们采用Harman单因素方法进行检验,在未旋转的情况下进行因子分析,提取的第一主成分为11.154%,累计方差解释量为67.406。因此,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变异问题并不严重。未来研究可以尝试从不同来源获取数据来消除共同变异的影响。
[1]Piquero N L,Piquero A R,Craig J M,et al.Assessing Research On Workplace Violence,2000-2012[J].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2013,18(3):383-394.
[2]Neuman J H,Baron R A.Workplace Violence and Workplace Aggression:Evidence Concerning Specific Forms,Potential Causes,and Preferred Targets[J].Journal of Management,1998,24(3):391-419.
[3]Hills D,Joyce C.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Prevalence,Antecedents,Consequences and Prevention of Workplace Aggression in Clinical Medical Practice[J].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2013,18(5):554-569.
[4]Leung A S M,Wu L Z,Chen Y Y,et al.The Impact of Workplace Ostracism In Service Organization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2011,30(4):836-844.
[5]Zhao H,Peng Z,Sheard G.Workplace Ostracism and Hospitality Employees’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s:The Joint Moderating Effects of Proactive Personality and Political Skill[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2013,33:219-227.
[6]Marshall G W,Michaels C E,Mulki J P.Workplace Isolation:Exploring the Construct and Its Measurement[J].Psychologyamp;Marketing,2007,24(3):195-223.
[7]Mulki J P,Locander W B,Mairshall G W,et al.Workplace isolation,Salesperson Commitment and Job Performance[J].Journal of Personal Sellingamp;Sales Management,2008,28(1):67-78.
[8]Mulki J P,Jaramillo F.Workplace Isolation:Salespeople and Supervisors in USA[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2011,22(4):902-923.
[9]子强.再冷的暴力也是暴力[N].南方都市报,2009-08-12.
[10]王红芳.劳动力市场职业性别隔离行为分析[J].求实,2005(10):44-47.
[11]迈尔斯.社会心理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
[12]巴纳德.经理人员的职能[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13]Parasuraman A,Zeithaml V A,Berry L L.A Conceptual Model of Service Qualit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J].Journal of Marketing,1985,49(4):41-50.
[14]Parasuraman A,Zeithaml V A,Berry L L.Servqual:A Multiple-Item Scale for Measuring Consumer Perceptions of Service Quality[J].Journal of Retailing,1988,64(1):12-40.
[15]Kamasak,Rifat.Workplace Isolation and Job Performance:A Study on Carpet Weaving Women[J].China-USA Business Review,2010,9(8):26-36.
[16]吴隆增,刘军,许浚.职场排斥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组织认同与集体主义倾向的作用[J].南开管理评论,2010,13(3):36-44.
[17]李锐.职场排斥对员工职外绩效的影响:组织认同和工作投入的中介效应[J].管理科学,2010,23(3):23-31.
[18]程苏.职场排斥与抑郁: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中介作用[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1,19(4):423-425.
[19]Allen N J,Meyer J P.The Measurement and Antecedents of Affective,Continuance and Normative Commitment to the Organization[J].Journal of Occupational Psychology,1990,63(1):1-18.
[20]Allen N J,Meyer J P.Affective,Continuance and Normative Commitment to the Organization:An Examination of Construct Validity[J].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1996,49(3):252-276.
[21]Kirkman B L,Rosen,B,Gibson C B,et al.Five challenges to Virtual Team Success:Lessons from Sabre,Inc[J].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2002,16(3):67-78.
[22]Wiesenfeld B M,Raghuram S,Garud R.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mong Virtual Workers:The Role of Need for Affiliation and Perceived Work-based Social Support[J].Journal of Management,2001,27(2):213-229.
[23]Riketta M.Attitudinal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Job Performance:A Meta-analysis[J].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2002,23(3):257-266.
[24]方志斌,林志扬.职场排斥与员工进谏行为:组织认同的作用[J].现代管理科学,2011,21(11):94-96.
[25]李超平,李晓轩,时勘,等.授权的测量及其与员工工作态度的关系[J].心理学报,2006,38(1):99-106.
[26]Johnston R.The Determinants of Service Quality:Satisfiers and Dissatisfier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rvice Industry Management,1995,6(5):53-71.
[27]凌茜,汪纯孝,张秀娟,等.公仆型领导对服务氛围与服务质量的影响[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
[28]Dail L Fields.工作评价——组织诊断与研究使用量表[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
[29]Baron R M,Kenny D A.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Conceptual,Strategic,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6,51(6):1173-1182.
[30]陈刚.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19-24.
[31]黄囇莉.华人人际和谐与冲突:本土化的理论与研究[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32]Podsakoff P M,MacKenzie S B,Lee J Y,et al.Common Method Biases in Behavioral Research: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ed Remedies[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03,88(5):879-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