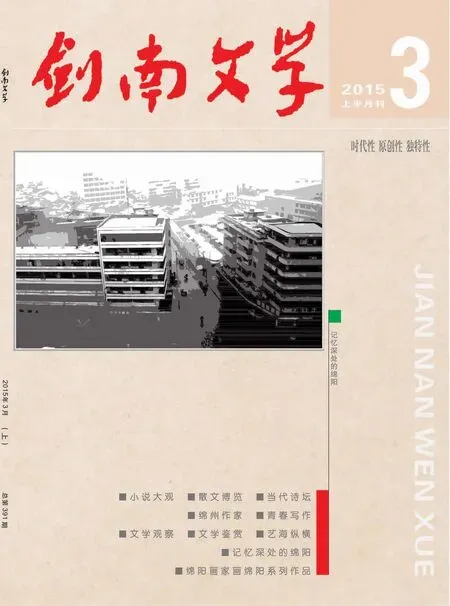布谷鸟(组诗)
■发 雷
一夜蛛网
一片熟悉的青山躺于眼底,
我竟不知哪处坟冢是你的居所?
我的早晨被你牵着
荡漾于乡土的波浪;
陌生孩子群拦住一个归乡者,
纵然未被截,我也走不进故乡的锦绣:
新的邻居,新的门庭
有新的朝向——那阳关的金道;
坍塌的祖屋,是人生一场败仗的遗址,
阳光里,湿气、阴影生发阴寒,
年复一年的藤蔓又长又乱,
它早已被缠野了,古怪异物定居……
“醒来”,匆匆洗漱,吃过一碗面条后
走下楼梯,将欲开锁,自行车上竟生蛛网。
这一夜营造的新网,鲜白如童年之肌。
我寻找那个家伙,它躲在一个角落,小小的。
“真很抱歉,才有新家,便要破碎……”
它初始留恋,缠绕不愿离去,
我好不容易把它吹到墙上,
踏上车上班去了。
雪
雪,近一尺厚,晨光照在上面——明亮的美。
雪,使交通缓慢了下来,造成了很多不便,
但从汽车上看雪是美的,不过,
也许不如古人雪地驻马林边那样美;
而美引起的冻馁也不能让人遗忘:
仍有被冻死或房间里缺少暖气的人。
当然,古代也是如此,一直以来就是如此。
但雪仍是美的,古人尤能欣赏雪景,
现代人却忘记了它,或者不再能够欣赏它,
应该是什么时候都要走出门房
或者将汽车玻璃上的霜冻擦掉一小片
去看看雪景。雪的确是美的——
尤其阳光照在雪原使雪白更白的那种美:
那种美像一种骄傲,像一种富有质地的美的
竞赛。
这美拨动了我的心弦,一条激流便显现……
我坐在汽车上,看着想着看着想着……这雪:
这雪多有意思啊,你看它那白,比最好的棉花还白;
它是均匀的,如果是邻居,那屋顶上的雪会是一样厚,
甚至一个城市,甚至更广大的地区,也是如此;
更了不起的是,雪不是随便来的:
它的脸紧贴着肮脏的土地的脸,
它一点点地融化,黑乎乎的土地贪婪地吸吮它,
雪的乳汁融进土地里面,滴进了各种生命的根部,
而且雪最后的形态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丑陋的。
父亲属虎
你天赋了老虎的属性。
一只老虎注定了要走一条老虎的路。
九岁,你的母亲撇开了你和你的父亲,
她执意去往一个挤满死人的地方。
十三岁,你的父亲死于心裂病,
传说,这是一种猛虎才有资格生的病。
你以幼虎的懵懂无知度过了
童年、短暂的学生生涯,
自由散漫、不受管教,而嗜爱赌博
这早年养成的不良爱好更是贯穿了你的一生。
十八岁,你开始闯荡江湖、四海为家,
背着行囊,寻觅食物,
体味孤独和压抑。
二十二岁,你遇到了一只羞答答的雌兔,
你在她身边躺下来,使她成为你的妻子。
噢!强悍的老虎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你有了幼虎,此时你二十三岁,
依然过于年轻,但已肩负着一个家庭。
你开始狩猎,作为先行者开辟“食道”,
你深沉的脚步步武向棕色的城市之林。
噢!老虎麇集的城市囚禁着老虎,
老虎觅食的城市压迫着老虎。
三十岁,你厌恶了城市,
它成为你的梦魇,你向你的幼崽们
描述城市,过于夸张,
尤其说到苍蝇:它们布满墨线,使墨线陡然变粗。
为了自由,你意图在“荆棘丛中”建功立业。
你是一只老虎,你回归了“山林”,
这里,你成为主人,将你的“王者风范”朝向天空,
你是一只老虎,你老虎的气质从你的皮毛中射出,
熠熠生辉,如同朝阳之光。
你没有成功,而总是失败,
这并不阻碍你成为一只多么让人崇敬的老虎,
多么耀眼的老虎,多么伟岸的老虎。
你成为这片“不毛”村庄家家户户餐桌上的话题,
效仿者因你蠢蠢欲动,年轻人宽容你的失败,
你成为他们灵魂的启蒙者和行动的向导。
成功,或是失败,
对于敏感和包容的民众和大地已轻若鸿毛,
啊,你跟这五千年大地上的一棵不朽之树没有什么不同。
三十八岁,你为了孩子果断放弃你的梦,
你的皮毛已经灰黄,光泽不再,
而你的儿子已非昔日幼崽。
那是另一只老虎,另一只老虎。
你退却成为父亲,真正的父亲,真正的老虎。
我的父亲,今年你已经四十七岁,
在我眼里,你一直是一只老虎,
一只已经四十七岁的老虎……
布谷鸟
我循着鸟声起床,来不及更衣,
它的叫声真是清晰,像经过这黑色池塘的濯洗。
晨光微冷,阴云抹在天边,窗户上有风吹拂着寒毛。
它的声音是无性的,在空气里游走如同闪电,
对,这叫声就在我的感觉里闪电,没有雷音。
它的鸣叫或远或近,不知是在时间此岸或彼岸,
它像远离晨光而去,又像挨近晨光而来。
它用一种声音鸣叫,
像一个人在一片飘忽不定的麦田里刈麦,
在麦田的宽广里,它用镰刀唱——
唱词与唱腔既不华丽,也不媚俗,
它唱的仅是它生命的声音,而不是一首赞歌,
这声音有点像纤夫的口头号子,
但它的声音没有饥饿,没有责任,没有义务,没有痛苦。
哦那种美!那美似同美本身!那真是如饮琼浆般的美!
它有肉体吗,如同凡夫的我们?
也许没有,而是来自天国,诗神的声音,
它人间一闪,无影无踪,留下美的余味。
那只鸟的叫声让我感到熟悉,
那只鸟有一朵美丽的名字:布谷鸟!
这个词永远是我的,我叫它的时候
与你们叫它的时候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