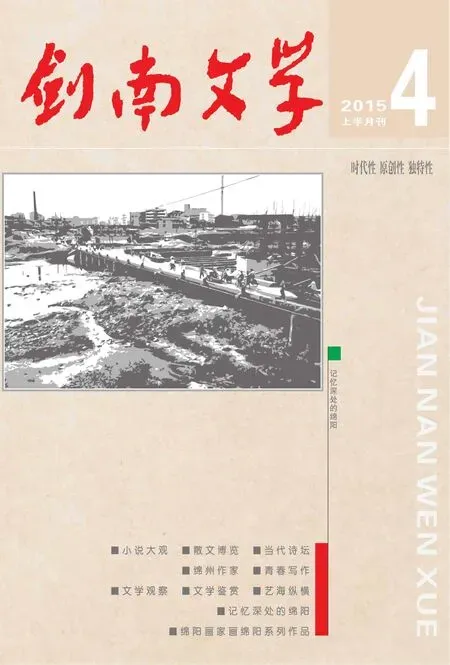重构历史:莫里森《宠儿》的喻指性书写
■唐 琳
托尼·莫里森是当代美国黑人文坛小说家的杰出代表。1988 年获得普利策奖的 《宠儿》作为其历史三部曲中第一部,也是其荣膺1993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基石作品。在小说中,莫里森从一名非裔女作家的视角,追溯了一百多年前,尘封在黑人记忆中的历史。在对历史的追溯中,莫里森打破传统的叙事模式,借助喻指这一非洲传统文化中独有的修辞手段,重新构筑了黑人民族的历史。
喻指是黑人独具特色的语言修辞实践,是非裔美国人核心的修辞策略。非裔美国文学评论家亨利·路易斯·盖茨在其主要著作:《黑人形象: 词语、 符号与种族性的自我》(1987)和《意指的猴子---一个非裔美国文学批评理论》(1988)中提出了喻指修辞理论。他发现非裔美国人的喻指修辞手段起源于古老的泛非洲文化。 在尼日利亚、贝宁、巴西、古巴、海地等地的黑人文化中存在一个精灵的形象,在贝宁的芳族文化和尼日利亚的约鲁巴文化中分别被称为拉巴和埃苏。埃苏(拉巴)是天神的唯一信使,他将天神的意愿向人类阐释,也将人类的意愿传达给天神。作为语言的阐释者,埃苏对种种寓意进行解码,对语言阐释行为拥有绝对的统治权。由此,埃苏的形象代表了语言阐释意义的多重性和不确定性,同时也是黑人土语传统中语言元层面的象征。黑人被贩卖到美洲后,丧失了公开表达自我的权利,作为被征服者,其族裔文化也丧失了合法和正式传播的途径。而喻指则满足了黑人在“失语”的语言环境下的真实情感的表达诉求。黑人喻指涵盖了隐喻、转喻、提喻、反讽、夸张、婉言法、双关并包括“间接表达法”、“嘲弄”、“高谈论阔”(loud talking)“谩骂”等多种黑人转义,是独具黑人特色的修辞方式。喻指是一种有极为有力的修辞手段和修辞策略。它将人们的注意力从语义层面转向修辞层面,从而充分体现了喻指者(能指)的力量。
作为一名非裔女作家,莫里森深刻认识到自己民族语言的力量。她认为自己的写作就是要“恢复黑人运用语言的初始力量”。而喻指正是莫里森的“黑色书写”所借重的重要手段。历史对于黑人来说一直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尽管奴隶制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被废除,其带给黑人文化和民族的伤痛却不会轻易消退。这段历史“黑人不愿回忆,白人不愿回忆。我是说,这是全民记忆缺失症。”黑人历史长期置身于历史进程之外,处于被书写、被强加、被忽略的地位。在这种白人主流社会虚构的历史中,黑人始终处于沉默和失语状态。而作为非裔美国作家,莫里森力图通过自己的”黑色”书写,重塑黑人历史。在她的小说中,人物被赋予言说的权利,掌握了话语权。他们在书中讲述自己的故事,同时也在构筑自己民族的历史。
《宠儿》取材于一份真实的历史资料。70年代莫里森在为兰登书屋做编辑工作时接触了不少黑人历史上的惨案。其中的一份资料记录了一个名叫玛格丽特·加纳的女奴在逃跑的途中,为了不再使自己的孩子沦为奴隶,在奴隶主追来的时候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在她还想杀其余的两个时,人们赶来制服了她并阻止了她的这种绝望行动。多年来,有关于这一事件的报道和专访一直在莫里森脑海里萦绕着。玛格丽特一百多年前的杀女行动无疑是对莫里森的心灵的极大震撼,也激发了她的创作灵感。然而,在莫里森看来,这个被历史记录下来的“案件”却问题重重。作为当时主流媒体的报业所报道的仅仅是事件发生的始末,不可能对当时黑人所遭受的惨绝人寰的压迫和奴役做出如实的报道。在《宠儿》中,莫里森就对这种状况进行了揭露。当斯坦普·沛德向保罗·D 出示那张有关赛斯杀婴行为的剪报时,激起了保罗·D 强烈的心理反应:“因为即便在地狱里,一张黑脸也不可能上报纸,就算那个故事有人想听。一旦你在报上看见一张黑人的脸,恐惧的鞭挞就会掠过你的心房,因为那张脸上报,不可能是由于那个人生了个健康的婴儿,或是逃脱了一群暴徒。也不会因为那个人被杀害、被致残、被抓获、被烧死、被投进牢房、被鞭打、被驱赶、被蹂躏、被奸污、被欺骗,那些根本够不上作为新闻报道的资格。它必须是件离奇的事——白人会感兴趣的事情,确实非同凡响,值得他们回味几分钟,起码够倒吸一口凉气的。而找到一则值得辛辛那提的白人公民屏息咋舌的有关黑人的新闻,肯定非常困难。”
保罗·D 对这则剪报的反应表明,即便他不识字,他对书面媒体的官方规则也了如指掌,因为重要的是,书面媒体是为白人读者建立、服务的。通过保罗·D 讽刺性的分析,莫里森喻指了被白人主流文化操纵和篡改的黑人历史,对这种“失去真相”的历史提出了质疑和批判。而在《宠儿》中,莫里森就如何书写黑人民族的历史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在莫里森的笔下,历史被置换成种种特殊的意象,通过喻指这种艺术手法间接的表达出来。黑人在奴隶制下所受的痛苦众人皆知,几乎所有的黑人都不愿回顾这段历史。正如莫里森所言:“除非迫不得已,没有人肯开口,肯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不想谈论,他们不想记得,他们不想提及,因为他们害怕。”面对这些失语的客体,莫里森运用喻指这一传统修辞手法,间接却又准确的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使 “沉默的客体成长为言说的主体”。《宠儿》中的主人公塞斯可以选择对不堪回首的往事闭口不谈,却不能抵制“重现的记忆”(rememory)对她的冲击。“重现的记忆”(rememory)是塞斯的独创,它喻指着梦魇般的过去对现在的不断侵袭。正如塞斯对小女儿丹芙的感慨:“有些东西你会忘,有些东西你永远也忘不了。如果房子烧掉,它就消失了,但地点——它的形象——还在,它不仅留在我的记忆里,而且还留在那里,留在世界上。”同塞斯一样,保罗·D 也选择把关于过去的记忆尘封在一个生锈的烟盒里,一直放在胸口,却不敢触碰。自己的胸口本来应该是心脏跳动的地方,现在成为了尘封记忆的角落。就这样,小说中的人物虽说摆脱了奴隶制,却无法治愈奴隶制给他们造成的心理创伤。然而无法走出过去历史的阴霾,就不可能去幸福的拥有未来。既然过去无法回避,只有勇敢的去面对。莫里森在小说中索性让被塞死杀死的女儿借尸还魂,重新来到124 号。宠儿的亡灵代表着塞斯在奴隶制下饱受折磨、最后惨痛杀女的过去,同时她也是三百多年来奴隶制期间惨死的所有的冤魂的缩影。宠儿的到来又一次让塞斯陷入过去痛苦的深渊。然而宠儿的不断纠缠也开启了塞斯的记忆的阀门,也打开了保罗·D 胸前封存已久的烟草盒。莫里森曾说,“让鬼魂现身的 真实目的是弥补那段历史,使得记忆更真实”。宠儿的出现使塞斯和保罗·D 重新面对过去,从而获得了更加完整的自我。奴隶制使美国黑人的历史上留下了太多的空白,莫里森以“重现的记忆”,烟草盒、宠儿的亡灵等饱含意义的意象的喻指了那段“被遗忘”的历史,填补了有关奴隶叙事的空白,将掩盖在书面历史文献下的事实公之于众,重构了黑人民族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