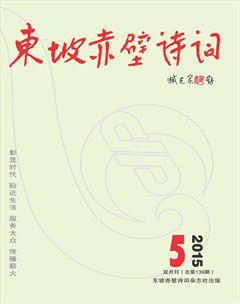从《沙哥杂话》谈到新旧体诗
宋自重
朱光潜先生说:“中国向来有诗话而无诗论。”但他在指出中国传统诗话“不成系统,缺乏科学精神和方法”的同时,也肯定它有“片言中肯,简练亲切”的长处。实际上诗话也是诗论。绵延一千多年的诗话写作,就是对诗词创作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对于中华诗词的高度繁荣、高度成熟,使中国成为备受推崇的泱泱诗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到了现代,这种文艺随笔仍不时载于报头刊尾,供广大读者随时翻阅,只需三两分钟便能有所得,有所悟,余味悠长。尤其在当下生活节奏快、网络传媒大普及的条件下,长篇巨制的理论专著能坐下来读的人不多,短而精的诗话却因其突出“关键词”而颇具优势。
阔别60余年的老同学徐文华,近来以他的《沙哥杂话》(稿)示我。其内容庞杂而丰富,透过散点剖析的思想火花,连贯起来思考,原来是一本以传统诗话形式写成的诗学著作。其中有少数涉及小说、杂文、戏剧、绘画,也都属于广义诗学范畴。绝大多数是讲诗歌的。涵盖诗歌源流论、情志论、语言论、格律论、风格论及新旧体诗比较论等诸多方面。行文短小精致,形式不拘,生动活泼,“片言明百义”,其中不乏精到见解。字里行间,饱含博览群书、知人阅世和写作实践的体验,吸取历代诗论成果,扬优辨劣,发微显隐,触类旁通。他很注重摘引古今优秀诗词的名篇佳句,寓理论诠释于诗意品赏之中,使读者在赏心悦目中获得丰富、深刻的美学营养,避免把干巴巴的说教塞给读者,深入浅出,颇显功力。
文华对新旧体诗现状的批评,引起我的共鸣。他主张批评要有辣味,要讲实话,力求准确,反对华而不实。认为发展文学事业只凭“几个文人艺客”“一捧成名”,给“名人权士”锦上添花,难以持恒。他深知新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旗帜下高歌猛进,主宰诗坛几十年,但对其现状并不满意。觉得它“自由奔放”但“奔而无羁”,“拖泥带水”,诗句比散文句子还长;以堆砌形容词代替意境、形象的塑造,弄巧成拙;以朦胧混淆含蓄,故弄玄虚,不知所云;空间上“大跳跃”,逻辑上“大颠倒”,语无伦次,“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不接地气,靠书本上得来的感受写诗,“以文字之花哨掩生活之贫乏”;一句诗分五行便吹嘘为“建筑美”,还有更离奇的“一字诗”。如此等等,怪诗叠出。在新诗举步艰难之时,旧体诗词出现复兴局面。“不薄新诗爱旧诗”甚至“勒马回缰写旧诗”的,大有人在。运用传统诗词精美的格律形式,抒写新时期社会现实、人生经历和人民心声,势不可挡。但应酬、应制、应景的“三应”诗和附庸风雅的“格律溜”等平庸之作太多,真正称得上诗的精品凤毛麟角。看得出文华是更喜爱旧体诗词的,他呼吁全面发挥诗词的社会功能。作为时代号角和鼓点的政治抒情诗,是诗坛的强音,散发着浩然正气。但不能一花独放,要适应人民群众多元审美情趣,培植一座千姿百态的诗词百花园。他列举的田园诗、闲适诗、情爱诗、理趣诗、讽喻诗、咏物诗都渊源有自。他认为,“诗不能脱离政治,但也不能成为政治的附庸”。更多关注民间疾苦和社会良知,爱憎分明,歌斥得当,诗人责无旁贷。“暴露文学永存,歌德文学易折”的议论发人深思。“不见流派,只见风派”的感叹令人警醒。关于灵感的生成,构思的孕育,情景的触发与交融,意象、意境的溶铸与升华、语言的精选与锤炼,“赋比兴”的理解与运用,格律的继承与改革,都是提高诗词创作质量的重要因素,他含英咀华,一一道来。
诗话、诗论,都是以对诗歌现状的批判和诗歌发展的导向为旨趣的。中国诗歌走向何方?是几十年来诗学争论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讲了旧体诗一万年也打不倒。又讲了中国诗歌发展要以新诗为主,要在民歌和古典诗歌基础上发展新诗。改革开放以来,这些意见仍得到主流舆论的认同。因为这是现代大众文学发展总趋势决定的。不过,作为发展方向的新诗,自应是在民歌和古典诗歌基础上的新诗,是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神韵的新诗,而不是西化、散文化、“去中国化”的新诗。毛泽东还讲了旧体诗不宜在青年人中提倡,此话遭到不少人质疑。旧体诗重现生机以来,其作者在青年人群中大量涌现,不少人在各种诗刊、诗赛中崭露头角,他们更是蓬勃兴起的网络诗词的主力。这里涉及到许多人视为镣铐的格律问题。正是高度完美的格律,使中华诗词具有无与伦比的音乐美,也促使诗词愈臻精致。而削弱音乐美,自由放任,正是新诗发展中的一个败笔,一条歧路。毛泽东自己也讲:“不论平仄,不讲押韵,还算什么格律诗?掌握了格律,就觉得自由了。”事实正是如此,对于青年人,格律并不神秘,在经过对一些经典诗词的熟读、背诵,具备一定欣赏能力之后,便心驰神往,跃跃欲试,欣然走上旧体诗词写作之路,欲罢不能。格律不仅未成为束缚诗情的镣铐,而且从中感受到因难见巧,因严见工的无穷乐趣。几十年来,对诗词格律放宽和改革的讨论一直在进行中,一些诗界达人都反对泥古不化,有的提出“押大致相同的韵”或“邻韵通押”,主张在声韵和内容实难两全之处,允许突破,不以辞害意。中华诗词学会大力倡导以普通话为基础的新声新韵,组织制订出版新韵书,提出“倡今知古”、“求正容变”等指导方针,引导中华诗词更好地适应时代,面向大众。不久前,习近平主席,针对上海把一部分古典诗文从中小学教材中删掉引发广泛批评的事件指出:“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这是非常正确的。在民歌和古典诗词基础上发展新诗,从杂交、融合、孕育、优选到成熟、完善,将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实践进程。从词的发展历史看,不算以敦煌曲子为代表的民间词,仅以相传为李白所作之《菩萨蛮》、《忆秦娥》作为文人词的开端,经过中晚唐、五代,到北宋初年令詞成为气候,花了250年,其后到北宋中叶才臻于极盛。这期间诗与词一直并驾齐驱,蔚为壮观。当代诗人、诗论家丁芒先生的观察与判断很值得关注。他认为目前新诗与旧体诗已成“双峰并峙、二水分流”之势,旧体诗需要走向现代,新诗在面向世界的同时需要回归民族。“新旧体诗必然在前进中互相吸收、补充、矫正、融合”,“当两条非水平线交叉之日,就是产生新体诗之时”。我对这样的路径和前景持乐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