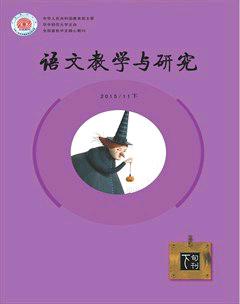相遇老建筑
秦文君
建筑犹如一把尺子,能衡量历史和文化,衡量人类对美的理解、不同时代的趣味,衡量人心。我对建筑是门外汉,可以说我的尺子是自制的,不标准,但上海的老建筑中有一些曾与我的生命和生活轨迹默默相连,我的尺子只听从我内心的声音。
外白渡桥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桥,除了它,我没有用情更深的桥了。我出生那会,父母住东大名路325号,紧挨着外白渡桥,从满月后的第一天起我就被父亲抱出来认识这座桥,以后的那几年,开门见桥,它成了我幼年最亲切的景象,很多梦里都有它。后来搬离了,去新的寓所之前,父母郑重地为我和桥合影留念,照片就贴在新家醒目的地方。在我的心目中,这座古老的桥是看着我长大的长者,也是我精神成长的见证。1971年我获准去黑龙江上山下乡,离开上海之前去了一趟外白渡桥,不是仅和它告别,而是长久地坐在外白渡桥不远的地方,看着桥上车来人往,对它诉说难言的迷惘。年轻的时候每个人要确立自我,寻找自己的位置,当时我没有找到方向,却面临背井离乡,成了最心痛的人,而肃立的外白渡桥给了我无言的情感支持。
和我童年生活有关的老建筑还有文庙。当时外婆住在净土街29号,那是一幢有年头的石库门房子,大门黑漆厚木,门上有圆圆的铜环一副。进大门是一个小天井,有客堂间,二楼有安静的内室和厢房。感觉这种建筑的好处是保持对外封闭的合围,身居闹市,大门紧闭就自成一统,好像一个独立王国。
只是通往二楼的楼梯太过狭窄,笔直的,像一条羊道。外婆是小脚,不知她老人家多年来是怎么来回从底楼攀登到楼上的。每次我去探望她,外婆都会殷切地要我陪她一起吃饭,桌子上放满了小碟子小碗,种种菜肴,她还要从瓶瓶罐罐里倒出储存的苔条花生、龙头烤什么的。
有时去的时候挨不到饭点,外婆和我说上三两句话,会急巴巴地到附近的小桥头买点心招待我,有时是一客酒酿小圆子,有时是一对糯米油墩子,一甜一咸。有时是生煎馒头、锅贴这一类的,哪怕我刚吃了午饭也要接受。不让买不行,外婆讲究礼数,有客人到,都要走一下吃饭或者吃点心的程序,老少无欺,不然她老人家于心不安。
吃饱了,和外婆说一会家常,我会和邻居家的孩子一起去文庙玩。
上海文庙是祭祀儒家文化创始人孔子的,有一个庙学合一的古建筑群。那时的我并不会体味到其中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只是暗地里仰慕这曾是古代上海的最高学府。还知道文庙好玩,地方大,还能在园子里找到新鲜的花草和飞虫。
文庙对外开放的时间不多,我和小伙伴们只好各显神通,有的趁大人不备溜进去,有的冒险翻墙,还有的用其他混进去的方式,反正一帮人最后都能在里面碰头,曲折的过程更让人觉得意趣盎然。其实小伙伴们对文庙里著名的三顶桥、大成殿、崇圣祠、明伦堂、魁星阁等建筑不在意,还奇怪大人为什么都喜欢魁星阁。我们往往会在魁星阁前的池塘及石桥边玩。印象中,魁星阁老是在修葺中,成年后才了解它是中国木构架结构的典型,体现了古代完美的结构工艺。
有一年深秋,下雨的日子,我们去文庙,守门的人并不在,小伙伴们全大摇大摆进去了。那天,文庙像是被我们几个包场了。在无比安静的环境里,我第一次发现里面的荷花池很美,在雨天里有一种特别的韵味,也许是添入了文庙的底气和文脉,有古诗里“留得残荷听雨声”的境界。
当然,哪一次去文庙也不会忘记在文庙附近逛上几圈,看看旁边书摊上的古书,沾一点文气,淘回来几张外国邮票,还有泛黄的小人书,都有烟纸店的封存已久的气味。
后来,净土街的石库门房子拆了,外婆家搬走。从此说起南市区,说起老西门,我唯一的牵挂好像就是文庙了。
多少年后,我调入出版社工作,有一次为了取稿费,去新华路上找邮局。明明是第一次抵达,感觉却熟稔到极点,呼之欲出的亲切。觉得这条路很是通透,干干净净的,沿街的小洋房把明媚的花园向外敞开着,宁静安谧之中又有着俏丽单纯。尤其是弄堂里的那些老建筑群,令我兜兜转转,在那一带走了好久,总感觉哪里有隐隐的琴声在招呼我。
从一个小寺庙发展而来的新华路被称为“外国弄堂”,那里有英国乡村式花园住宅,白色的粉墙露出黑色的木框架。有法式风情风格建筑,布局上突出轴线的对称,恢宏的气势,廊柱、雕花、线条,制作工艺精细考究,屋顶上多有精致的老虎窗。这一群老洋房,多带有庭院,庭院四周植物茂密,成为主角,房子好像成了绿树中的美妙点缀。
为了这份好感,我把家搬到了附近,从此把这条路看成是“自己的地方”。我爱在夜间散步,新华路的夜晚如散淡柔美的美少女,灯光下有优越的风情,比白天迷人多了。
一座城市要有骄人面貌和深厚的底蕴,最金贵的东西有两条:文化品位和历史沿革。横跨世纪的上海的优秀老建筑已经越来越少了,它们真是应该被当成一颗颗亮丽的珠子这么精心衬托的。
(选自《解放日报》)endprint
——巍山文庙
- 语文教学与研究(读写天地)的其它文章
- 拿来成性
- 金谷园
- 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
- 《〈师友箴〉并序》译评
- 明月寺
- 三点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