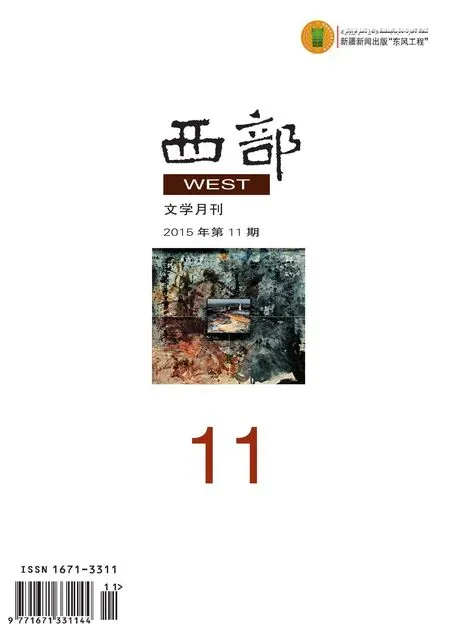陈超诗选
陈超诗选
终曲
在月光下浇灌花园的人
你竟夜的劳动使黑暗有了核心
花园:落到地面的云色
果树:吹号天使的臂膊
但硕大的泪滴在水渠中反光
月亮……正将终曲弹响
最后的劳动在“虚构”中沉湎
明天词语的花园将是悲风一片
热爱诗歌的人置身在火灾中
他失败的脸比余烬还要纯净
骤变
骤然,那一切都空了。
雪为城市压上厚厚的石膏。
他试着活动肢体
干涩的髋球窝节,传来
秘密的三角锉声。
寡言的人几乎闭嘴。
激烈的人变得寡言。
时令从初夏被骤然踹进严冬。
他的脑袋和书桌都空荡寒冷。
像是冬日晚八点钟后平壤的某条街道。
沉哀
太阳照耀着好人也照耀着坏人
太阳照耀着热情的人
也照耀着信心尽失的人
那奋争的人和超然的人
睿智者木讷的人和成功人士
太阳如斯祷祝也照在失败者和穷人身上
今天,我从吊唁厅
推出英年早逝的友人
从吊唁厅到火化室大约十步
太阳最后照耀着他,一分钟
醉酒
像老朋友韩东说的那样
在所有的愿望中我有个喝醉的愿望
万事如麻我一再延误
今番它袭来得出人意想
眩晕中我听到神经列队轮唱
朋友们的安慰却仿佛听不到声响
在我与“他们”之间被什么分开
七张嘴在动——有如隔着厚玻璃窗
快乐啊,我脸贴着春天的泥浆
博物馆、民警、女工在倒影里奔忙
连命运对我也莫可奈何
它知趣地呆在中山东路一旁
我看到另一个“我”跨入密室
把台灯打开写下简单憨实的诗行:
唯一的愿望是大醉一次的愿望
是卡通片中戴宽边帽的侠客的愿望
风车
冥界的冠冕。行走但无踪迹。
血液被狂风吹空,
留下十字架的创伤。
在冬夜,谁疼痛地把你仰望,
谁的泪水,像云阵中依衡的星光?
我看见逝者正找回还乡的草径,
诗篇过处,万籁都是悲响。
乌托邦最后的留守者,
灰烬中旋转的毛瑟枪,
走在天空的傻瓜方阵,噢风车
谁的灵魂被你的叶片刨得雪亮?
这疲倦的童子军在坚持巷战,
禁欲的天空又纯洁又凄凉!
瞧,一茎高标在引路……
离心啊,眩晕啊,这摔出体外的心脏!
站在污染的海岸谁向你致敬?
波涛中沉没着家乡的谷仓,
暮色阴郁,风推乌云,来路苍茫,
谁,还在坚持听从你的吁唤:
在广阔的伤痛中拼命高蹈
在贫穷中感受狂飙的方向?
此刻之诗
本白色的提花桌布
绣着七颗草莓
玻璃冰水瓶里橙汁的投影
加重了其中三颗的色彩
桌角的骆驼牌香烟还剩四支
足够我消受到黄昏
此刻是夏日午后四点
空调发出蜂儿的嗡鸣
我刚从充足的睡眠中醒来
明晰和无所事事,教我愉快
堆满废稿的房间
小林的披肩在微颤
播撒出香膏和残叶的气味
她的双休日架在叠句和泪水之间
她想像自己是低语的“爱玛”
等着接她私奔的马车敲击路面
在她的书房,我踏实坐着
翻看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
它与修辞无关,没有伤心的“夜莺”;
“火焰”燃烧后产生一氧化碳
它是一个词,与“捐躯”无关
词典在一个外省教书匠手上
其意义在于控制“能指”无边的发展
三十八岁已不是涂鸦的年龄
只要准确,我不再担心意象的暗淡。
诗是准确的力学,无论拉近或推远
小林甩动她深棕色的长发
拖过地板的长裙使房间的格局随之变幻
三年前我曾为这个动作心跳
有如面对一张十九世纪的倩女照片。
如今,我只注意到窗外赤日炎炎
一个二十六岁的姑娘在挥霍语言
她的废稿在堆积,比她更慵懒
我已从她心上缓缓滑落
不会再为趣味起劲地争辩。
我喜欢踏实坐着,随便聊天
小林的手指抠着水杯
她微蹙的眉尖流露出叹怨
我已不习惯不期然中的罗曼司发生
衰老是美的,干吗要“赎回时间”?
讨论开始了——“我们俩谁更荒诞”
夜烤烟草
大头,最近我常想起你
运了一天粪,军绿棉袄斑斑点点
和衣躺在知青户火炕上
向我诉说对广播站彭金凤的爱恋
门缝钻进的风摇晃着十五瓦灯泡
堆柴的地上,牙狗懵懂着双眼
烟瘾在催促,呼神唤鬼舞蹁跹
我躬背在炕火中翻烤受潮的烟草
那年月,咱们抽不起三毛五的“瑞金”烟
烟草在瓦刀下忽悠忽悠发出香味儿
像金色的草褥,集拢起清贫中的温暖
你单相思的故事教我腻烦……“烤得嘞”
旧报纸条儿变戏法似地卷成两门大炮
腮帮子嗖嗖鼓翼,脑袋紧跟着晕眩
烟草质地粗劣还混着丝瓜蔓
“妈的,这孬烟让老子喷不成烟圈”
像你对彭金凤的单恋还没成形就已溃散
剩下的事是睡前右手在兴奋中忙活
后半夜才发出一个“革命青年”的雷鼾
大头,最近我常常把你思念
我勺多菜少、瘾大烟缺年代的伙伴
如今,我跑遍全城到处找不到散烟草
每逢冬夜里饥情往上涌
只能在心里不断翻烤那些受潮的陈年
秋日效外散步
京深高速公路的护栏加深了草场
暮色中我们散步在郊外干涸的河床,
你散开洗过的秀发,谈起孩子病情好转,
夕阳闪烁的金点将我的悒郁镀亮。
秋天深了,柳条转黄是那么匆忙,
凤仙花和草勾子也发出干燥的金光……
雾幔安详缭绕徐徐合上四野,
大自然的筵宴依依惜别地收场。
西西,我们的心苍老得多么快,多么快!
疲倦和岑寂道着珍重近年已频频叩访。
十八年我们习惯了数不清的争辩与和解,
是呵,有一道暗影就伴随一道光芒。
你瞧,在离河岸二百米的棕色缓丘上,
乡村墓群又将一对对辛劳的农人夫妇合葬;
可记得就在十年之前的夏日,
那儿曾是我们游泳后晾衣的地方?
携手漫游的青春已隔在岁月那一边,
翻开旧相册,我们依然结伴倚窗。
不容易的人生像河床荒凉又发热的沙土路,
在上帝的疏忽里也有上帝的慈祥……
除夕
豪放的一群群大雪在黄昏变得零碎
但半尺深的雪毯已足够让我插稳炮仗
厨房里蒸汽旋舞
飘出平时很少闻到的
红烧肉的香味儿
妈妈用药皂为我洗着小脏头
爸爸在往刚削好的陀螺锥尖上镶进钢珠
——三只炮仗,一枚手制陀螺
就是我新年丰厚的礼物
我记得,那是在太原
荒凉的1964年除夕,我六岁的心感到
过度的幸福,恍惚,和膨胀
日记:天亮前结束写作
就这么着啦。我为一部书稿画上最后的句号。
一年零四个月,焦灼与喜悦相随。
该叫它走了,词语的镜子,钥匙,鞋,尘埃。
此后,我得以享受一段日子的空寂。
天光渐蓝,我辛劳的眼睑有舒服的细涩。
从后窗望出去,是对楼爬墙虎有力的绿漩涡。
我封好要邮寄的书稿,像黎明中的农夫勒紧卖粮的大车。
哦,你有多好听——清晨送奶人嘹亮的哨子。
一只大熊蜂北上,是整个春天的晴空!
“所有的朋友都如此怪僻”
“你所有的朋友都如此怪僻,”
那时,妻子总爱这么说。
可我知道她也喜欢这帮写诗的人,
因为她曾是他们中间“退役”的一个。
那时,门房大爷笑对咸带鱼般的长发,
朋友还未问话,他就会指出我家。
后来新朋友又兴剃大秃瓢,
未卜先知的大爷照样不用他们东寻西找。
那时我邋遢的小书房时常抑扬顿挫,
朋友们吟述和讨论刚写成的诗歌;
也有时朋友蓦地脸容愀然,
很可能他受到一个坏韵的折磨。
有些朋友性情偏狭而自恋,
彼此间话语还常常带着某种怨毒;
我也时常受到无端的猜忌指责,
内心留下过丝丝痛楚。
但说到底,他们是为“无用的诗歌”而来,
再偏狭自恋的人,仍称得上骨子里的慷慨!
兰波说得对:“诗人是兄弟。”
实用时代一个人还写诗,就不失可爱。
请相信我们那时鄙薄过世俗的名利之心,
忠实于心灵不能发表又有何要紧?
请相信曾有过那样短暂的年代,
认为怎样写诗就该怎样活人。
……你瞧,年岁不饶人!诗情荏苒,
充满活力的八十年代已像虚幻的寓言。
如今怪僻变得圆通,诗歌文胜于质,
我也只是偶然冲洗这记忆模糊的底片。
天道远,吾道迩
岁月的流逝已教会我平静地面对写作的,无用。
所谓的傲慢就是不再慌着走向,未来。
我索性把空虚弄得更空。
我把空虚从体内的黑窖,一块一块掏出来,
再往下,我将掏出肝脏中石油咕噜的喘息。
因持久开采,我的脸容有疲倦中的秘密欣喜。
我冥顽不已,浪掷“泰初有道”的提醒;
它与我有什么关系?
我什么也不想改变,
我希望自己再彻底一些,
直到变成随风而去的纸屑。
书呆子巨大的奢侈。柔情侠骨两消融。
我不可能生在一个比诗歌无用的时代更美好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