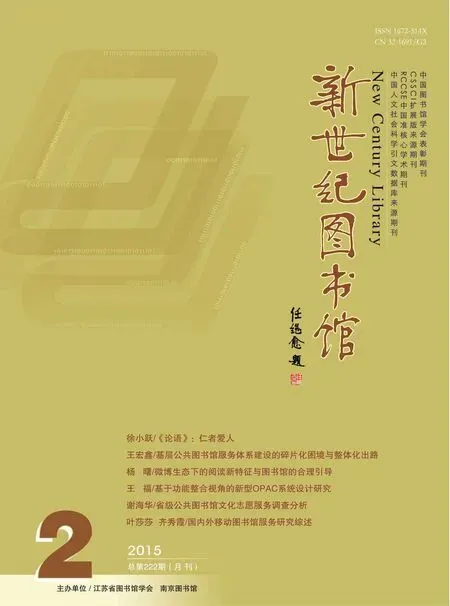来新夏新志编纂思想述论
On Lai Xinxia’s Thoughts of New Local Chronicles Compilation
Zhu Xiaomei
Abstract As a famous scholar of local chronicles, Lai Xinxia formed rich thoughts in the process of new local chronicles compilation practice. It mainly includes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redefinition the concept of local chronicles, the comparison of the new and old local chronicles, the attention to its value and function of "mentor", "education", "history", and the regulations on the style, schema, summary and other specific principles of compilation provisions, etc. He also proposed a new compilation standards known as the "morality"、"distinct"、"determines" and "orderly", and the view of multi-advancement on the local chronicles of Zhen Cun and Qu. As a historian and philologist, his ideas has not only profound consciousness of history and document, but also the learned attitude to the culture and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thus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new resources to Chinese new chorography writing practice.
Keywords Lai Xinxia. New local chronicles. Compilation thought.
来新夏(1923—2014)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学者,一生涉猎甚广,“纵横‘三学’求真知”,其在历史学、方志学、图书文献学等领域的建树,早已广为人知。
近年来,学界对先生在图书文献学和历史学方面的贡献关注稍多,而对其在地方志学方面建树的研究则显得相对薄弱,因此本文拟从地方志编纂思想入手,对来新夏先生的相关学术思想有一个大致的勾勒。
1 来新夏从事方志研究简述
从实际情形来说,来新夏从事方志学的历史,比历史学和文献学都要早得多,“治史志流略之学殆五十余年” [1]92,据先生自述,立志于地方志研究,可以追溯到他的少年时期。由于祖父曾是民国时期《萧山县志》的独立纂修者,家学渊源深厚,他在发蒙之际就能够受到志学的专业训练。据他讲,四五十年代之交,他就阅读了大量旧志,为修志工作积累了不少感性认识,并产生了“继承祖父研究地方文献的传统”的想法。不过,真正从事地方志研究,是在1980年代初。斯时,梁寒冰负责主持全国的修志工作,他担任了梁氏的第一助手。这次修志活动,不仅为其地方志编修提供了实践机会,而且唤醒了其深厚的文史知识储备,为他开始地方志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总结起来,他从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对中国方志学做出了杰出贡献,就实践而言,他参与了全国新志编修的启动工作,负责起草了全国新志编修规划和第一次启动报告;参与了若干新志的评审工作;培养了数以千计的新志纂修人才,参加了华中华北中南西北四个地区的修志培训工作;倡导和参与了旧志的整理研究工作 [2]5-6。而在理论方面,也是成果丰硕,在1980至2000年代这二十多年时间内,他先后出版了《方志学概论》《中国地方志》《中国地方志通览》《志域探步》《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等大量学术专著。同时,他也给全国几百个县、市、区甚至村镇的地方志写序。这些专著和序文,大多是评述性文字,“述”多“论”少。单从个别篇章来看,我们还无法获得其关于志学的体系性认识;但系统阅读这些著述会发现,那些分散在不同文本之中的若干言述,有如散落在地的颗颗珍珠,只要稍加连缀就能构成一副完整的志学思想轮廓。
2 方志概念及其功能、价值
2.1 方志性质、概念辨析
无疑,方志在中国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文章体裁,历代以来人们习惯将其与历史并列,并在“历史”的范畴内认定其价值和功能,如章学诚就认为志能补史、参史等,很少有对其与他种体裁(如历史、族谱等)进行细分的。而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又出现了志书的“新旧”问题,使问题显得更为复杂。所以,新志编写首先面临“辨体”问题,只有把体裁问题解决好了,才能更为自觉地编纂。来新夏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自己独特看法的。
首先,方志与历史尽管属于近亲,但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在他看来,方志的重点在于记述“地情”,侧重之点在于空间记叙,而历史的重点在乎记录“时情”,侧重之处在于时间叙述,二者虽然截然不能分割,但撰写侧重是有很大区别的,“地方志记述着各个地区历史与现状的社会文化现象,即一般所谓的‘地情’记述。” [3]100侧重点不同,写法当然也就不一样。
其次,志与族谱也有侧重点和写法的不同,他比较认同这样一种观点,“方志与族谱,均是地方性之资料,各有其价值。方志之研究,重点在‘地’;族谱之研究,重点在‘人’”。 [1]100当然,方志与族谱毕竟还有撰写内容宽窄、范围大小、对象不同等各方面的区别。
再次,旧志与新志也有很多不同的所在。在他看来,从现在的功能来看,旧志主要用于“考镜源流”,“整理旧志,首在搜求积存” [4]150,而新志则主要是为将来准备史料,是为“存史”之用的。但是新旧二志也有一脉相承的地方,“那就是注重文献资料的搜求、整理、使用、保存,这是修志和用志各方的共识。” [4]34
此外,关于现代方志的性质问题,来氏也有新的看法。在他眼里,方志的文体性质既不能算做纯粹社会科学文体,也不能算做纯粹自然科学文体,而是自然和社会科学有机结合之后的新型文体,“它既是自然科学性质的,也不完全单纯是社会科学的,而是有机地结合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精髓,体现出人类社会各种文化活动,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依据。” [3]100作为一种志书,既要记录社会科学知识,又要有记录自然科学知识,它是超越文理边界的新型文献形式,需要有跨越文理界限的新的记录方法。应该说,这种文体变化是过去志界所未曾遇到的问题,来氏的文体论是一种超越前人的志学新观点。
2.2 方志的功能、价值
地方志在中国起源甚早,上自战国《禹贡》下至当今新志,历经数千年历史。志书是一邑一地的总撰述,透过这种百科全书式的资料,不仅使人了解当地的历史、地理、经济、户口、贡赋,还可使知晓其地的人文、教育、民情、风俗,“地方志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一种著述。它记载着某一地区的自然、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文化等内容。” [4]32因此修志被历代统治者所看重。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来新夏确立了修志的重要价值,“修志为一代一地之大事” [5]12。从志学传统出发,他认为修志之所以为“大事”,是因为它具备“资政、教化、存史”三方面的功能。
首先看“资政”,所谓“资政”,当然是指为治国安邦提供有价值的资讯。在他看来,中国地方志事业具有“资治”的优良传统,“旧志若干名序也多以资治为言,新志映现之资料可供资治之需者颇多。” [3]100其次是“教化”功能,他认为这是历来编志的主要目的之一,他举《华阳国志》所列“五善”要求为例,说明历史上修志的出发点所在,“教化是历来编志的主要目的之一……《华阳国志》序中标举出著书的‘五善’要求,即达道义、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勋、旌贤能,基本上是要求发挥教化职能。” [3]101在他看来,这个职能至今并未过时,不过“教化”的内容和方式发生了变化而已。再次是“存史”,前述二者是就当前价值而言的,而“存史”则是着眼于未来价值。不论旧志新志,这个功能不能改变,“旧志虽难称尽善,而保存部分资料,备后世所参用,为新编县志史源之一,已为修志者所共识。” [6]6在他看来,既然地方志是对某一地区自然、地理、历史、社会、经济、文化情况的综合著述,那么这种撰述本身就是当地历史素材之一,它本身的体裁尚有别于“史”,但功能和历史一样,都详细保存了该地的真实情况,“它是撰述历史借以取材的资料宝库之一。它和史虽然体裁各异,但却是相辅相成不可缺一的两个方面。” [7]46所以他认为,以资料为基础的地方志,在最低的意义上应具有“储存史料”的功能。那么,如何“存史”呢?他认同章学诚有关志之于史作用的论断,即志对史而言,可以“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往往今日信志,即可备他日信史之需。” [3]102所以他希望新编地方志,在创编之始就要明白资料搜集的重要意义,备作某一邑地未来“信史”的第一手可靠资料。
3 方志编纂原则
作为传统文献形式,方志早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编纂规则;面临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这种规则又不得不进行某些方面的调整,大到体制目次,小到数字图表,不论内容还是形式,都需要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进行新的规定。在传统志学基础上,根据新志实际需要,来新夏对新方志的各个部分,提炼出了相应的编纂原则。
3.1 首明体例,次制纲目
在方志的编纂之先,明确“体例”被来新夏放在第一的位置。他曾多次阐明这个观点:“修志之要,莫过于定体例” [5]11;“志书首重篇章体例” [6]5。那么他心目中的“体例”何所指呢?在我们看来,它是指根据某种编纂思想确立的统摄全书的纲目制式,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通常所说的“篇章结构”。在他看来,这个纲要是全志的决定性因素,“篇章结构为一志之大纲,纲举方能目张。” [8]39有了这个明确的纲要,才可以编制清晰的目录,因此目录在方志的整个结构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也许会问,来新夏为什么如此注重体制、纲目的作用呢?这其实跟他对方志的价值定位有关的。在他的观念里,凡是图书典籍,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即精读书、浏览书和翻检书,精读书指的是“经典要集及具特识卓见之著作”,浏览书指的是“一般读物与文艺作品”,翻检书指的是一般“辞书、工具书与资料书”。方志在这三类书中,大体属于工具书之列,功能主要是供人们查阅翻检,而不是精读泛读,因此,目录的功用就显示出来了,“从地方志查阅某一有关地方事务之资料,往往须从头至尾阅读,行之实有难度,是以有编制目录以供检阅之需。” [1]94所以,他判断方志成色高下,有一个首要标准,就是看结构是否合理、纲目是否清晰,“一志之优劣,首察其篇章结构。” [9]31
3.2 概要为“新志之创例”
传统方志在书之始页往往有一概要性文字,以作提纲挈领之用,“小序一体,有两千余年历史,但所用多在书录,而近年新编方志有于篇首立无题小序者,大都为全篇之提要” [10]13。新志编写不再沿用“小序”之名,而代之以“概论”“概述”抑或“总述”,名称虽异而功能实同。来新夏肯定了这种做法的正当性,对于其各种灵活变体也予充分理解。“或分类论述,或浓缩全书,或分段提要,或按阶段概括,诸事并存,尚难一致,似亦无需一致。” [5]11他认为这种做法不单单是继承传统的问题,还是一种体例创新,在给不同县志所写序言或评述文字中,他明白地表示了这一层意思,他说“概述之立为新编县志之创例” [6]5,它的功能不仅在于引发阅者兴趣,“可概一地之盛及一书之要,进而引发通读全志之兴趣” [11]37,还在于引导进读,“读之可得……一地古今纵横之面貌,苟欲深究,又奏引导进读全志之效。” [10]13因此不管是哪种形式的概要,“终当以简要为是” [10]13,这是他对概述写作的基本要求。他总结出概述的三种写法:“全志浓缩法”“特点勾勒法”“分段提要法” [12]3,各种写法理应根据内容或体例的需要,各尽其宜,各尽其妙;三种写法没有一定之规,也没有优劣高下之判,只要能达到引起兴趣、引导进读的目的,就称得上是一个好的概要。
3.3 “大事记为一志之纲目”
大事记与概要有所不同,概要是将志书内容综括于前,而大事记则更进一步,将书志(甚至概要)中的核心事件撮录于首,所以大事记是志书的核心内容,是概要中的概要。对于新志编写中出现的这种罗列大事记做法,来新夏是十分肯定的,“大事记已为新志之定例,近年多为编年与纪事本末相结合之体。” [13]51他认为这是传统史书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结合,它叙事简约、中心突出,“较旧体更便阅读” [4]226,因此应该在新志编写中得到推广。
关于大事记的功能,他总结出这么几条,一是提纲挈领,得一书之要,条理史事,得一地之要,“凡阅读志书者无不先读大事记以得一地之要,得一书之要。有提纲挈领,条理史事之效。我读新志殆百余种,无论作序或评说,无不先读其大事记” [4]225。二是补缺查漏,有利于志书记载之完善,“检阅全志大事记述之有无遗漏,而一些虽为大事而难以详述于志文者,则可以记事本末之体入于编年大事之中,可具取精用宏之效。” [5]11三是有利于对某地历史大事有一纵向之整体把握,“上迄远古,下迄1949年10月,上下古今数千年,大事必备,梳理浙江数千年历史,了如指掌。” [4]225因此,在他眼里,“大事记为一志之纲目” [6]5,具有钩玄纂要、纲举目张等多重效果,是对中国志书优秀传统的一种创造性继承,应该在新志书编写中得到进一步推广。
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大事记编纂过程中,不可忽视“人”在事件中的作用,所以他强调,“人物为一志之灵魂,见物见人,斯为整体,但诸志多单立人物传以示别立于志体。” [5]12在他看来,抓住了“人”,才算抓住了志学的根本。
3.4 数字无离奇、方志外语化
中国虽是方志大国,具有悠久历史,但新方志编写是一项现代事业,不仅需要继承传统,更要开拓创新,因此势必涉及到“新”与“旧”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来新夏完全持一种客观务实的科学态度,一方面,新志不同于旧志,旧志很少涉及具体的数字统计,而新志涉及得最多的是一些社会经济发展的数字图表,如何采信这些数字文献,是方志学编纂史上的一个新课题。来氏充分理解数字文献在新方志编纂中的重要作用,并肯定其所具有多方面意义:“表列数字以概括全志内容,使读者一目了然,并与综述接合一体,相辅相成,不读全志文字,几已尽知晋城之基本面貌” [13]51。本着一种科学精神,他要求新志编纂者特别注意数字文献,“一是要全志数字无矛盾,二是不要出现离奇的数字” [3]103。数字之所以“矛盾”,甚至出现“离奇”,这不仅仅是一个统计技术问题,还是一个史家态度问题。来新夏指出这种倾向,显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意有所指的。
新方志编纂有一种越编越长的趋向,少则几十万言,多则百万甚至千万言,对于一般读者来说,通读几无可能,检读也不容易,所以来新夏主张应将索引附于志末,便于阅者检索,提高新志利用率,不少新志采用了这种观点,精编索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另外,在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世界一体化趋势日益加强的当今,新志编写还涉及到不同语言的互译问题,来氏对于方志的国际交流秉持积极的建设态度,他说,“我尝于多次审评志书会议上倡导,新志应增概述英译,虽颇获赞同,而以兹事较难,尚未见诸实施。今《河西区志》不顾艰难,将概述译为英文,使仰慕中华文化而苦于不娴中文之海外人士亦能因此而窥中华之地情风物,中华文化亦将广被宇外。《河西区志》创始之功,固不可没。” [14]39这些观点,反映了他宽阔的世界眼光和浓厚的现代意识。
4 新志编纂的标准及其他问题
4.1 新志的标准问题
关于新志编纂标准,来新夏写过一篇专文《新编地方志的标准问题》进行过详细系统的阐述。在他看来,任何史志都无法逃脱于意识形态的控制,新志当然不能例外。在他看来,封建社会的任何志书都有两条基本要求:“一条是为了巩固封建制度,统治者要从志书中寻求进行封建统治的资料依据。另一条是为封建官僚制度服务,是为地方官提供‘护官符’的依据。” [15]59而“社会主义新志”,当然要服务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政治标准是首要的,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导思想上的马克思主义化,二是修志的目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两个根本原则指导之下,一部新志应该具有三种素质,即:“(1)全面反映本地区的历史和现状;(2)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3)进行爱国主义与革命创痛教育的乡土教材。” [15]59这是新志纂修的第一个标准,也就是政治标准。
他还详细论述了编纂的论述标准、资料标准和文字表达标准。新志论述,第一要具有全面性,涵盖所有重要内容;第二要有时代性,是写具体时代的地方志;第三要有地方性,地方志是记录具体地方实情的文献。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调动所有文献资源,举凡文字资料、口碑资料、实物遗迹,都是方志的资料来源,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史料的真实性、可靠性、权威性。他认为,一部地方志在满足以上条件后,还要在文字表达上做到“清、定、齐”:“清是文字清楚;问题清楚;定是内容论点、资料征引,完全可以定下来;齐是各方面附表、附图、附资料都齐备。” [15]62无疑,这一根据古今方志理论与实践总结出的编写标准,对于今后中国新地方志的编写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4.2 各种志书均有一席之地
言及地方志,人们总是自然联想到省志、县志,以为只有这些才是地方志的“正宗”,其实并不尽然,地区志、村镇志乃至城区志,都应该有自己的存在价值。来新夏非常肯定这些正统志外的方志编修。首先,他认为,地区志应有自己的独立品格,它不是省志的补遗,也不是县志的叠加,恰恰相反,它“从本身功能出发,立足全区,面向民众,反映整体,体现特色”,具有“补省志所缺,详省志之略,通县志所不通”的独特价值 [16]49。而对于志界颇有异议的城区志,他也持肯定态度,认为一个城区也有自己的历史文化、经济地理,理应有自己的历史记载,所以他对编写天津市的《河西区志》称赞有加,专门为其撰写序文 [14]39。另外,在当今志界更为边缘的村志、镇志,他也秉持积极的支持态度,认为那是一个需要抢修的遗产。他阅读过《长河镇志》、江苏《震泽镇志》和天津《小站镇志》等镇志数十种,并为其写序做论,表现了极大的热情 [17]39。他认为村镇志的范围,其实还可以进一步细分,应该包括乡志、镇志、村志、里志、场志、团志、坊志等在内,而这些志都应该“于中国方志史上有其一席之地” [18]18。如今,城市化浪潮已经席卷中国城乡,传统的村落大面积消失自不待言,就是城市里的街区也变得面目全非,为这些地方立志实际是为留住一种文化遗迹,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来新夏先生的上述观点是非常富有历史意识的。
4.3 不拘一格,力求创新
一般认为,地方志是地方资料文献,撰写编修也是一种资料长编式的资料汇编工作,它要求按部就班、循规蹈矩,不要求过浓的主观色彩,也不需要过多的体例创新。但在来新夏看来,这个观点是有待商榷的,他在不同地方强调,地方志也不是没有创新的余地,比如他称赞《榆次市志》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能吸取当代新编诸志之优点而自有主张,并独创因地而异之特色” [9]31。
此外,在方志的使用或消费方面,来氏的不少观点也颇有新意。他主张地方志的存在形态应该由“静态”变为“动态”,要改变过去被动提供信息的姿态,变为以生动的形式吸引阅读群体的注意,这在方志观念史上都是未曾耳闻的新见。“应当改变地方志的静态存在,不能只等待别人来使用,原封不动地提供,任人采录;而是要使地方志资料变成信息化的动态。认真研究和参与各地区的地情研究,把志书中的资料结合现实,适时地发布各类信息,引起领导关注,诱发群众兴趣。” [3]103为了做到这一点,不仅要做到让撰写形式为群众喜闻乐见,还要做到利用现代营销形式主动推广自己,让志书由书库走向广场,变成商品为一般群众消费,“使志书这一典籍商品化,向社会市场推销自己,用典型效果大力开展宣传工作,组织各种以志书内容为依据的知识竞赛、演讲会和展览会,使志书立体化,全方位地普及于群众,使其从懂得读志书到用志书,则志书自可不胫而走” [3]103。
5 结语
在数十年的志学编纂实践中,来新夏对于新志概念、功能、价值,对于新志的各个构成部分的编纂原则,对于新志的编写标准,对于各体方志的多元存在价值等,都做了全面而精到的阐述。通过简单梳理,我们不难发现,来新夏先生之于方志编纂,采取的是一种非常通达博洽的写作姿态。历史学家和文献学家的双重修养,使他对方志编修充满一种深厚的历史意识和文献意识;而传统的涵养在他那里又变成了创新的无穷动力,他总能在“通”与“变”关系中找到自己的最佳调适位置,因此他的方志观念既有厚重的历史含量,又有强烈的现实诉求。不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强调得更多的还是方志的“信史”品格。他鼓励志书突破历来志书避讳褒贬之规训,“力求直书” [9]31,对敢于揭露历史真相,敢于言他人所不敢言的良史品格赞佩有加。他还要求,入志资料,必须“事事有来源,字字有出处” [3]103,并对这些材料认真进行校订、考证,尽可能做到系统、完整、准确,具有可征性、可信性。这些要求恐怕才是地方志编纂的最根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