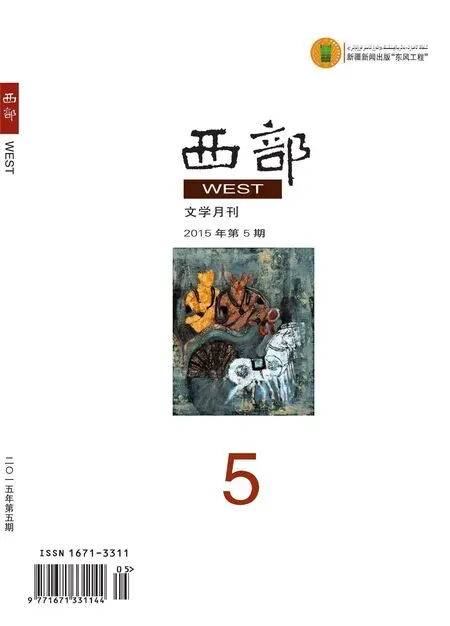生死之间
朱凤鸣
生死之间
朱凤鸣
凝固的九月
九月,又是九月。我讨厌九月,就在四天前,儿子小安的爷爷去世了。去年的九月,女儿辛夷的奶奶去世。
我是个没有婆婆缘的人。2012年,我订了大农业别墅,一直希望等别墅交工、收拾出来,能够让女儿的爷爷奶奶来和我们一起住。女儿的奶奶特别喜欢花花草草,如果我们住在别墅里,白日里看看花、拔拔草、浇浇水,必然是很开心快乐的。谁知道别墅连地基还没开始挖,老太太就已经撑不住了。我只陪护了她一个晚上,第二天晚上,她已经用不着我陪护了。人送进殡仪馆,我留在病房收拾东西,收拾着收拾着,眼泪哗哗地往下流。对面病床的陪护亲友里,有公司财务处的叶姐在,她有劝我。这么复杂的关系她可能也是知道的吧。我对自己的事情一向不愿对外说,不过公司就这么大,时间长了总是知道的。我们平时几乎从无交往,她竟然也理解了我对前婆婆的感情。我只是后悔陪护得太少,就一晚,仅仅一个晚上。
我陪护的那晚,婆婆的情况比较稳定。我跟她说要好好养病啊,我等着她帮我去别墅种地呢。她使劲握着我的手,着急说话,却说不出,就让我拿纸笔来。凭扭曲颤抖的笔迹,附带比划,我们勉强知道,她让我们找乌鲁木齐的一个医生。那医生是她二十年前在乌鲁木齐住院时相识的,已多年没联系,多半不可能找着。她的思维已经不知在哪里神游了。
人死前会想些什么,我还是没弄明白。只是我当时看监测屏上指标稳定,还是很有信心她能挺过来的,至少能再拖个一年半载。前姑子尽心照顾着,我和护工在,她仍不肯走,最后我催着,三个人轮流睡觉,她才勉强睡了一会儿。
隔了一天,说好晚上我陪护,还没到时间,就接到医院电话。等把女儿带上匆匆赶到医院,已经晚了。老太太一会儿就断了呼吸,绿色的屏幕上只剩下一条直线。护士来抢救仍然没有用。老太太的外孙女海伦也来了,我听见她尖锐的哭叫:“我没有奶奶了!”姑夫回家拿来寿衣,旁边一位阿姨帮着我一起为老太太擦洗身体换衣服。
之后的好长一段时间,我几乎处于失忆状态。我想不起来我是否参加了追悼会,是否上了山看老太太入土,女儿辛夷是否去送了奶奶。她是唯一的孙女,应该是上山了吧。我想了很长时间也没有结果。直到公公去世,我又回想老太太去世时的事情,终于想起来下山后在餐馆里的几个片段。我一定是上山送老太太了,不然不会有答谢宴这一出。辛夷只去了殡仪馆,并没有送奶奶上山,到小西湖墓地。她还小,我没舍得让她到阴气太重的地方,怕有什么不好。
我再婚生子,担心儿子没人带。因为妹妹才生了双胞胎,我妈要帮着照看那一双小人,而儿子的奶奶早已去世,爷爷年纪又大了,更不可能帮着带孙子。我曾托人问前婆婆公公,要是儿子小安实在没人带,就托付给他们帮着带,他们竟然也答应了。虽然后来我没有把儿子送过去一天,但是我还是很高兴,毕竟他们心里是有我的,连带小安都能接受、喜爱。
十五号那天早上,我正在开早上例行的碰头会。丈夫晓峰打来电话,说公公住院了,他要去白区看看。我让他等等我,等开完会我也去。他问十分钟内能不能开完,我回答困难,于是他放下电话先走了。公公以前也因“房颤”住过院,没几天就出院了,这次也不会有问题,万事都往好里想吧。谁知道没过多会儿晓峰又打来电话,哽咽得泣不成声,说爸爸已经走了。
我从来都知道生命生生不息的道理就在于有生有死,也知道难以接受死亡的原因是心理习惯而已,不过事到临头仍然觉得止不住地悲痛。星球按着轨道运行,突然间身边的星球少了,引力变化总是会失衡的吧,重新适应只有依靠时间。
我并不是一个喜怒形于色的人,哪怕一个人在角落里,都不愿面对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我也常常教育女儿要学会不动声色控制自己。不过这一回,我又一次不得不面对。
生生不息
我都忘了,九月里还有儿子安安的生日。儿子天天盼着过生日,从姐姐八月底过完生日,他就天天倒算着自己过生日的时间,到最后十天了、八天了、七天了,一日日算着,到十六号,晚上我从儿子爷爷房子那边赶回来,儿子还在提醒我,明天就要给他订蛋糕了,晚上就该把买好的BRT公交车玩具送给他了。
儿子爷爷下葬的时候,我们一致决定不要儿子跟着去,从头至尾他一点都没有参与。我们只是告诉他爷爷已经去世了,要埋在土里。女儿辛夷十六岁,虽然不是亲生的爷爷,但过六一、过年的压岁钱、礼物,爷爷一向是和亲孙子外孙们一样给的,这份心意沉甸结实。她已经十六岁了,有一些事情她该知道,也该去经历,所以让她跟着参加了追悼会、上了山。
十七号送老爷子下了葬。十八号却是儿子小安的生日。
晚上小安的三姑叫吃饭,摆了一桌子,把在城区的姐弟都叫来了,说老爷子虽然走了,但我们要过好,才是给爸爸最大的安慰。吃完饭切蛋糕,大家把躲在哥哥屋子里的小安叫出来点蜡烛,唱歌。小安是真的觉得幸福,自己先把灯关了,又把旁边哥哥屋子的门关了,以求黑暗里的烛光照耀他的快乐。我们拍手唱生日歌时,他转着圈儿一脸的陶醉,一如早秋的阴雨天里,灰蒙蒙的天空下仍然闪着金黄的大叶白蜡树叶。
儿子,生日快乐,成长快乐!要让爷爷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心慰!
世俗的好
我表面乖顺,实则长有反骨,而且有时候不愿加以掩饰。反抗世俗,许多琐屑懒得理会,身外的鸡毛蒜皮更是懒得听、不想问。对于身后事,一样是不愿像世俗那样被人摆布,聚集亲友折腾喧哗一番。我宁愿悄悄地走,纵然做不到张爱玲那样的遗世独立,绝不愿按部就班地埋进土里,再烧一堆纸灰。我知道死也许不过是生命另一种形式的转换或者空间的迁移,只是害怕死亡来临时的太过疼痛与太过难堪,还有几乎可以断定的毫无尊严。为此,我不止一次冷言冷面地告诉晓峰,我死后,火化,不通知任何人,不需再买墓地,就埋在我爸的坟包里陪着我爸。每次他听了都不作声,我知道他不愿意这么早就面对这样的问题,甚至还觉得我有些无理取闹。但这是迟早要面对的事,我不过打个预防针罢了,谁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呢?那些意外早夭的人,多半以为自己离死亡还很遥远。
这一回,加上参加过很多次葬礼的经验,我更加明白了,怎么死、甚至死以后的事,都是不由自己决定的。虽然,我更愿意静悄悄地走远。
意外的是,这一回,我却觉得世俗的好来。
总是生死事大,好歹要把人好好地送走,大到穿寿衣、买棺木或者骨灰盒、通知亲友、联系退管站、敲定坟坑位置、落实随车吊装载机和干活的人工、写悼词,还有安排外地赶来的亲戚,小到洗相片、折黄纸、剪方孔纸钱、叠金元宝、准备干鲜贡品、找干活的手套,都要安排好,我甚至找同事帮我到工业园区偷偷砍了两节拇指粗的柳枝用来做孝棒。我在殡仪馆和坟坑之间奔波,一遍一遍商量讨论葬礼的事项和程序,生怕哪里会有错漏。更不要提接待一波一波来看望的同事、亲友、同学。短短两天时间里,大家总要打起精神应对这些繁复的程序和琐屑事务,这无形中分散了许多的注意力和悲伤。
我的父亲去世时日已久,差不多有二十年了。那时我才工作不久,什么都不懂,什么心都没有操,主要是我妈和父母的老乡同事在忙活。葬礼上的许多事情我既不知晓也早遗忘了。但我还记得最要好的同学来看我,我抱着她哭。记得在灵车上看着路两边雅丹地貌的土山,凛冽的寒风刮着,脸早已僵硬。
以前也帮同事同学家打理过丧事,剪孔方钱,叠纸元宝,也有帮着联系用车之类的事宜。但未曾像这次一样,突然理解和体会了世俗的好处来,于是反省自己,是不是有点儿自私。将来死去给家人找的麻烦,如果能抒解他们的悲伤,那是不是应该考虑就这么接受繁琐又吵闹的世俗的死法。经年累月多少代人传下来的习俗,我忽然理解了,这固然是对挚爱的生命的敬重和难以割舍,可又何尝不是为了排解那些悲伤,平衡只有时间才能治疗的心理惯性。如此,觉得从俗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只是死都不能如自己的愿,多少有些不甘心。
死的事
小时候觉得死是太可怕的事。
第一次见到死人是小学四年级。那时我家还住在郊外一个油田建设单位,附近有一些树林和田地,地里种菜、麦子、玉米,也种苜蓿。有时候我一个人或偕几个伙伴去树林、田地逛,早上跑步时也会跑到那边,因为有人工渠道,那一片即使没有种庄稼地的地方,也因为多了这一点水,开了许多野喇叭花,粉白的野喇叭花热热闹闹的,十分可爱,可没想到我第一次见到死人就在那里。是个年轻小伙子,穿着深灰色衣服,膝盖弯曲挂在电线上,我至今还能记得那人皮肤已经被电打得灰黑。
我们从此开始想,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更早的时候,也是知道死人的,涉及一桩旧案。在中学附近,四连(那时还按兵团的老建制称呼)那边最后一排房子,据说是那家男人把老婆杀死后逃走了,直到女尸发臭有人报警才发现。我听说后也跟着去看,只远远看到警察进出,人们在外间围看,没见着死者的尸体,不过刺鼻腥臭味是闻得到的。我都记不得是不是夏天了,只记得那一片空气中漫天漫地的臭味,太久远的记忆了。
再接触死亡,已经到了上中专的时候了。我那时刚上独山子石油学校不到一学期,数学老师赵吾生就因煤气中毒去世。老师是陕西人,穷孩子出身,刻苦上进,好容易一切好转,结婚成家,却又突然去世。我们几个同学在他中毒第二天去医院看的时候,他躺在病床上,脸上仍有着煤气中毒后的淡粉色,当时他还和我们点头示意打招呼。和老师同时中毒的还有他新婚不久已经怀孕的妻子,师母的情况比他要好一些。我们都很乐观地以为老师没有什么问题了,放心地回到了学校,没想到第二天就传来噩耗。师母还好,只是孩子没保住。送老师上山的时候,山头有很多乌鸦,不停在头顶盘旋,呱呱啼叫。很多年以后,我依然能想起赵老师戴着眼镜,在阶梯教室里给我们开模糊数学讲座的样子,一脸微笑一脸温润善良。这么多年,也不知道还有谁记得他,有没有人上山去给他上坟。
我父亲去世前,和后来去世的前婆婆一样,有好长时间,紧紧地、用力地攥着我的手,不愿意松开。护士来了,我看着护士给父亲做心脏按压,然后放弃抢救。老乡刘阿姨帮着我妈为他擦洗身体、换寿衣。即使因为生病多年没有到工地干重活了,父亲的身体依然是一块块的肌肉,这得是干了多少重活积累出来的!我看着父亲的脸变色,皮肤变黄,慢慢渗出一层细密的油脂。
这些年来参加过许多葬礼,大多还是和单位有关。有时候车间的员工亲属去世,办公室主管工会的同事、主任都不在,我就代表单位去参加葬礼。见得多了,世态也看得多。子女多、混得好的,葬礼就热闹,人多车多花圈多,显得排场;子女单薄、又无权无势的,就冷清得多。代表单位参加葬礼,我大多数时候是不上山的,只参加追悼会,有时候看到葬礼实在冷清的,就也带车上山,稍微给撑点面子。前婆婆走的时候,家里人决绝,并没有刻意地通知谁,甚至在乌鲁木齐的亲戚,都是追悼会的前一晚才告知,他们根本没时间赶来。做主的是我的前姑子,女儿的姑姑,她这举动倒是很合我心意。
现今已经不觉得死人有多可怕了,反倒是有时候希望,这世上真的有灵魂或者鬼魂,至少我还能再次见到我爱的人,可是不能如愿。丈夫晓峰曾不止一次地说,要是妈在就好了,她一定很喜欢我。我就答,要是她老人家在,我就给她买裘皮大衣,哄她高兴。只是说说而已,好比无数次午夜梦回,我希望父亲过来看看我们。可惜,这世间其实没有如果。
生死一线
我生儿子小安的时候,进了医院,老何怕晓峰受不住压力,特意跑来医院陪着他。有过生孩子经验的我,知道生孩子说起来伟大,其实是最难堪不过的。我那时已经开始宫缩,一阵阵痛不可忍,却闹着让晓峰无论如何把老何劝走。假如可以的话,我希望一个人把孩子生下来,那时候的自己不想让任何人看见。
生女儿辛夷的时候还年轻,才二十六岁,顺产,却一样的难堪。生产前后的情形不消说了,生完后推出产房进入病房预备上床时,盖在身上的床单直接掀开,孩子的爸爸、姑姑、姑夫都在场,帮着一起把赤身裸体的我抱到病床上。我筋疲力尽,没有任何反抗的心思和力气。
生的时候,我明明听到医生护士说要侧切,但根本没感觉到。过了几天护士来拆线,我才确切地知道真是侧切了。可想而知那时有多疼啊,平时针扎一下手指头就嫌疼,生孩子时剪开身体最娇气的部分竟然都没察觉。
等到我再生儿子小安时,已经三十六了,这意外到来的孩子我终究是没舍得不要。然后呢,就是自讨苦吃了。阵痛时时发作,我根本无法忍受,闹着让晓峰去找医生给剖腹,顺便把卵巢里的囊肿给剥掉。我的主治医生不同意,说我第一胎是顺产,这一胎孩子也不是很大,让自己生,卵巢囊肿可以以后再做手术。可我越到最后越觉得不对,明明做B超都说孩子比较大,四公斤以上了,和主治医生的判断差别也太大了,加上阵痛没完没了无法忍受,我让晓峰再去找医生。所有的医生护士都觉得我太娇气,无理取闹,说可能我对疼痛比较敏感。天知道我一直以为自己坚强勇敢甚至是强悍,谁晓得生个孩子完全刷新了我对自己的认知,原来我又怕疼又娇气。那时我的宫口已经开了一公分半,医生来问我,还是坚决说剖。于是安排了剖腹产。幸而当晚值班的是医院技术派的“蒲一刀”大夫,我顺利剖产,像母鸡肚子里的蛋黄一样的卵巢囊肿也被剥掉,儿子称重四公斤八,体长六十公分。我躺在手术床上听大夫和护士们聊天说,怪不得闹着要剖,这么的大孩子是应该剖的。
事后我无数次想,如果我没有闹着坚持剖腹产会是什么结果。这么胖的孩子,根本不可能自己生下来。听说有孩子卡住被锯开盆骨的,我不寒而栗!生孩子痛得我已经快死掉了,如果再锯开盆骨……我自小到大最大的手术,就只有第一次生产时的侧切手术和生儿子时的剖腹产了,真的难以想象!
回到病房以后,我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冷的时候全身发抖,牙齿打战,热的时候全身是汗,冷热轮流交替,没完没了。我抱着被子闭着眼睛,暗暗想,这一回恐怕在劫难逃,我是不是见不到明早的太阳了?却忍着没敢说出来。丈夫显然也被吓住,去问了医生也不明所以。后来,干脆给我打了两针镇定剂,折腾了大半夜总算慢慢消停下来。
今年夏天表妹生孩子,我年纪越大反而越知道危险,所以紧张了许多。表妹宫缩早,持续时间特别长,到医院产科又人满为患,我放不下心,开始找朋友找同学拉关系帮助鉴定情况、联系住院,其实我自己生孩子都没有找任何关系。表妹面临的情况和我有些像,宫口开了,却开得很慢,到最后忍不住闹着要剖腹产。照例医生护士们都认为她情况不错,羊水清澈,应该自己生,让她坚持。她一人在待产室里,我在外面听见她连自己丈夫都不叫了,一声声绝望叫我“大姐,我要剖”。我心惊胆战,在待产室门外大声说话哄着她,然后去找医生交涉。等到前面一名孕妇的双胞胎生产手术做完,终于轮到她手术。她的情况比我要好得多,孩子是正常体重。我在手术室外面对表妹夫说,决不许说她一个“不”字。我是过来人,知道要不是疼得受不了,不会不想顺产,表妹农村出身,自小干农活长大,绝不是娇气的人。
我生了小安,女儿很高兴,对弟弟稀罕得不行。中午儿子午睡,我们把他放在客厅的圈线地毯上。女儿凑过去,偎在她弟弟身边睡着了。阳光从窗外照进来,打在白色地毯上的两个孩子,一室安宁。她在日记里写道:“我有自己的弟弟了,亲生的弟弟。”
但是那时,我好长时间不高兴。为了给儿子取名字不高兴,为了自己莫名沦为生育工具不高兴,种种不高兴,只觉得生而绝望,郁不可解。这种情况持续了三年之久。又过了两三年,有一天,我突然回想起来,奇怪自己当时怎么会那么悲伤绝望,才恍然明白,我中了一种叫做产后抑郁的毒,当时自己毫不自知,家里人全无觉察。我一直以为像我这样开朗又理性大的人,精神疾患和我不会有一星半点儿关系。刚工作在电厂上班时,听说有一个同事的妻子因为产后抑郁,在孩子两岁时自杀身亡。那是我第一次听说产后抑郁,却很不理解,孩子都两岁了呀,正可爱的时候。唏嘘感慨一番,也就过去了,从没把它和自己联系起来。等我反应过来,天已大亮,好几年都过去了。
生死一线,生的喜悦和忧郁也是相形相生。
秘密
每个人都为探究生死的秘密而来的。上天很仁慈,给每个人都恩赐了一次机会。可是,只有一次。而且,这次机会不能积攒经验。别人的生死体验对于自己来说,没有任何借鉴作用,哪怕是再亲近的人。旁人的死亡于自己总是隔靴搔痒,等到自己终于明白了死到底是怎么样的,却又没法再告诉给任何人。
濒死时会感到愉悦吗?会见到白色耀眼的光吗?会经过长长的黑色通道吗?会有三点七克的灵魂脱离肉体飘浮到空中吗?活着的我们无从知道。我问过经历生死一线抢救过来的人,那人回答说,什么都没有,没有光,没有黑色的通道,没有飘浮在空中。
我沉迷了很久佛教道家的修炼。我当然知道自己并没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去修真炼气,只是一直好奇,人生究竟会到什么样的境界。会像傍晚时分坐在飞机上一样,飘浮在浩浩荡荡的云层之上看见万道金光吗?我曾去天台山拜访一位道家龙门派传人。天台山中有五百和尚坐化地,师傅说那里气场非常强大,他喜欢在子夜时分在山谷中的一块平地打坐,不论寒暑,盘膝坐在一只蒲团上。他说,闭关时,会一一倒溯过去的经历。在山里,他还不止一次地看到穿着古代衣服的道士的身影,每每要出现时他的心里必会有感应,然后抬头,就看到那身影或从山头或从松林间飘过来,离得很近,然后又飘走。师傅也只是看着,没有更多的交流。传说昆仑山中有修炼的高人类于神仙,我在想,他们是不是像传说中的那样食金风餐玉露?对于庸碌的人们,他们会嫌很臭的吧?可是,即使是寻访过许多隐士,写出《空谷幽兰》的作者比尔·波特,怕也是没有见过这样的修真神人,更遑论他们所能达到的人生境地,以及生与死的秘密。到了那种境界,是不是就能超越生死?
我的膝盖上有一片榆树叶子一样大小的淡褐斑块。我妈说那是我生下来就有的胎记。小时候家里人常说,我要是丢了,凭着这块胎记也能找回来。我是个迟钝的人,长大以后才明白,若是连我的人都不见,怎么可能凭着腿上的胎记找到我?香港的钟茂森先生写过一本名为《生死轮回的科学证明》,据说在大量调查实证的基础上写成,其中讲到身体印记是从前世带来。我就猜想,大概我前世里曾经因为摔过跤,在膝盖上留下了这么一小块疤痕,所以留到了这一世。我小的时候经常做同一个梦,梦见天崩地裂大地震,许多人奔逃,我却怎么跑也跑不动,腿磕在地缝边沿的土石上,身后的地面是更大的一条裂缝。我那时候还没上学,并不知道什么是地震,但这场景反复出现在梦里,生动惊悚,犹如美国灾难大片。我怀疑,这个我反复做过的梦,应该就是我前世留下的记忆残片。
我以前有位领导,喜欢耍个二杆子,说自己定然是活不到七十岁的,“早点死了算球!”他在国企重组改制时内部退休,不过一年光景就发现肺癌合并骨转移瘤,痛不可忍,几次想要自杀,家里人只得偷偷把剪刀之类的危险物品都藏起来,小心看顾。他并不像以前表现的那么大义凛然,甚至做个胆囊手术,都忐忑不安的。从他身上我知道,怕不怕死真不由自己说了算啊!所以,我不再预设自己死亡的场景,肯定不能像预想的从容面对,害怕就害怕吧,那是人之常情。
我无数次想象自己死亡的场景,被汽车撞得身体支离破碎或是长年疾病奄奄一息。这么想象的时候,有时候很镇定,因为知道每个人都必然一死,有时候不免慌张,不知道临终之际会有多痛,到时候自己受不受得了,会不会很难堪而且毫无尊严。我想问问谁,可真的无从去问。这生死之间的秘密,无从窥视,不能预设,只得自己穿越过芸芸众生,穿越过漫长一生的爱与美,舍下今生的花开和花落,亲身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