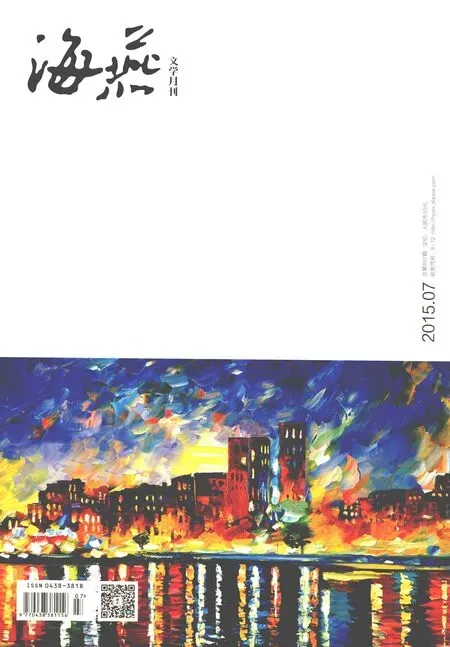打冒支
□董晓葵
近日,人民网舆情研究室发布了关于网络低俗粗鄙语言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检索中文报刊媒体发现,媒体在标题中使用最多的三个用词是“屌丝”“逗比”和“叫兽”。2014年网络低俗词语排行榜中,“尼玛”“屌丝”和“逗比”位列前三。
打量这些网络低俗语会发现,它们的诞生有三种途径:一是脏话的变形记;二是英文发音的中文化、方言发音的文字化,如“碧池”“滚粗”等;三是网民自我贬损的创造性词语,如“屌丝”“心机婊”等。
互联网的去中心化与权威解构,使网民们在话语权上获得平等,有那么一小撮网民,将网络视为可撒野的“自留地”,以低俗语言谩骂他人、攻击社会宣泄个人情绪。这样的人一旦形成规模,势必会放大网络负能量与文化粗鄙现象。网络愈是开放,“公地”的属性愈明显。网络给了每个人“存在感”,这种“存在感”一定是公认的文化认知和共守的道德规范。为所欲为是行不通的。
调查报告显示,一些纸媒无视社会责任,对文字缺乏敬畏,为吸引眼球,使用网络低俗语制作标题,其中“屌丝”“逗比”和“叫兽”在纸媒标题区出镜率最高。网络低俗语向纸媒转移,活像一群小瘪三登上了大雅之堂,令人不忍目睹的不是小瘪三的恶形恶状,而是纸媒高大上的节操碎了。在报网融合的发展趋势下,传统媒体纷纷创建新媒体平台。采编人员转变思路的首要功课,就是改变文风。如何改变文风?网络低俗语成了笔上的救命稻草。写一篇在新媒体平台推送的文章,标题里至少要有一条网络流行语,在内文的垄间,三句一个“屌丝”,五句一个“滚粗”,都是稗子。写得顺手了自感风生水起,对字里行间充斥的痞气浑然不觉,久而久之,就彻底陷入了网络表达的恶俗狂欢。说实话,每次读到这样的文章,我心里总有说不出的难过。
自媒体节目《吴晓波频道》在爱奇艺上线300天时,吴晓波写了一篇《300天报告》,讲述这档节目突破60万订户数背后的故事与理念。有一段话令我特别惊喜有力量:“天下所有以笔为生的同学们,相信我,我们不必去迎合这个时代,不必刻意搞笑,不必二,不必哗众取宠,只需做好自己的专业。这个世界总有那么一些喜欢我们的人,在你看不见的城市乡村遥望相吸。”
不要丢得太彻底。今天丢一点,明天丢一点,就彻底将自己弄丢了。
在本刊续写大连话,得到编辑部同仁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副主编曲圣文在本刊写过多篇“民间语文”,“民间语文”与方言关系密切。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各地报刊纷纷开设“民间语文”栏目,对“民间语文”的理解与定位分为两种:“民间语文”即地方方言。通过对一个地区方言的解读,展现这个地区的历史文化与风俗人情;“民间语文”是指网络上出现的新词汇、新句式、新文体。这些诞生于民间,或被民间改装过的语文,生动地描摹了当下的中国社会,表达了当下的民众心态。那种一语道破的直接,一针见血的痛快,是新闻不便报道的,是文学羞于表达的。民间语文,既可彰显社会正能量,也可透视畸形世态。
写大连话,首先要找大连话词条,有时我从菜市场打捞到鲜活的大连话,有时在与父母长辈聊天中捕捉到地道的大连话,有时在餐馆听到邻座迸溅出生猛的大连话。大连话入耳就身心大悦,归宿感非常强烈。
大连人语速普遍快,像一股急着入海的河流,大连话跳跃其间姿态撩人,有时候我担心忘了,就记在手机上。那天和朋友在餐馆吃饭,与一对中年女士邻座,胖妇在诉说,瘦女在倾听。“我一生下来,我妈就把我送到上海的姥姥家,我在上海一憋气长到19岁才回大连,你想想,我跟我妈能有多少感情?”一憋气,在这里就有了方言意味,一个孩子寄人篱下长期与父母疏离将产生的问题,在“一憋气”这个词里发出了预警。
有些方言词,是在普通话的义项上进一步引申改造,很容易被理解,没有太多嚼头和写头,“一憋气”就属于此例。有些方言词,沉淀在老百姓的日子深处,是老辈人的老话,我们很少听过,所以会觉得陌生。我要寻找的正是这些方言。网络上被编成各种段子、小品的方言,我们已经很熟悉了。
一位朋友住在寸土寸金的高尚地段,他每周必回工人村看父母,不仅是尽孝道,也是歇息的必归之处。当推开楼道的破门,老楼的气息兜面而来,他一头扎进去,身心温暖慵懒。随成功阶层保健养生修身养性的潮流,他也熏香,那无比名贵的白棋楠也闻过,可都没有老楼道的气息令他陶醉。夏季这里蚊蝇飞舞,他像一只光鲜的大猩猩又蹦又跳躲避着,没有嫌弃,尽是愉悦。他说,老宅的气息,是岁月的味道,让人心平静而舒服。
回到父母家,褪去一身皮,他就是“老王家的二小子”。吃母亲自制大酱焖的鲜鱼,和父亲用大连话唠嗑,唇齿留香,心里开花。那些纯正地道的海蛎子味大连话,就沉淀在老楼道里,沉淀在父母老派的生活方式里。
与父母唠嗑,涉及到对人的品质的评价,父母常会说“打冒支”这个词。从字面意义上看,找不到丝毫头绪。
每次写大连话,我都要与编辑部各位同仁交流探讨,开阔思路,尽量挖掘词条背后的历史信息和生活意象。这令我想起那些年喝茶,喝的是普洱茶,刚开始喝不明白,不会识辨一饼茶的品质与内涵,掰下一块儿,找明白人喝一喝、品一品,这茶到底是干仓还是湿仓?是纯料还是拼配?有哪些风味特点?写大连话亦如此,拎出一条大连话,让同事们帮我品一品,这条大连话里有哪些生活故事,有哪些独属于这一方水土所孕育的性情秉赋。
经编辑部曲老师确认,“打冒支”是非常典型的大连话,大致有两个意思:一是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扯大旗做虎皮,用有权有势的人抬高或粉饰自己;二是为了满足私欲,以不正当手段冒名顶替,将钱物据为己有。
我将“打冒支”记录在案,却一直没有写,因为找不到感觉。它对我来说,太陌生了。
不久前,某出版社领导将一位写小说的业余作者推荐给我,他写了一部长篇,要自费出版。出版社向我介绍了他,向他介绍了我。文人心意相通,惺惺相惜,有能力为文友们提供出版服务,举手之劳,我是很乐意的。该作者在电话里一开腔,我就婉拒了。阅人识物,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评判体系,有时候不一定科学公正,就要讲缘分了。缘分好,我们对撇子“三观”趋同是一路子人。
他又打电话来,说出版社领导是他好朋友,还抬出了几位本地文化大腕。我心里反感,口头却有些迟疑了。
在多数情况下,“打冒支”是无法进行核实的。他说自己是市长家哪门子亲戚,你总不能找市长问个清楚吧。但我就进行核实了,出版社领导明确表示该作者系上门投稿类型的,有交集无交情。
“打冒支”是非常令人讨厌的行为,有些人“打冒支”就像吐痰一样随便。
一位同事提醒我说:“你不是一直对‘打冒支’没有感觉吗?这个作者的行为不就是‘打冒支’吗?”
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方言所描摹的人情世态,就发生在我这里。
在生活中,我们都有过“打冒支”的行为,重的事关人的品质,轻的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布置工作或开展改革,没有一呼百应,反而暗礁重重,此时将更高级别的领导抬出来,编几句领导口谕,通常会扭转局势。
与“打冒支”有关联的一条方言词是“吐口唾沫都是钉”,意思是说话算数,说到做到。也说“一口唾沫一个钉”。《东北方言口语词汇例释》记载了这样几条例句:
“妈办事吐口吐沫是个钉,我说不行,就是不行,说到猴年马月,俩字儿,不行!”(《朝阳小戏选》第33页)
“我黑蝴蝶红口白牙不说黑话,一口唾沫一个钉!”(《新剧选》第59页)
大连人也常说这个方言词。东北人的爽快果断的处事风格,被这一句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男人话不多,一句是一句,句句是真经,一口唾沫一口钉。这样的男人魅力值无穷大。不光是男人,咱女人说话也要算数。
现实安稳,内心熨帖,少不得大连话的润泽。
大连话从不期期艾艾、碎碎念,也从不隐蕴词锋,像锋快的霜刀,像奔腾不息的大江大河;大连话旁若无人,像夏天穿的大裤衩,怎么舒服怎么来。有大连话的地方,庄谐杂出,四座皆春。如果你累了,厌了,就回父母家,回老房子住几天吧。
责任编辑 张明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