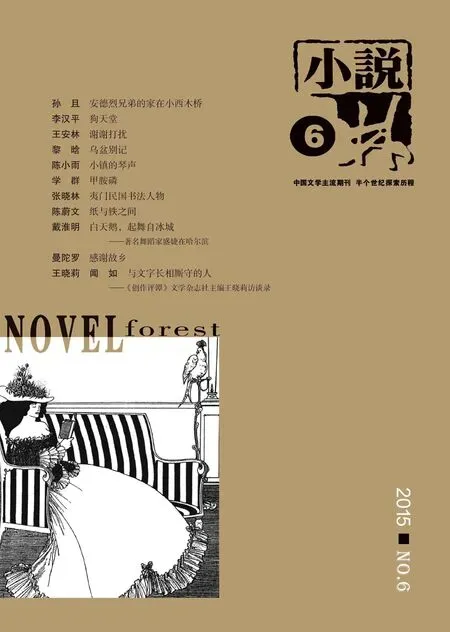小镇的琴声
◎陈小雨
大幕拉开,我走上台,向观众深深鞠了一个躬。然后坐下,把油光乌亮的京胡搁在膝盖上,静默了两分钟,立刻,伍子胥在昭关被阻的满腹幽怨袭来,牵动起我同样哀怨的心弦,我抖弓捋弦,情动手动,伍子胥那深沉凝重的唱腔顿时在耳边响起:
一轮明月照窗前
愁人心中似箭穿
小时候学琴,爸爸教我的第一首曲子就是《文昭关》。
父亲是个琴师,用京剧的行话说,是拉弦的。在京剧班子里,伴奏的乐队分文场和武场,武场是打锣鼓的,用现在的话属打击乐。文场是拉弦的,用现在的话属丝竹乐。乐队里,除了司鼓指挥全场,是乐队的灵魂,琴师是京剧的主要伴奏者,是乐队的主力。爸爸对自己是个琴师非常自豪,曾扒拉着手指头跟我说过一些著名琴师的名字,只是父亲说的这些人,都是过去年代的名家,现在的人只知道好声音和天王天后。
父亲第一次教我拉琴的时候,是在镇上那三间平房里。那天停电了,月光幽幽地从窗户上照进来,父亲坐在炕沿上,在膝盖上铺好布垫,小心翼翼地拿起那把油光乌亮的京胡,架在膝上,调了调弦说:我先拉段《文昭关》你听听。接着父亲便拉了起来,父亲眯着眼睛,微仰着头,像沉浸在尘世之外的另一个世界里,随着弓弦的抖动,琴声和月光便一起流淌起来,父亲边拉边用虽不嘹亮但却浑厚的嗓音唱了起来:
实指望到吴国借兵回转
谁知昭关有阻拦
《文昭关》讲述的是春秋时期,楚平王无道,宰相伍奢直谏被杀。伍奢之子伍子胥一人逃出,前往吴国借兵报仇。路过昭关时被阻。楚平王在各处悬挂图像,缉拿伍子胥。伍子胥被阻于昭关,幸遇隐士东皋公,将其藏在家中,一连数日计无所出。伍子胥辗转反侧不能成眠,一夜之间竟须发皆白。
父亲当时刚从省城调到县剧团,与小学教师的母亲结束了十几年的分居生活,十岁的我也是刚刚与父亲朝夕相处,唱段里的含义虽然不懂,但听起来还是觉得父亲拉的唱的都那么柔情和绵长。父亲拉完把京胡递给我,说你试试?我很忸怩,不肯接父亲的胡琴,父亲硬把带着他手温的京胡塞到我手里,说不怕,拉吧。虽然我经过了两年推磨压碾,能拉出点调调来了,但在师从过梅兰芳琴师的父亲面前还是不敢碰那琴弦,只是怯怯地拉了一句便停住了,父亲摇摇头说了句:不成啊。
父亲调到县剧团以后,回家的时候多了,对我学琴的要求更严了。然而当时的我,并不认为跟着父亲学琴有多么重要,小孩子贪玩的天性也常常使我忘了练琴。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刚拿起京胡,试了试弦,窗外便传来小朋友们的喊声:燕子!来玩!我迟疑地拿着京胡,想了一下,把京胡装进了琴袋。我低头向外跑去,与刚进门的爸爸撞了个满怀。爸爸一把揪住我,严肃地问道:今天练琴了吗?我脱口而出:练了。爸爸阴沉着脸,不相信地:练了?我咋没听见琴声?我脑子一转,回答:我写作业前练的。爸爸仍然不相信我说的话,命令道:去把琴拿来我看看。无奈,我只好把京胡从琴袋里拿出来,递给爸爸。爸爸看了一眼琴筒,立刻眉头竖起:练了松香怎么是平的?我愣住了,无话可答,哀求地:爸爸,让我玩一会儿吧?没想到爸爸厉声喝道:不行!
舞台上,随着手指的捋动和手腕的颤抖,琴声和灯光交融到一起,弥漫到全场的每一个角落。观众席上没有一点声音,只有我的琴声像风一样掠过宁静的水面,像蜻蜓一样划出一圈圈的涟漪。命运多舛的伍子胥,蛟龙搁浅的伍子胥,困顿无助的伍子胥,只有面对一轮明月,唱出自己的九曲愁肠:
一连几天我的眉不展
夜夜何曾得安眠
父亲调到县剧团不久,由于京剧不景气,剧团解散了。那是个深夜,我正在床上熟睡,只听到大门哐当一声被撞开了,一辆摩托车的声音进到院子里。母亲披着衣服下了床,看到父亲,惊愕地问:你?这么晚了,怎么半夜回来了?父亲严肃的声音回答:有件事要跟你商量,所以连夜赶回来了。母亲问:什么事情?父亲走进屋里说:县剧团要解散了,要大伙重新就业,你说我改行做什么?听到这话,我不由得睁大眼睛。妈妈嗫嚅地说:散了也好,干个拉弦的,一年到头到处跑,累人不说,还挣不了几个钱。爸爸说:县里给剧团安排重新就业,让大家报志愿,你说我报什么?母亲沉思了一会儿,说:以前你拉胡琴没人瞧在眼里,要钱没钱,要权没权,连个看门的也不如,看门的逢年过节还得送礼呢!不送礼不给你方便。这回趁机会,咱不如实惠点,找个实惠的事情干干,你说呢?父亲呻吟了好一会儿,说:那好,我明白了。接着父亲又说道:我要连夜赶回去,明天八点就填表。不知什么时候,我迷迷糊糊睡着了,等我早晨醒来的时候,父亲早已回城了。
第二天下午,一辆大卡车停到我家门口,不停地按着喇叭。我和母亲诧异地走出家门,伸手拍打着卡车驾驶室的窗户:师傅!干吗?有事吗?开车师傅摇下车窗,指着副驾驶室里一位穿制服的人说:你问他,他让我按的!我和母亲把目光转向穿制服的男子,男子转过身,我和母亲霎时愣住了!爸爸?我脱口喊了一声。穿着制服的爸爸把驾驶室的门打开,跳下车,朝母亲行了一个不太标准的敬礼:报告燕子她妈,陈斌前来报到!母亲高兴极了,嘴巴咧到脑门后,伸手打了爸爸一巴掌:看你个德行!爸爸告诉母亲,县里照顾他这样的老艺人,在重新就业的选择上,尽量满足老艺人的要求,所以他被安排到镇上的公路站,负责检查车辆。查车是个轻松又实惠的行当,能改行到这个行业实在是幸运。爸爸把崭新的大盖帽拿下又戴上,身板拔得笔直,伸手做了个挡车的姿势,喊道:停车!爸爸挡车的照片从此镶在了客厅墙上的镜框里。
爸爸调到镇上以后,每天都逼着我学琴练琴,稍有懈怠,轻则斥责,重则处罚。在爸爸的指导和监督下,我的琴艺一天天有了长进,但心里头的不满也一天天增加。一天晚上,电视里播放动画片,我忍不住上前看了起来。爸爸总是很晚才下班回来,他拖着疲惫的脚步走进客厅,看到我在看电视,阴沉着脸问我:今天练琴了吗?我忙回答:练了。嘴上说练了,但还是心虚地关上了电视。爸爸仰脸靠到沙发上,说:把琴拿来我看看。我知道这是爸爸要检查琴了,因为早有准备,所以毫不胆怯地把京胡递到爸爸手上。爸爸看了看琴筒,琴筒的松香上有道磨损的沟痕。我瞥了爸爸一眼,爸爸满意地点点头,说:好,拉一遍我听听。我愣住了,我只想到了爸爸检查琴筒,没想到爸爸要检查成果,我一时没了主意,站在那里,迟疑地看着爸爸。爸爸瞪大眼睛问:怎么,没听见?拉给我听。无奈,我只好接过琴,拉了起来,刚拉了几句,爸爸便吼道:别拉了!你老实说,练了没有?我知道瞒不过爸爸,只得低下头承认:没有。爸爸不解地:没练过?那松香的沟痕是怎么来的?我的头更低了,嗫嚅地说道:是我用小锯刀刮的。爸爸愤怒地站起身,指着我的鼻子骂道:让你学琴拉琴,是为了你好!没想到小小年纪,这么没有出息!爸爸的话让我长期练琴积压的不满爆发出来,我语不择言地顶撞父亲:拉琴拉琴,拉琴有什么用?你琴拉好了,为啥还要改行?爸爸被我戗住了,呆呆地站在那里,好久才缓和语调说道:你还小,跟你说不清楚……
俺伍员好似丧家犬
满腹的含冤向谁言
吴国大夫伍子胥,英雄好汉伍子胥,雄才大略伍子胥,面对重兵把守的昭关无计可施,只好把诸多无奈藏进心里,将锋鸣的宝剑封到匣中。我手中的弓抖动着,心也随着弓弦在颤抖,低回婉转和苍凉凄楚的琴声打动了观众,也打动了我自己……
爸爸当上了公路检查员,很是潇洒了一阵子。我看见过爸爸查车时的样子,穿着制服的爸爸很威严地站在公路旁,看到有车辆驶来,手中的旗子一挥,来车便老老实实地停到了路边。爸爸和同事走上前去,一个敬礼:对不起,证件拿出来看看。爸爸的表情非常严肃,司机看了一眼,从怀里掏出驾驶证和行驶证等证件递到爸爸手里。有一次,一位司机认出了爸爸,惊讶地问道:这不是剧团的陈琴师吗?怎么?爸爸尴尬地:我不是陈琴师,你认错人了。司机很为自己的发现得意,执著地:错不了,我也喜欢拉弦,早就认识你,陈琴师,啥时候改行了?爸爸无奈,只好承认,红着脸说:怎么,改行不好吗?司机点点头:好好,当然好,查车可比你拉弦滋润多了。爸爸骄傲地抬起头:那当然了,要不谁改行呀?对吧?爸爸把证件还给司机,笑容可掬地手一挥:注意安全!
可是时间不长,父亲脸上的笑容便渐渐消失了。公路站缺少会计,上级又迟迟调不来人,站长对爸爸说:咱这一伙人里就你算个知识分子,你就当这个会计吧。于是,爸爸就当上了小镇公路站的会计,开始与阿拉伯数字打起交道。父亲能玩转“叨来米发”,却玩不转1234,那时计算器还没那么普及,大部分财会人员还是用老祖宗留下的算盘。半路学珠算的父亲经常算错账,也经常受到站长的训斥。每次我放学回家,都看到爸爸坐在沙发上,在吃力拨着算盘,嘴里还念念有词:一五得五,二五一十……月底是爸爸最难过的坎,爸爸费尽周身之力把账算完,把账本送到站长跟前,小心翼翼地:站长,算好了,你看看?站长接过账本,立刻皱紧眉头:这个月才两万二?不对不对!爸爸好像也不相信自己,犹疑地:对了,不是两万二,是两万五。站长眉头竖起:我看你是二百五!再算!
一天晚上,我在客厅里写作业,爸爸很晚才回到家里,母亲在学校还没回来,父亲走到房间里,一个人在炕沿上坐了好长时间。爸,你为啥不开灯?我走进房间,想去拉开关。父亲伸出一只手说:不用了,我想就这么坐会儿。我想转身出去,爸爸突然又说:燕,你想拉琴吗?我不知道爸爸为什么这样问我,想了想,点点头,爸爸说:你把胡琴拿过来。我从衣柜里拿出京胡递给父亲,父亲铺好布垫,轻轻地拿起那把油光乌亮的京胡,调了调弦说:我教你拉《文昭关》。月光从窗户上斜照进来,映着父亲略显苍白的脸庞。父亲拉了起来,过门之后,是父亲浑厚低沉的声音:
我好比哀哀长空雁
我好比龙游在浅沙滩
我只觉得爸爸的声音和琴声充满着说不出的惆怅和迷茫,如同灰白色的月光覆盖着整个小镇和山野。父亲后来学会了珠算,算错账的时候少了,站长也很少训斥爸爸了,爸爸逐渐适应了会计工作,脸上又有了初戴大盖帽时的春风。可谁知,一件意外事情又打破了爸爸内心的平静。
那年夏天,省城的一个剧团下乡演出来到镇上,爸爸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剧团就是他当年工作过的剧团。当时父亲正在路边查车,一辆装满货物的卡车开了过来。爸爸伸出手,卡车缓缓停在了路边。爸爸走上前去:对不起,请拿出证件!司机摇下车窗,突然,坐在副驾驶位置的男子叫了起来:师傅!爸爸抬起头,男子扑到窗前:师傅!不认识我了?我是你徒弟王军呀!爸爸惊喜地张大嘴:小,小军子!王军从车上跳下来,师徒两人兴奋地抱在一起。王军说:师傅,穿这一身真神气呀!差点认不出你了!爸爸也说:师傅也认不出你了!小军子变成大军子了!哎,你咋到这来了呢?王军说:剧团搞送戏下乡,我们是到这演出的。你看,他们这不是都来了么!顺着王军的手,果然几辆大巴车开了过来,缓缓停住,几个男女从大巴上下来和爸爸握手,拥抱——
爸爸穿着崭新的制服在饭店里宴请老友,酒席桌上,摆满了丰盛的菜肴。王军及一些剧团朋友坐在桌旁。爸爸举起酒杯,感慨地说道:我以为这辈子再见不着你们了,没想到你们送上门来了!来,为咱们相逢干杯!干!干!大家说着举杯,一饮而尽。王军站起来,激动地:我王军没有师傅就没有今天。师傅,我有个提议,我师傅《文昭关》拉的最出色,今晚上演出《文昭关》,我想让师傅操一回琴,让大家听听什么是金石之音!咋样?大家立刻拍手响应,爸爸连连摆手说:不行不行,手生了,手生了。最了解师傅的是徒弟,王军诚恳地:师傅,你说过,艺人心不死艺不丢,你肯定行。大家一齐劝说:陈师傅,没关系,你就操一回吧!其实,王军的提议触动了爸爸的心弦,但爸爸还是矜持地望着左右:大家不嫌弃,那我就,再操一回?
记得父亲当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练了一个下午,青砖瓦房里传出悠扬的琴声,引得路过的人都驻足倾听,许多人诧异地说,小镇还从来没听过这么好听的胡琴,从来没听说过还有这么一个高水平的琴师。
那天晚上,我早早地来到戏场,等着看父亲操琴。说实话,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见过爸爸在演出现场拉琴,所以内心的兴奋和渴望可想而知。我故意坐在几个熟悉的女孩跟前,骄傲地对她们说:今天是我爸拉弦,你们信不信?几个女孩狐疑地看着我,摇摇头。不信你们就等着看吧!我故意扭过头去,不再搭理她们,专心地看着舞台上面。大幕徐徐拉动,锣鼓响起来了。接着,悠扬的琴声响起来,我激动地拉着旁边的女孩站起来:快看!我爸!我和女孩的目光同时向舞台侧旁看去,同时落在了坐在台首拉京胡的人身上,然而拉京胡的不是我爸,而是王军!我一下子愣住了,张大嘴说不出话来。女孩转过头看着我,我顿时觉得无地自容,转过身朝场外跑去——
我一口气跑回家里。家里门开着,黑糊糊的,我喊着:爸!爸!径直冲进爸爸的房间,见爸爸一动不动坐在炕沿上,月光从窗户上倾泻进来,父亲的面庞就像一尊石像。我不满地质问爸爸:爸!你不是说操琴吗?为啥不去?爸爸看见我,身子动了一下,说:燕,你回来了?爸爸身体不舒服,不去了。我不相信爸爸说的话:不!你不是刚刚还练琴的吗?我看到旁边的京胡,还没有装到琴袋里去。爸爸见掩饰不过去,苦苦一笑,说:爸现在不是琴师了,人家领导不愿意,爸去讨那个厌干啥?你说是不是?爸爸用无奈的眼睛看着我,我一时无话可说了:可是,我已经告诉她们今晚你拉琴——爸爸又笑了笑说:燕,是不是你想听爸爸拉琴了?来,爸爸在家拉给你听,给你拉一场完整的《文昭关》,好吗?说着,爸爸拿起旁边的京胡,调了调弦,面对我一个观众,郑重地拉了起来。我不知道爸爸在舞台演出时拉琴是个什么样子,只觉得这是我听过的爸爸拉的最好最完美的一次,琴声深沉稳健,流畅多姿。不仅有低音区的婉转迂回,缠绵苍凉,更有高音区的苍凉高亢,悲愤激切。爸爸的琴声如泣如诉,月光似乎也在这倾诉中融化了,一滴一滴从房檐上落下来。和着琴声,爸爸用他那沙哑的声音唱道:
我好比哀哀长空雁
我好比龙游在浅沙滩
我好比鱼儿吞了钩线
我好比波浪中失舵的舟船
省剧团离开小镇后,爸爸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脸上失去了过去少有的笑容。父亲开始失眠,开始是躺下几个小时不能入睡,后来是半夜里早早就醒来,接着是整夜整夜地睡不着。每当爸爸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妈妈总是不解地问:你怎么了?爸爸无奈地笑笑:没怎么,我睡不着。妈妈又问:劳累了一天,怎么会睡不着?爸爸回答:我也不知道,一点都不困。有一天半夜,妈妈感觉爸爸的手在不停地动,翻过身问:又怎么了?爸爸说:没怎么,你睡吧。妈妈说:没怎么你手在抓摸什么?爸爸停顿了一下,说:手生了,练练指法。
爸爸的记忆力开始下降,经常想着这个忘了那个。母亲领爸爸到过几家医院,都说是心理和精神问题,劝爸爸想开点,爸爸这时才像个听话的孩子一样笑笑,点点头。母亲有时唠叨,有吃有喝工作好好的,工资也不少,比你拉弦那时候强多了,有啥想不开的?爸爸听了也像个孩子似的笑笑,但笑得有些无奈和苦涩。
爸爸是在那天傍晚出事的。爸爸和同事站在路边检查车辆,快下班了,恰巧一辆载货大卡车开了过来,爸爸挥了一下手中的旗子,卡车停了下来。爸爸和同事上前例行检查,让驾驶员拿出证件和货单。检查完毕,爸爸和同事后退一步,卡车发动了起来。突然,健忘的爸爸好像又想起来了什么,又回到车前,刚刚启动的卡车没注意,将爸爸碾到了车轮之下……
爸爸被送进了医院抢救。我背着书包闯进病房,只见爸爸躺在病床上,闭着眼睛一动不动。我撕心裂肺地喊着:爸!爸!你怎么了?你怎么了?爸爸在病床上一直昏迷了四天四夜,我和妈妈一直守着爸爸四天四夜。第五天晚上,爸爸突然醒了,妈妈惊喜地招呼我:燕子!燕子!你爸醒了!我忙扑到病床前喊着:爸?爸!爸爸慢慢睁开眼睛,挣扎喘息着:扶我,起来。我和妈妈急忙把爸爸扶起,靠在床头上。爸爸好像刚刚从梦中醒来,他看看妈妈和我问:我是不是,睡了,好几天了?妈妈和我点点头,爸爸似乎感叹地:好久,没这么睡过了。妈妈难过地捂住脸,转过身去。爸爸说:我做了个梦,梦见燕子,在拉琴。我急忙拿起放在旁边的京胡,说:爸,琴在这,我这就拉给你听。爸爸住院的第二天,妈妈就让我把爸爸的京胡拿了来,放在爸爸的枕旁。我和妈妈都知道,这是爸爸的心爱之物。爸爸看了看京胡,满意地点点头,喃喃地说道:燕,记着,琴是人拉的,人也是琴拉的,人这辈子要是拉起了琴,恐怕就再也分不开了,明白吗?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爸爸又说:你可能还,不明白,爸爸是真明白了,人如果能,再活一次,多好。说着爸爸摇摇头,闭上了眼睛,我急忙拿起京胡,哭着说:爸,你放心吧,我会明白的。爸爸睁开眼,拉着我的手,期待地说道:燕,爸爸还没听你,拉完《文昭关》,拉给爸听,好吗?我擦掉眼泪,点点头,拿起旁边的京胡。爸爸像个孩子似的依在母亲怀里,看着我。我抚摩着京胡上的琴弦,第一次在爸爸面前没有怯懦地拉了起来,我只觉得心在颤抖,手在颤抖,伍子胥那满腹愁肠和哀怨都通过我的琴弦倾泻出来,爸爸的忧郁愤懑和感伤也都通过我的琴弦倾泻出来,它无边无际,汹涌澎湃,溢满了整个房间,淹没了漫漫的黑夜,我似乎听到伍子胥和爸爸的心同时在喊:
我好比波浪中失舵的舟船
思来想去我的肝肠断
今夜晚怎能够盼到明天
爸爸倚在母亲怀里,在我的琴声中慢慢闭上了眼睛。这时,我看到窗外月如寒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