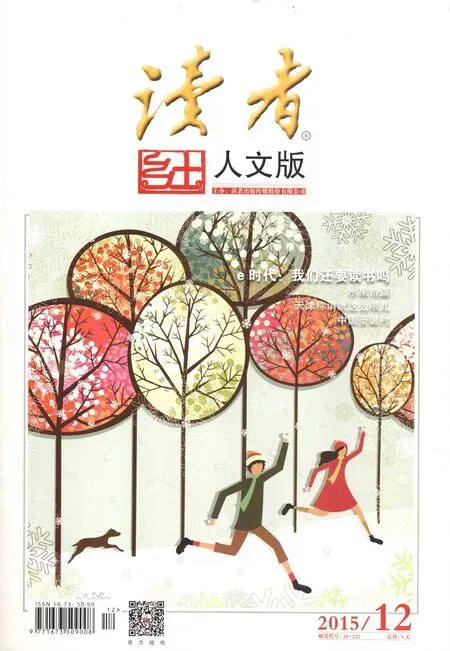旺家媳妇
文/蔚新敏 图/陈明贵
旺家媳妇
文/蔚新敏 图/陈明贵
嫂子进了我家的门,我家就炸了窝。
那是结婚后的第三天,从娘家回来后,嫂子拿起剪刀,“咔咔”两下把新褥子和新被子的线挑开,抱着那黑不溜秋的老棉套跟爹说:“什么年头了,还用这,没有白棉花,就是用红棉花也不能用这个吧。”说完把棉套往爹的炕头一扔,从她屋拿出从娘家带来的新棉花,重新做新褥子新被子。爹愣怔着,被呛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吧嗒吧嗒”地吸烟。
那晚,嫂子将两床大红大绿的被褥做好,已是点灯时候。吃晚饭时,我爹、我哥和我都没敢说话,生怕喘口气就惹着她。
吃着饭,嫂子说:“爹,好几亩地荒着,不如你也种个棉花,到时候收了棉花,我把你和我兄弟的被褥都做个新的。”
我爹在我们村有个雅号,叫“活佛”。我爹不打工,不种经济作物。别人家种草莓、种棉花、种土豆、种西瓜,我爹呢,只种玉米和小麦,不费脑子不费劲。
爹说:“你种吧,你种我给你干活。”
嫂子立刻挑起了眉,说:“爹,我种,卖了钱就是我的了;你种呢,我帮你干活,卖了钱揣你的腰包。这样你花着多方便啊。”
三个男人又都没吭声。那一年,我爹种的棉花丰收了,嫂子给我们做了几床新被子,剩下的卖了500块钱。平生第一次,我爹创造了经济效益。
我哥常年在外打工,有一段时间,嫂子跟我哥去了城里,回来后,我哥把我家临街的偏房开了个门洞,挂上牌子,放了一串鞭炮,我嫂子的理发馆开张了。
那时候我上中学了,放假对我给客人洗头,嫂子理发。嫂子说:“无论如何,立红,你得考出去,将来干最轻松的工作,挣最多的钱。”我说:“嫂子,你掉钱眼里了吧,张口闭口都是钱。”嫂子说:“小毛孩不知道柴米贵。”
农忙时候,理发的人不多,嫂子就把缝纫机放在理发店,边做手套边等顾客。乡亲们都称赞嫂子有一双抓钱的好手。
逢学校里要交钱,我不找爹要,找我爹要也没有。我在店门口喊嫂子:“嫂子,嫂子,给我拿5块钱。”嫂子就给,递上来的同时还有一句:“别乱花。”
初三毕业,我没有考上县重点高中。我跟嫂子说我不上学了,我种地。嫂子吼我:“你敢!不上学你试试!”开学的那天,我正跟爹在地里耪地,我嫂子“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来了,抢过我手里的锄头,一扔三丈远,说:“整天‘刮嚓刮嚓’的,能刮嚓出金子来?走,去上学。”就这样,我被嫂子提溜进了复读的教室。那时,我的个子比嫂子高一头多,嫂子拎着我,像拎着小鸡仔。
4年后,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我爹拿不出学费,我哥嫂刚盖了新房,我不忍心张口,只好申请助学贷款。嫂子同意,说让我体验体验生活的艰辛。第三年,学校突然不给学生贷款了,嫂子说:“别怕,你还有哥嫂呢。”她怕我尴尬,每次给我钱,嫂子都说是借给我的,待我挣了钱,得还她。
男大当婚。我领着女朋友回了家。女朋友左看右看,半天都没喝我家的一口水,没坐我家的炕沿一下,没跟我爹唠一句话,仿佛凤凰落在了草垛上。我嫂子那天特严肃,告诉我:“立红,这个女孩不适合咱们家,找对象,要善良、通情达理、勤俭持家、孝顺长辈……”由于嫂子的坚持,我们分手了。
“一个好媳妇,三代好子孙,找媳妇马虎不得。”这是嫂子给我敲的警钟。后来,我参加工作,一个女同事不错,带回家。嫂子看着很有眼缘,嫂子的这一关过了。结婚后,我们在城里买了房,安了家,和和美美,非常幸福。
谁也没想到,当初那个在风雨中飘摇的家会过得如此幸福,嫂子是乡里公认的旺家女人。
我媳妇生孩子,嫂子给我打了5000块钱,说是用来请月嫂伺候我媳妇的。我媳妇很感动,说:“看嫂子,总把我们当孩子管着。”我说:“那当然,我嫂子进门的时候,我不到10岁,长嫂如母。”
(柴中云摘自《北京青年报》2015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