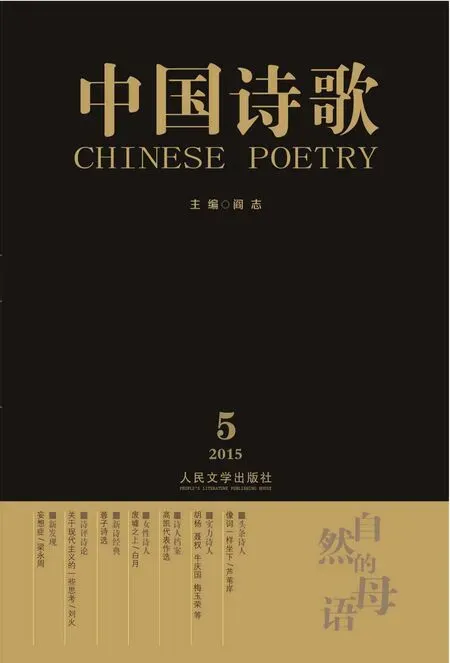高凯的诗:乡愁何处?
□唐翰存
高凯的诗:乡愁何处?
□唐翰存
诗人高凯,是乡土中国多愁善感的儿子。
高凯将他新出版的一本诗集命名为《乡愁时代》。按说,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的乡愁情绪较之古人,是大为减弱了。现代科技破坏人的古典情怀,由于通信、交通的发达,那种“少小离家老大回”、“家书抵万金”的怀乡病几乎不可能发生了。“乡愁”在今天,成了一个几近陌生的词。高凯之所以说这个时代是“乡愁时代”,自有他的用意在。他的“乡愁”,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乡愁”。他的“乡愁”不仅是思乡、怀乡,更多添了一层“愁乡”之意:愁被挤对之乡、被侵蚀之乡、被沉沦之乡。乡村、乡土在今天的处境,亦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乡村生态的异化,面对乡土文明的沦落,诗人那种深重的忧患,是隐隐可见的。他敢于说这是一个“乡愁时代”,即是用自己的亲身体察,作了这个时代的深刻表征。
一如他在《还乡记》一诗中所言:“回来了/回来了/这一辈子我终于磕磕绊绊地回来了/真是千里迢迢呵//一路上/我都在想进村时/大槐树上那一窝叽叽喳喳的花喜鹊/一定会欢喜地叫个不停//没想到/进村时不但没有一只花喜鹊的影子/甚至连那棵日思夜想的大槐树/也不见了//一切都不是自己想的那样”,这首诗正好写的是一种美的失落,是曾经的美好经验遭到乡土现实的冷落。美失落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了真实。曾经的美也不失其真实。我们看到诗人在早年的作品里,那么着力描绘他的乡土之美,那些“取着暖暖”的土窑洞,那月亮下爬在院墙上的一对子“青梅和竹马”,那些“姓高的高粱”,那“叫喳喳”的花喜鹊,唤起何等美好的叙事与抒情。在诗人的念想里,那是真实的。面对乡土,诗人甚至保持了一种天真的状态,心灵向着乡土全然敞开。不料,乡土却已经向他设防了。在他“还乡”时,原有的美好经验被浇了冷水,被“真实”撕碎。乡土的理想主义,大打了折扣。也就是说,那种理想主义的乡土,从物理上已经回不去了,乡土已经变了。那么,不妨随遇而安,就活在城市,写一写城市,如何呢?这对诗人是一个极大的考验。高凯写过城市,可他心里想的,还是那一把土。推土机挖开的路面里有乡土,爆米花爆出的花是乡土,楼顶上的青草找到了乡土,就连写在城市百年之后,眷恋的还是乡土:“走到尽头/我只想在城市的边边上/寄存一盒骨灰而一把黄土/竟然和金子一样昂贵/吓得我不敢死了//但死不死由不了自己/在乡下人一过五十/黄土就会亲热地涌上来/父亲和母亲那时真是太有福了/殁后都有一个土墓窑”。似乎没有办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理宿命。一个有乡土生活背景的现代人的两难处境,就在于,他与乡土之间,不光有割舍不掉的血缘关系,还有割舍不掉的精神关系。活在城市,乡土却是精神的命根子。
在创作中,这种对乡土的依恋,坚守到一定程度,会变成一种文学自觉。我们知道中外许多优秀的作家、诗人,都有自己的文学根据地,有一个能被反复、深入书写的地域空间。文学需要那个空间,是因为那个空间能更熟稔、更深厚地造就文学,造就文学意义上的“物自体”。在那个世界,往往有可能产生最真切的体验,最熟悉的语体,最刻骨的艺术表现,乃至产生稳定的个人美学风格。乡土,因为其承载的农耕时代的诗意美学,故为许多有乡土情结的作家、诗人所着意书写。可惜的是,许多人对地域化、乡土化因素还没写透,就急着要超越地域,蔑视乡土,这不仅是不明智的,甚至可以说是轻率的。对此,高凯有自己的公开宣示,他在《掌上的陇东》一文中说:“守着地球上最厚的一块黄土写诗,不仅是我的姿态,而且是我的归宿。”他甚至认为:“没有故乡的诗人是可疑的。”“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认为没有故乡的诗人的写作是没有来路和去路的写作,其诗歌的态度十分可疑!”这些话底气十足,几乎不容置疑。究其因,不仅在于高凯对地域写作的理念化认知,更在于他身体力行的执着坚守,他“被黄土里一个招魂般的声音牵引着,不由自主”。他三十多年的诗歌创作,其主路,始终没有离开过陇东那片土地,始终以高度自觉的姿态回忆和发掘故土上的人和物。在高凯那里,守住陇东,就是守住了他诗歌的生命之根。
2014年5月,以高凯、第广龙、郭晓琦、李满强等为代表性诗人的陇东诗人群从全国200家诗群流派中脱颖而出,入选“二十一世纪中国十二家影响力现代诗群流派”。同年底,这一事件成为本年度“甘肃文学十大新闻”之一。在参展过程中,笔者有幸较为全面地目睹了陇东阵容。我发现这是一个庞大的诗歌群体,无论是“代表性诗人”、“在场诗人”,还是“曾经的诗人”、“新生代”,其人数远远超出我的预料。陇东诗人群里的大多数,都持守着某种自觉的地域意识,写过乡土色彩浓烈的作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反过来以各自的书写,重新塑造了一方水土。陇东,曾经是周祖的发祥地,是《诗经·豳风》流传的地方。黄土地的母性孕育了剪纸、皮影戏、香包和窑洞,也催生了人们恋土、怀旧,认祖归宗的家园意识。当代陇东诗歌的主流,是在割舍不掉的家园意识中行进的。不仅在甘肃,放眼中国,陇东诗人群体呈现的家园意识,恐怕也是最为浓烈的。在他们许多人的作品里,有乡有土,乡是故乡,土是黄土。正因为如此,他们诗歌的“来路”与“去路”,往往是很清晰的。其中许多作品,不仅有根,其艺术表现的深度与高度,令人看好。
笔者在某些文章中,也曾经不止一次地谈到“乡土”与“诗”的关系问题。乡土本身并不是诗,被审美化、对象化了的乡土,才是诗。为了获得这样的诗,诗人必须做到:既要守住乡土,又要出离乡土。这是一个吊诡的辩证。“守住”是一种投身的姿态,是创作面对特定对象的持久度和专注度,一如荷尔德林当年所言,由于一种“深情的关系”和“如此在他所效命的特定方向上的前行”,一切可以在诗人那里“得其时得其位”。对于乡土来说,那些在它面前只知道浮光掠影的诗人,想要真正“得其时得其位”,是不太可能的。而“出离”,却是一种方法论。“出离”是为了再度审视,从而获得诗意的性质。“出离”是为了更好地回归。农耕发达的时代,乡土形态是几乎人人可经历的、无度存在着的现象,惟其如此,乡土上的主体性仍旧是乡土,呈现一种被遮蔽的、无差别的状态,昏冥地与农事融合在一起,乡土需要一个异质的介入,才能做到“自明”。另外,阅读乡土文学作品的人,往往并非真正的乡土人,倒是在异质的环境中,在城市,乡土文学的读者要比乡土上的读者多得多。乡土文学被乡土本己的力量冷落了。乡土叙事被异质环境里的人去阅读,被乡土味日益淡薄的发达区域的人感兴趣,正说明乡土惟有被出离、被对象化以后,文学活动才成为可能。对创作者而言,他们的一个普遍经验,即,离开乡土才能写好乡土。离开乡土,即离开乡土的劳动及生活环境,出离那种与乡土的物因素昏冥一体的状态,才能不被遮蔽。海德格尔说:“人归属于存在,却又在存在中保持为一个异乡人。”就是指人的这种自由同时又不自由的状况,尽管他所说的“存在”,并不仅仅指生存环境。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诗人具有了双重身份。作为乡土人,高凯的许多诗歌土得掉渣,土得地地道道。作为异乡人,他却又是现代的,有现代人的立足点,有现代人的眼光和审美表现力。他与陇东乡土的那种“深情的关系”,由于他的出离,而变得更有诗意了。他的“遍地乡愁”,也由于他的出离,才有了为“沉默的大多数”言说的可能。我们读那首名诗《村小:生字课》,觉得亲切,又那么有艺术发现,可是,那首诗并不是一个小学教师在其工作岗位上写出来的,那种反映生活普遍体验的东西,让常年体验那种生活的人未能发现其中的诗意,真是遗憾之极。反过来,一个完全没有生字课教学经历的人,能不能写出那样的诗呢,恐怕也难。这时,乡土人和异乡人的身份同时在发挥作用。由于在“特定方向上”的效命,以及有条件在“特定方向上”效命,高凯不仅写出一首好诗,而且写出一首有广泛影响力的诗,成为其代表作。有代表作,在这个时代,无疑意味着一个诗人的巨大成功。
文学里的乡土,天然地与地方色彩融合在一起。我们说某个人笔下的乡土,潜在的究问必然包含着哪个地方的乡土这么一层意思。乡土写作本身意味着,你写什么地方的乡土,怎样去写这个地方的乡土。地方色彩,正是构成乡土风俗的根本因素,是生命力所在。“显然,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的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地方色彩可以比作一个人无穷地、不断地涌现出来的魅力。我们首先对差别发生兴趣,雷同从来不能那样吸引我们,不能像差别那样有刺激性,那样令人鼓舞。”赫姆林·加兰说这话是在一百年前,那时人们已经严重注意到文学雷同的问题。说“雷同”,是指工业化和现代社会发展导致的地方性差别消失、文化和艺术趋同的情况,到今天,这种情况更为严重了。今天是“全球化”时代,“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性,正以飞快的速度消灭地方差别。今天的乡土,被称为“后乡土时代”乃因其完全不同于费孝通《乡土中国》中所描述的那个样子——社会主体的非流动性、社会空间的地方性、社会关系的熟悉性——不仅地方差别正在飞快地消失,传统的民情、民俗、民风日益衰微,而且诗人们所赖以抒情的乡村的诗意美学,正一天天被现代实用理性所消解、撕毁,乃至于无地抒情、无可抒情。这真是一件残酷无比的事情。乡土真诚的儿女们,许多人无语了,许多人写不出东西了。
惟有少数有“免疫力”的人,才可以排除乡土上“非诗因素”的干扰,数十年如一日甚至一辈子保持那种童心般的诗意抒发状态。高凯无疑属于少数有“免疫力”的诗人之一。他三十几年的创作生涯,始终将最美好的情感投射在那片日益缺乏诗意的故乡土地上,当现实不足以支撑他的诗意美学时,他就调动回忆。是的,个人化回忆,往往成为他召唤诗歌、接近乡土的最无助、也最温暖的方式。回忆是为了挽留诗意。在回忆中,他将某种“创伤体验”转化成了“愉悦体验”,以此在潜意识中塑造了乡土在整体上的那个“趋美”形象。这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在人人憋着一股火气的年代,将事物写得美一点,可能比写得丑一点更难。赞美也需要勇气,需要一颗善良之心。何况,他的赞美是有艺术水准的,比如有时用白描做底色,有时采用高度的艺术概括。更何况,他的“趋美”,意味着他对故乡的态度以及抒情基调上的某种“终身不渝”。
高凯对陇东乡土数十年如一日的深情书写,使他获得了稳定的地方体验。可以说,那种稳定的地方体验不仅在当代诗坛上是可贵的,在百年新诗史上也不多见。我们知道新诗的较早时期,有所谓的“民歌体”诗派,写过一些“土布粗,洋布细”之类的诗,因为缺乏深厚的地方体验,那些诗看上去还是很幼稚的。后来,“泥土诗人”们写过几首有点意思的乡土诗,但总体上看,他们笔下的“泥土”因为让人不知晓是什么地方的泥土,因为缺乏对地方的稳定性表现,故成就也不算高。诗人真正能围绕一个地方,付出那么多的心血和精力,将一个地方的风土人物写广泛、写深厚、写扎实、写出彩,还是新时期以来才出现的事,是“新乡土诗派”能做到的事。对于高凯而言,有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就是,人们一谈到他的创作,必然会想到他的“陇东乡土诗”,一谈到“陇东乡土诗”,必然会首先想到高凯其人。高凯与陇东乡土之间,已形成生命意义上的同构。高凯的乡土诗,有浓厚的地方色彩,那些作品,从意象到语言,一看就是属于西部的,属于甘肃的,属于陇东的,而不是其他地方的“特产”。要说成功,这才是高凯乡土诗的最大成功。写什么像什么,写某个地方,便如其所是地成为那个地方,这并非什么新鲜的创作经验,奇怪的是,中外文学史上,那么多越是注重地方性并且能将某个地方写深、写透的作家、诗人,反而更容易“超越地方性”,更容易被地方和地方以外的人们所欣赏,甚至更能进入“世界文学”的视野。这无疑是一个微妙的辩证。具体到高凯,他也不难在文学活动中体味这种辩证。他的诗歌在读者接受过程中,也经历了从“地方性”到“超越地方性”的辩证。高凯以其“地方性”的写作,以诗歌的方式,重新塑造了一个地方,使他成为陇东的一张名片,同时也跻身于当代著名诗人的行列。
一个好诗人,能顶十个宣传部长。这是我在回顾高凯创作生涯时突然想到的一句话。此话似乎冒昧,想想不无道理。当年,左翼文学营垒中曾发生过“文艺”与“宣传”之争。鲁迅说“一切文艺固然是宣传,但一切宣传并非都是文艺”,针对的是“左而不作”的那种文艺现状,可谓至理。鲁迅是肯定文艺的宣传作用的,他批评的只是离开文艺本体而制造出来的那种宣传。那样的“宣传”往往只是一时的泡沫,在文学接受视野中难以持久。一部作品能长期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力,最重要的还是看作品的本色和质地。当年“朦胧诗”的崛起,固然有时代因素,可是“朦胧诗”相比于“放声歌唱”的诗歌,其艺术精神与语言气质方面,不知要高明多少倍。“乡土诗”也是一样,只不过它的艺术精神是向“农耕”的回归,它的语言气质是向“乡土”的回归,在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全球化时代,照样有它高明的艺术魅力存在,也照样能产生震撼人心的宣传力量。诗人高凯能将陇东这么一个地方“宣传”到全国诗坛,产生一定影响,最主要的,还在于他没有离开诗歌本体,为一个地方死心塌地下了那么多年的功夫,用各种意象下功夫,用多种手法下功夫,才有了“出彩”的结果。当然,高凯也聪明地知道,要想在创作上有好结果,必须如此死心塌地下功夫。高凯的诗歌有灵气,这是阅读他作品的人的共同感受。我觉得除此之外,他的诗歌里还有某种乡土人的“拙气”。那首《我和小鸟落在一棵树上》,写得就很“拙”:人说鸟语,获得一只小鸟的信任,“啾啾的鸟语说得长了/我想和小鸟说一阵人话/但刚探头说了一句/而且是一句亲切的问候/小鸟就不再出声//我重新用大叶子/把自己深深藏起/重新猫下腰而且/重新用鸟语一声声叫它/小鸟都不答应”,诗坛上写鸟儿的诗歌多了,有的隐喻很深,这首诗却纯粹是一个成年人的童心白描,读来新鲜有趣。高凯并非不能将诗写得更深邃一些,实际上他的某些作品如《风中》、《苍茫》等,在意象的自然伸张背后,文学意蕴颇深,甚至有了哲理味。这首写小鸟的诗,作者似乎有意描绘得很浅,有意“不明事理”,只是展现一种自然状态的东西。如果说那只鸟儿就是乡土,那么“我”的所作所为,暗示的就是“我”与乡土的某种关系:乡土需要乡土所能接受的亲近方式。当然这么阐释,已经是笔者的臆测了,原诗并没有在这些意思上用力。还有《那座山》:“那座山太阳落下去了/一只鹰也跟着落下去了//后来那座山上撒了米粒大的/七八盏灯//一会远了一会近了/一会熄了一会亮了//那座山是那个去过的曹家老庄呢/还是那个没去过的高家岭”,全诗共三节,第一、二节颇见语言才气,不过,但凡有才气的诗人也能写到那个程度,第三节就不同了,落得十分朴拙,出人意料。看似不经意的两句,看似随心的疑问,道出的是诗人特殊的心灵隐私——他属于乡土,他的思维惯势也自然回归于具体的乡土。这种朴拙的背后,想必有匠心的运用,显示的正是诗人独特的“这一个”,而与那些浮光掠影者不同。
极希望高凯在他的诗歌里,能将这种“拙气”保持下去。他的诗歌里不缺乏聪明、灵动的东西,他有将“创伤体验”转变为“愉悦体验”的能力。对于文学而言,这是必要的。文学首先要使人感到愉悦,哪怕是“痛苦的愉悦”,过于沉重或过于苦难,都是对艺术审美的伤害。从这个意义上看,有时候轻描淡写,要比呼天抢地更具感染力。高凯的诗歌里很少有那种呼天抢地式的表达,甚至很少有批判和讽刺,哪怕面对乡愁,面对乡村诗意美学的沦落,他的笔调仍然是朴拙的,仍然在坚持“美的历程”。如果一阵子写成那样、一首诗或几首诗写成那样,似乎并不能说明什么,而几十年如此,诗歌的总体笔调如此,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他对乡土的爱,似乎是无条件的,似乎蕴含着不竭的感情,以及无比的真诚和善意。人们常说距离产生美,其实善良也能产生美。因为善良,所以本真;因为善良,所以美。真诚和善良在高凯那里,是他留存给乡土和亲人的最大回馈,也是他创作的最大态度。他的精神还乡,因为有这样的态度,而显得诗意浓浓。
与高凯一如既往的乡土情结相比,他在诗歌的艺术创作方法上,却是自觉追求多样化的。在一个大的母题之下,他想尽可能多地变换一些花样。有的诗幽默,有的诗散淡,有的诗简练,有的偏白描,有的诗知性,有的口语化很强,有的民间味很足。在修辞上他也体现出自觉的探索。“一辈子/心上放一个人/心上藏一个人/心上疼一个人/心上恨一个人/心上害一个人/心上死一个人/心上哭一个人//到头来/心上埋一个人”(《心上人》),像这样的诗,在修辞方式上复沓简单,明显不同于他那些以散淡白描为主的诗歌,却也直指人心,表现力蛮不错的。还有这首《远方》:“天的尽头是远方/山的外面是远方/路的前方是远方/二亩地的边沿是远方/一把锄头够不着的地方是远方/被黄土就地掩埋的地方/是远方”,几句话,看上去一气呵成,却也别致有味。写远方,别人是从近往远写,他是从远往近写。对于乡土人来说,近处的“远方”才可能是真正的“远方”,关系着他们的生活、生存,甚至关系着他们的生死。“被黄土就地掩埋的地方”,后面有个分行停顿,一方面是节奏舒缓的需要,一方面也是语义的加重、强调,因为那个地方是事物消逝的地方,是阴阳相隔的地方,是再也回不来的“远方”。
有评论者在谈论高凯诗歌的语感问题时,专门用了一个“字思维”的概念,认为“高凯善于以字词作为生发联想的契机,由此产生连绵不断的诗意”。可以说,这抓住了高凯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不仅从高凯,从中国不少诗人和作家的创作中也能看到所谓“字思维”的迹象。汉字以象形字、形声字、会意字居多,这为文学活动以及文化活动中的“字思维”提供了条件。由几个字、词,或者字词的组合,“衍生”出意象、画面,形成一首诗,这种创作方法很常见,同时也很危险。因为这种方法用不好,会给人以取巧之嫌。中国的文字游戏那么发达,望字生义、望文生义的现象那么多,大概都是与所谓的“字思维”有关系的。“字思维”方法过盛,会极大地削弱作者体验生活的深切度和真切度,影响汉语诗的能指品质。文学创作首先面对的是存在,而不是字词,当语言对事物的言说仅仅滑落在字面的能指时,其深度的所指往往被庸常化了,甚至庸俗化了。就高凯诗歌而言,他的《村小:生字课》,看似是“字思维”,实际上不是,它切近的还是某种生活存在本身。至于被评论者看好的那首《陇上》,望字生义的痕迹太重,艺术上并不成功。此外类似的,还有《木耳》、《关于乌鸦》等。这类东西在高凯作品里为数不多,危害却不小。它们让高凯的创作“灵巧”得过了头,更致命的一点是,它们会极大地影响诗人高凯与他所效命的那片土地的扎心关系。
因为他的乡愁,不仅止于字面,而且融化在血脉里。他的体验,不仅是“趋美”的,而且是以极大的身心、极大的真诚和爱扎入那片根性的土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