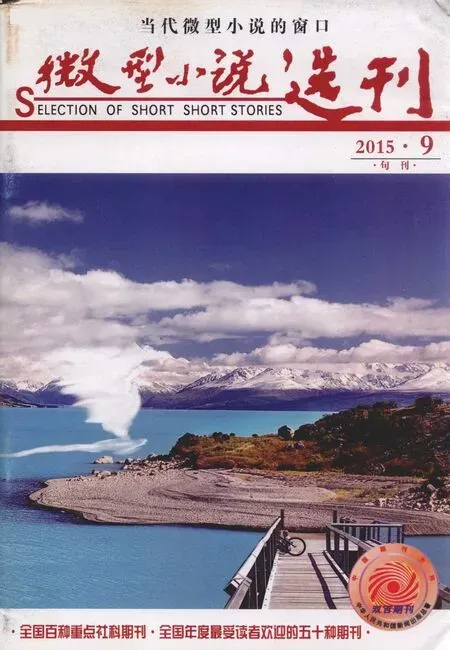是我杀的
□符浩勇
是我杀的
□符浩勇
贾德强突然产生一个可怕的想法:我要杀人!
这最初只是一个模糊的念头。它就像在他的躯体里过电一般,“砰”的一声炸开了,继而在脑海里生根发芽,蔓延到心里,逐步演变为一种确定急切的想法。甚至他本人都不敢相信,他的思绪连日来被搅得乱七八糟,像蛇一样缠绕着他,闹腾得他寝食不安。
其实,同从乡下来的老乡都知道,他胆子很小。
刚进城时,他只是做收旧货的营生,经常出入多个小区。有时居民丢失了东西,报案来了警察,他听不懂他们说的方言,但看得懂人家的目光,就觉得芒刺在背,慌得就好像真的偷了东西。后来,他改在一家临时工厂流水线做零件,车间里有的人零件丢失了,报了案,人人都成为可疑对象。他却神魂不安,眼皮老跳,警察找不到丢失的零件最终还是走了,他却耿耿于怀,担心别人怀疑他。有时有警车鸣笛在街上开过,他希望这警车能来查清楚,才能证明他的清白。
这些事成了同乡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人家背地里总说,胆小老实的家伙进城来就像让他赴一场宴会,抢食都不如他人哩。
然而,他并不在乎别人的嘴巴和目光,做工卖力而且勤勉。一年下来,他省吃俭用,居然有了积蓄。
有了积蓄就可养家糊口,他趁回家过端午节的机会,带来了鲜活水嫩的媳妇,在他租居的工棚住下了。一时间,郊外那家临时搭建的厂房,以及昏暗的车间透亮起来,他媳妇出出入入的,腰肢像藤条一样,一步三摇摆,落进了车间包工头老黄贪婪的目光里。
包工头老黄找到他,说,你不用做零件了,跟车跑县城送货去,工钱是做零件的两倍。他当然高兴,别过媳妇就跟车走了。但跑了县城他才知道,每周两趟,每跟车一趟都要过夜,次日中午才回来。
两个月下来,事关媳妇的风言风语就来了,说得有板有眼。有说,他跟车跑县城去的夜里,工棚里的老鼠就特猖狂,常常闹腾到下半夜,有时要到了黎明时分才静下来。厂房临着一条小溪,溪边长满了密密的水草。他媳妇去割草,包工头老黄总会去帮忙,就滚在草丛里,那日没起风,可草丛却在翻动,就像巨蟒游过,好哟,草丛中两个人像赤条条的白鱼,游在碧水里。人家挤眉弄眼对着他酸笑,他枯叶般的脸孔就黑下来,像抹了锅灰,堵着一团恶气,心里就隐约浮现出杀人的念头。
他问媳妇:“我忙里忙外的,你别让我戴绿帽子!”他居然懂戴绿帽子的意思,但闹不明白为什么当兵的都戴绿帽。媳妇起先忸怩地说:“别听人胡扯,没有的事啦……”他不由得兴起,拥抱媳妇,媳妇就任由着他。但到后来,媳妇动辄以身子不净为由,不让他随心所欲,他醋意大起,还动了拳脚,媳妇却哭着认了,末了还埋怨他虽是男人,却护不了自家女人。
他去找包工头老黄说,他不想跟车跑县城了。包工头老黄对他说,你不跟车就走人,反正有人惦记着去跑县城。要是肯留下,你媳妇可安排杂工干,有一份工钱。
他转而劝媳妇说,你别作践自己,多躲着人家,给我个面子。媳妇果真给他面子,只有他跟车跑县城了,才到约定的溪边草丛去。说是留个面子,却只是背着他一个人而已,媳妇去车间做杂工很轻松,时时在众人眼皮底下同包工头老黄打情骂俏,卖弄风情。
同乡见他居然没起脾气,自己的女人都管不住,都鄙视他,背地议论说,这家伙给乡下人丢脸了,不配做个男人,早该阉割结扎,蹲着撒尿算了。
他时时处处都感觉到同乡的指指戳戳,心里常浮起一种万念俱灰的痛楚。不跟车跑县城时,他总爱往厂房边上的酒店钻,喝得酩酊大醉发酒疯,拿出一把长锈的尖刀,往桌上一掷,吼道:“哪个再惹老子不顺心,我宰了他!”有时把烟抽得很凶,把自己罩在烟雾里,压抑心里的波澜。就是这时候,他坚定了杀人的想法。
一个夜里,他梦见自己已控制住包工头老黄,就像扼住了一只待宰羊羔的喉咙,恨不得剥他的皮,抽他的筋,他拿出了那把已磨亮的尖刀,意欲抠出他淫毒的眼珠,心里不由得涌起一阵强烈的快意……然而,当他握紧尖刀喊杀人时,待宰的羊羔成为疯狂的凶狗,汪汪狂吠。他忽地醒了,是一阵警车鸣笛的声音唤醒了他,他吓出了一身冷汗,瞬间,他像刺猬一样缩成一团,生怕一不小心,杀人的喊声蹦出喉咙。
他还是跟车跑县城送货去,但买了一部廉价的小灵通。他刚在县城停顿,媳妇打来电话哭着告诉他,包工头老黄被杀了,死在厂房外的干草垛边。他挂了电话,就租了一辆车赶回厂里。
警察正在现场勘察,警车的笛声还在不停地鸣响着。他挤进围观人群中去,嚷道:“别白忙了,好汉做事好汉当,是我杀的,我坦白!”
警察要抓走他,可同乡们拥上去作证,说他并不存在现场作案的时间。他却吼道:“不,不!是我杀的,我在心里已经杀过他几百遍了,那把磨亮的尖刀就搁在家里!”
他媳妇盯着他的眼神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说:“你是不是疯了?”
(原载《微型小说月报》2014年第12期 河北赵功成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