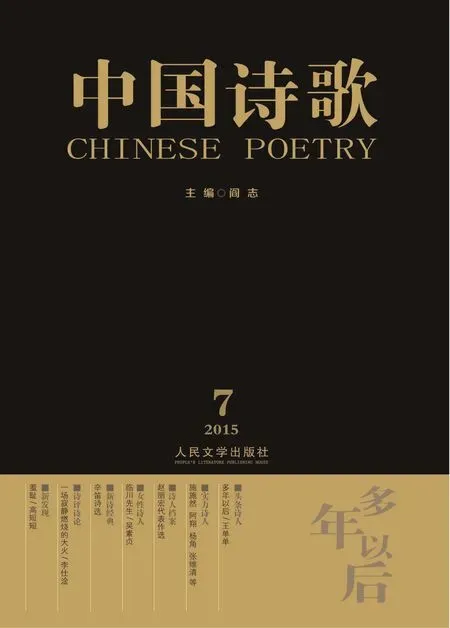嫩绿的美,金黄的美
——评王单单的诗歌写作流变
□茅草
嫩绿的美,金黄的美
——评王单单的诗歌写作流变
□茅草
我在《人民文学》2012年第9期上首次接触到王单单。时隔三年,《中国诗歌》以其“头条诗人”的显著位置重磅推出王单单,我再次研读他的诗歌,又有新的发现:他已由“嫩绿”转变为“金黄”。他在《诗歌做伴好还乡》的写作体会中写道:“在语言的田垄间播撒诗歌的种子,除草,施肥,看着它抽芽破土,由嫩绿变为金黄,结出饱满的麦穗。”也许,他只是在描述一个由稚嫩到成熟的过程,而我则以为稚嫩也好,成熟也好,二者都是美。写作领域显然有异于谷物,虽然诗人也在成长,写作的技术也日臻娴熟,作品却未必有稚嫩和成熟的差异,至少从王单单前后两个时期的作品来看是这样的。王单单前期的“稚嫩”是新鲜的生活,是精神的愉快,是诗意的浓郁,王单单后期的“金黄”是丰富的内心,是反思的沉重,是语言的闲淡。这种转变,是“外”与“内”、“轻”与“重”、“浓”与“淡”的转变。
一、“外”与“内”的转变
“外”是新鲜的生活场面,“内”是丰富的内心世界。《人民文学》2012年第9期上所刊发的12首诗,代表了他在那一个阶段写作的基本面貌:面向故乡、面向亲人的“生活诗”。路边的理发匠、顺平叔叔、父亲、二哥、镇雄的夜晚、赵家沟的山体滑坡……这些人,这些事,都发生在他的身边,他睁眼可见,伸手可触。写劳动的场景,写父辈的艰辛,写镇雄在市场经济中的变化,写赵家沟的自然灾害,十分逼真,十分鲜活,十分细致,具有感人的力量。诗的主体是“他者”,“我”几乎没有在诗中出现。诗人观察到的、关注到的都是“我”以外的生活世界:底层的人,普通的事。这表达了他心系底层、热爱生活的立场和情怀。如《路边的理发匠》:“这个在别人头上开荒的男人/始终找不到自己的春天/二十多年了,路边设摊/匆匆过客,不问姓名和出处/他以为,剪掉太阳的胡须/整个世界就年轻了”。一个老单身,一个马路上的手艺人,过着流浪的、单调的生活。如《赵家沟纪事》:“没有事先约定,大家就死在一起/躬身泥土,一个魂喊另一个魂/声音稍大,就把对方吹到石头的背面/最后咽气的人,负责关闭天空的后门/让云彩擦过的蓝,成为今生最后的重”。一群生也默默无闻、死也默默无闻的人,生被沉重的生活掩盖,死被沉重的山体掩埋。多年以后,我们读到他的《多年以后——兼致刘年》:“有朋自远方来,只谈诗歌/不说政治。也可陪我采菊东篱/在南山下煮茶//那时我已经不能打铁/但还会去竹林里,喝酒,抚琴/给走远的人写绝交书”。这种感觉与前阶段迥然有异:题材变了,观察的对象变了,视觉变了。陶渊明也好,山巨源也好,都是中国古代文学里隐居山林、回归内心的符号,王单单借助这个符号浇灌了自己心中的块垒。抒情的内涵已经由外在的现实生活转向了内心的人生态度。“他者”形象被暂时搁置,“自我”的观念闪亮登场。《中国诗歌》把《多年以后——兼致刘年》放到诗人的27首诗之首,似乎是有意识提示这种变化。副标题与正文关系不大,不是硬要标明应酬之作,而是有意设置一个可以诉说的对象,或者寻找到一个见证者。《两个人的交响乐》、《在孤山》、《舍身崖》、《悲伤之诗》、《山行》、《一个梦》、《酒不够,到江边接着喝》、《一个人在山中走》、《玉案山中,向守墓人问路》、《酒后,送杨昭回家》、《游戏》、《夤夜思》、《下了飞机,转乘地铁》、《夜游湘江》、《长沙》15首诗,全都是转向内心抒写的诗:表明诗人在这一阶段的写作重点是面向自我。《一个人在山中走》似乎交代了这个变化的过程:“一个人在山中走/有必要投石,问路/打草,惊蛇,向着/开阔地带慢跑。一个人/站在山垭风口上,眺望/反思,修剪内心的枝叶/……/一个人在山中走,一直走/就会走进黄昏,走进/黑夜笼罩下的寂静”。转向总是艰难的:需要独自求索,需要辨识方向,需要思考,需要规避风险。“一个人在山中走”在诗中出现两次,或许是诗人有意设置的重复,或许是诗人在写作中根据内心表达的需要自然而然的流露,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它都表明这个“转”的过程的艰难而又必要。
二、“轻”与“重”的转变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作为肉体的生命,肩膀上承载的重量不能超过他应有的体力;作为精神的生命,其心理对外界信息的刺激不能超过它应有的负荷。肉体的承受力超过了,人就成为残疾;精神的负荷力超过了,人就成为神经病。可是,米兰·昆德拉发现了人类的另一个精神现象: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人虽然追求轻松、自由、快乐,但在极端的放纵、无所事事之时,就会陷入空虚和无聊,甚至失去生存的意义。轻与重看似对立,实质上是交叉关系,交叉的位置在于那个神秘的度。
我看王单单前期的诗,感觉到诗所反映的生活是沉重的:无论是赵家沟死去的灵魂,还是病中的父亲,还是采石场的女人,还是路边的理发匠,他们的命运都“成为今生最后的重”(《赵家沟纪事》),可是,王单单的诗又恰恰表现出“让云彩擦过的蓝”(《赵家沟纪事》),显得格外的飘逸、轻灵。他以诗的宁静致了生活之远,他以诗之轻举起了“他者”的生活之重。如《痛哭的人》:“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斜挂在你脸庞的那滴泪/是一片小小的海/我是不是可以说/它只是天空剥落的一粒蔚蓝//可事实上,我看见的/是你抽泣的痉挛/我看不见的那片海/才是你的泪”。尽管诗中直接出现了“泪”、“抽泣”、“痉挛”这样体现痛苦的情状,诗人却以“我是不是可以”的询问句式和“小小的海”、“剥落”、“蔚蓝”之类的颇见色彩的词,减轻了生活应有的重量,而给予诗以浪漫的轻。《病父记》则走得更远:“你说球没事,我说不可小觑/你说没做亏心事,我说与生病无关/你说从不打针,我说这次例外/你说祖上无病,我说非关遗传/你说看病花钱,我说花钱看病/你说休息就好,我说好再休息”。这样写父亲别具一格且非常独到:丢掉一般的庄重和敬畏的心态,以“你说”、“我说”、“球没事”之类的口头语,以及嬉皮士式的语调来写,以轻显重,以美含悲。这就是王单单诗艺上的度的把握,这就是他举重若轻的个性和特色。
后期的诗是怎样变化的呢?前面我们列举了《多年以后——兼致刘年》和《一个人在山中走》两首,除了内心的态度和变化显而易见之外,我们还能感受到这两首诗所表现的深沉内涵。米兰·昆德拉说,人类一沉思,上帝就发笑。我的理解是:人类的思考是有限的,思考离它所要抵达的真理的距离难以企及。结合王单单的诗来思考这一命题,那就是:只要是主体的活动,那一定就是沉重的。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还有《酒不够,到江边接着喝》:“这一次,兄弟我有言在先/只许喝酒,不准流泪/谁先喊出命中的疼,罚酒一杯/兄弟你应该知道,回不去了/所有的老去都在一夜之间/兄弟你只管喝,不言钱少/酒家打烊前,整条船/都是我们的,包括/这船上的寂静,以及我们/一次又一次深陷的沉默”。主体直接在场,直接“喊出命中的疼”。“我”已经不再是一个人称代词,也不是诗中的一个角色,而是“主体性”,是抒情的出发点。抒情的视角已经从前期的“他者”转移到自己的内心,一个个词的砝码压到诗人的心上,诗就显得愈来愈沉重。15首写诗人内心的诗跟前期写生活的诗迥然有异,就像一个人痛哭和看到他人痛哭的心理重量完全不同一样:自己痛哭是不能承受之重,看他人痛哭则是不能承受之轻,两者交叉在“心理压力”这个“度”上。
三、“浓”与“淡”的转变
现在,我们要谈到王单单诗语言的转变。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这个常识性命题就像数学上的1+1=2一样,并不只是小学生的答案。不是人人都会想到:诗体裁的不同、诗写法的不同,竟然是诗的语言的不同。写诗的人都追求诗的内涵越深越好,说到哪一首诗好,哪一首诗更好,哪一首诗不好,多半会想到诗的内涵深浅,然后才是语言的简洁与否、凝练与否、形象与否、生动与否、传神与否,却很少有人想到古典诗与今诗的不同,今诗中抒情诗与先锋诗的不同,先锋诗中象征诗、意象诗与叙事性诗、语象诗的不同,竟然都是语言的不同。这就是说,是语言的面貌而不是内涵的深浅决定了诗的面貌,内涵往往具有同一性:生死,爱情,善良,友谊,古今中外的诗莫不写这些。古汉语决定了古诗的面貌;现代汉语决定了现代诗的面貌。北岛、顾城以象征的语言和意象性语言写诗,决定了他们所写的诗为象征体和意象体,“朦胧诗”的命名起源于当时对这样的语言的不理解。于坚以口语写诗,雷平阳以叙事写诗,因此才有于坚的“口语诗”和雷平阳的“叙事性诗”。语言之于诗在这个维度上至少跟内涵同等重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樵客出来山带雨,渔舟过去水生风”等千古名句,不都是语言技术和内涵达到了同等的境界吗?
语言哲学的转向改变了哲学领域对本体论的关注方向:人们对世界起源的思考,不再在物质和意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中兜圈子,而转向了对语言中的词与物的思考。语言成为了哲学本体论的承载。这一观念的出现对作为语言艺术的诗的影响是致命的。它首先帮助了那个提倡写“口语诗”的威廉斯战胜了他的对手——那个追求主体深度、意义广博而又晦涩难懂的艾略特。所以,后现代诗、以于坚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的诗,绝不是诗坛上一次兴之所至的实验,而是哲学和文化发展到了一定的历史阶段所出现的必然结果。于坚的“诗止于语言”的美学内涵有多深,不知道有几个诗人真的想清楚了。
或许是正当我思考这一问题时,恰逢王单单的诗语言转型,触发了我的理论兴趣,我不得不以他的诗歌文本作为范例,来谈一谈我在这方面的感受。
“把日子扔进碎石机/磨成粉,和上新鲜奶水/就能把一个婴孩,喂成/铁石心肠的男人”(《采石场的女人》);“流水的骨骼,雨的肉身/整个冬天,我都在/照着父亲生前的样子/堆一个雪人/堆他的心,堆他的肝/堆他融化之前苦不堪言的一生”(《堆父亲》);还有前面已经引用的《路边的理发匠》、《痛哭的人》等诗的语言,颠覆了现实主义的传统,颠覆了作为散文语言的语言。作为诗的语言,王单单的选择具有代表性意义:不局限于传统的表意功能,而是最大限度地发掘语言自身具有的表达能量,改装、改造生活的本来面貌,再造一个新奇的、独特的、色彩浓郁的、喻意深刻的语言现实。在美学层面,诗语言寻求摆脱或者超越主体性,它的目标或者说使命是要再建一个独立的语言系统。在写作层面,诗语言永远在路上,没有终点。这样的写作才是真正地把诗归于语言艺术的写作。
可是,王单单说,“语言是诗歌存在的道具”。他强调“生活的质感”,认为“情感的真实比技巧更重要”。这一观念来自传统的语言“工具论”,其要义是“得意忘言”,它强调的是语言所表达的意义,而不是语言本身,它不在意语言本身的增值意义和创造性,对语言创造的技巧不屑一顾,甚至视作故弄玄虚。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王单单后期的诗歌语言转向了明白、平淡。前后对比,我们不难看到:“打扫灰尘,布置房屋/重新生火造饭,喂鸡养猪/回到官抵坎。哪怕/我一个人就是一个村”(《多年以后——兼致刘年》),其语言是朴实无华的,语言所承载的意义与它反映的现实中的意义几乎可以画等号。“我把所有的孤岛都看成/水中坐牢的石头,不说话/终日忍受惊涛拍岸的酷刑”(《在孤山》)和“古人说的话,我不信/江水清不清,月亮都是白的/这样的夜晚,浪涛拍击被缚的旧船”(《酒不够,到江边接着喝》),也都是直抒胸臆式的表达,甚至连含蓄都放弃了。《采石场的女人》、《堆父亲》所使用的语言就不同了: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它的可能性只能在语言再造的语境中,也就是说,它的诗意更多地来自语言自身的附加意义,而不仅仅是语言作为“工具”反映的现实中的意义。这就是“语言是诗歌存在的道具”与“语言是诗歌本身”的区别。
在美学上,两者都是美:“蓦然回首”的美和“清水芙蓉”的美;在写作上,两者都是技术:“鬼斧神功”的技术和“波澜不惊”的技术。在美学的选择上,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选择;在写作技术的选择上,不同的写作个性、不同的题材需要有不同的选择。不过,就当下写作的潮流看,趋之若鹜的是“语言写作”,王单单放弃了这一写作方式同时远离了他自己前期的成就,似乎是有意走一条回归“传统”的路。到底是喜欢时尚还是喜欢传统,恐怕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表现内心、追求深邃,也未必非要选择平淡的语言,王单单的《寂寞令》、《夜游湘江》、《长沙》等篇,就是既没有放弃语言技术追求,也没有耽误自我深刻表达的范例:“在一粒沙中雕刻一座城/黑夜的小,刚好盖住一米蓝天/雕一盏灯,刻出微弱的光/照着它的祖国,把一场革命/拦在天亮之前。我还要雕刻/身后的寂静,城中草木/以及湘江枯竭的样子/荒废的渡轮堆在岸边/我正在和一个人/作最后的告别。她的马/拴在岳麓山下”(《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