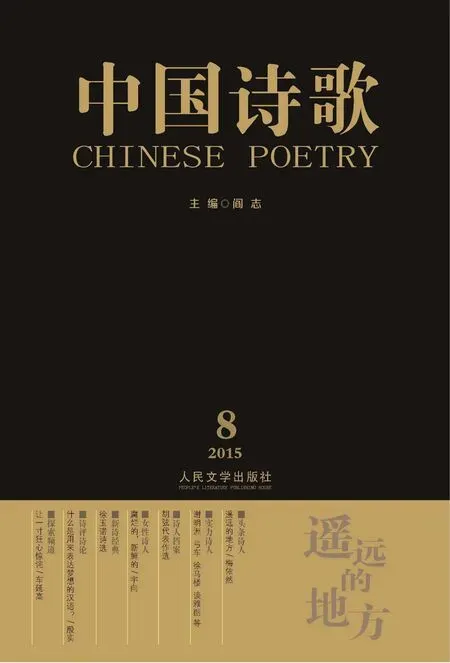什么是用来表达梦想的汉语?
■殷实
什么是用来表达梦想的汉语?
■殷实
在此我想讨论一个问题:什么是用来表达梦想的汉语?
在中国,在汉语的历史中,只有痴人和诗人才说梦,对吗?这样的历史已经相当久远了——诗,总是与古老的象征世界相联系,诗的写作,意味着一种泛灵论态度,即人类对精神存在的坚定信仰。此外,诗的语词特点、句法关系,更接近早期巫祝中的谶语这一点,大概也会加深上述印象吧?所以,正常人都会把听起来不那么正常的语言组织、修辞方式称之为“作诗”,暗示可能有妄想和颠三倒四的成分。
所以,一般世俗的文人、精明的官吏,都更喜欢讲凡尘中具体而琐碎的事物。就连宗教到了中国也要变身,入乡随俗,用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世俗化方针转述其训谕,比如禅宗。不过,现在发生的一个状况是,“梦”突然间好像成了一个热词,被添加到了政治文件、意识形态话语的行列,被频频用来点缀报纸社论,描绘政府的发展蓝图之类,就连电视节目主持人也要在大街上拿着话筒追问路人:你的梦是什么?我想,这可能多少会让今天的一些诗人们略感尴尬吧?以梦想为业者,出于某种同样古老的洁癖,或所谓精神上的特立独行,会不会考虑绕开这个词呢?但是我想说,这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因为问题本来并不出在个别词汇的使用,以及由谁来使用这些方面,而是在作为职业梦想家们的精神实质方面。从艺术语言的角度看,较长一段时间以来的现代汉语新诗写作中,一直都在发生着某些无意义的分裂,或可称之为是一种情志的变异:用于呈现天真梦幻、自然歌咏的这一文体,在今天正逐渐丧失其根本,愈发沉迷于伤谗疾恶和不平之气的发泄,偏离了温柔敦厚的方向,丧失了“思无邪”的品质。当然,这种情况并非现在才有。比如在唐代,虽说李白和杜甫齐名,正如韩愈所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但是,以时人或后人的评价来看,自诩方外之人,时常“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的李白,其地位实际上是低于心系社稷苍生的杜老夫子的。原因何在?我想,除了儒家传统这个强大背景之外,古代贤者对诗人自律问题的警觉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例如杜甫在提到李白时,曾有“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的期待,也可以说是遗憾。他到底想“细论”什么呢?这大可玩味。李白的写作飘洒、俊逸,但他的想象很可能太过于无边无际,或者太沉湎于风月草木和神仙虚无之间了,有时未免不够缜密,难达义理。所以苏辙在《乐城集》中就说:“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而不知义理之所在也。”而王荆公的看法是:“李白诗词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什么是“识污”呢?就是思想的糊涂,是认识的虚浮,心性的偏执。单从审美立场来看,这些批评其实是很值得重视的。
神仙虚无也罢,花、酒和风月也罢,出现在诗人笔下并无不可。但从中国古代文人的入世与出世模式来看,则入世是原动力,出世是对入世而不能得志后失望的策略性表达,与宗教那样的超人间信仰不同,甚至连庄子那样的相忘于江湖的通达都不及。这种内在的矛盾和沮丧,是文人寄情山水、纵情花酒的主要原因,所谓对社会政治的批判与拒斥,从来都不过是借口。由此而呈现出的文学表达,多只是对一己悲愤和抑郁的释放;由此带来的生命或个性“解放”,则不过是对文明范式的疏离心态。如果我们从现代主体的心理建构来看,这就是有缺陷的。我的意思是,出世、厌世之类冲动,未必导向理性的清明,也很难达致艺术的崇高和静穆,即艺术审美的那种无功利性、合目的性。乘桂舟,驾玉车,游戏万物,谈鬼论仙,人生得意须尽欢——落拓不羁一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佯醉装疯甚至借酒浇愁亦无不可,但如果诗人对“自由”意志的表达,已经到了不知义理之所在,或诗歌本身的语义矛盾、词句晦涩,已经到了读者无法理解时,就实在不必曲为之护。
自新文化运动发轫,经历了1949年那样剧烈的社会文化变革,甚至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现代汉语新诗的历史虽说短暂,但也大致形成了自己的某些传统,那就是对语言、体制的彻底解放,对民族传统、民间文化的整合吸收,对自由、民主、科学等价值的强烈诉求,以及对腐朽文化、封建传统的深层颠覆,等等。这个路线看上去是没有什么问题的。1976年的天安门广场群众诗歌运动,后来北岛等人的那些抗议式的命题模式,今天我们都可以从一种诗歌政治的意义上获得理解,言其在思想解放、社会解放的进程中有一定的“先声”作用,包括像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个人价值的高扬等,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究其艺术本身的价值,则恐怕还有待时间的检验。问题在于,这种以反叛为特征的艺术思维方式,以反讽为主要修辞策略的写作理路,以及常常自外于主流社会价值观念与情感的疏离心态,实际上演变成了近三十年以来汉语诗歌写作的一个主要取向:那就是文学(诗歌)愈来愈有演化为一种次级意识形态的趋势,诗人则热衷于成为并没有什么真实政治抱负的“反对派”,或者是悲苦的流亡者、愤怒的异见人士之类。表现在具体的写作中,就是反经典、反崇高,甚至反文化——至少是反对本民族文化和本国的当代文化。体现在写作中,就是无尽的尖刻嘲弄、怨怼谑浪,也是自我中心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病态爆发。同时,诗歌语汇也前所未有地粗俗化了,失去了应有的庄严华美,不再讲究音韵节奏,不再重视形式的意味。如前所述,历史上的这类现象,人们是警惕过、反思过的,只不过苏辙、王荆公等人原本是美学上意见,很可能因其官员身份或因其背后的儒家道统而被误判了、忽视了。况且,古代人即便如李白那样的天纵之才,也绝没有简慢涣散到像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体统全无!李白的格调在整体上无疑是明亮的,诗里诗外也都遵循着一定的法度。
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想到1949年以后中国汉语新诗探索中的另一路径,那就是何其芳、艾青、臧克家、闻捷、贺敬之、郭小川等人的诗歌实践,包括像郑敏、绿原、牛汉、屠岸、彭燕郊(且不论香港、台湾地区和海外的诸多汉语诗人)等不计其数的前辈诗人的诗歌建树。这个更注重民族语言、传统音韵格律和大众阅读习惯的优良传统,可以说是奠基性的。但由于这个传统本身还没能纯熟到经典化程度,不大理会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也不捡拾西方现代派诗人的牙慧,更没有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做什么分割,就难免被后知后觉者讥为“传声筒”、“喉舌”之类。这些诗人及其写作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在一些研究者、特别是今天的某些学院派批评家那里,不是被颠覆、解构,就是视而不见,这些诗人的作品也正在被当代一些文学史的写作者刻意遗忘。
从本土出发,在民族语言的历史性发展中有所继承和创新,不过分追逐新奇——特别是外来“技艺”方面的新奇,并力求传达公共感情、群体意志。这就是我认为我们在今天有必要重提现代汉语新诗中这个重要传统的原因。何其芳、艾青、臧克家、闻捷、贺敬之、郭小川等诗人所遵循的路径,如果不过分追究其个别内容上曲度歌颂的成分,在诗歌的大众化努力,在语言态度方面,就会让我们想到唐时的元稹、白居易等人。如果我们足够诚实的话,也会发现,在他们的严肃实践中,有现代经验,也有远古的回声,例如对人民性问题的沉思,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弘扬等。同时,在表现上又可见《诗经》里的那种活泼与天真,指事言情,词意简远,适合朗诵。相对于一直在方法论迷津中打转的所谓现代派们的呓语,他们的作品更具中国气质,也更遵循中国的文化精神:不悲观绝望,不放弃对尘世生活的关注。即便他们“干预教化”的意图太过明显,甚至在特殊情况下可能被工具化了,从他们的诗歌理想中,我们也仍可追溯到一种可以扩展至全人类的“公天下”视野,以及像事功精神、济世情怀这样的珍贵遗产。上下求索,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最终达成“风谣善恶”、“厚人伦,美风化”的理想之境,这正是历来我们所熟知的诗人之梦、诗歌之梦的根本。
从痴人之梦、诗人之梦,到古人之梦和今人之梦,这些想来也都平常。对我们中国人而言,近现代以来最显著的事件其实是西人之梦的侵入,因为这些梦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梦!我在上文已经表明了这样的意思:拜“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赐,中国的汉语新诗几乎在一夜间呈现出了某种现代面貌。这个现代面貌,形式上是白话文、自由体,思想旨要则在于启蒙,也就是对人的解放主题,社会革命、文化革命等主题的拥抱。坦率地说,作为负载这些观念的文学艺术,包括现代汉语新诗这样的语言艺术,实际上只获得了一个初创的,也可以说是草率的根基。放眼今天差不多已经成“主流”的自由体诗,其体制问题实际上从未真正解决。不要说声律节奏、语言的典雅精致之类,最糟糕的情况下,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语义逻辑和句法规律都被抛弃了。在一些不明就里的初学者那里,写诗不过是开口说话而已,在少数死守欧化句式和翻译体例的“精英”写作者中间,最容易被津津乐道的则是“现代”和“国际化”之类含糊其辞的东西。这就涉及了现代汉语的命运问题。
今天我们正在使用的、欧化色彩浓重的书面汉语,是近代中国所受外来影响的重要指征之一。一般认为,由胡适、陈独秀、鲁迅、傅斯年等为代表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大规模实践,是现代白话文的起始。或者稍早一点,清末的话本、小说,包括《红楼梦》等著作中,已经有了本土语言中较为接近口语的书面白话文。但这都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汉语。有学者在研究过西方入华传教士自十六世纪以来留下的各类文本,如《华英词典》、《天路历程官话》等著作后发现,正是在传教士们使用汉语翻译基督教经典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欧化特征鲜明的现代汉语白话文,这才是对中国本土语文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吸收的较早范例。在化欧为汉的过程中形成的白话文,从词汇、语法到句子结构,都和本土汉语明显不同。其后还有大量日文转义词的植入等等,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称的现代书面汉语。我们一定都还记得,在学校读书时,写作、翻译中的“欧化”痕迹,往往是会被作为不够炉火纯青的汉语而诟病的,这表明我们中文教育中的语言自觉是存在的。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欧化特征鲜明的现代汉语,包括外来语的不断增加,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到目前为止也仍然在进化中,自然也就存在着消化不良的问题。实用层面或无大碍,但在以此为根基的中国文学的写作及现代性阐释中,却微妙复杂,存在着变动的无限可能。即便如诗歌弄潮者们所津津乐道的“现代”和“国际化”之意涵,其真正的所指我们也有必要一探究竟。
启蒙时代,与线性时间观念同时被接纳的,是科技力量的神奇、人文思想的宽广,也伴随着先进与落后、进步与倒退之类的历史观念。特别是民主、自由、个人解放等价值观,在专制色彩浓厚的东方土地上尤为深入人心。但在现实层面,不同文明之间的竞争和力量角逐,往往使处于不利地位者甘拜下风,对优胜者的顶礼膜拜由此产生。而对“先进文化”的尊尚,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对优胜者语言的尊尚,继而造成“道”与“器”分家。如此,中国现代诗歌在语言、体式上长时间走不出欧化阴影,难以回归母语的自信,而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精神,像科学、理性、个人道德及法、哲学这些东西,则被慢慢遗失了。今天我们已经十分清楚,“朦胧诗”的所谓“朦胧”,并非诗境诗意的含蓄朦胧,其阅读障碍更多是来自其体式、句子的杂乱和语法残缺,有时完全是语言不通所致。举一个例子:当北岛在早期模仿贺敬之等人的诗歌语言和体例——尽管在思想上相去甚远——写下像《回答》、《结局或开始》等诗作时,这些作品是明白易懂的,而当他在西方现代主义、意象派之类偶像的方法中盘桓太久,缠绕过多以后,就似乎再也无法从容驾驭自己的母语,也就是现代汉语了,像后期的《白日梦》之类。
梦与诗难分,诗人与梦难解。中国最早也最著名的梦,属于哲学家庄周,这个全世界都知道。从《诗经》、两汉乐府、魏晋时代的诗歌,再到后来的律诗词曲,两千多年时空中,我相信汉语里的“梦”这个字从未被错用过,无论“颠倒梦幻”这样的对妄念的揭穿,还是“梦断香消四十年”这样的对刻骨怀念的表达。事实上,无论任何时代,表达梦想的汉语亦即诗歌,都是不可或缺的,那些以梦想为职业的人也都受到了持久的敬仰。在这里,我们只需要弄明白一点:什么是用来表达梦想的汉语?在前面我曾经提到李白的某种恃才傲物和狂放不羁,其实那都不过是一种天性的活泼浪漫罢了,从整体上看,他仍有绮丽豪放的诗格。今天的汉语诗人则不同,可以说已经天真全无!狭隘、偏执、世故、孤芳自赏、崇洋媚外,对凡俗众生的忤逆甚至冒犯等等,不一而足,总之他们似乎不大会做梦了。与此同时,现在又出现了所谓回归传统诗歌的情况——旧体诗词正卷土重来!无论是否真通音律,也无论社会文化语境已是多么不同,很多人都在积极尝试。我们知道,传统诗歌,特别是唐代以后的近体诗,在历时久远且规模庞大的精研苦练中不断踵事增华,无论曾经承载多么高妙的思想感情,实践了怎样唯美的艺术精神,在形式上其实都已经登峰造极,几乎再无发展空间。在当代,大约除了毛泽东这样的特例,以及后来又被发现的胡风、聂绀弩、牟宜之等极少数人创作的旧体诗词尚可阅读之外,真正有成者不过是凤毛麟角。
传统样式的再度时新,政治领导人语言风格的影响,或是诗人们专属的精神特权、语言特权被取缔了,这都不是问题。任何时候,诗人们须力戒的,主要还是语言空洞化,是意义的简单循环,是文化命运的悲剧性轮回。道器分离的情况下,古代大部分所谓的正统文人作诗,不免思想僵化、趣味低级。而历史上那些离经叛道者的游戏之作,也多半陈陈相因,沿袭套路。所以,回去几无可能,至少是非常困难的。倘若我们能够超越国粹的层面,着眼于远古时期“公天下”之普世理念,着眼于儒、释、道这些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要素,并对其进行现代转换,则用于表达梦想的汉语之路仍然存在。
今天我们已经看到,在一些打工者身份的诗人笔下,在某些底层劳动者的信笔涂鸦或网络歌谣中,都依稀可见《诗经》中“风”的传统,或是杜甫那样的苍生之爱、人道情怀。而且这些作品大都语言简朴,体式自在,风趣可读。虽然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仍属嬉戏之作,亦难摆脱怨愤之态,但至少在表意方法和策略上,已经大大地中国化了,或者说已经不那么西化了,也许我们需要从中发掘提拔的,只是一点点艺术的自觉,是一份真正诗人的情怀品格。与世俗生活合拍,与大众阅读和解,整合熔铸时代审美经验,坚守责任与良知,忧思共同体的命运,呵护生命的家园,这恐怕是现代汉语诗歌臻于完美的必由之路。最后,我认为如下条件也至关重要,那就是摆脱域外文学的阴影,特别是摆脱对翻译诗歌样式的低劣模仿,摈弃诋毁、亵渎、诅咒、玩世不恭一类的诗歌腔调,回到汉语天然本真的自由状态,回到中国人喜怒哀乐的生活世界,和光同尘,自在自为。换言之,也许只有在对中国的现实文明,包括政治文明意涵、一般社会发展目标和价值理想持开放包容而非疏离的态度时,诗人对民族精神文化现实和语言现实的关切才不至于落空。
(这是作者在第四届中国诗歌节〈绵阳〉诗歌论坛上的发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