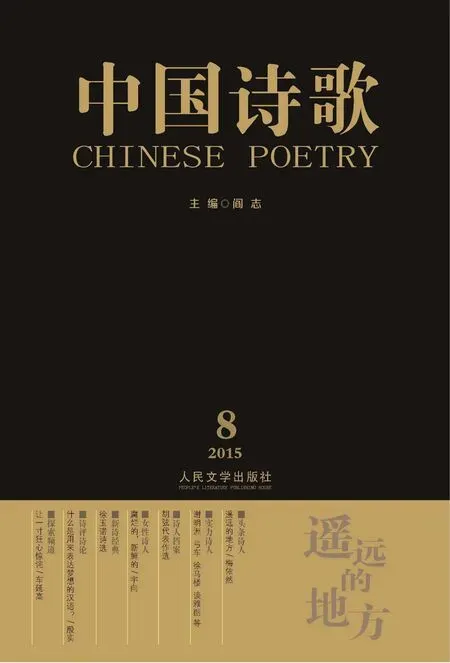中原赤子的忧伤
——徐玉诺新诗导读
□王金黄
中原赤子的忧伤
——徐玉诺新诗导读
□王金黄
作为中国新诗的开端,五四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提倡并积极投身于白话新诗创作的诗人,徐玉诺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一位,无论他的作品数量还是质量都堪称佼佼者,他也是较早以新诗的形式结集的诗人。虽然相比于同时期的胡适、周作人、俞平伯、刘大白、郭沫若等,今天的读者对徐玉诺并不熟悉,甚至完全陌生(徐玉诺自身性格上的原因,致使其人其诗自建国以来很少被提及和被评论),但在风云突起、流派林立的二十年代,王任叔、茅盾、瞿秋白、郑振铎、周作人乃至鲁迅都对他的诗歌作出过评价。闻一多在给梁实秋的信中,更是对徐玉诺的诗歌赞赏有加:“《将来之花园》在其种类中要算佳品,它或可以与《繁星》并肩。我并不看轻它。《记忆》、《海鸥》、《杂诗》、《故乡》是上等的作品,《夜声》、《踏梦》是超等的作品。”直到近些年来,徐玉诺才重新被关注,谢冕主编《中国新诗总系·第一卷》收录了他的19首诗作,张新颖主编《中国新诗》和陆耀东著的《中国新诗史》中,对他都有专门的评价。
徐玉诺出生于河南鲁山贫苦农民家庭,他在求学期间就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在短短几年内创作出几百首诗歌(秦方奇编校的《徐玉诺诗文辑存》中收录了341首,同人合集《雪朝》收录了48首,个人诗集《将来之花园》收录了116首)。叶圣陶称其诗有“奇妙的表现力、微妙的思想、绘画般的技术和吸引人的格调”(叶圣陶《玉诺的诗》,1922年《文学旬刊》)。时至今日,当我们朝花夕拾,再次与诗人相遇,发现这位中原赤子的诗作以其独特的思想和审美价值,仍然值得我们细细回味与认真研究。
一
徐玉诺一生颠簸流离,辗转奔走于全国各地,亲眼目睹和经历了中原大地的凋敝、积年累月的战乱以及民不聊生的苦难,却始终怀着一颗博爱仁慈的赤子之心,写下一首首忧国忧民的悲歌。
第一,对黑暗时代的控诉和对人间疾苦的质问。中原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战火、饥饿、贫穷、疾病和死亡对于成长于此的徐玉诺来说从未远离,它们既是恐惧之源,也被诗人深恶痛绝,这在《农村的歌》、《杂诗》(1921年10月22日)、《教我如何睡去》等诗中都有所体现。“我的轮儿涩滞,/我的牛儿瘦削,/连天连夜的送兵车,/饥寒说奈何!//绵羊儿正在孕育,/藏在树林里,/又被支办局找着;/羊肉送进了衙门,/羊皮羊毛便卖了,/还敌不上宰税多!//黄风又刮起来了!/这不是种麦时候?/眼看着海绵一般的土壤/变作石头一般坚硬!//粮食谁甘便卖!/家中没有一粒米,/锅中水沸着!//寒风刺刺的逼人,/冬天的霜已经弥布在晨间了。/单衣不主贵,/不褴也透风!”(《农村的歌》)在诗中,诗人除了表现贫穷和战争,还表达了对“支办局”的苛税和重赋的不满,更令人绝望的是干旱导致庄稼颗粒无收,不仅没有口粮,还要挨饿受冻。诗人通过对农村一户人家的日常生活以及心理的真实描写,展现了暗无天日下人民走入了生活的绝境。时代之黑暗不仅仅是政治腐败与战争导致的,还有不得不面对的各种自然灾害,黄河泛滥或旱季严重缺水在河南时有发生,天灾和人祸的双重重压让诗人无限愤怒。“喇叭吹的是进攻,/更声一点一点地沉默了,/嫁你过活的不是诗,/勿劳你微笑着写!/只为那可怜的小孩子/哭着饿,/典当还有一件衣,/恰遇着户闭封门戒严夜。”(《杂诗》,1921年10月22日)对于无止无休的战争,诗人已然无力再用诗歌来讨伐其罪恶,生存下去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戒严而不能外出典当以买得生活必需品,仿佛听到“那可怜的小孩子”饿着哭如战争的号角一般无休无止了。直到战火烧到了家门,“尸身臭烂,遍地血泥。/现在干了,焦了,/白骨也都自烧了!”“弟弟在死尸垒就的/战壕里作战;/父亲母亲避弹/躲在烧了房屋的墙角里;/小孩子饿得受不住了,/拨开被血泥糊着的眼睛,/跑到白骨堆里扒弹壳,/去到枪炮局换饭吃。/天啊,/这样的时候,/教我如何睡去!”(《教我如何睡去》)相比刘大白《教我如何不想她》,不禁把我们拉回现实悲惨之中,家人的生离死别使睡觉也成为一种奢望,惟有那个“跑到白骨堆里扒弹壳/去到枪炮局换饭吃”的饥饿小孩成为痛斥时代黑暗的最强音,达到“无声胜有声”的振聋发聩,也使得无奈而又麻木了的诗人不得不质问人间疾苦的根源,“我尝以为上帝是凶残的,/不然,/为什么现为人造下生,/又设了多路的死?”(《悲哀的人生》)然而,上帝是不会回答的,诗人试图通过质疑和拷问来捍卫人的尊严和权利,自然也没有任何结果,但诗人对时代的鞭笞和揭露无疑是令人钦佩的!
第二,对人生忧愁与绝望的抒写。作为时代的经历者,徐玉诺不仅要承受自然灾害导致的饥饿、政府剥削下的贫困以及战争中的伤残与疾病,而且更要承受个人的流离失所与亲人之间的生离死别,这才是最可怕的切肤之痛。6岁时他的姐姐徐然早夭,17岁时叔叔徐海被土匪杀害,尸体被野狗分食,25岁时弟弟徐倬病故,最亲的人接二连三地离世,诗人不免感到迷梦一般的寂寞而凄凉,“刚才是梦;/现在是梦呢?/在那里我是一只小鸟;/温柔的山石,/浓香的树林,/围绕着我;/我正要且飞且鸣了。//现在是梦;/刚才是梦呢?/我是一个孤独的堕废者;/北风如刺,/冰雪盖地,/没有黑夜和白昼,/我不止地蜷缩我的四肢、躯体,/我将蜷缩蜷缩至于没有!/我将变作这寂寞而寂寞中的一点了。”(《谜》)即使面对自然的秋天,也不过徒增心中的寂寞和忧愁,“我何恨于秋风呢?/年年都是这样,/它是自然之气;/可怜我落伍的小鸟,/零丁,/寂寞。//懒涩涩的这枝绿到那枝,/没心的飞出林去。/最伤心晚间归来,/似梦非梦的,/索性忘却了我是零丁,寂寞。/秋风啊!/你虽说是咯咯的响个不住——/借红叶儿宣布你的肃杀和凄凉,/但是我有什么怀恨与你?”(《秋晚》)在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诗人在开封第一师范积极投身青年运动,一度被推举为学生领袖,但好景不长,1920年他带领开封学生罢课以声援北平各界反对日本,“河南督军赵倜密令属下收买学联中的不坚定分子,致使学联分化,徐玉诺悲愤异常,痛不欲生,意欲卧轨自杀,警醒同胞,幸经嵇文甫先生耐心劝导,才打消轻生念头”,但是学生运动的失败,使满腔激愤的诗人郁结于心,从此烦恼便像“一条长蛇”,又像“红线一般无数小蛇”,“麻一般的普遍在田野村庄间;/开眼是他,/闭眼也是他了。//啊!/他什么东西都不是!/他只是恩惠我的跟随者,/他很尽职,/一刻不离地跟着我。”(《跟随者》)为了避开人生的愁苦,诗人开始了漂泊不定的生活,先后于鲁山、福州、苏州、临颍、厦门、北京、开封、吉林、烟台等地留下足迹,或是教书数月,或是筹办杂志,然而都不了了之。更荒诞的是,1938年初,“徐玉诺赶到洛阳要求政府派给抗日工作,却获令‘回家休息’”,1943年6月,“他在课堂上继续宣传抗日,一个学期后,学校当局要解聘他”。经过一系列报效祖国的尝试失败、努力实现人生理想的落空以及沦落异乡为异客的人生流转,诗人彻底感到生活的虚无和绝望,好似船上的旅客,“把生命全交给机器了:/在无边无际的波浪上摇摆着,/他们对于他们前途的/观察,计划,努力及希望全归无效。/呵,宇宙间没趣味,再莫过于人生了!”(《船》)因此,在徐玉诺的许多诗作里都充斥着悲哀的气息,“字典里只有愁字/最美丽而有意义/和厚味。”(《小诗·十三》,1923年5月)甚至以绝望的笑声来聊以自慰,“黑暗、垢污、屈辱,/是我每日的三餐,/大笑是我的音乐。”(《小诗·九》,1923年5月)对社会和人生,诗人由最初的忧愁到悲观,乃至绝望,虽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却是源自个人最真切的体验,“一个渴望人生意义的人,/他带着火一般的眼睛,/赤着足跑遍了世界;/他的呻吟是苦处,/他的歌唱是无聊。//他的眼睛晕花了,/他的足骨磨透了,/世界也找遍了,/人生还是没意义;/他气绝了呻吟,/无聊的歌唱也唱不出来了。”(《没意义的人生》)这个深深地沉在污泥里“气馁而且疲倦了的”诗人那颗出淤泥而不染的赤子之心,我们不得不为之感动,在绝望之中就仿佛也有了再次勃发的力量。
第三,把自我的情感寄托于自然之美和未来之世。在当时北洋军阀相互混战的背景下,诗人对整个社会充满了绝望,看不到丝毫的光明,然而大自然的秀美与生机又逐渐驱散了他心头的阴霾,当“春天踏过了世界,/风光十分温润而且和蔼;/凸凸的墓场里满满都走出青草,/山果又开起花来。/我跳在小草上,/我的步伐是无心而安静;/在那小小的米一般的黄或红的小花/放出来的香气里,/觉出极神秘极浓厚的爱味来”,突然,诗人笔锋一转,“墓下的死者呵!/你们对人生是不是乏味;/或者有些疑惑?/为什么不宣告了同伴,/大家都来到墓的世界?/春光更是绚烂,/坟场更是沉寂;/我慢慢地提着足,/向墓的深处走着。”(《墓地之花》)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诗人心中剧烈的思想斗争,一边是令人窒息的灰暗现实,像墓地一样死寂,而在另一边春光惹人怜爱;作为中原大地的赤子,父老乡亲尚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不如墓下死者的生活,诗人又怎能全身心地投入这明媚的春色之中呢?但是面对夕阳下“山、树、石、河”的静穆和庄严,“一切伟大的建筑都埋在黑影里;/人类很有趣的点了他们的小灯:/喜悦他们所见到的;/希望找着他们所要的。”(《小诗》)从而映衬下的人间烟火也成为希望的象征。在《旅客的苍前山·轻歌二首》中,我们更能体会到诗人沉浸于山水湖川时的愉快和恣意,“细风吹,白云踏过林梢走;/林梢常依风摆动,白云一去不回头。”(《旅客的苍前山·轻歌·1》)如果说自然的美好使徐玉诺重新燃起了思想之光,那么,作为未来的建设者——小孩子则成为他所呵护和珍爱的全部,“我坐在轻松松的草原里,/慢慢地把破布一般折叠着的梦开展;/这就是我的工作呵!/我细细心心地把我心中/更美丽、更新鲜、更适合于我们的花纹,/织在边上;/预备着……后来……/这就是小孩子们的花园!”(《将来之花园》)鲁迅曾在《狂人日记》中发出过“救救孩子”的呼声,而这座“将来之花园”无疑是最为理想的庇护所,小孩子们健康地茁壮成长,诗人不禁激动万分,甚至想象着未来的蓝图胜景,“我的小指,万能而且神秘;/能指着太阳,使那太阳不敢行走;/能在汪洋的大海上,/划出一道大而且长的桥。”(《小诗》)虽然有所幻想总聊胜于无,但现实之残酷使诗人时刻清醒着,“现代地上满满都是刺”,“世界满满尽是疽”,自然之大美和未来之憧憬不过是“水上鞋”、“云中鞋”,都无济于事,徐玉诺未曾想从根本上改变现状,这些寄托只是一种暂时性的缓解,“我已造下梦中鞋。//张哥,来!李哥,来!/一齐穿上梦中鞋。”(《问鞋匠》)如此呓语式的隔空对话,好似醉酒了一般麻痹着自己,成为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二
徐玉诺的诗在艺术上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风格,成为中国新诗发展之初的一颗耀眼明星。
首先,他以忧郁悲凉的感情基调,将死亡诗化处理,注入浪漫主义的情思。这与诗人对现实彻底地悲观绝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既没有优雅的闲情来自顾自怜、潜入南山,坚守传统士大夫的“哀而不伤”;同时,他也缺乏战斗的勇气去慷慨激昂、鱼死网破。“当我意志一刻一刻地萎靡,/呼吸一息一息地低微的时候,/我很平安很甘心;/我将静待沉入死神的罗幕了。/但当一个生活问题来我床边时,/我的感觉重新又恢复起来:/伤心伤心过去,/又怅惘怅惘将来。”(《杂诗·三》)除了死亡,只剩下无边无尽的哀伤,“今天悲哀的美味/比起江南的香蕉来还要浓厚。”(《小诗·四》)诗人以津津有味的品尝来嘲弄自我生存于人间的悲哀,虽然赋予了形象化的浪漫色彩,但死亡的气息扑面而来。然而,死亡又并非想象中的那么随意和简单,“自杀还算得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人生,/他觉得自杀也是没趣味。”(《小诗》)这体现出诗人对待死亡的理性思考和清醒认识,个人的死亡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我想着立刻将这世界毁灭了,/这或者是我的恶意,/但除此之外,更没有什么希望了。”(《小诗·一》)向死而生成为诗人的理想和使命,他把死亡作为一种可能的现实性,通过对生命之有限的凝视和对存在之无常的感悟,获得了超越忧郁和悲怆的欢喜之心,“当我把生活结算一下/发觉了死的门径时,/死的门就嘎的一声开了。/不期然的/就有一个小鬼立在门后,/默默地向我示意;/我立时也觉得死之美了。”(《小诗》)“门”的设置和门后的“小鬼”形象达到了对死亡的高度诗化,对于“死之美”的由衷称赞则剥离了原本语言含混着的戏谑成分,这首诗代表着徐玉诺奇异而独特的审美趣味,也成为他个人生死观的鲜明例证。伴随着肉身的毁灭,时间将成为死亡不可逾越的界限,当自我意识认识到不朽的荒谬时,生命的本真状态就显示出来,“大浪一刻不停地流去了。/小浪们啊!/我们怎样保持我们一闪的生命,/作为彼此的相照?/小浪们一看也不看地翻下去了。”(《杂诗·六》)诗人在对死亡的不懈追问和艺术观照中,打开了意义与价值的生门,虽然有着被“翻下去”的代价,但却拥有了瞬间之美。
第二,把丰富的哲理寓于鲜活的意象之中。冰心诗歌同样以凝练简洁、融理于诗著称,建构了一系列关于“爱的哲学”的意象群,具有“理”附于“物”的特点。徐玉诺的小诗则打破了趋同化的桎梏,展现出纵向人生的多维度可能,“‘……杀杀杀……时代吃着生命的声响。’同叶圣陶所写的‘这一个树叶拍着那一个的声响’可谓两个声响的绝唱!只冰心才有这种句子!实秋,我们不应忽视不与我们同调的作品。只要是个艺术家,以思想为骨髓也可,以情感为骨髓也无不可;以冲淡为风格也可,以浓丽为风格也无不可。徐玉诺是个诗人。”在此,闻一多对其诗作意象与哲理的多样化做了积极肯定。徐诗既有我们日常所见的各种事物,如“长蛇”、“浪花”、“小灯”、“花园”和“鞋子”,它们与诗人所要表达的显在喻意形成一对一的关系;也有以具体形象与理性价值判断构成的意象混合体,“假设我没有记忆,/现在我已是自由的了。/人类用记忆/把自己缠在笨重的木桩上。”(《杂诗·3》)具有箴言式的直观和先知式的警世,把隐性的哲理彰投射在“自由——木桩”之间的相互对应中,从而产生一种发人深省的力量;此外,还有一类抽象化和概念化的意象,如“谜”和“鬼”。庄子有云:“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意象的塑造说到底是一种特定情境下思维的具象,然而,对于非物化的意象来说,所指更不明确,因而,更有利于哲思的共存和彼此碰撞。“什么东西不变成鬼呢?/但是人的鬼,比/臭蒜的鬼,狗的鬼,狼的鬼更可怕;/因为我们料定/他会演出人类的丑来。/他能带着礼貌……同人一样,/并且做着人的事情。”(《鬼》)“在黑暗而且寂寞的夜间,/什么也不能看见;/只听得……杀杀杀……时代吃着生命的声响。”(《夜声》)其入木三分的描画令读者毛骨悚然,这全部得益于“鬼”这一意象的概括性与多元阐释之间产生的巨大张力以及诗人对时代本质的高度把握,在解读之时“杀杀杀”的磨牙声萦绕心头、不寒而栗。同时,诗人也能够跳出现实的观照,宏观上把握人世的变幻,“湿漉漉的伟大的榕树/罩着的曲曲折折的马路,/我一步一步地走下,/随随便便地听着清脆的鸟声,/嗅着不可名的异味……/这连一点思想也不费,/到一个地方也好,/什么地方都不能到也好,/这就是行路的本身了。”(《小诗》)诗人把个体的存在纳入自然天地之中,从而获得思想上的澄静,“欲辩已忘言”的前行就通向了“此中有真意”的至境。
第三,从整体上完善和弥补了白话新诗开创之初的不足,尤其在诗体形式和诗歌语言方面,为新诗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诗歌体式上,以自由散体为主,同时又富于变化,进行各种尝试,有独语体(《将来之花园》)、对话体(《问鞋匠》)、诘问体(《悲哀的人生》)、小诗体(《夜声》、《船》)、叙事体(《教我如何睡去》、《农村的歌》)、半格律体(《杂诗·一》、《杂诗·六》)等多种形式。同时,他还注重向中国古典诗词学习,创作了《旅客的苍前山·轻歌二首》:“细风吹,白云踏过林梢走;/林梢常依风摆动,白云一去不回头。”(其一)“细风吹,白云踏过林梢走;/白云随风远远去,空留林梢思悠悠。”(其二)这两首短诗既传承了《忆江南》二十七字令的明丽轻快,也汇入了巴蜀民歌《竹枝词》的情趣,既有西方油画的色彩感,也有现代汉语的灵活与机智,呈现出一种美轮美奂的动态美,映衬着主人公沉浸于宜人风光的飘逸心境与淡淡的忧思。另一方面,徐玉诺也注意到新诗的格律问题,却并不拘泥于传统严格的押韵规范,而是采用了顶真或回环,比如“一次模仿,/一阵思念,/一阵思念,/一次模仿”(《杂诗·一》);“可怜我落伍的小鸟,/零丁,/寂寞”,“索性忘却了我是零丁,寂寞”(《秋晚》);“刚才是梦;/现在是梦呢?”“现在是梦;/刚才是梦呢?”(《谜》)虽然不如闻一多新格律体所特有的固定性,但反复回环对诗人情感起到了多层渲染和深化作用,在两种事物与时间先后之间形成一种对照关系,便于感情的铺陈和空间的展开。徐玉诺对河南西部地区的俚俗之语了然于胸,他毫不吝啬地将其运用于自己的诗歌之中,极大地丰富了白话新诗的语言,如“门限”、“不主贵”、“过活”、“天爷”、“鏊子”、“泥糊着”、“胡憨樊寇”等,对这些底层民间的话语形态的运用,既可见诗人对家乡浓厚的血脉深情,也体现出诗人为广大失语者代言的平民意识。此外,徐玉诺坚持“我手写我口”,其诗的语言明白晓畅、通俗易懂,既有口语式的酣畅淋漓,“大战,小战,经月,经年;/尸身臭烂,遍地血泥。/现在干了,焦了,/白骨也都自烧了!/这样时候,/这样天气,/我待要午睡,/教我如何睡去!”(《教我如何睡去》)也有抒情式的清新流转,“一念/给她写在信里。/抬头看时,/麻雀飞去了,/风起了,/桂花只是一株树,/黄沙干涸在笔尖上。”(《杂诗·一》)可以说,徐玉诺的诗歌语言不仅给人以强烈的时代感和浓郁的地域气息,而且赋予审美感官以深切的体验。
然而,诗人大半生的漂泊流转,居无定所,造成其诗歌创作的长期断裂。直到建国后诗人才重新拾起诗笔,但已不能与他的早期风韵相提并论。1950年代他写下的诗歌,多为粗陋直白的打油诗,歌颂国家领袖的伟岸和不朽,或是揭露封建地主和反动派的罪恶行径,配合儿歌式的工整对仗,押韵到底,诗人的自我完全泯灭在“大我”之中,沦为没有任何生命情感的宣传口号。因此,徐玉诺的诗歌生命只属于二十年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下的结晶,堪称民国时代的“新乐府”。然而,就是在这些新乐府诗歌中也是存在问题的:主要表现乡村生活的苦难与个人的情感,对于大时代生活的观察与抒写不够;“五四”新文化运动里所提出的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思想,以及个性解放、思想解放的思潮,在他的早期诗歌里没有得到集中与深入的反映;诗的语言比较简洁,但有的时候也比较生硬;意象的创新不够,所以没有强大的表现力;思想境界与艺术境界也不够开阔,在思想情感上难于与郭沫若、徐志摩等诗人相比,在艺术上也难于与闻一多、戴望舒等诗人相比。因此,我们如果对他的诗评价太高的话,也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与艺术的现实。不过,他也只是属于那样一个特定的时代,能够关注民生疾苦,也注重对自然的观察与表达,也就很不错了。特别是他的一些诗植根于生他养他的那一片土地,从人到物都来自于特定的地域,在早期中国新诗中形成了一种地方主义的传统,并且对后来的诗人有所启示。他很早就加入了文学研究会,积极关注时事和社会弊端,有感而发下笔成诗,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注重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表达直切而饱含忧患之情,同时克服了元白新乐府忽视艺术性的缺陷,短小精练,想象丰富。徐玉诺融汇中西,加以贯通,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优势:“在外,摄取了异域,特别是泰戈尔、屠格涅夫的有益营养;在内,他以较深的古典文学修养作基础,直接继承了《新青年》上鲁迅、沈尹默、刘半农、周作人等作者在文学革命初期所形成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战斗传统”,同时,各取所长,兼容并包,使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现代主义三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交融。然而,由于受到主客观种种因素的限制,赤子的忧歌最终化作时代之殇,成为中国新诗史的遗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