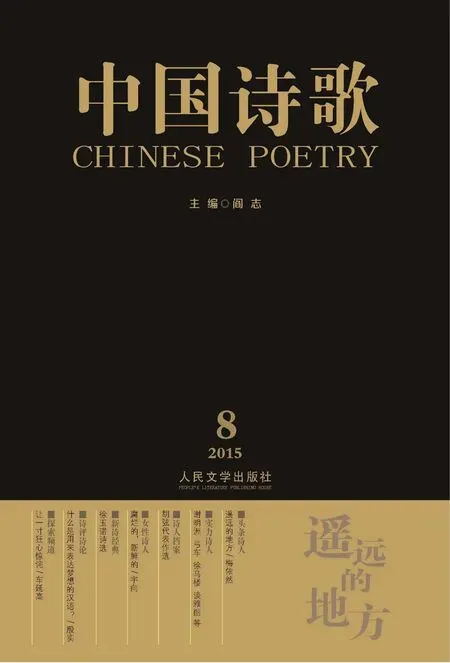曾瀑的诗
曾瀑的诗
回望西藏
安多轶事
在安多草原,才知道什么是雪山净土
像经卷上等待超度的灵魂,静静地坐在玛尼堆旁
会感觉到,那些从地球背面远道而来的人
将一张旧报纸垫在身下,是多么滑稽可笑
本来就是垃圾,置身其中者何以洁身自好
最新的消息说,人类越来越臃肿,肥胖的屁股
已经压不住不断膨胀的欲望和贪婪
坐在一座火山上,怎么会没有一点预感
稍一松动,喧嚣的世界,就会漂过扁平的海洋
从分开的大胯下钻出来,翩翩起舞
只有那些怀揣莲花的人,此时会睁大警惕的眼睛
一张四处乱窜的报纸,可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垃圾
兴风作浪,试图把折叠的版面全部打开
将满载的谎言、丑闻、内乱和战争统统抖落出来
硝烟味十足的文字,随时都会在草原上制造一场火灾
为了这一片宁静,必须及时清除这张不洁的报纸
半裸的乳房。三尺长的大舌头。版面后的脏手脚
抓住,并粉碎,放到该放的地方
下海的河流。远游的白云。幸福的前世
迟早都会从转经筒上归来。要让来自地球
每一个角落的游客都知道,这是神圣的天堂
严禁乱扔垃圾
胸脯
青藏高原上的那一次梦中奇遇
使我终生坚信,在生命中的某一个冬天
一定有一趟列车载着你,驶向一片辽阔而又春光无限的胸脯
停靠在一对丰满而又动荡的乳房中间
年轻的旅途上,忘记带上母亲厚厚的嘱咐
匆匆忙忙爬上那一片苍凉的高原,爬上一个白雪皑皑的季节
命运中有一趟列车,从一场暴风雪的东面准时出发
沿着一条冻死的河流,驶进两个季节间幽深的峡谷
面对一座拦路抢劫的山脉,豁出老命一头撞过去
轰轰隆隆地撞出一条比黑夜还要漫长的隧道
那是世界上海拔最高、最雄伟、最霸气的冬天
在它深不可测的腹地,沉睡的大草原与万劫不复的湖泊之间
暴动的风在我的肋骨上打孔,鹅毛大雪纷纷飘落在我的肺上
青春被蹂躏成废墟,抛弃在记忆深处最阴暗的角落
老式车厢载着瑟瑟发抖的灵魂,咣当咣当逃离说着胡话的僵尸
就在我命若游丝的时候,那女神驾一朵祥云莅临了
这是梦吗?她爱怜的目光注视着我,俯下身解开厚厚的皮袄
漫天风雪被挡在美丽的背后,坦荡而又温暖的胸脯
像慈悲的波浪,铺天盖地流淌过来,将我深深地包裹、淹没
千古冰川中,我被重新孵化,破壳而出
浑身的欲望,无边无际,毛茸茸地生长出来
每当我看到浩浩荡荡、奔流不息的长江和黄河
我就会固执地认为,它们绝对不是来自唐古拉山和巴颜喀拉山
而是从那一对闪耀着神性光芒的乳房流淌下来的
旧军装
许多年以前,我就是穿着这一身军装,去了青海
谈起理想,我们三个人都不想当官,只想做一个诗人
挂在嘴边的,除了酒、猪头肉、女人,就是诗
总是搜肠刮肚,翻箱倒柜,寻找一些形容军装的词语
成忠义用星星比喻帽徽,我和李骞泼了他一头冷水
我说领章就像少女两片性感的红嘴唇,他俩忍俊不禁
喷了我一脸。如此呕心沥血,脑壳里渐渐有了积蓄
词汇就像嘴上疯长的胡须,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
远处的天葬台上,每天都能看到成群的乌鸦飞过
我们的眼睛,逐渐学会识别穿着各种制服的黑夜
开始将身上的军装,比喻作一小片再生的西部
这种感觉地形复杂,雄浑、苍凉、辽阔,起伏不定
一排纽扣,总是摇摇欲坠,无法整合心中的爱与恨
衣袋似乎深不见底,有着掏不尽的灾难、痛苦和悲伤
有时候,我们会迎着凛冽的北风,挥舞着衣服疯狂奔跑
仿佛要把那皱褶里隐藏的黑暗,一股脑儿抖落干净
怀孕的大头鞋,会在死寂的沙漠中分娩出脆弱的前途
裤腿卷起茫茫的沼泽,膝盖露出流血的岩石
一屁股坐下去,地球上就会多出一个迷人的盆地
怀里揣着脱缰的野马、牦牛、羊群,古边塞诗的意境
左肩祁连,右肩昆仑。背上一片雪山净土
每当此时,我们都会有一种心血来潮的感觉
洗得发白的衣襟后面,涌动着源远流长的江河水
转场
那时,难产的青藏铁路,在草原露出端倪
部队的行踪,总是随着它的前途漂泊不定
才将一片冻土焐热,我们又要开拔
自打离开故乡来到青海,已记不清这是第几次转场
我们的目的地,是一张刚刚晒好的蓝色图纸
一个陌生的名词。这样两个名词之间的缝隙
是先遣连数天的行程,隔着三座以上的雪山
浩瀚的沙漠。眉毛和胡茬之间,是辽阔的冬季
出发不久,就听到冰碴在血管里吱吱作响
一个个冰棍似的跳下汽车,呐喊着在地上拼命跺脚
每个人都在发生雪崩。整座高原都在颤抖
戈壁滩上,一些走投无路的石头已经定居下来
和我们打成一片的,是狂放不羁的长毛风
大酒鬼。打着尖利的唿哨,狼一样追赶着我们
突然一声怪叫,打马从我们的头顶野蛮踩过
踉跄着,在前方为我们开路。倒拖着那杆破旗
看上去二极了。弟兄们远远地跟在它的身后
大气都不敢喘,生怕它突然回过头来跟我们玩命
暮色中,它终于乘机将我们连人带车一起灌醉
放倒在茫茫无边的荒原上,然后扬长而去
梦里醒来,眼前是一片向着无限展开的蔚蓝
被浪花推搡到岸边的星星,一小撮一小撮地贼亮着
吓跑的影子,又悄悄跟了上来,发出轻声的叹息
忍着眼泪向后看,古老的大地,月光如水
漫漫长路上,到处都是洒落的故乡
柴达木
那个年代,祖国还在乡下
满头霜雪,佝偻着腰,将柴达木端在胸前
望着这一盆千古苍凉,两眼欲哭无泪
我们穿上宽大的军装,此起彼伏
一遍遍唱着雄壮的歌,为自己的海拔而陶醉
双手接过八百里瀚海,誓言要还她一个锦绣江南
游猎的风冷笑着,将我们的帐篷和梦幻一次次捏碎
自打在草原边一脚踩空,我们就在沙漠中不停地转辗、迁徙
男人,是遥远的荒原上惟一活着的生物
对异性高度敏感,连石头都能看出公母
偶尔瞅见女人的照片,便会一齐发出歇斯底里的怪叫
找不到地址的牛皮纸信封,揣着绝望的爱情在天空乱飞
新修的简易公路,被风沙一条条吞噬
只有将它撑个半死,慢慢反刍的时候,钢轨才能乘机长出来
我们风餐露宿,将那些流浪的湖泊,大风吹跑的绿洲
黄沙活埋的矿山,逃离蓝图的集镇,一个个寻找回来
好言相抚,难民一样安置在铁路两旁
复员的时候,我们全都掉光了叶子
浑身上下,里里外外,找不到一丝儿绿色
一道出来的弟兄,有一些人再也回不到故乡了
临死的时候,要我们将他们像土豆一样种在荒野里
最大的愿望,就是祖国将来有个好收成
我的西部
许多年以后,我忽然发现
我身体的一隅,隐藏着一片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
我背阴的那一面,太阳落下去的地方
沿逆时针方向扫描。地形辽阔,气候严寒,矿藏丰饶
勘探到军营、草原、神山、圣湖、汗血马、雄鹰和雪豹
储存了足够我使用一生的盐、铁、风、月光、闪电和泪水
轻轻闭上眼睛,就可以开采出沉积在岁月深处的青春
一群高喊着女人名字的男人,前仆后继,扛着带血的铁路
向西,向西,像梯子一样搭在离天堂最近的高原上
风吹草低。吉祥的羊群、云朵,向我的后半生缓缓飘动
我的生命,业已演变成东西两个悖谬的板块
郊外散步,一只脚刚刚踏上大平原上的田野
另一只脚,却深深地陷进了浩瀚无边的沙漠
我的肉体,踌躇满志,一路高歌奔向东部的喧嚣和繁华
我的灵魂,筚路蓝缕,义无反顾回归西部的孤寂与清高
向阳的一半,在肮脏的雾霾中塌陷、变质、溃烂
背阴的另一半,在凛冽的寒风中隐忍,沉默成一座冰山
我雄伟的左半身,一条条江河浩浩荡荡,奔流而下
无情地荡涤着堕落的右半身,深入骨髓的污浊和悲哀
怀头他拉的麦田
这是一片怎样的沙漠
如此成色。沉默、内敛、凝重、温暖的颗粒
在茫茫雪域高原,千古冻土之上
需要隐忍、修行多少年,才能终成正果
脱颖而出,为神所眷顾
遴选、点化,赋予灵魂、生命
卑贱的黄沙,顿时活色生香
优美地站立起来,摇身一变
化作这一畦大慈大悲、大善大美的金黄
犹如时光中流浪或沉睡的文字,被激活
分行,赋予灵感、词牌、平仄、韵律
一首古诗词,熠熠生辉,光芒四射
深情而又典雅、厚道、饱满、蕴藉、隽永
被无数次咀嚼、品味、默写、朗诵、歌唱
夕阳下,那些在风中不时低语的影子
如各自忙碌,又相互提醒、映照的隐喻、象征
人间烟火,在现实之外氤氲开来
成为一个古老预言的最新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