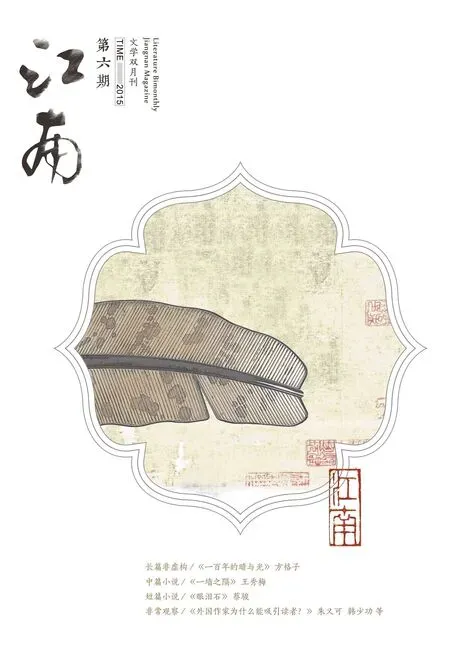你的鞋
□ 但 及
一
这天,是立夏。空气是潮的,连纸都变软了。弄堂里有一只猫,像去了骨头似地缩躺着,在树下避太阳。树叶静默,闪着光,不动声色,有风来时,才晃一下。门,吱地一声开了,一股清香像从幽深的山谷里吹来。黑亮的头发首先探了进来,后面是两只闪亮的眼睛和半张羞涩的脸。
“修鞋吗?”她开口了,轻声轻气,怕吵醒他似的。
“修,当然修。”他想,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店里到处是鞋。
她飘了进来。连衣裙,长波浪,身材修长。
她在小凳上坐下,面对着他。坐时,拉了拉裙子,把裙沿放到膝盖下。这时,窜出一条小哈巴狗,贴着她的裙子,亲昵地转,长长的毛触碰着她的脚踝处。
“鲁西来,鲁西不要跑。”
它叫鲁西,他记住了。她手里拎着个塑料袋,隐约透出一双鞋的轮廓。他正在修一根长拉链,拉上,又拉下,眼光忽高忽低。她的眼里满是好奇,盯着他的手,也来回地动。她,二十多岁。脸,白白的,一缕头发从额头挂下,像屋檐一样挡住了前额。穿着花格子裙,胸口还有朵蝴蝶结,蝴蝶结是白的。头发不时挂下来,她用手去撩,一下,又一下。
他,五十多了,黑眉,大眼,但眼不好使了,鼻梁上已经架起了老花镜。屋子里堆满了鞋,架子上有,地上也有,各种款式,各种颜色。鞋子中,又以女鞋居多。屋里有股鞋油味,皮革味,甚至还有淡淡的脚味。他的后面是个机器,打磨、刨光用的,此刻,她看到一把巨大的静默的刷子,那刷子就装在机器上。
修完拉链,他侧过头,耸了耸眉毛,斜斜地看她。她依然不吭声,安静地坐着,对他的活表现出兴趣。
“真是一份细致的活啊。”她突然冒出这样一句来。
心头一热,一股暖意涌了上来。他喜欢听赞叹,喜欢别人夸耀他,这样的话他经常听到,但还是喜欢听。这些话就像蜜糖一样,让他滋生出甜意。她又说了一遍,称赞他的手巧,他觉得有些难为情,有点不自然。心想,这小姑娘有点特别。
四天后,她来取鞋。街头刚洒过水,地上湿湿的,有灰尘夹着阳光的味道。鲁西先进门,转着头,东嗅西闻,然后是她蹦跳的身影,手里拿着一枝小野花。紫色的小花朵,像小伞,撑开着。她把小紫花往柜台上一插,那柜台一下子有了风景。花与鞋混在一起,花像旗帜一样鲜艳。她嚼着口香糖,香味从双唇里逃出,那清香就钻进他鼻子里。他吸了吸,不敢用力。
她掏了一阵,从包里掏出个相机,红色的,问能不能拍拍他。她说要宣传,要把这店里的手艺挂到网上去。
“我,这,这个破地方,有什么好拍的呀?”
“这叫味道,这里有味道啊。”她得意地说。
镜头伸缩起来,呜呜地叫着。他怔了怔,想不拍,又有些犹豫,最后还是端正好了坐姿。他还是不习惯,从来没人来拍照,手有些异样。照相机咔嚓咔嚓地响,闪光灯在跳动,一亮一亮,弄得他的眼睛不舒服,心也扑通扑通了。她里里外外地跑,蹲下了,又站起,过一会又蹲下。她还跑到门外,趴在窗口。“你别动,别动,就这样,手再抬高点,眼睛再朝下些,对,就这样,不要动啊,千万不要动……”
拍完了。她坐下了,但又不安歇,她拿起了一双架子上的鞋。“这鞋,刚修的吗?”她问。
“嗯,以前是尖头,这两年不流行了,就改成了平头。”他答。
她嘴里发出啧啧声。“奇了怪了,那怎么好像和新的一样呢?你不说,别人肯定以为本来就是平头呢,你真是个聪明人,太聪明了。”她拿着鞋,举上举下,似乎想从中找出破绽来。
“你太聪明了,有本事。”一边说,一边又拍了起来。他尴尬极了。这会儿,她就像个长者,一个洞察世事的人。在她面前,他却成了儿童。他不停用手挡着镜头,一味地说,好了,好了,不要拍了,再也不要拍了。
“不,我偏不,我要好好宣传你。”她就像个学校里的老师,口气柔软,但又不容拒绝。她还命令他,这样,或者那样。“对对对,就这样坐,头侧一点,表情自然些,不要看我,千万不要看我,你做你的。”他只听见相机的声音,咔嚓,咔嚓,咔嚓嚓,像一梭子一梭子的子弹在飞。
她还不罢休,从包里取出本子和笔,坐下来,好好问他。那架势又变成了记者。
她问他,什么时候学的手艺?怎么学的?师傅是谁?要做好的关键是什么?……她煞有介事,一本正经,笔写得沙沙响。有时还托着腮帮子,想上一阵子。他边做边答,有时也答不出来,断断续续。心里在想,是个可爱的姑娘,真是个可爱的姑娘。
二
他的店,在干戈弄,朝西。很小,大约只有六个平方。
与周围的高楼一比,干戈弄显得破旧、潮湿与衰败。他来这里快十年了,每天守着这小铺子,修拉链、鞋子、雨伞和皮包。也算是老店了,也可能是嘉兴城独此一家了。来往的都是老顾客,生意半死不活,勉强糊口。
自从姑娘来了后,他发现变了,屋子亮了些,他的心也亮了。他会想她的脸,那是一张灿烂的脸,满脸的无邪,就像一块玉,安静,透明,没有杂质。开店以来,他一直就是这个样,东西像杂草般东横西歪。但姑娘拍过照后,他觉得要整理了,太乱了,太不像样了。于是,他卷起袖子,花了一个多小时,把东西理了理,重新归类,又重新摆放。他想,她下次来的时候会体面些。
然而,他的努力没有换来赞扬。下次,她来了,立在门口,有些呆,她就站着,不进来。“怎么啦?怎么变了呢?怎么会这样呢?”她仿佛走错了地方。“呆板了,没有生机啊,你知道吗,你这样放不对。”说着,她就进来了,话里带着指责。她的脸好严肃。
他一惊,想,好心办坏事了。
她满脸不高兴,然后,就自作主张地动起手来。她要把这里弄乱,弄得像以前一样乱。她放来放去,可就是放不出以前那种味道。她求救他,他也没有办法。折腾了好一会,屋子倒是乱了,可就是没了以前那个感觉。她坐在小凳上,明显是失落。
照片冲印了,拿来了,放在他工作台上。她的摄影水平一般般,好几张把他的脸拍虚了。
他不敢多看,因为她板着脸,他觉得自己做错了事。不该,不该,他心里这样想。他还想到了道歉,但终究没有说出口来。
姑娘把照片上了网。挂到网后,还真引来了人,有记者来了,扛着摄像机,说他这里有老嘉兴的味道。他推来推去,不肯接受采访。但记者像牛皮糖,一直粘着他,还递给他香烟。死缠硬磨,他终于红着脸说了几句。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什么,脑子是空的,大大的摄像机像个黑洞,把他吞进洞里。他觉得丢人,说完就后悔了,说不要,刚才说的都不要。记者说,挺好的,真的挺好的,我们就是这样采访的。
这以后,生意陡然好了起来,他有点应接不暇了。不时有人来夸他,朝他竖拇指,说看了电视,说他牛。姑娘偶尔也会来,她不来修东西,纯粹来看。她就坐在他前面,看上一、二个小时。鲁西却不安静,一会儿进,一会儿出,跑里跑外,有时还会叫上几声,有时也会傻傻地看他们。
他手拿麻线,在鞋底上一针针地穿。针,缓慢地钻进牛皮里,又从另一头冒出来。针在空中来回穿梭,一来一回,鞋就一点点成形。有时,他会给鞋子抛光。他用小牙刷轻轻地剔,除去皮上的污垢……她看着鞋在他的动作中闪亮起来,光辉起来,最后光彩夺目。原来那双蓬头垢面的鞋,脱胎换骨了。
她说他的手灵巧,一拨弄,一折腾,一件破损的东西就像变魔术一样,变成一件光洁、漂亮的东西。
她还说,她很享受这个过程,这是一个奇妙的过程,是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过程。
她说起来,一套套。有些他听得懂,有些他听不懂。听得他头晕乎乎的。他从来没有被人这样无休止地称赞过,有些恍恍惚惚,但内心还是得意。
三
他失眠了。脑海里,会不时出现她。
她就像只小蝴蝶,瑟瑟地,在面前舞。妻子带着儿子离家后,他还从没这样烦躁过。妻子,是云南人,他花了五万块钱把她娶进了家。这个语言沟通有难度的陌生女人,与他一起生活了三年,竟不辞而别,消失在了茫茫人海里。从此,他的世界就没了女人缘。他的顾客主要是女人,但从情感说,他与女人无缘。他只是服务,用他那双勤劳的手为女人服务而已。
他也想儿子,写过信,打过电话,还到妻子的老家去寻找过,结果却是徒手而归。女人失踪了,最要命的是连儿子也失踪了。这对他的打击是致命的,这些年,他昏昏沉沉,像梦游一样。对外面的世界失去了兴趣,甚至还有点厌恶。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小生意中,一双手忙个不停。忙着时,不会想其他的事,这样他的心情也会好受些。
现在,平静打破了,一个叫不出名字的姑娘给了他惊喜。没有一个人给他说过如此多的好话。在这个世界上,他从来都是可有可无的,多一个他,不稀奇;少一个他,也无所谓。如果,哪一天,他死了,门一关,世界照样,什么也不会缺。但现在,这个陌生的姑娘却搅乱了他,让他感到这个世界还有一份亲切与可爱。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啊。
他承认,自己有些念她。她没出现,就有失落感。他有些盼,盼望她亲切的脸蛋和鲁西一起在面前晃。
是不是喜欢上她了?
这个问题,连他自己都会摇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她还是个姑娘,他可以做她的长辈。他为自己的胡思乱想感到恐慌,也感到羞耻。他觉得自己是阴暗的,见不得人的。
尽管这样,还是想她。想她的模样,说话的声音,一蹦一跳走路的样子。他觉得她漂亮极了,简直把全世界的美都集中到了一起。晚上,躺在床上,床前仿佛有个影子,那就是她。他知道没有,是自己胡想,但他又相信在,肯定在。想赶走,却赶不走,越赶越多,越赶越烦。他起来,就咕噜咕噜地喝水。
他还会站在小店门口,向外眺望,期盼她的影子能从弄堂里闪出来,一跳一跳地过来。他当然为自己羞涩。他不该。厚颜无耻。虽然,他一次次自我批判,但心里还是惦念,抹也抹不去。
有时,他会看到一个小点从弄堂那头闪动,小点一点点大起来,清晰起来,裙子飘扬,脚步声清脆。他脖子伸长,精神提起,期待那个影子幻化成她。但好几次,都让他失望。他没有一次盼到过。
倒是对面的香烟摊老段会扔过话来。老段在一把太阳伞下坐着,老段说,“你还在盼老婆回来吗?你老婆兴许真的哪一天回来了,这是说不定的。”这样的话就像一盆水,把他浇得凉透凉透。他慌忙躲回屋里,脖子通红,像是被别人识破了秘密。不许这样了,不许了,他对自己说。
终于,在一个烈日炎炎的中午,她出现了。她是和阳光一起进来的,一套粉红的运动装,手里拎着冬天的高帮棉皮鞋。她一出现,小屋子就显现出生机,连香味也有了。她说,这鞋的拉链不好,常常拉不开。他试了试,说要换,换新的拉链。
他正在修伞。伞的表面拆除了,只剩下一副空空的骨架,就像医院里的骨头标本。她坐在一旁,摇着小扇子。鲁西也来了,这回没有跑,也安静地坐着,享受着她的小扇子,还时不时地用鼻子蹭蹭她的腿肚子。
她坐着时,他就心慌。一心慌,手脚就不灵。
他骂自己混账,别这样,但就是控制不好。那手好像一下子成了别人的了。自己这个手从来没这样笨过,像粘了东西似的,舒展不开来。她的目光就在面前,直直在探过来,像一盏炽热的灯。这灯,让他热,不止是热,还有些烫。额上汗水也有了。
“你这里要装个空调,太热了。”她说。
“是啊,热,太阳西晒,特别热。”边擦汗,他边说。
“我就佩服手艺人,可这个世界手艺人越来越少了。”她把扇子伸过来,给他扇风。风滑过来,落在手背上,他没觉得凉,反而感到燥热。汗更多了。
“没办法,没有其他本事,只好这样做。”他用衣袖擦汗。
这时,他摸到了一瓶橙汁饮料。这是他几天前买的,或者说是特意准备的。他要在她到来的时候给她,让她解解渴。此刻,就颤悠悠地拿了出来。
“饮料,你喝。”
“啊。”她有些惊讶,但还是接了。她握在手里,那是一只纤细的手。她没有喝,只是拿着,也好像没有兴趣打开来。她还在谈。
“手艺,跟机器不一样,机器是死的,手艺是活的,手艺有灵气,用起来也舒服,所以我最佩服手艺人。手艺人做的东西还带着手艺人身上那股子味道呢。”她说。
他从来没有这样听说过。他的师傅当年也没这样教过。
“嗯,嗯。”他不停地应和着。
“你把你的精神用在了里面,所以做出来的东西特别挺刮。”姑娘临走前扔下了这样一句话,这句话让他想了好久好久。他好像有点懂,又好像不懂。精神,什么是精神呢?这个他真的一点也不知道。这个姑娘是个天使,只有天使才会说出这样不一般的话来。
她把棉皮鞋留在了店里。
后来,他发现那瓶橙汁还在,放在了一边,也没有打开。他拿起橙汁,看了看,摇了摇头。透过一面小镜子,他发觉自己的脸也红了,有些高兴,也有些惶恐。窗外,马路上,有一辆三轮车飞驰而过。
四
转眼到了秋天。
金黄的树叶子旋转着,从街上头又落下。风像蛇一样在弄堂里钻来钻去。马路对面在建高楼,咣当咣当的声音,不时传来。高楼一点点长高,巨大的阴影开始笼罩干戈弄。阴影有时会落到他的小店里。
姑娘一直没有出现。
她的棉皮鞋修好了,一直放在架子醒目的位置。鞋上积了灰,他就拿抹布轻轻擦去。过几天,新的灰尘再度落上去,他又重新去擦。别的鞋啊包啊雨伞啊,进出只有几天,几天前进来,几天后必然会出去,唯独这姑娘的鞋,一直静静地待在架子上。每天进门,他就看到这双鞋。这双鞋很突兀,一直在面前亮着。
他隐约感到一丝不安。
他不知道她叫什么,住哪里,家里有什么人,他从来不曾打听。曾经想打听过,但又觉得突兀,所以一直没敢开口。现在,他有些后悔,早该打听。他变得心事重重,常常,会倚在窗口,脸朝外,希望面前走过的人摇身一变,变出那个靓丽的她来。这也影响了他工作,他变得不专心了,变得丢三落四了。
一个人时,他会取出那双棉皮鞋。皮质凉凉的,他会把鼻子放在鞋前,希望从皮革中嗅出她的气息来。他想象她穿在脚上的样子,她在跳,在软绵绵的草地上来回地跑,在雪地里笑嘻嘻地打雪仗……一个美好的影子在轻盈地舞动,高雅,舒展……有一天,他看到了抽屉里留着的记者名片。他想,记者或许知道她的下落,于是就胆怯地给记者电话。
电话放下时,他感到脑子糊了,脚步飘了。记者告诉他一个惊天的事,她出事了,车祸,还被截了肢。
从公用电话亭,到他小店只有几十米,他不知自己是怎么回来的。他走不动了,脚好像不长在身上,他是扶着墙壁走回店里的。回来后,一直坐着,一动不动。冷汗在流,后背都贴住了,连呼吸都困难了。他从来没有这样过,连妻子出走也不是这样的。
他全身冰凉,反复说着两个字:可怕!
他想不好,要不要去看她。他不能想象见到她的这一刻,他会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是天底下最残忍的事。这最残忍的事怎么轮到了她的身上呢?
他还从记者那里打听到了她的小区——放鹤小区。他到了放鹤小区,在里面一圈圈地走。他不知道她住哪一幢哪一间,但她肯定在,就在这里面。他的眼像探照灯一样扫。他既期望看到她,又怕看到她。他很想问一问小区里的人,她怎么样了?好不好?……他相信,这里的人会知道一些,但一次次话涌到舌头上,又退了回去。他的样子引起了保安的关注,保安盯上了他,说他有嫌疑。一盘问,他吓坏了,失魂一样逃了出来。
春节过后的一天上午,也可能是中午,他听到窗上有声响,是有人用手指在敲,他抬起头,吓了一跳,以为在做梦。
直到看到她的微笑,才相信是真的。她来了,坐在轮椅上,就在他店门口。她围了一条很大的围巾,紫色的,看上去就像个披风。气色还好,但有些苍白。后面有一个长者推着,看上去像是她的母亲。再后面跟着鲁西,鲁西好像胖了。
他站起来。紧张,慌乱,害怕,又夹杂着一丝的兴奋,他走了出去。
面对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嘴唇一直在颤抖。她又朝他笑了笑,这笑里带着苦涩,很勉强,很做作。他尴尬地回应了一下,也很做作。
她坐在轮椅上,大腿以下是空的。她只有上半身。他不敢朝下看,眼光扫过,马上逃开了。他怎么可以往那里看呢?这时,他的呼吸是困难的,气就堵在胸口。
她的母亲好像在说话,他什么也没听进去。他只是站着,像傻瓜一样直挺挺。他目光恍惚又迷离,脑子像烂泥一样的糊。他想请她进屋,但轮椅无法跨进门槛,他只是朝门槛瞄了一眼,就放弃了这个打算。
就在这时,他想到了什么,于是迅速地回屋,从架子上取下那双擦得锃亮的棉皮鞋。已经等她许久了,终于等到了。他拿着鞋出来,颤悠悠捧着,朝她递去。
“你的鞋……”
刹那间,她的脸大变。他看到她的脸变得通红通红。
他递着。她想接,又没有接。鞋,停在空中,停在他们面前。
他还在坚持,往她这边挪,眼神里充满了鼓励,仿佛在说,看,我给你的鞋修得多好,还抛了光,又亮又整洁。她犹豫着,退缩着,像是个烫东西。
但她终于还是接了。拿着鞋的手在抖,越抖越厉害,越抖越厉害。他看着,不明白,不明白她为什么如此激动。
最后,她把鞋举起,涨红着脸,大叫一声,用力地一扔,鞋就从她手里飞了出去。鞋,在空中翻滚,扭出一道凌乱的曲线,重重地栽在地上。两只鞋东倒西歪。
哇——她大声地哭了出来。
直到这时,他才明白自己闯祸了。闯大祸了,但已经来不及了,
她在轮椅上发疯似地叫着嚷着,身子胡乱地扭动着。那个女人,也就是她的母亲紧紧地捂着她,怕她从车上摔落下来。母亲的眼神里带着凶光,仿佛要把他撕了,吃了。
鲁西看到她哭,就跟着叫了起来。汪,汪汪,汪汪汪。声音一片嘈杂。
五
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呢?怎么会这么没脑子呢?
她走后,他一直坐在凳子上,眼睛直勾勾,木呆呆。鬼差神使啊,当时,他一点意识不到这是个问题。这双鞋放在架子上几个月了,理所应当要还给她。他恨自己,竟然弱智到这种地步。
一切已经发生,再说,再想,都是多余。他伤害了她。
两个星期后,一个修包的女士无意中带来了一个噩耗。那女士是当作一个笑话说的,女士说,放鹤小区一个双腿截肢的女孩子,觉得生活无望,昨天夜里自杀了。是吃安眠药死的,早晨他们小区里围着一大堆人,都在说这事。此刻,他正在给一双鞋后跟敲钉子,咣当一声,榔头落地,重重地砸在了自己的脚上。
他脸色刷白,连呼吸都困难了。
“你干什么?是不是病了?你的脸色怎么成了这样?”女士惊呼起来。
他的胸口被堵塞了,气一下子都接不上了。于是,他把手撑到了桌子的角上。不会的,不会的,肯定弄错了,他心里这样在说。
等那女士走后,他艰难地起来,关上了门,把自己锁在里面。他的心一直在狂跳,心像是要扑出来一样。他六神无主,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又坐下。甚至,两排牙齿都在不停地打着架,他想要制止,但怎么也制止不了。
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好好的姑娘怎么可能呢?
厚厚的窗帘闭上了,他坐到了黑暗里,他需要黑暗来陪自己。他取出了被她扔出去的那双棉皮鞋,那鞋捧在手里有点沉,像两个大铁块。外面有人敲门,他没理睬。行人的走路声和吆喝声,一概没有入耳。他好像在一艘风浪中的船上,一沉一浮,动荡不宁。胸口在绞痛,一阵阵,很剧烈。那痛是从肺部升腾起来,然后一点点蔓延到全身……
几个小时后,他开了门。开门后不久,他从对面烟摊里得到了证实,老段也在说这事,话从他被熏黑的牙缝里露出来。老段说,一个姑娘,没有两腿,死了。老段说得更可恶,说她像个冬瓜,说完以后还嘿嘿地笑了一阵。他有些恼怒,恶狠狠地甩出一句:讲话要积德!口气像在教训人
然后,他关了店,决定做一件事。首先,他到花店去买了花,五颜六色各种花。又去了文具店,买了纸板、胶水和装饰纸。最后,他又去了冥器店。
回到家,关上门,拉亮灯,开始行动。他要为她做双鞋,一双她到另一个世界穿的鞋。
工具在桌上铺开了,他一头扎了进去。这是一双纸鞋,他从来没有做过,但他发誓要做最好的。剪刀在手里咔嚓咔嚓地响,他用上了针,也用上了胶。眼眶含着泪,鼻孔也是酸酸的。他剪啊剪,缝啊缝,每一个细节都精益求精。
做着,做着,他觉得不是在做鞋,而是在跟她说话。每一个动作里,都有他的话,他边说边做,边做边说。他不停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伤害了你,我太蠢了,你一定要原谅我的蠢。
他想,鞋的大小,形状,无关紧要,关键是要把他的心意做出来,让她在另一个世界拥有一双完整的脚,让她穿着这双鞋能快乐地奔跑。他觉得,只要有鞋,她就有脚。只要有脚,她肯定也是快乐的。
他取来珠子,在鞋上进行装饰。一串串的珠子,像星星一样散落在上面。
这双纸鞋,做到半夜。一抬头,发现夜已墨黑一团,窗子半开着,外面有雾气在飘荡。鞋,小巧,精致,镶满了饰品。他还用一个精致的硬纸板做了托盘,鞋的边上围着花卉,花朵热闹地绽放着。他用花卉搭成一个“心”字形状,鞋在“心”的包围中。
次日清晨,雾蒙蒙的,路面潮潮的。他骑上了三轮车,左一脚,右一脚,目标是殡仪馆。他相信她肯定在那边,应该在那边。
街道冷清又寂寞,雾霭重重地顶在城市的上方。三轮车吱吱嘎嘎,在他身体与内心的双重摇晃中,孤单地行驶着,辐条碰撞着,发出低回的声音。汽车一辆辆从身边刮擦而过,掀起风,扑到他脸上。骑到半路上,他突然停下了。一种无形的压力笼罩在他的上方,蹬板变重了,脚踝也乏力了,似乎没有勇气再往前了。直到现在,他都叫不出她的名字,如此唐突地闯入她的葬礼,会引来什么呢?
他回头,看到了身后的花鞋。鞋上也罩上了雾气,于是,他下来,用手掌擦了擦。看着鞋,就看到了她,这会儿,她就在那花丛里。是她,恰恰是她,让他第一次感到生命的鲜亮,让他呼吸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清新空气,甚至让他重新审视了自己。她曾经像阳光一样照亮了他。她是太阳啊。
这样一想,他的脚下生出了力量,于是,他低下头,继续蹬踩。他要去,无论如何都要去。即使别人不欢迎,也要去。他给了自己决心。
到殡仪馆时,太阳来了,从云层里探出。他停好车,向殡仪馆门卫一位戴鸭舌帽的老人打听。
“是那位没有脚的小姑娘吗?她在松鹤厅,真是太糟蹋了。听说是自杀的。”鸭舌帽说的时候带着惋惜和同情。
阳光里,他放轻脚步,绕道而行,悄悄来到松鹤厅后面。透过玻璃门窗,能看到里面的情形,那里放满了花圈,一批批人正在进来。在大厅的中央,有个玻璃盒,冷冷地摆放着。他知道那是什么,但不忍心设想这里面躺着的就是她。
他很想进去啊。他不怕她的家人了,即使他被赶出来,他也不怕。但他怕的是她的脸,这张脸是他不敢目睹的。曾经的美丽笑脸,活泼的身躯,一直在他眼前,挥也挥不去。
他决定不看她的遗容,他要保留她的那份美丽,他不想让他心里的那个她受到损害。这对他来说很重要。于是,他重新返回大门口。
“给你五十块钱,你能不能替我把这送进去?送到那个姑娘那里。”他对鸭舌帽说,又指了指车上的花鞋。花和鞋都很鲜亮,把老人的眼光也拎起了。
“能。”鸭舌帽不假思索地说。
“那能不能与她烧在一起?”他继续问。
“这,这好像……”
“我加钱,我给你一百元,把这双鞋跟她一起烧掉。”他平时节约,这回却大度得令自己也意外。
“好吧,你放心,我跟里面的人打招呼。”老人说。
“一定要烧进去。”
“放心,会的。”
“不会出错吧?”
“绝对不会,你放心。”
他掏出一张崭新的一百元,老人验了验钞票,放进了口袋。“你放心,如果你要骨灰,我也会弄出来的。”
鸭舌帽老人捧起了鲜花包裹的纸鞋,看了看,又用手理了理。他在一旁喊着小心,唯恐老人把花鞋弄散了。风从过道里透过来,带着深深的寒意和莫名的阴森。老人脚步小,走得慢,朝着松鹤厅方向过去。
过了一会儿,里面传来哭喊声,人群在移动,工作人员在推那个玻璃盒。他在大厅的外面,缩在一个角落。这时,他急忙挪后,躲了起来。他看到那个移动的玻璃盒,正一点点一点点朝着幽暗的方面远去。他看到了鸭舌帽老人,手里捧着他做的花鞋,跟在后面。哭声响成一片,里面有人在扭动,在呼号。他闭上眼,不敢再看下去。
他侧身进了一片树林,这会儿,太阳又没了,成了灰蒙蒙的天。不久,他看到了烟,那淡淡的烟,从高高的烟囱里升腾起来,一缕缕,一丝丝,若隐若现。这是她吗?这难道真的会是她吗?冷从皮肤里渗出来,开始弥漫开来。他想,他做的鞋与她化成一体了。
想到以后,想到再也见不到她,他的身子抽搐起来。
她的死与自己有关,肯定有关。尽管,没有人来追究他,但他一直在追究自己。他觉得自己自私自利,与她相比,他简直就是个一无是处的小虫子。
烟变浓了,冲了出来,向着更灰的天。然后,烟与这个灰天,再也分不清了,就好像整个灰的天,都成了她。她就在天空里,在看不见的高处。最后,烟囱里的烟越来越淡,化成了袅袅细丝……
他哭了,声音也一点点响起来。他站着,又站不稳,于是就蹲了下来。蹲下时,有一根树枝甚至还刮擦到了他的脸,但他没觉察。他开始起劲地哭,止也止不住。他蹲得很低,能看到大地上纹路,看到有蚂蚁在草缝里忙碌。
他感到无助,感到自己的魂也跟着那缕烟一起飞走了。飞到了空中,越来越高,越来越远。他颠簸得厉害,上下翻飞……
下蹲的腿在发抖,脚指头紧收着。好像整双脚都陷进了大地,好像整个人也陷进了大地。
六
依然还是老时间开门。
门口,他支了个小摊,放着鞋垫、鞋油、板刷、鞋袜除臭剂。自行车和电瓶车不时经过,也有扫垃圾的工人在门口晃悠。对面的电杆上,密密麻麻地缠着电线,有一两只麻雀会不时从树丛里跳出来,在电线上抖抖翅膀,伸伸腿。
鞋还是一样的多,但他的动作好像变慢了。做着做着,会不时抬起头来,出神许久。斜对面的小超市里,做起了鲜肉月饼,那月饼的香味不时会飘来。
有个妇人进来了,还带来了一堆抱怨,抱怨这天在变。他朝窗口一瞟,发现街上阴了,连纸片和塑料袋都在起飞。她站着,喘着气,来问鞋好没好,但他找了许久也没找到。“你说今天拿的,你明明说得很清楚的,是今天。”妇人有些责怪。鞋子堆成了堆,像座小山。他在鞋子堆里找,他真的没记得了,他好像没收过这双鞋。
那妇人也在鞋子堆里找,也没找到。
“你会不会弄错了?会不会和别人的搞混了?”
“不会的,不会的,从来没有过。”他说。
“你这里这么乱,又没有登记,你不弄错才怪呢?你会不会给了别人了?”
“不会的,慢慢找,会找出来的,你不要急。”
“我不急,我的鞋不见了,你叫我不要急,你这叫什么话?我看你是越老越糊涂了。”
面对这小山,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他真的记不得有这么一双鞋了。这样的事,从没发生过。妇人一下子变脸了,发起了怒,还拍起桌子。他一动不动,只是重复着同一句话。“在的话,会找到的。”
妇人气呼呼地走了,留下一个扭动的背影。她那些恶毒的话,令他蒙羞。
他开始扔东西。抓到一样,扔一样。鞋在屋子里横飞,发出砰砰的撞击声。有一面大镜子也落地了,碎了,变成了一地的亮闪闪。但,没有人听到这些声音,也没有人来,即使刚刚出门的那位妇女也没听见。
但他没有停手,在继续扔。
就在这时,看到了那双用塑料袋包起来的棉皮鞋。它在架子的最上方。看到它,他停下了手,不再继续扔。那鞋子就像一块烙铁,烫的,也是痛的。
他一直把它放在那个不起眼的位置。看到这鞋,他更难受了,简直像在掏他的心。他恨自己,也恨自己的职业。他罗列了自己的一生,竟然发现一无是处。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他恨这个行当。以前,他都是认真干这个事,默默地,一丝不苟地,但现在他好像不这样认为了。他恨,真的是恨。他没有心思像以前一样,没有,一点也没有。
他想把这个店给关了,尽管他知道很难,他要赖以生存,养活自己,但现在他没有了半点兴趣,做不好东西,丢三落四。他还认为自己是杀人犯,是他把她杀了,这一点,他常常给予否定,但在梦中,在迷迷糊糊中,他又认为这是真的。是他推了一把,是他把她间接地杀了。他在自责,也在逃避,但他又无路可逃。他能逃到哪里呢?
这双鞋还在。他想丢,想了好几次,提起又放下,但终究不能,也做不到。鞋就在他面前,一直钉在那里,像永远胶住了一样。他看一眼,眼睛就会生痛,就会像遇上烙铁时的闪光。那样亮,又那样的刺,它会刺瞎了他的双眼。
摇晃着身子,来到门口,看着这条长长的干戈弄。街上更暗了,老段收起了打盹的眼,正在收摊。收音机里还有越剧的唱腔,那长长的拖音传到弄堂的深处。刚才那妇人在弄堂对面的厕所旁推电瓶车,沉重的车身与这个人不成比例。妇人还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妇人的背影远去了。他在门槛上坐下来,硬硬的门槛顶着他的屁股。收旧货的人,又闪现了。骑着三轮,车上放着电喇叭,“收旧货,洗衣机、冰箱、空调、手机,价格从优……”乌云就在弄堂口,好像要下起雨来。
就在这一刻,他作出了一个决定,明天起,关店,继续踏上寻找妻儿的旅程。他不能再失去了。
他坐着,身子塌陷。他想象着关门以后的景象,想象着走在茫茫人海里的景象。实际上,他涌起的是一种恐惧,关店以后带来的恐惧。他不敢继续往下想,想下去仿佛是深渊。
天暗得很快,有风从弄堂那面像扫把一样拂来,也是凉的,带着雨的潮味。烟摊老段在街上奔跑起来,在喊,下雨了,下雨了。
“你去死吧,被雨淋死,所有的香烟都淋光。”他自言自语。他这样说的时候,雨声就哗哗地在街上回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