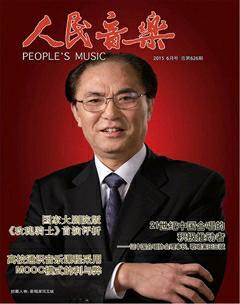作曲:总要写下一串有意味、有组织、有个性的音
一转眼,杨立青老师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他的音乐文章,仍将激励年轻一代继续攀登艺术高峰。这里,实录2013年6月23日上海东方电视台艺术人文频道“纵横经典”栏目《杨立青》专题,以为纪念。
毕祎: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很高兴地请到了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馆长钱仁平教授{2},来跟我们一起追忆我们的一位先辈,也是这个月{3}刚刚离我们而去的杨立青教授。钱老师你好!说起这个事情我们都觉得非常沉痛,因为整个六月份大家没有想到杨老师就走得那么快,一下子就离我们而去了,感觉短短的一段时间里面,就好像一个鲜活的人就跟我们隔开了一样。当时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您是有一个什么感觉?
钱仁平:还是比较震惊,因为杨老师查出这个病,我们都是知道的,一年前,但是我们实在是没想到这么快。
毕:当时我记得我在上班,然后我们在微博上看到,有同学、老师转发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非常难过。在音乐学院这么多年,好像我记得杨老师跟我们,因为他没直接上过我们的课,但是我们有过很多交流,包括我们以前做节目的时候,也经常请他过来做嘉宾,当时就觉得这个老师特别的平易近人,我不知道你当年做学生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种感受。
钱: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是2001年,是在天津开一个全国作曲家会议,杨老师非常客气,我当时是个小孩,他是真正的大师。“钱仁平,久闻大名”,他居然这样子跟我讲,我很紧张。然后他就讲了一句,“你要到我们上海音乐学院读博士”,他讲完就走了。对于一些同辈、前辈,包括学生辈,他心里是非常惦记的。过了一段时间,上海就有电话打过来,他甚至连老师都帮我选好,并不是说你去跟他读。
毕:当时他给你推荐了老师?
钱:他都想好了,所以说我们那一年,2002年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班,全国影响很大的有张千一、吴粤北,还有张旭儒、曲致正,还有西藏的第一个作曲博士觉嘎。几乎是他自己心里有一盘棋,每个学生适合跟哪个老师进一步进修,他都设计得非常好,让你觉得说不出的感动。
毕:对,杨先生好像对青年人,是非常地爱护,在我们的资料库里面也有一些非常珍贵的影像,也许是他最后上台的影像了。2011年,他在上海大剧院给沈洋做过一次钢琴伴奏。这在国际上可能还没听说过吧,一个院长给自己一个学生做钢琴伴奏。当时音乐会,你去了没有?
钱:我去了,这个音乐会,我以及图书馆的同事都参与了一些策划,后来在《人民音乐》上也发表了一篇沈洋的访谈{4}。他跟我说杨老师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因为音乐会的曲目也是很有意思,近现代音乐史上面,包括我们上海音乐学院很多前辈的作品,尤其像赵元任、黄自、贺绿汀、陈田鹤、刘雪庵这些前辈,中国近现代声乐艺术史的代表人物。这样一个很有分量的音乐会,能请到我们的院长、大音乐家,当然杨老师的钢琴就不要说,我们都是领略过的,特别是视奏总谱,更重要的是音乐的品味。这也透露出一个老教育家对年轻人的提携。
毕:应该讲杨先生其实当初进入我们的视线,主要是因为他留学回来的那段时间。当时我记得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乌江恨》这样的东西,大家觉得这个作曲家好像跟我们以往听到的中国作曲家很不一样。您给我们来谈一谈,他的留学以及他留学之后,到底给我们的创作带来了一些什么东西?
钱:杨先生是1978年前后,从沈阳到上海音乐学院来读作曲的硕士,桑桐先生带他,然后他考取了国家公派留学的资格,而且考得成绩很好,第一名。1980年作为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以作曲博士研究生的身份公派去联邦德国汉诺威高等音乐专科学校。去年(2012年)9月份他跟我讲{5},他去的时候开始一段时间也不适应,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西方现代派的东西,他不太喜欢。
B:尤其好像西德应该是整体序列更强一些的地方。
钱:它是现代音乐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基本上已经到了老巢。他写信回来,写给国内的王建中老师、邓尔敬老师,觉得太难听,是不是我们中国作曲家追求的?国内老师给他回信说,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你以后用不用这个东西写作是另外一回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既然进去了,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一定要很认真地把它学透。然后杨先生就调整了他的心绪,一头扎进了这方面的学习。后来因为要延长学习时间,学校的教授在给大使馆的推荐信中说,杨立青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亚洲学生。杨老师还跟我开玩笑,他说这个评价蛮高,但是他还不满意,为什么不拿我跟欧美的学生比?在那个期间他写了一组作品,完全是用他在德国训练的技巧,当然还有自己的想法,比如中国题材《唐诗四首》,但是技法是非常严格的,比如整体序列。
毕:我们比较幸运的是,有一些80年代初期,杨老师创作的那批作品的音像资料。可以看到,他当时用的手法是很激进的,很先锋的,跟我们后面所熟悉的他不太一样。但是就像您说的,也许就是他当时尝试着,或者说去学习的时候,去把那些东西给学到手,您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他80年代初的这些作品的写作水平如何?比如说像《洛尔迦诗三首》《唐诗四首》这样的一些作品。
钱:即使用现在的眼光看,杨老师在他德国留学期间写的这一组作品,仍然是有很高的水平,也就是他真正学到了欧洲现代音乐的精髓。
毕:在这个方面,包括他的那本重要的著作——《配器法》{6},同样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钱:其实在欧洲并没有相对独立的配器课,配器就是作曲,都是一个老师教。
毕:所以我觉得读他这本《配器法》的时候,不像在读《配器法》,像是在读《作曲法》。
钱:大家知道,20世纪以来,音色、织体在创作里面的因素越来越大。最近20年来,由于杨先生的影响,年轻的学者,包括我们作曲理论界的研究,也很倾向以这个为切入点来观察当代的中西作曲家作品。但是,我想,杨老师在前几年突然间出版了另一本译著《二十世纪和声技法》{7}。我想,他自己可能也在观察中国音乐界的态势,创作、研究的态势。因为有一些年轻人,包括我在内,觉得这个东西很时髦,全民搞音色,搞很精细的东西,他可能有一点担心。
毕:是不是走得太过了?
钱:出版这一本译著,我觉得意味深长,他给我们一些启示,凡事不要太极端。我们可能有一天要静下心来想,在五线谱上写一串有意味、有组织、有个性的音,仍然是音乐创作发展之路上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杨老师总是这样用他的授课、他的著作、他的作品来引导整个音乐界,我想这可能正是先生最伟大之处。
毕: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创作,我相信杨先生有非常多的看法,但是很难找一篇,他直接明确地说,应该怎么走或者不应该怎么走的。他更多的是用自己的创作,慢慢的告诉你,我认为是怎么样的,然后你们看行不行,好像是这样一个概念。由此我想到近现代中国音乐创作中间,比较常见的所谓的民乐交响化问题,杨老师当然也为民乐写过很多作品,但他好像更多采取的是独奏加西洋乐队的模式,而不是民族管弦乐队的形式,你有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钱:其实中国的民族管弦乐方面的音乐家,如彭修文先生,包括上海的李民雄先生、胡登跳先生等人都做了几十年的探索,取得了很多很好的成就,但是确实这个问题,仿佛是一直没有得到最完满的解决。我甚至想,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模仿西洋管弦乐队,这也许是民族音乐的梦吧。但怎么样既能把这个梦做好、做远、做大,又能把这个梦做实,怎么样来考虑这个问题?杨老师最终选择了一个西洋大型的交响乐队跟一个独奏的民族器乐合作的形式,很巧妙,民族器乐的个性很强烈的,一把二胡可以跟大型的管弦乐队抗衡,一支笛子、一把琵琶,都是没有问题的。
毕:因为它很有特点。
钱:它不是靠音量,而是靠发音法、音质、形态,靠它的配器,绝对是相得益彰,所以当初出来的《乌江恨》是上世纪80年代耳目一新的作品。
毕:对,尤其是《乌江恨》。
钱:《乌江恨》是他自己个人的代表作,当然我是一个学生,不好把先生的作品来给他排排队,但那一定是先生的三部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作品在当年出来的时候,全国音乐界是非常轰动的。我记得,很快人民音乐出版社就给他出了单行本乐谱。那个时候在人民音乐出版社要出本谱子是很难的事情。
毕:作品是一个完整的协奏曲的模式。
钱:是的,杨先生在管弦乐艺术方面的造诣第一次得到非常充分的体现。民族独奏器乐和西洋管弦乐队的协奏做法,我觉得倒不失为我们民族音乐发展的一个途径。当然,这不是唯一途径,但是毕竟是目前看来,又能够体现大型的作品创作,又能够推广中国的民族音乐的尝试,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毕:我相信杨老师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把民族和西洋割裂开来看,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音乐只要最后成形,融在一起,而且能够成为一个好的音乐作品,就是可行的。
钱:你讲的非常好。我们都听过很多民族室内乐,这是民族音乐吗?有好多民族室内乐,你说它是一个德国人写的,我一定不怀疑。是不是这样?当然我们不想讲得那么玄,所谓气和道的关系,但确实存在。不是说天天写笛子,写的就是民族音乐。
毕:不是这个意思。
钱:那就要讲到《木卡姆印象》这个曲子,它当然是一个典型的交响乐。
毕:这也是他最后一个作品。
钱:这个作品叫《木卡姆印象》,大提琴协奏曲,写的时候里面有一点木卡姆的音调。但是这个作品的音高上面,杨先生花了大心思。为什么呢?他写的《印子、吟腔与快板》,还有《乌江恨》,毕竟是民间音调的素材保留得相对比较完整。
毕:对,一个是《一枝花》,一个是《十面埋伏》。
钱:民间音调完整的话,乐队的音高不能离得太远。这一次木卡姆的音调用得少,管弦乐队拓展空间大了,因而难度要求也大了。我们都知道木卡姆这样的民间音乐,歌、舞、乐是一体的,里面有很多微分音,
毕:不是很严格的,一个一个弄得很清楚。
钱:上一次我对他访谈的时候专门问了这个问题。他说听了采风收集的资料以后觉得很麻烦。微分音非常丰富、非常复杂。当地的民族乐器本身也很复杂,很有特点,一用那个乐器就是我们讲的广义新疆风格。怎么来做这个东西?他很困惑。最终他选择了用大提琴协奏曲的方式。我问他是不是说木卡姆的形态主要是靠大提琴来表达?他非常快就回答,不是。大提琴承载的是一种外在的态,木卡姆的神还是要靠乐队和大提琴一起来塑造。他在音高上面做了很多这样的处理,就是从木卡姆的微分音的一个系统里,他做了很多生发性的工作,但是在他的谱面上并不能看出太多。
毕:不是很复杂,这个谱子写得太干净了。
钱:和《荒漠暮色》相比,加引号地让步了。
毕:传统了,甚少看上去很传统。
钱:声部的关系,当然不是纯粹纵向和弦,声部的碰撞,复调化的碰撞,他做了很多的思考。
毕:今天也很高兴,请到钱老师到我们节目中间来,回忆杨先生的教学、创作以及经历。我觉得一位20世纪的作曲家,一个以现代音乐创作为主要内容的作曲家,能够有这样的影响力、号召力是很了不起的,很让人羡慕的一件事。我们就最后在《木卡姆印象》的音响中结束今天的节目。通过这个音乐,再一次怀念我们的杨立青先生,谢谢。
{1}此文根据上海东方电视台艺术人文频道“纵横经典”栏目2013年6月21日录制、6月23日播出《怀念杨立青》专题实录并略加注释而成。
{2}2008年8月底任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馆长,2014年6月初调任上海音乐学院科研处处长。
{3}2013年6月10日。
{4}钱仁平《寻找“不存在”的声音——沈洋访谈录》,《人民音乐》2011年第9期。
{5}钱仁平《杨立青访谈录》,《人民音乐》2013年第4期。
{6}杨立青《管弦乐配器教程》(上中下),上海音乐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
{7}[德]瓦尔特·基泽勒著、杨立青译《二十世纪音乐的和声技法》,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钱仁平 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音乐学院科研处处长
毕 祎 硕士,上海东方电视台艺术人文频道主持人
(责任编辑 张萌)
——以新疆莎车县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