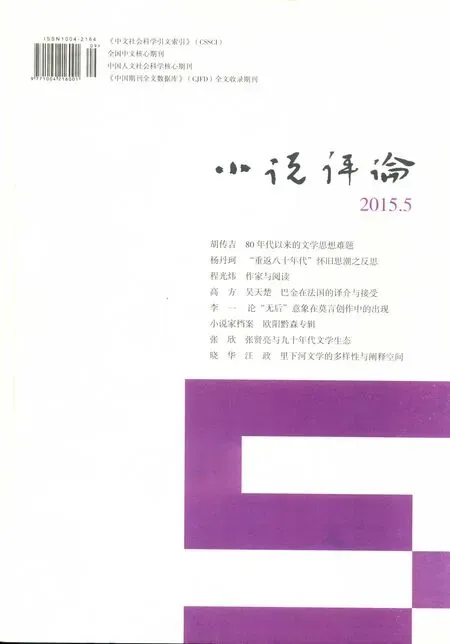论《笨花》的审美空间建构
李 骞
《笨花》是著名女作家铁凝颇具影响力的长篇巨著,也是中国当文学史上比较优秀的小说,这部作品与作家过去在文坛上取得良好声誉;并以“女性语言”完成的《玫瑰门》《大浴女》《无雨之城》等长篇小说相比较,少了才气的秀丽轻盈,多了叙事的内敛深刻。《笨花》不再是依附生活经验来建构小说的故事内容,而是将叙事话语置于历史厚重资源的语境之中,重视历史背景对人物、故事所起的特殊作用,重视历史责任对现实社会道德秩序的建立,而忽略史料在作品中的真实再现。由于《笨花》不是纯粹的历史文学,因而小说就没有对历史的真实与否做出阐释的责任和义务,只是在浩如烟海的民国历史的档案里,寻找叙述的时空契机,将人物的活动与历史的发展进程紧密结合起来,使作品的思想意蕴更具有广阔的社会性和艺术的审美力度。作品所建构的故事/结构的话语艺术空间是独树一帜的,随着叙事情节的展开,《笨花》向我们倾诉了一个历史内涵十分丰硕、社会现实又格外真实的动人故事。从文本的阅读效果上分析,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是,《笨花》对历史的灵活抒写是新颖的,对历史背景下的人物、故事、情节的描述是逼真的。这种把历史资料与小说艺术融会贯通的写作策略,尽管不是铁凝首开先河,但是,《笨花》却在历史的层面上构建了一个变形的、夸张的、象征的,独立于历史之外而逼近现实的人的故事。
一
《笨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小说,也不是“演义”性质的作品,更不是从文学的层面来戏说、虚拟、闲话历史,而是借历史真像的言说来刻画人性的真实,因而故事的叙述推衍就不讲求历史的真实性,更没有“七分历史三分文学”之类的写作规则的约束。作家旨在历史的尘埃里发现人、抒写人、鞭笞人。作品所提供的史料当然是确凿无疑的,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发生在史料中的人是什么和干了什么?也就是说,作家的叙事话语是以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为基础,让虚拟人物的人性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得到重塑。
爱弥尔·左拉认为:“小说家同时也是观察者也是实验者。作为观察者来说,他所提供他所观察到的事实,定下出发点,构筑坚实的场地,让人物可以在这场地上活动,现象可以在这里展开。”《笨花》以清末至抗日战争胜利这一段特殊的中国历史为叙述背景,这是作为作家的观察者所提供的事实。小说以冀中平原上一个叫“笨花”的村庄为描述蓝本,这是作家为小说文本“构筑坚实的场地”。有了出发点和场地,自然就有了人物在场地上的活动,小说中的生活现象理所当然地在这里展开。正是如此,作家在时空交错中彰显向氏家族的发展,而这个家族的发展又与风云变幻的历史线索紧扣在一起。《笨花》叙事的成功就在于将历史的大变革融入到凡人小事的描写中,将时代风云的繁杂多变汇聚于世态情怀的娓娓叙写中。由于作家为小说文本框定的叙事时空是真实可靠的,所以作品才为阅读者构筑了一幅历史与生活互通共容的现代历史的生活图画。
《笨花》的叙事体验是追求“故事”与“内容”的相对应,两者之间互为补充,让人性的光辉在历史与生活的巧妙结合处闪现。小说中的向氏家族及其这个家族中的每一个成员是作家重点描绘对像,这些人物当然是虚拟的,但是围绕小说前半段的主人公向中和身边的人物却又是真实的,比如袁世凯、黎元洪、王占元、王士珍、曹琨、段祺瑞、靳云鹏、孙传芳等人。由于向中和的身份是民国初年的陆军第十三混成旅少将旅长,那么这一段时间发生的复杂波澜的战争当然与他有着必然的联系,因此,孙传芳、王占元、曹琨这些历史上的军阀名流自然成了向中和“真实性”的陪衬。也有人在网络上说:《笨花》里向中和的原型是铁凝的曾祖父,原姓姓屈,和孙传芳是好友,而书中他的三个儿子也确有其人,其中三子是哀乐的创造者杨戈,而铁凝就是书中向有备的女儿。因为本人对作家铁凝的家族史一无所知,也不曾考证,所以对网络上的这一说法只能存疑。但是从文本叙事的角度说,向中和这个人物形象是作家倾力打造的“完人”。向中和虽然是虚拟的,但对他的描写却是建立在历史话语的真实语境中完成的,作家恰到好处地运用历史资料、历史掌故、历史人物的真实性来衬托这个形象的完成,增强了小说的历史厚度,让人物在历史潮流中凝练成长,如此一来,作品中的所有形象都在向中和的影响下具有了生活“真实”的审美力量。这种灵活运用历史素材来完成小说叙事的体验,使得小说中的人物群像都具备了审美的客观属性。
向家在“笨花”这个村子里虽然不是大姓,但是家族的历史却悠久,族中弟子从小跟随乡村名师习孔孟之学,长大了则耕田种地,属于“耕读传家”型家族。作品的前半部以向中和为叙述轴心,并以此阐释历史的寓意性。尽管《笨花》呈现了许多历史事实,但这只是小说展开深度描写的依据,是人物性格成长的历史场所。小说的历史意义在于作者在叙事框架中确定一个现实世界——“笨花”,这个现实生活中的村庄没有明确的历史指涉,而是社会历史中虚拟的人物群像生活的场所。所以说不管作品中的向中和是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但是向中和的生活却是由史料来佐证的。比如参军这一节的描写,作品是这样介绍时代背景的:
公元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日本发动对中国不宣而战的甲午之战,中方失利。皇帝召见曾参与黄海之战的德国军事顾问汉纳根,咨询甲午之战失利之原因。汉纳根向皇帝坦陈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大清失利,乃缺乏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军纪严、能征善战的新军。该新军应以“洋人西械加练”“新军应在十万”。光绪重视汉纳根的建议,……并鼓励朝内各路诸侯为演练新军献计献策。
有了这样的描写,就有了袁世凯及他著名的练兵十三条的出笼。并为常年挑豆腐到石桥镇卖的向喜(入伍后改向中和)的参军和之后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的军旅生涯找到了历史的必然性。由于作家把描述的重心置于历史的叙事空间中,读者沿着文本的叙述嵌入特定的时间、地点,与作品里的人物对话,并体验作家的讲述和叙事经验时,我们才理解小说的叙事者挖掘历史资源的审美目的,那就是通过现场文本的叙述,重写历史风云中人性的光辉。
小说的后半部以向文成为描述核心。
“七七”事变后,向中和因为不愿意与日本侵略者合作而退隐粪厂,这样他的儿子向文成就成为小说的叙事主角。当阅读者进入作品所提供的生活环境与小说情节平行并进时,以向文成为主体构成的叙事空间就成为作品艺术价值的重要参数。《笨花》不是历史小说,也不是乡间生活的历史原生态书写,面是一部力求将历史经验的事件转换成一种审美叙事的文体,并通过文本向阅读者传递历史的强大声音。向中和与向文成不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关系,尽管这父子两人的人生经历差异较大,父亲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叱咤风云的将军,儿子则是一个文弱多病且有残疾的乡村医生。但是这两个人的骨子里的血脉却是相通的,那就是在国家、民族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的勇于担当和强烈的责任感。当少将向中和采取变相隐居的方式消极对抗侵略者时,向文成便无声地接过父辈的担子,在冀中平原点燃抗日战争的火焰。
作为两个意义相近的符号,向文成是向中和意义的延伸,从叙事学的立场上看,这是一种线性描写的继续。西文学者认为:“将各种历史联系起来,使其成为总体性的、形而上的历史概念的共同特征的不是别的,而是线性特征。其含义是一件事导致另一件事,这样就撑起了意义的整个系统”。作为一个大的叙事系统,《笨花》的描写技巧就在于撰写了一部正史背景下的有较大审美特性的小说。向文成一系列活动的大环境是冀中平原的抗日战争,小环境则是他行医的世安堂。虽然时间、场地与他父亲向中和不同,但是父子两人将两段历史联系起来,并构成了《笨花》的艺术整体。
二
作家在《笨花》中从头至尾要告之阅读者的一个信息就是,作品的历史材料是真实的,这是作者的叙事立场。所以小说才将大量的史料放置于文本之中,以增加历史审美意识的厚度。比如光绪年间的“招兵告示”“大总统令”,《大公报》对兵变的报道内容,《申报》对时局的报道,《圣经》的内容摘抄,毛泽东《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文章等。这些史料所蕴涵的叙事结构则是一种小说理念的历史主义态度,即传送历史真实的思想。这样的叙事方式,不仅彰显了历史语境的自觉性,同进又调动了资源为故事的真实性作注释,这就是《笨花》的审美结构所具有的艺术魅力。
在小说描述过程中,叙事空间的共同性是作家创作时特用的一种审美立场,比如作品中的“大总统令”。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根据作品描写进展的需求而出的“大总统令”,都有着特别的审美目的,所有标识都是叙事结构中的意义释放。如向中和参军之后的第一道总统令:
大总统令
任命向中和为陆军第十三混成旅步兵第一团团长授陆军步兵上校衔此令。
中华民国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国务总理 龚心湛
陆军总长 靳云鹏
之所以有这个“大总统令”,是因为向中和在1911年的武汉战事中的突出表现,当然也是他的上司、北洋陆军将领、陆军二师师长王占元赏识的结果。“大总统令”颁发的时间是历史上“南北议和”之后,因此,这是小说创作的一个特殊信息,是主人公向中和人生拐点的重标志。“意义是从空间结构中分析得来的,而空间结构又与临时从总体的语言系统中随手抓来的片言只语有关。”《笨花》叙事的内在时间是按一定的顺序完成的,虽然作家在叙述过程中并没有对所写到的历史事件作任何评说,但是,从小说透露出的历史语境中仍然可以探测到作品的美学意义。这第一道“大总统令”的内涵和外延的指向都非常明白,那就是向中和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小镇卖豆腐的农民,一跃而成为这个家族、甚至这个社会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的人生历程。这“大总统令”和多年前的“招兵告示”的所指,构成了向中和人生转移的重要内容。
现在来分析第二次“大总统令”:
大总统令
任命向中和为陆军第十三混成旅旅长,授陆军少将衔,授三等嘉禾章。
中华民国八年十月十四日
国务总理 陆军部总长 靳云鹏
这一次的“大总统令”是对上一次的补充,虽然时间相差不过三个月,但是意义却不同寻常,这是向中和军旅生涯的顶峰标记。从此,来自“笨花”村的粗通文墨的泥杆子农民向中和成为了将军向中和。这两次“大总统令”的意义、时间与小说中的历史信息作为一种存在的叙事基础,其相互相通的理念很明了,叙事的逻辑性将这两次“大总统令”统辖成一个描绘平台,共同见证了作为在历史社会中的人的向中和的奋斗痕迹。
历史知识在小说中出现,是一种笔写的文本经验,即使这个文本与战争、与革命有关。发生在20世纪的中国大地上的战争,如果排出战争本身的性质,那么《笨花》所描绘的战争场面并不是一种历史知识的外在表征,而是叙事结构中的文本表现。也就是说,《笨花》中的历史事件并不是一种单一的话语存在,而是审美的叙事结构。因为纯粹的历史知识并不能传导叙事的艺术力量,一个单一的历史故事、一个简单的历史事件也不可能成为小说审美的结构基础。《笨花》讲述的虽然是发生在冀中平原上的一个家族发展史,但是,作家在记录向氏家族的发展、壮大、繁荣的过程中,艺术地将20世纪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史料融合在小说的描述视野中,形成一种社会现象的同质叙事,并传达了中华民族面对外国侵略者入侵时的集体正能量。特别是小说的后半部分,当国内的阶级矛盾上升到民族矛盾时,民族意识便成为作品描述的中心线索。所以,一旦我们用解构主义的方法来分析《笨花》,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作家的叙述是依附于一个民族与社会的时空背景之上的艺术想象。
《笨花》虽然是一部虚构的小说,但是作家在对现实生活进行描绘的过程中,将许多历史上真实的事置于描写的框图中。作为表达内容的历史,是为了确立艺术想象的阐释需求。作家把真实的历史材料组织起来,当然是为了确立小说审美的真实意义,从而达到填补作品在叙事结构中遇到的艺术真空。历史是真实的,艺术是虚构的,但是经过作家想象的艺术处理,《笨花》在虚构的叙事结构中借用了历史材料,使历史叙事与艺术叙事兼容并包,无法区分,最终在历史主义的现实叙事中完成了小说的宏大结构。比如作品中提到的1935年由日寇策动的、旨在脱离中国政府管辖的“华北自治”,还有更早的“塘沽协定”,西安“双十二事变”等等。这些历史元素通过作家的艺术组织,给小说的叙事情节增加了较广泛的审美意义。“历史学家的题材是由叙事再现的可能对象构成的,而叙事再现是通过历史学家用以描述可能对象的语言来进行的。正是转义诗学为我们划分历史想象的各种深层结构形式提供了基础”。用历史元素来代替叙事语言,通过“再现的可能对象构成”小说的审美感知,这是《笨花》的叙事原则。当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把审美的客体(作品中提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看作小说描写的纯自然现实时,这就意味着作品中的真实史料在阅读过程中可能被读者忽略,那些遥远的历史符号在读者的内心世界已经转化为具有审美功能的社会内涵。比如小说描写伪省长高凌霨派心腹带着日本人小坂去向中和家里做说客的一段:
小坂沉吟片刻,知道已是进入正题的时候了,便开门见山地说:“向将军一定知道华北这个概念。华北本是个地理概念,而这两个字早已超出了地理概念范围。为什么呢?向将军是个有见地、有卓识的中国人,《塘沽协定》的签订和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建立就是个标志,它的建立才使许多中国的优秀分子有了同我们合作的机会。比如像将军熟悉的齐燮元,还有你的正定老乡吴赞周。当然也有有识之士不愿意与日本合作的,比如像先生熟悉的宋哲元、张自忠他们,还有直系元老吴佩孚,有的做事莽撞,有的显得不合时宜。”
不管是人品还是军才能,向中和都是有口皆碑的重量级人物,所以“七七”事变后成为社会各界力量争取的对象。小坂的这一段话中所提到的事,如《塘沽协定》和“华北政务委员会”,及人物齐燮元、吴赞周、宋哲元、张自忠、吴佩孚都是真事真人,而叙事结构中的讲述者小坂和被听讲述者向中和则是虚拟的符号,但是作家通过转义诗学的叙事功能,将历史与虚构进行同质同构,历史上的事和人作为一种特定的情节结构,被作家赋予艺术的特殊意义。这样一来,历史叙事只是一种事实印痕在虚构叙事中升华。历史及历史上的人物在《笨花》中不是古老的沉积物,而是叙事结构中鲜明的审美基石,是阐明小说审美价值的新的社会意识材料。这就是《笨花》不同于当下其它长篇小说在叙事结构上的审美意义。
三
《笨花》的审美价值是在历史叙事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是历史元素和文学审美价值的结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因此,在叙事结构中,作为表象对象的历史只是小说审美虚构的外在依附,这种依附要由审美形式的各种叙事技巧来完成。无论从艺术形式,还是从历史社会学的意义上讲,《笨花》多元叙事视角的描摹艺术都是成功的典范。
由于作家在叙述过程中试图通过各种艺术方式展示历史的力量,把人物放进历史的环境中进行评说,这样一来,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作家的美学视阈就会受到特定历史环境的限制,为了弥补这个难题,作家在叙事结构的处理上用了“反常的”省叙(“paradoxical”paralipsis)来完成小说故事的内部描写。“所谓‘反常的省叙’就是当同故事叙述者进行回顾性叙述时,略去或歪曲某些信息,这看上去与叙述者现在的知识和眼光不相吻合。常见的情况是,这种省叙发生在同故事叙述的前面阶段,后面则会涉及叙述者眼光的某种重大改变——某种揭示、醒悟或立场的变化。”纵观《笨花》的描述,故事叙述者铁凝在小说的全部描述中,都是以回顾性叙述来完成的。所以,作为描写素材的历史元素所释放的信息,完全是根据作家的主观审美意识进行剪裁,适宜表现小说意蕴的材料便在小说的叙述中产生美学意义,而那些不适合作品叙写的历史元素则被作家隐蔽或省略。尽管读者在初次阅读作品时不会关心叙述者的历史态度,也不会被“反常的省叙”误导,但是当我们耐心观察某些审美细节时,更能体会到作家叙事结构的独出心裁。比如对1911年武昌战役之后“南北议和”的描述。这次议和的历史真相是: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外国势力为诱胁革命军向袁世凯妥协,向湖北军政府多次试探,并于11月26日由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葛福出面“调停”,向湖北军政府提出议和条件。湖北都督黎元洪等以军事失利,竭力主张妥协。12月初,南北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双方代表随即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举行谈判。但是小说为了突出北洋新军中的下级军官向喜(向中和)作战勇敢的才干,故意安排他指挥了一场强攻龟山的战斗,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辛亥革命时,清军的确在1911年11月27日进驻汉阳,占领龟山炮台。但小说在描写龟山之战时,为了增强情感的艺术感染力,故意隐蔽真相,将向喜指挥的这一场战争写得绘声绘色。这样的叙事技术当然是为了弱化事物的真相,突出叙述者的感知和判断。小说这样写道:
龟山之战在这次战役中举足轻重,攻下龟山,队伍当应再向武昌进发,但当时令向喜不解的是,他的一营在夺取龟山之后士气正旺,武昌城轻易可下,他却突然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他的队伍即止于龟山。向喜尚不知,此时南北战事正酝酿着一个新的动向,即:因起义军的暂时失利、北洋陆军占取上风,最终导致了举国瞩目的“南北议和”,以至于孙中山将大总统的位置谦让于袁世凯的局面。
这一段描述把“南北议和”的复杂背景全部省略,似乎向喜指挥的龟山之战就可以定乾坤。“他的一营在夺取龟山之后士气正旺,武昌城轻易可下”,但是却接到了不准前进的军令。历史的真相当然不是这样,这是叙述者的故意遮蔽和省略,其目的是让读者参与到作品人物的思想活动中,为叙述者的审美理想形象树立绝对权威。好像如果没有上司停止前进的命令,向喜领导的一个营的士兵就足以夺取武昌的胜利。事实当然并非如此,这不过是作家为了寻求一个有序的叙事而选择的角度。如同美国叙事学家华莱士·马丁所说:“我们将一种模式强加于过去,这样我们就能够讲一个有关过去的连贯统一的故事”。为了人物形象的前后统一,给被叙述对象增加艺术感性的色彩,这种脱离历史语境“强加于过去”的叙事模式,更能逼真地凸现文本深层叙事结构的艺术功力。
《笨花》是用第三人称完成的小说,也就是说,这是一部作者站在全知全能的叙述角度来发言的作品。如此一来,小说中的“我”对现实世界的看法是通过全知的陈述进行的。“我们无法对第三人称叙述者的可靠性提出疑问,因为他们是把他们创造的人物和环境安放在可疑或可信的范围之间的。”应该说《笨花》所创造的环境都是安放在可信的范围之内,人物的构成和环境的指向都非常明了,这也是这部小说审美真实性的基础。第三人称小说叙事的目的是为读者创造更多的信息,要带领阅读者进入一个已经布局好的叙事的“场”,通过“场”的渲染而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叙事的场作为外在陈述的标志,是小说中的人物语言交流的活动中心,对于作品中的人物来说,这个叙事之场就是他们存在的现实。“场”作为叙事表现结构的焦点,为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形象提供行动的保障。《笨花》的叙事之“场”很多,主要是根据时间的推移或者以核心人物的活动来来确定。当向中和以粪厂作为隐退的藏身之地后,向文成就成为小说中的人物核心,作品的叙事环境就是他治病救人的世安堂,一批年轻的抗日志士都成为这里的常客。作品这样描述道:
这时,夜深人静,甘子明来到世安堂。向文成把灯点亮,又用条夹被把窗户遮严。灯下坐着武备、甘子明、向文成三个人。甘子明看着向家父子,对武备说:“武备呀,我有个提议,咱们见面的范围还应再扩大一些。应该再叫俩人参加,一个是你们的邻居叫时令,一个就是恁家的取灯。我研究过这俩个人,在这一拨青年人里,都是出类拔萃的,各自都有抱负。时令靠近组织的要求很强烈;取灯这孩子也不能小看,断事的能力很像向家的人。”
这一段叙述有时间“夜深人静时”;有特写“用条夹被把窗户遮严”;有人物“灯下坐着武备、甘子明、向文成三个人。”还有议事主题,即增加基层抗日组织的力量。必须指出的是这样的叙述段落在《笨花》中俯首即拾,这种穿越外部世界与人物内心的讲述,就是第三人称“全知叙事”的主要特征。这样的叙事,作者似乎一直在场,而阅读者则通过作者的表述进入人物的思想,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作品叙事的表现结构不再单是语言的表达,而是一种审美信息的再传达。通过阅读,我们得知甘子明、向文成、向武备三个人的关系是:向武备既是上级领导又是向文成的儿子,甘子明是基层抗日组织的领导者,向文成只是一个有眼疾的乡村医生,但是这个医生却是笨花村人的精神导师。向武备、甘子明这俩位领导者的许多策略都是来自向文成。后来的许多重要活动,包括办抗日夜校都是在向文成的倡议、领导下完成的。“向文成把灯点亮”的含义,实际上就是黑暗中方向指路人的象征。
《笨花》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叙事作品,但又不是用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小说形式进行创作的,而是从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演变中寻找叙事的契机,并力图用作品中的情节和人物活动,向读者展示20世纪第一个50年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事实。《笨花》昭示着一种小说描述的发展方向——回归历史途径的叙事结构。小说以叙事时间的内在性进行描述,艺术地再现了20世纪前五十年在冀中平原发生的重大历史社会现象,是一部融历史、社会、民族为一体的具有开创性的诗史型的力作。
注释:
①伍蠡甫 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第2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8月。
②④⑥⑧⑩⑬铁凝:《笨花》第20页、58页、95页、305页、50页、第29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月。
③⑤[英]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第87页、85页,宁一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
⑦[美]戴卫·赫尔曼主编:《新叙事学》第180页,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
⑨[美]James peter J.Rabinowitz 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第358页,申丹 马海良 宁一中 乔国强 陈永国 周靖波等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
⑪⑫[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第33页、第143页,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