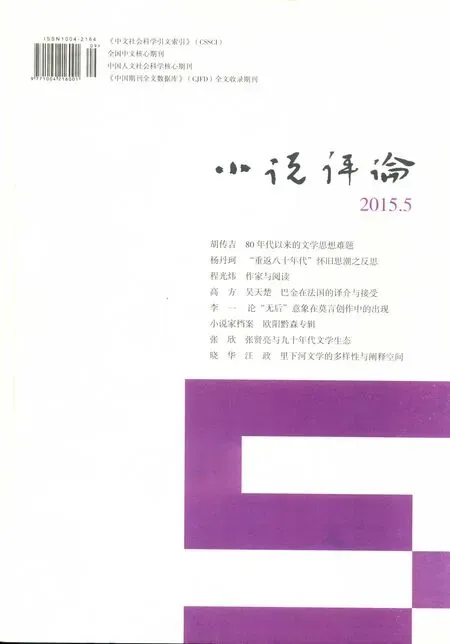“底层文学”需要怎样的批评?
杨胜刚
关于底层文学的讨论已经很多。过多莫衷一是的纷纷议论对它并非好事,因为底层文学写作已经面临被不断增殖的话语泡沫淹没而不知所终的危险。在这场热议中,有一种反感和拒斥底层写作的倾向值得注意。有论者坚持文学的非功利立场,认为“小说承担的应该是它本来应该承担的‘娱乐’和‘美’”,“底层关怀与写作”的倡导是“重新启动左翼文化的陈旧话题”,进而否定其价值。有论者认为底层文学及关于底层文学的讨论被一些人所操控,排斥异己,对不同意见者构成危压,因而心怀抵触。也有论者指出,底层文学所依恃的是道义的优越,当下对底层文学的倡导,以“政治正确性”压制“文学性”,以“道德标准”取消“艺术标准”和“艺术自律”,因此对“底层文学”持不认同态度。
上世纪30年代,以状写工农大众苦难不堪的生活及其愤怒乃至反抗的左翼小说风行一时。由于大多数左翼作家出身农家,有的家庭还十分贫困,如洪灵菲、叶紫等,并有沦落底层、仓皇流亡、生活无着的经历,所以他们在状写工农生活时能充分调动起潜藏的记忆和观察体验,使许多作家能够深入工农生活内部的细节,以侵人肌肤的真实再现这个无声的群体悲苦无告的骇人生存风景。又由于这些作家此前大部分都没有许多写作经验,不以职业作家名世,缺乏深厚的文学修炼,其写作也主要不是出于自我表达,也不是要以惊人的艺术创造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境界为目的。他们的写作反而能极其质朴和本色,洗尽铅华,无所修饰,只是直接呈现。他们在描述工农的生活事实时,摒弃了通行的文人化的对这些普罗大众想象和文人通常附加在这类题材上的意义指向。
上个世界20年代,受鲁迅启示而兴盛起来的乡土文学,又大量把农村和农人作为表述的主体。不过这个时期的乡土文学仍然改变不了被文人精神视域所主导的命运。因为这个时期的乡土作家主要站在现代启蒙思想的立场之上,把农村视为古老、落后、闭塞的地方,农人也被目为麻木、蒙昧的“老中国子民”。那个时代的乡土作家更多在这类作品里居高临下地对潜藏在“老中国儿女”身上的国民劣根性和不开化、乡间陈规陋习进行鞭挞。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共和国文学,工农成为表现的主体。不过工农在这个时期的文学中,早已被意识形态化,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化身。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乡村又一次在文学里大放异彩。不过,这个时代的文学,乡村和农人更则更经常地被文人想象所左右。譬如在《爸爸爸》《白鹿原》这类作品里,乡村甚至农人都被作家设置了太多的文化隐喻与文化符码,成为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一种隐喻,乡土农村生存的农民的现实生活被虚化了,作家明显是按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去图解了乡土。而在莫言的《红高粱》、刘恒的《伏羲伏羲》等作品里,作家更是让一幅幅野性勃发或原始欲望肆意流淌的场景在乡村发生,农人也因此被图腾化了。其他如汪曾祺、贾平凹的许多小说,以描绘风俗画的方式展示乡间的民风民俗或乡野风情,农人成为生意盎然的民情风俗一个有机部分被表现。张炜等作家则把农村及农村代表的生活方式抽象化作为人的精神母亲的大地,以此作为抵御现代文明的盾牌,这同样借农村来进行文人情怀的自我抒发。30年代左翼小说坚定地站在工农大众的立场上,要坚决地为工农大众代言,而不是把农民的生存作为素材,让这些素材去服从这些作家的需要或自我表达的愿望,也不想借助对这一题材的书写来成就作家自己的文学事业,实现自己的文学野心,放纵自我的艺术创造欲望。那一群大多没有多少文学修炼但也没有文学的种种成规束缚的年轻左翼小说作家,还没有能力去虚构一种生活形态,他们急切地要介入和干涉现实的冲动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他们进行独立审美创造和艺术锤炼的可能。对他们来说,能把自我所体察到的底层民众生活更准确无误的描述出来,就已是大功告成。所以大多数革命小说作品都处处暴露出习作者急于描述清楚的笨重描写,正因为这一点,革命小说作家才能“秉笔直书”,能纪实性地进入工农大众生存现场的本真状态,把笔触伸进底层大众微观的生活现场,触摸底层的深层肌理,呈现出在一个完全不顾广大底层民众的利益以及他们的生存发展的不义社会,底层灾难性的生存事实。
在我看来,30年代书写工农大众的左翼小说实际上已构成了对习以为常的文人文学观念的挑战。首先,左翼小说拒绝了通行文学中文人趣味和文人自我精神的渗透。一般的文学主要在文人与世界结成的精神关系之内来表达文人对自我生命与世界的认识、理解与情感,表达作家个人对生存的意义、价值的领会、体验及文人自主自由的精神追求。三十年代写底层工农生存状况的左翼小说呈现的内容是广大底层民众粗糙、艰辛、灾难性的生存现实,讲述这些人日常生活状态的滞重、困苦,在生命的绝处像卑微的动物一样的挣命,它以其坚硬拒绝或阻断了作家美好想象的可能。这些作品背后也没有一个超越性的维度,并不想将民众无声的愁苦生活引向“存在之维”,它表现的生活内容板滞、灰暗、沉重,不可能给文人以崇高或惨烈的美感。所以状写工农的左翼小说直指底层民众的基本生存事实,与文人的精神和趣味实施了较为有效的分离。其次,由于左翼小说拒绝了文人想象和创造对底层生存的粗糙的渗透,所以这些小说在表现的手段上是近乎纪实、实录的,没有更丰富的文学表现手法和表现方式的创造,不追求精致文雅的描绘,无文人的笔墨之趣。我认为30年代描写工农的左翼小说正因它们排斥了文人情趣和审美加工,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还原了不义社会民众的基本生存现实,使这一事实得以裸露出来。维·什克罗夫斯基认为艺术的存在是“为了恢复对生活的感受,为了感受到事物,为了使石头成为石头”。这些左翼小说,以拒绝文人在表现这方面内容方面形成的意义成规和审美规范的姿态,恢复了广大底层真正的生活事实,真正“使石头成为石头”,打破了职业文学者对文学的审美期待和美学理解,以秉笔直书的方式窒息了我们对文学通常的审美期待。左翼小说实际上创造了一种不同于既有文人文学的“新的美学原则”,虽然还不是很成熟,但以其素朴的真实显示其在表达底层工农坚硬的生活现实的有效性,显示出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坚实的力量,一个衣衫褴褛、面容悲苦、天聋地哑的群体就从这些文字中被勾勒出来。
然而它们毕竟是一丛生长在姹紫嫣红的文学花园里的荆棘,它们缺乏水分又粗野地向四周伸展着他们干瘦的枝条和尖刺,给人以冒犯之感,它在文学上的合法性及其意义也因此一直受到质疑。在它们问世之时,就遭到新月派等的抵制,甚至包括左翼文坛亦不重视这类纯“诉苦”的文学。李初梨就认为革命的文学不应该是“血和泪”的,而应该是“机关枪,迫击炮”,要有鼓动性、教导性。左翼文学界大多持这样的文学观,对停留于表达“时代的惨痛的呼声”的作品始终持批评态度。自上世纪80年代后,当“纯文学”的观念似乎已成为一种不屑于再让专业人士费口舌的常识时,30年代这类为工农诉苦的小说由于没有“经典”,它因为艺术上的粗糙更是被轻视,完全淡出文人的视野。然而它们的存在、它们对于文学的价值并不能被视为“非文学”而轻易地否定掉。
当然,自1949年后,中国文学不乏工农大众的身影。新时期以前的共和国文学中,工农大众成为文学当然的主角,不过这个时期的文学在现实主义的名义之下、按中心政治意识形态对工农进行了“最文学”也最虚假的书写。新时期以后,“当代文学并非不关注底层民众的贫困现实,而这一点恰恰是当今文学始终存在的主导潮流……”。但大量这样的作品,像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写的往往是过去历史中的苦难,甚至因为作家力图把现实生存转化为一种哲学意味的存在,使他们笔下的生存现实抽象化,过分地文学化、审美化,以致牺牲了底层民众生存的常态性、实在性。这种纯文人的写作,其实在本质上不是“为了”底层的写作,而是为“文学”本身的写作,是为了作家的自我表达而进行的作家个人的精神跋涉和创造。在这里并不是要否认这类写作的重大意义和价值,只是想说明这类写作由于作家本人的姿态是精英化的,是以表达自我对大众的生存诠释和意义附加为表现的终点,这样的写作实际上封存在作家自我的想象和精神领地里,在根本上是远离底层生存的基本事实的。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也往往丧失了具体的社会现实身份,虚化为“文学人物”或体现“普遍的人性”的抽象人物。由于这些作品的抽象化表达,使它们总体上是“非及物的”,不关涉现实,所以不会激发读者的现实义愤,对现实也缺乏批判性,它们为了文学遗弃了现实。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当代文学虽充斥着众多苦难兮兮的作品,但只有在曹征路的《那儿》出现后,人们才惊呼“底层文学”出现了。历史自有公论,公论自在人心。人们不会出错,不会把高悬于空中、实则冷漠的文学与充满关怀、品质真诚的文学相混同。《那儿》刺破了经济腾飞的华丽表象,坚持社会正义和良知,以强烈的义愤揭示了一个阶层被发展的快车所践踏、所遗弃的现实,揭开了被“新意识形态”(王晓明的说法)所遮蔽的一个群体真实的当下命运,它的出现和备受关注都是现实的必然。刘继明说:“《那儿》为我们呈现的‘底层’也好,‘苦难’也好,都不是抽象的、空洞的、缺少历史上下文的,而是具有鲜明的现实指涉意向,那些在底层中挣扎的人们,也不是像某些小说中的人物面目模糊、单向度的或寓言化,而彰显出强烈的主体色彩……,‘人’在这儿得到了富有历史感的表达,这跟那种现代或后现代式的叙述,无疑是大异其趣的……它为我们有效地接近底层,提供了一条有别于目前大多数叙述视角的新途径。”这段话相当深刻地揭示了《那儿》相对于当下向西方文学认祖归宗的中国大陆文人文学的异质性和对中国现实表达的有效性。它那种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精神,表明作者力图接续上具备强烈的现实批评精神的左翼文学传统的努力。
阿多诺说过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我想阿多诺这里的“诗”应该是指那些沉醉于风花雪月、或纯粹属于诗人个人,以传达诗人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现实和精神经验的诗。一方面,现实中存在着像奥斯威辛集中营那样巨大的人道灾难;另一方面,一些诗人置现实中奥斯维辛那样的人道灾难于不顾,基本上把精力奉献给个体的生命经验的传达,让文学高悬于辽远、幽深的精神领地,追求个体精神的安顿。阿多诺正是看到这种文学与现实的巨大分裂而感到诗(文学)漠视现实的残忍,所以他才会说,如此“写诗是野蛮的”。不过阿多诺并没有否定所有的写诗行为(文学写作行为),他后来在其他场合曾补充说:“长期受苦更有权表达,就像被折磨者要叫喊。因此关于奥斯维辛后不能写诗的说法或许是错的。”阿多诺这句不太明确的话实际上还是承认了写诗(写作)的意义,不过在这里,在他看来,在一个还存在“长期受苦”者的社会和时代,有意义的诗(文学)应该是表达这些“被折磨者”的“叫喊”的诗(文学)。这与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所说的“奥斯维辛之后只能写奥斯维辛的诗”何其相似,他们都表达了要求诗(文学)在一个残酷的事实还很普遍的年代,直面现实、直接介入现实的严峻的意愿。现今,时事仍如坚冰。包围繁华都市的广大农村迅速走向凋敝,而在城市光鲜的外表下,到处是生活无着的人们。底层的农民、工人由于一些严重不合理的政策、官僚机构和官员无人道的掠夺,贫穷是当然的,更可悲的是,他们及其子孙想要改变命运的机会都非常渺茫,无助、无力、无奈、无望正笼罩着广大的底层民众。底层的生存处境的严峻已逼得社会各方面无法无视,思想界、知识界对这方面问题已有深刻而热烈的研究和思考。在这样的时势下,阿多诺、凯尔泰斯的话仍然具有警示意义。只要受苦(物质的贫困、公民权遭受践踏)仍然是底层民众生活的主要内容,就需要表达“长期受苦者”“叫喊”的文学。上个世纪30年代,在中国底层民众的苦难是那样深重、那么普遍的时候,左翼作家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示下,发现了这一现实,并它说出来。现在,严峻的社会现实迫使《那儿》这样直面严峻现实的“底层文学”出现。在不同时代出现的这两股文学力量,有诸多相通之处。在它们的叙述中,许多时候揭发真相的冲动很容易压倒在语言、形式方面的锤炼,这类小说文本因而基本上是粗糙的,甚至在直接为穷人的辩护时还简单地图解政治理念,有观念化的倾向;但这些作品以穷人的贫困、底层的受辱、被压迫和被损害者的愤怒为中心的陈述,无不显示了作家们内心明确的是非感、内心的道德感,也显示了文学应该有的良心。它们充满了侵犯性的野蛮气质,又与大地血脉相连,与大地上的苦难呼吸相吹,有着泼辣粗放的勃勃生气。正是它们集体的横空出世,才使中国文学走出了文人习以为常的精神和文人文学的领地,向更广大的人群开放,扩大了文学的表现领域,丰富了文学的精神,扩展了文学的精神视界,揭开了没有话语能力和权力、处于无声处的中国人真实的生活处境和真实的中国心情。所以在严重的社会真相被人无视的时候,在民众的贫困和遭受非人道对待是社会最普遍、最基本现实的年代,“底层文学”的产生无论对社会还是对我们的文学,都是极有启示意义的,与30年代左翼文学一样,它以极其写实的方式,直呈民众生存的苦难真相,这种素朴而充满道义的叙述也许是与这个时代极为匹配、能非常有效地表达现实的叙述。这样一种非常富有现实意义、有不同文学追求、还不成气候的新文学,应该获得应有的尊重、理解和包容。那种从“纯文学”的角度对“底层文学”进行全盘否定的做法,无疑是粗暴的;而那种怀疑“底层文学”会形成一种话语霸权而拒绝“底层文学”或对“底层文学”的讨论的文学批评,同样有因噎废食的偏颇。
当然,“底层文学”自身的问题,也是应该被指出和拿出来讨论的。由于从事“底层文学”写作的作家缺乏明确、统一和坚定的思想理念,使当下的所谓“底层文学”写作出现极为混杂的样态,众多的作品在精神指向上极为含混和暧昧。其中消费主义文学的惯性和因袭对“底层文学”写作的影响最为严重。比如,有些作品在情节设置上过分追求戏剧化,或把人物置于极端的环境,表现人物极端的行为或人性释放,以至远离底层民众的生存常态;有些作品在叙述中故意将性叙事扩张,坠入表现“普遍的人性”的泥沼;还有些作品用俏皮与滑稽的叙事笔调来稀释故事。凡此种种,都在化解作品所表现的底层生存现实的严峻性,对“底层文学”的严肃性构成消解,使“底层文学”丧失其现实的批判力量,消弭掉它的革命性和独特性,“底层文学”实际上已有被淹没的危险,这直接地威胁到底层文学的健康发展。由于其思想的混乱和表达的轻飘,当下的“底层文学”欲追随30年代左翼文学而不得。底层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如此类的问题应该接受文学批评的质询。
尽管“底层文学”有许多不容无视的缺陷,但它试图介入现实的坚硬、重新唤起文学的良心、突破“纯文学”规范的异质性,对中国文学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这样一个还不太稳定的文学力量,以一种有限的文学观念从根本上否定其合法性,欲将其从文坛驱逐出去是不理智的;而认为“底层文学”是当下唯一正确、欲把它定于一尊的做法同样偏颇。一哄而上、急吼吼地要将其拉入纠缠不清的“学理”讨论之中,或自认为高明地为其规定一个方向,也会给它的发展带来压力,让作家无所适从。一个宽松的言论环境,公允、中肯的批评是所有文学的发展(包括“底层文学”)都需要的。
注释:
①程光炜,小说的承担——新世纪文学读记〔J〕,文艺争鸣,2006,(4)。
②杨扬,走出“底层文学”的误区〔J〕,探索与争鸣,2006,(11)。
③郜元宝,《中国的“文学第三世界”》一文之歧见〔J〕,文艺争鸣,2005,(5)。
④〔俄〕维·什克罗夫斯基.艺术作为手法〔A〕,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65。
⑤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J〕,文化批判,1928,(2)。
⑥陈晓明,从“底层”眺望纯文学〔A〕,不死的纯文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12。
⑦刘继明,我们怎样叙述底层?〔J〕,天涯,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