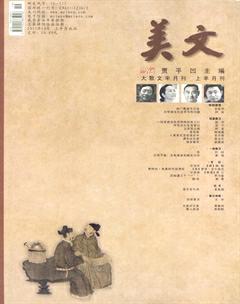一位老游击队员和他的亲人们
郭杰
我的外祖父,曾经是一名抗日游击队员。
他出生于皖北乡村一个还算富足的乡绅之家。那个地方叫伊桥,我少年时曾蹬自行车去过几回。柳树,麦地,沟渠,黄土,路边稀稀落落的野草,再普通不过的乡村的样子。听说家里有百余亩地,雇过一个长工,还有一个炮楼,一杆枪。这样的身家,后来土改时划为地主成分,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地主”是他的父亲,我母亲的祖父,我叫做“老爷爷”。我小时候,老爷爷就住在我们家,苍白的胡茬,苍白的头发茬,满脸皱纹,沉默寡言,没什么喜怒哀乐的表情。夏天就搬个小凳子,坐在家门口的院子里,摇着蒲扇乘凉,口里永远一成不变地哼着一支不知名的小曲。几十年以后,我偶尔出入山间林下的寺庙,才发现,那其实是佛教念经的梵呗之音。老爷爷晚年住在我家,生活费是外祖父大老远从西北寄来的。
还是回过来说说我的外祖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从皖北一所师范学校毕业,就回到了家乡,或许是教书,或许是务农。我小时候没弄明白,大人们也没说清楚。但总算当地一个有身份的人物吧。
后来,日本人打过来了,侵占了这一带地方。烧杀抢掠,兵荒马乱,老百姓东逃西躲,人心惶惶。不知何时,外祖父成了地方上的一个保长。那可是不得人心的伪职啊!
有一天,他独自从田地里行走,经过一条小河,走上了桥头。这时,河对岸的草丛里,正埋伏着几个游击队员。一个队员拿枪瞄准了他,嘟囔一声“狗汉奸”之类,就准备开枪了。游击队长赶紧一把摁住他,说道:“自己人!”这个队长名叫孙云汉,后来转战南北,成了将军,晚年在沈阳军区副参谋长的职位上离休。我家居沈阳时,曾到沈阳军区大院他家那栋将军楼拜访过一回,听说老两口到北京军区探望战友去了,没能见面。后来生活忙忙碌碌,多次迁徙,也就没有机会在再联系上了。但我想,我们这辈子人,真是要好好感谢这位老将军啊!要不是他当时及时揌住那个队员,一颗子弹“呯”地射出去,那我们家的历史真要改写了。虽然那时我母亲尚在童年(她生于一九三一年),但后来地主成分的帽子会压得她半辈子抬不起头来。而事实上,因为有一个革命干部的父亲,我母亲这一生还是顺顺利利度过来的,虽然经历过一次次运动,家庭成分问题从来没给她带来太大的麻烦。
外祖父是受组织安排打入敌伪政权中去的。在那种险恶环境中做地下工作,一定需要相当的勇气和毅力,也要很机敏、很果敢。但我小时候很少几次看到的外祖父,留下的却一直是一个斯文和气的小老头的印象,瘦长脸,瘦小身材,细声细语,不慌不忙,一身笔挺的浅灰色中山装。全家老少几代合影的照片中,就是这个样子。
不知是不是和这次险些酿成“大水冲倒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的意外有关,反正后来不久,外祖父就离开地下工作,回到队伍里,直截了当上山打游击去了。那时和他同在一个队伍里的,还有他的妻弟,我母亲的四舅,我称他“舅姥爷”。
风餐露宿,枪林弹雨。游击队里不仅生活艰苦,战斗更是随时随地充满了危险。舅姥爷在出身富裕家庭,在家里排行又小,自幼备受呵护。在游击队里实在受不了这份艰险磨难,就自行脱离队伍,回家务农去了。解放以后,他毕竟有些文化,又出来工作,在县里的卫生防疫站做干部。“文革”期间,在单位也受到一些冲击。不过,毕竟不是主要领导,冲击不太大,也算平安一辈子。他晚年患了甲状腺机能亢进,到我家这边的医院看病,戴一付老式圆框眼镜,两眼的眼球明显凸出。
外袓父在队伍上一直坚持下来,转战各地十几年。他一定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经历了很多危险。但当时疏于音讯,后来他也没怎么说起,家里人都不太知道,我自然就无从述说了。
五十年代初,我母亲在徐州的师范学校读书,外祖父随部队转移,路过徐州,父女俩见了一面。这次见面,我母亲印象很深,她后来多次给我们说起。冬季里的一天下午,一个年轻战士到学校来找她。原来是外祖父派警卫员去学校接她见面的。母亲被带到市中心一个叫做“聚福楼”的饭馆里。外祖父在二楼的雅间等她。父女俩已经多年不见了,我母亲感到有些拘谨。外祖父就开始点菜,问母亲喜欢吃什么?母亲一个农村女孩子,靠着自己的坚韧和努力,考到徐州读师范,当时算是进了大城市了。但她哪见过这样的场面啊!就咬咬牙点了一条红烧大鲤鱼。在她当时的心里头,这应该是极名贵的一道菜了。于是上了一条红烧大鲤鱼,还点了一些别的什么菜,我母亲已经完全不记其名了。外祖父说,喝点酒吧。于是上了一瓶红葡萄酒。后来,母亲回忆说,那是平生第一次喝红葡萄酒,那酒真好喝啊!真甜啊!她哪里知道,那葡萄酒后劲也真的很大啊!外祖父不怎么吃菜,只是不停地给我母亲夹菜,不停地说:吃吧,吃吧。多半瓶红酒是被我母亲喝下的。吃完饭,母亲已经迷迷糊糊有些醉意了。“脚下像是踩在棉花团上一样,”她说,“是警卫员把我送回宿舍的。”
第二天,部队就要出发了。外祖父又把我母亲找来,带到一个照像馆里,父女俩拍了一张合影。这张合影,一直摆在我们家庭影集的显要位置,我从小就常常看到。外祖父端坐在一张椅子上,戴一顶军棉帽,上缀五角星,穿一身呢子军装,左胸前缝有一块白色徽布,上面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几个字,是繁体字。他的神态宁静安详,很温和的样子,让人感到亲切。我母亲站在他身后右侧,一副女学生的妆扮,但也透出几分来自农村的质朴气息。母亲脸上虽没有流露明显的喜悦,但显得安定从容,是一种很有安全感的表情。
这次父女重逢,对我母亲来说,一定是她平生感情经历中的一个峰巅。终于能和离家多年的父亲重逢了,而且是一个多么光荣的父亲啊!经历过无数次残酷的战斗,多年的戎马生涯,她的父亲竟然没留下丝毫枪伤弹痕,那么亲切、那么温和地出现在自己面前!缺失多年的父爱,重新温暖着她、呵护着她!我的母亲,那时她的心,像喝下红葡萄酒一样甜美!
但是,越是甜美的酒,往往后劲越足、越大啊!不久,我的母亲就接到了令她、也令全家人极为惊愕的消息:她的父亲、我的外祖父,不久就要回乡探亲了。但他这次回来,却不是一个人,而是带着他在队伍上已经娶到的年轻、有文化的后妻一起回来。而在这时,我母亲的母亲、我那可怜的外祖母,正在辛辛苦苦地操持着家务、侍奉着公婆,正在日夜劳作地抚育着两女一儿三个孩子,正在望眼欲穿地盼望着自己离家多年、征战在外的丈夫,平平安安、早日归来!
外祖母真是一个坚强而宽容的人!她默默承受了这一切。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她像接待客人一样,接待自己的丈夫和他的新人,做饭做菜,礼数周全,并且平平静静地办完了离婚手续,直到他们离开。
没有人有资格责难我的外祖父!他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为了国家的独立解放,投笔从戎,义无反顾地走上前线,在枪林弹雨之下浴血奋战。无数战友倒在战场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牺牲了宝贵的生命。死神对任何人也不会怜悯半分。我的外祖父没有进入烈士的名单,他能够从长达十几年的残酷战争中活下来,多少也带有几分命运的侥幸。他在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中,结识了一位年轻、活泼、有活力、有文化的女战士,从共同的理想、相互的默契中萌发出真挚的爱情,在充满艰险、随时可能牺牲的战斗生活中走到了一起。为此,外祖父就不能不和父母包办的的旧式婚姻告别了,就不能不和整日忙于房前屋后、灶上厨下的还停留在过去岁月里的结发妻子分手了。
没有人有资格责难我的外祖父,除了我的外袓母,这个相夫教子、含辛茹苦、把生命的全部价值奉献给全家老少、把生活的全部希望留给自己苦苦等待十几载的丈夫的女人!但是,我的外祖母没有这样做。她只是默默承受住这一切,独自吞咽命运带来的苦水。
但是,等到我的外祖父带着他的新人离开之后,我的外祖母再也支撑不住,她终于病倒了。到徐州大医院去检查的结果,更是令人悲伤:她患的是肺结核,而且已经到了晚期。这在当时,根本就是不治之症啊!
外祖母留在这世上最后的岁月,是在身体患有绝症和心情近于绝望的双重煎熬中度过的。那时,她的大女儿、也就是我的母亲,仅仅二十出头,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在徐州从事教育工作;十六七岁的二女儿和更小些的儿子,还在农村家乡毫无着落,怎能不让她牵肠挂肚、眷念难舍!然而,发生在这样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村妇女命运中的一切,如果也能算作悲剧的话,那么这悲剧也行将结束了。我的外祖母,在命运和病魔的双重磨难下,她的生命之火终于熄灭了。这应该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前几年,但准确时间我已不得而知了。
外祖母最后几年卧病在床的医疗费,应该是一笔很大的开销。没人和我讲起,但我猜想,大部分应该是由外祖父承担的。因为当时除他之外,没有其他人具备这样的经济力量。但我想,这丝毫不能弥补他对我外祖母的亏欠,也丝毫不能减少他良心上的自责。可是,命运既然已做出这样的安排,舍此之外,他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母亲年轻时身体非常不好。二十几岁,正值青春年华,却显得很瘦弱,经常处于心慌、失眠、贫血、神经衰弱的困扰之中。这一切,显然是当时家庭变故的直接后果。但她的内心也像自己的母亲一样坚强。她勇敢地承担起作为长女的责任,把弟妹从乡下带了出来。我的姨,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参加了工作,取得了干部身份,和一位军人出身的民航飞行员结婚,恩恩爱爱度过一生。我的舅,因为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子,排行又是老小,年少时不免有些淘气,我母亲自然没少为他操心。后来果然争气,考上了著名的哈尔滨军工学院,毕业后先后在海军、空军服役。舅舅那一身军装的样子,英俊高大,是我童年时内心敬佩的榜样。他晚年以师级干部的身份从军队退休,现居西安的一个干休所。
毕竟血浓于水。我母亲后来还是谅解了自己的父亲,父女关系和好如初。在我的记忆里,每当讲到外祖父,母亲的语气总那么亲切温和,充满敬爱之情。五十年代中期,外祖父从东北的佳木斯兵役局局长任上,调往大西北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工作,一去就是几十年。直到晚年离休,才进了西安的干休所。那时,他的通讯地址是“兰州市五○八信箱”。至于实际地址,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其实远在兰州千里之外,是处于戈壁深处的一个现在已经解密的核试验基地。
据说,当初我母亲和我父亲恋爱时,曾写信向外祖父报告,同时附上我父亲的照片和一封信。外袓父反复读着信里的内容,仔细端详着照片,赞不绝口,感到非常满意。他表扬说,相貌、仪表、风度都很好;信的内容也很好,讲话诚恳,礼数周全;军人出身,干部身份,都很好!“只有一点遗憾,”他后来对我母亲说,“就是字写得稍差了一点儿。”我父亲是山东滕县人,抗战时日本飞机轰炸榺县,炸毁了我祖父的制鞋作坊,迫于生计,举家迁到徐州。父亲初中文化,一九四九参军入伍,参加过渡江战役、抗美援朝,回国后被选拔到北京坦克学校深造。毕业后进入长春的一个部队。后因身体原因,转业回到徐州。父亲的字,直直爽爽,刚劲有力,带有几分军人的风格,如果衡以书法艺术的标准,自然谈不到跌宕起伏、腾挪变化的韵致,难怪不入外祖父的法眼。
外祖父师范毕业,当时算是很有文化了,尤其工于书法。他晚年回乡探亲,在我家小住数日。那时我正在临帖练字,写得不伦不类。他顺手拿起毛笔,在纸上写了几个字。现在回想起来,那才真叫苍劲老到、笔力十足啊!可惜我当时年纪尚少,所知有限,不懂得珍惜这次和后来一两次难得的相聚机会,没能向他请教更多学问上、历史上的事情,也没请他题下一幅墨迹。如今回头想来,真是觉得遗憾!
有一次,母亲陪外祖父去西安旅游。他们来到了西安碑林。徜徉在林立的碑石中间,外祖父一块块、一排排地仔仔细细观赏揣摩,陶醉其间,流连忘返。母亲后来说:“他就是看啊看啊,看得那么认真,一看就是大半天!”古代书法艺术的丰富遗迹,给外祖父带来了极大的审美享受。而父女重聚的浓浓亲情,也让我母亲的内心感到无比温暖。
但我母亲和她的继母的关系,由于天然的原因,就显得有些尴尬,不能算是十分融洽了。这位继母,我母亲称作“婶子”,年龄上只比我母亲大一岁,是一位性情刚直、快言快语的湖南女性。她们之间难免有些猜疑、有些怨艾。记得小时候,我偶尔无意间从家中书桌的抽屉里,翻出她们之间往返的书信,从礼貌客气的措辞中,似乎能感到某种隐含的机锋。但毕竟,围绕一个共同的男人,那就是我的外祖父,她们彼此间也是脱不开、割不断的。更重要的是,随着时光的推移,共同的善良天性、日益加深的相互了解,也让她们变得更能够互相宽待和包容,虽然达不到无话不谈的程度,总也成为彼此认可拥有特别亲情的亲人了。
时光荏苒。当我提起笔叙述这些往事时,老辈子的亲人们已经几近凋零了。他们在那个年代里,所遭遇的苦难、所付出的牺牲、所经历的坎坷、所感受到的幸福和温暖,已经都如云烟散尽了。但那些往事,何尝不是后人们内心深处极为珍贵的精神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