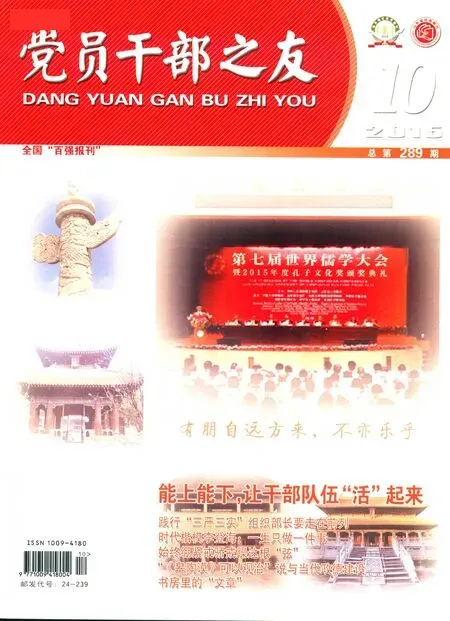老赵的家乡『去哪儿了』
□ 杨业君

安玉民/图
我的同事好友老赵对我说,说不清楚到底是家乡把他丢了,还是他把家乡丢了。他说他好眷恋那句“妈妈,如果有一朵浪花向你微笑,那就是我”的歌词!他在努力地回忆着,又像是自言自语地数说着……
家乡是妈妈怀你生你的地方吗?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大跃进”年代,妈妈怀我在关内,为了填饱肚子,妈妈一路乞讨生我在关外。不知是妈妈丢了家乡,还是家乡丢了妈妈。没“坐月子”的妈妈抱着我跟随“盲流”的人群,先是在一座小城排得长长的队伍里登记了一份临时工的工作,不久又被“下放”到祖国的“北极村”,从此开始了艰难的日子。关外的“臭糜籽”养我长大,这时我成了地道的新漠河人,新的家乡好像找到了我和妈妈。
一个崇尚英雄的年代,我怀揣一个坚定的梦想,自豪地迈进了祖国边陲的军营小哨所。唱着“这儿正是我最愿意守卫的地方”实现了“把全部青春献给国防事业”的铿锵誓言。这时,我是军人,军营给了我“第二个故乡”。
九亿神州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在联产承包的大包干浪潮中,妈妈回到孕育我的关内。从妈妈趟过墨河水那天起,我又成了即墨——新墨河人。妈妈又找回了家乡。
世纪之交,告别军营,和爱人一起耕耘“蓝海经济”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这时,我是青岛西海岸的建设者,“西海岸”又成了我的家乡。
什么是家乡?你可能会说记忆中有永恒的家乡。我记忆中的现实与新词汇却在不断地更新着:北极村、小哨所、联产承包、蓝海经济。
说到此,老赵像是一下子从“恍惚”中醒悟过来,我在祖国心中,祖国在我心中的依恋、依存、保卫和开发建设的心路历程,恰是这个时代巨变的写照。唯有对我的祖国、我的母亲、我的家乡的热爱依旧!
此时,我想宽慰老赵:两个好友,同处一隅,这儿就是咱的家。老赵看着我,深情地说:“妈妈曾对我说,孩子长大了,出息了,你在哪儿,哪儿就是咱的家。我接过妈妈的话说,妈妈呀,有妈的地方才是家乡!”
这时,老赵告诉我,有泪从我的眼眶溢出,我却浑然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