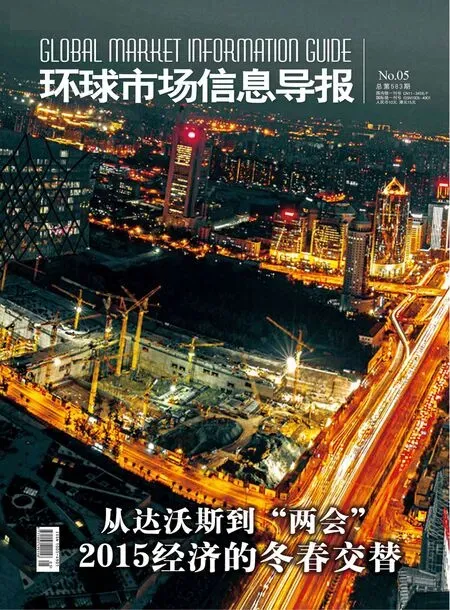吴念真:把生命经验作最诚实的交换
Point
《台北上午零时》是吴念真“用情最深”的一部戏,“它写的是我的青春期”。

第一次把话剧《台北上午零时》带到大陆,吴念真说自己“很忐忑“。这部2007年12月在台湾首演取得极高票房和社会赞誉的闽南语话剧,此番改成国语版,又拿到京沪两地演出,他心里有点没底。
1月22日,国家大剧院戏剧厅坐得黑压压的观众席内,弥漫着一种微妙的情绪。漆黑的剧场里时不时爆出爽朗的笑声,朴实的台词句句暗藏玄机,牵动着每个人的笑神经。但在剧情的转折处,场内一片静寂,大提琴的独奏哀叹着人物的命运,火车飞驰而过的轰鸣声碾碎了美好,观众席四处都能听得到轻微的抽泣声。
《台北上午零时》的票房火爆像是一个奇迹。并没有多少人听说过绿光剧团,也没人真的看过吴念真的“人间条件“系列话剧。但《台北上午零时》于1月22日在北京首演三场,1月30日至2月1日转战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消息,依然默默流传着。仅凭吴念真的名字,两地的票房均提前半个月就售罄,成为2015年开年最火的话剧。
“台北的爆笑点跟北京的有点不一样。“吴念真没想到,他的话剧竟能引起大陆观众的共鸣。在首演结束的那一夜,绿光剧团工作人员站在剧场外,一张张分发调查问卷,上千名观众涌出来时,许多人脸上还都挂着泪,接过笔,在人潮中站定,认认真真填写感受。“我看了所有的问卷调查。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位观众写,这部剧让他看到‘质朴’二字,感受到生活中真的东西。“吴念真说,他之前并不了解北京观众,通过这种沟通,他发现两岸的观众在内心深处是有共通的情感的,“创作形式的沟通是一件非常长期的事情。就像我以前看大陆的小说、电影、文学,才对大陆慢慢有一个轮廓,逐渐清楚起来。“他希望,《台北上午零时》能让大陆观众看到台湾人曾经历过的时代,而这个时代,正是今天的大陆青年所深切感受的。
温暖残酷的青春记忆
吴念真的“人间条件“作了六部,却选择第三部《台北上午零时》赴大陆,“这一部跟我的感情最深厚,因为写的是我青春年少的故事。我就想分享那一段时光,把自己的生命经验作为一个最诚实的交换。“从1986年跟侯孝贤合作《恋恋风尘》,吴念真就开始把自己的青春写进剧本。这一次,儿子吴定谦在《台北上午零时》里饰演少年阿生,他觉得,这个角色就是父亲的投射,一个压抑、老实、有文采也有兄弟情义的乡村少年。身为台湾戏剧界的新锐导演和演员,吴定谦说,“戏剧的有趣在于,这一次我真的可以穿越时空,回到父亲年轻的时候,体会他生命的片段。进入那样的时空、用那样的眼睛看风景,听那时候的列车声音,有很多细微的嗅觉、听觉把你拉到那个时代的情怀。“
《台北上午零时》是一个温暖又残酷的青春故事。舞台大部分时间定格在“盛昌铁工厂“的街景上,三个异乡青年阿生、阿荣、阿嘉到工厂做学徒,都爱上隔壁面摊老板娘的外甥女阿玲。铁工厂的老板暴躁而粗俗,在一个醉酒的夜晚性侵犯了阿玲,所有人的命运由此被改变——阿荣为女孩复仇,砍死老板,进了监狱;被强暴而怀孕的阿玲嫁给工伤断了手指的阿嘉;阿生离开小镇,连续九年以阿玲的名义写信给阿荣,鼓励他等到出狱那一天。每一个人物在舞台上都是个性鲜活的,他们就像你某个熟悉的邻居或是朋友,他们的怯懦、大胆、粗鄙与悲痛,他们之间的爱情、兄弟情,都以朴素真实的细节呈现出台湾上世纪60年代的面貌。吴念真的台词充满生活的琐碎气息,那些从生活经验里滚打出来的句子,带着泥土的气息,哪怕命运是哀恸的,也带有人间的情感温度。
“1960年代中晚期,是台湾岛内移民的高潮,经济开始起飞,转变为工商经济,乡下年轻人到城市来找工作机会。我这一代人,初中毕业就跑到城市里来。“ 吴念真说,《台北上午零时》里的三个青年,就是他离开家乡到台北的年纪,“1967年的秋天,我15岁,到台北工作,那时候你在台北街头看到很多‘刺猬头’在扫地、在修理脚踏车,穿着旧的制服,肯定就是乡下到城里来的青年,那时候我们都是剃光头。“

剧中的“盛昌铁工厂“老板,是吴念真对当年那些冷酷暴躁的老板的写真。阿荣带着野蛮的青春冲动怒杀老板的段落,改变了整部剧的走向。吴念真说,这个情节来自于台北1970年代的真实案件,一位十六七岁的原住民少年到台北工作,进了一家洗衣店,那个年代的老板都会把雇员身份证扣起来,“少年受不了工作的辛苦,想走,但老板拒绝还身份证,所以他杀了老板,第一件事就是去找自己的身份证。“吴念真在报纸上看到少年的照片,长得很好看,轮廓清秀,典型的原住民模样。
少年杀人的案件引发台湾热议,也让吴念真回想起自己的青春时代,“那时候我们当学徒,在私人诊所包药、打扫卫生,在办公室当工友,大家都很苦。一切都是老板至上,骂我们像骂狗一样。吃饭的时候,老板一家人先吃,等你开始吃的时候,老板娘已经把好的菜都收走了。我们不但要做工,还要洗衣服买菜,当佣人,做最卑微的工作。“在冷酷的环境下,少年吴念真对台北没有感情,“杀人的心都有。“但他也感激那种苦难,让他懂得人必须要有信念,他抱持“念书就会有好前途“的想法,半工半读,像剧中的阿生那样念夜间部,当兵、考大学,一步步成为今天的自己。
人情温暖和生命质感
从15岁到台北打工当学徒算起,吴念真在台北生活了47年。但他始终对这个城市没有感情。“台北对我只是一个生活的城市,不是你生命刚刚形成的时候的地方。“吴念真说,这种“异乡变成故乡“的感受,也许对今天的大陆青年也一样,“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也有很多城市的外来人,故乡变成回不去的地方。“
《台北上午零时》是他“用情最深“的一部戏,“它写的是我的青春期,是最真实的。里面有那种最单纯的寄望,单纯的世界,人与人的相处那么重情义的,现在转头不容易找到,所以有一种眷念。“吴念真说。话剧中令人泪涌的片段,都来自这种眷念,真挚淳朴,明亮而遥远。面对自己所爱的女孩的表白,阿生顾及兄弟情义,以沉默拒绝。当她嫁了人,生了孩子,白了发,两人在数十年后相逢时,阿玲带着泪和责备回忆这段苦爱带来的折磨,阿生却依然用沉默面对岁月的残酷流逝。这个人物的性格像极了吴念真,也像极了杨德昌电影《一一》里吴念真饰演的NJ——个胆怯,真诚,重情义而又极为隐忍的男人。

残酷现实中带着浓浓的人情温暖和生命质感,让整个观众席被笑与泪的浪潮包裹
《台北上午零时》让人想起日本国民导演山田洋次的作品,同样的小人物、小故事,同样的残酷现实中带着浓浓的人情温暖和生命质感,让整个观众席被笑与泪的浪潮包裹。吴念真笔下的人情世故,仍然是他记忆里最深刻的在九份矿区度过的时光,“那些乡土记忆形成了我自己的情感体验,让我看到人物的命运。“朋友们聚在一起说台北时,吴念真总说,他跟台北没有感情,“我小时候生长的是人跟人那么靠近的世界,没有人叫谁先生小姐,都是叫阿伯、阿姐、阿公、姑姑,全村都是这样的。我端起碗可以从村里这一家吃到村尾那一家,一个小孩子就是大家的。那时候的村里人,都是互相帮忙、同情、关怀的。“他也还记得,那时候村里有位少年抢劫,当年的台湾,这是重罪,于是村里所有的妈妈们整天聚在一起商量,研究怎么把钱塞给监狱里的男孩。母亲们最后想出一个办法,把生鸡蛋戳个洞,一百块裹紧,塞进洞,再煮熟,做成卤蛋,给监狱的孩子送去。“那样的情感,在后来的世界,我再也没有看到。我看不到人跟人的情感,怎么可能对这个城市有眷念。“吴念真笑了笑,有点无奈,“我有时候跟年轻人讲我们那时候的感情,他们都在笑。那时候我们朋友中间只要谁说一句,‘我好想追谁’,身边人一定退的。现在的人一定是去争取。所以时代是在退步嘛。“
去年,吴念真作了“人间条件“第六部《未来的主人翁》,将当下年轻人面对家庭、爱情的心酸与惆怅,诠释得丝丝入扣。跟吴念真那一代人所受的苦不同,今天的年轻人面对的是新的职场困局,薪水不涨房价与物价却飞涨,他们要解决的是工作与情感中的琐碎问题,也要解决与上一辈的观念冲突。这部由儿子吴定谦主演的话剧,在台北连演37场,场场爆满。“我用这部戏讲90年出生的小孩子此刻的忧喜。“62岁的吴念真试图去理解这一代人,过去他们所拥有的淳朴梦想,在这个年代变成“每一个人都想当马云,想当郭台铭,但是不可能啊“。吴定谦每一场都会在舞台上演到泪崩,尤其是“爸,我会不会让你失望“这句台词,仿佛是他与父亲隔着舞台在对话。那些年轻的观众走出剧场,也总是找到吴念真,跟他说一声谢谢。
“这些小孩子说,谢谢导演,我们被理解,被安抚了。我看到他们喜欢,也很开心,他们这一辈真的很辛苦。“这个时刻,吴念真会想起16岁时的自己,每天收工之后,筋疲力尽窝在阴暗的阁楼里,望不到未来,内心苦闷困顿。那时唯一安抚他的,是黑塞的一本《彷徨少年时》,反反复复读了又读,“那时候我常想,为什么会有一个伯伯那么理解16岁小孩的寂寞心情?“现在,吴念真用“人间条件“系列舞台剧安抚着所有内心有过失意彷徨的人们,他的观众席上总是男女老少、士农工商聚聚一堂,被媒体形容为“国民戏剧“。吴念真说,写剧本时,他常回头看着书架上祖父的照片,在心里跟祖父说:“阿公,这个戏,如果你来看,也一定看得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