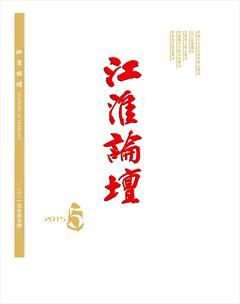论创作中移情的三种状态:投射、自居和感通
缪丽芳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合肥 230053)
在《歇斯底里症研究》的第四部分“歇斯底里症的心理分析”中,弗洛伊德第一次提及“移情”(transference),指的是治疗时,在治疗师和治疗者之间会产生一种在实际生活中不可能有的强烈的感情关系,这种关系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而且可能处于这两种感情中间的任何一点上,弗洛伊德把这种感情关系称为移情。而移情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具有更多的层次,在文艺心理学中,它包括了投射、自居和感通三个层面的含义,从而作品的风格和形态具有不同的意义和特征。
一、投射:我之影像附着于对象
根据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力比多是一种流动的能量,它并不固定地存在于个体的内部。自我犹如一个巨大的水库,力比多从那里流出,流向客体也可以从客体流回。于是,他将力比多区分为“自我力比多(ego-libido)”(又译:“自恋力比多)和“客体力比多”(object-libido)(又译:对象力比多)。这两方面存在着对立,一方面用得越多,另一方面则用得越少。移情正是力比多在主体与客体之间流动的一种状态,自恋力比多灌注到对象身上,对象于是便有了自我的特点。
这一概念在荣格那里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受到沃林格《抽象与移情》一书的影响,他认为移情是一种知觉过程,它通过情感的媒介而转化成一种基本的进入客体的心理内容。这种内容由于它与主体的密切关系而使客体同化于主体,使两者建立起某种联系,这样,不仅主体感觉到自己进入了客体,而且客体也完全感觉到自己被灌注了生命。[1]143荣格在他的分析心理学中称之为“外倾”(extroversion)。
人的意绪具有向外扩散的特性,周围的事物都或浓或淡地披戴人特定的情绪色调,这一过程称为“外射”或“投射”(projection),它指自恋力比多灌注到对象身上,对象成为自我特点的一种载体。按照英国美学家李斯托威尔在《近代美学史述评》中的说法,就是“我们对于周围世界的审美观照,其基本的特点是一种自发的外射作用。那就是说,它不仅只是主观的感受,而是把真正的心灵的感情投射到我们的眼睛所感知到的人物和事物中去。一句话,它不是‘Einempfiindung’(‘感受’)”,而是‘Einfuhlung’(‘移情’)”[2]。 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指出:“外射作用就是把我的知觉或情感外投到物的身上去,使它们变为在物的。”[3]30德国美学家罗伯特·费肖尔说:“这种把每一对象加以人化的作法,可以采取极其多样的来进行。它因对象的不同而不同,有的采取自然界无意识的生命,有的属于人类的范围,有的对象则又属于无生命的或有生命的自然。借助于经常提到的亲切的象征主义,人把自己投射到自然中去,艺术家或诗人把我们投射出去。”[4]黑格尔说过:“只有在人把他的心灵的定性纳入自然事物里,把他的意志贯彻到外在世界里的时候,自然事物才达到一种较大的单整性。因此,人把他的环境人化了,他显出那环境可以使他得到满足,对他不能保持任何独立自在的力量。”[5]宗白华也曾说:“一切美的光来自心灵的源泉:没有心灵的映射,是无所谓美的。 ”[6]
那么,投射的过程是否可以达到 “物我同一”?立普斯认为,“美感”不是源自外界事物,而是由主体自身内心的情感在客观事物中的投射而发生的。在“移情”的过程中,这种转移了的情感就是“美感”,移情就是主体自身的这种内在的情感投射转移到了客观对象那里。所以,对于立普斯来说,审美对象实际上是审美主体自身。“审美的欣赏并非对于一个对象的欣赏,而是对于一个自我的欣赏。它是一种位于人自己身上的直接的价值感觉。”[7]470审美享受是一种客观化的自我享受,是把自我移入到对象中去,在一个与自我不同的对象中玩味自我本身。“我移入到对象中去的东西,整个地来看就是生命,而生命就是力、内心活动、努力和成功。用一句话来说,生命就是活动,这种活动就是我于其中体验到某种力量损耗的东西,这也就是一种意志活动,它在不停地努力或追求。”[8]在立普斯那里,移情是主体对外物的生命灌注,这也意味着,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它是自恋力比多向外流动的结果,用科胡特的话来说,一切客体变为了自体——客体,成为了“我”之外延。在这种情形中似乎也有某种“物我同一”的错觉,因为立普斯说:“移情的作用就是这里所确定的一种事实:对象就是我自己,根据这一标志,我的这种自我就是对象;也就是说,自我和对象的对立消失了,或者说,并不曾存在。 ”[7]471并且移情 “就是要把自我移入自然事物之中,把自我移入宇宙人生之内,从而达到一种‘物我为一’的境界”[9]。然而对象的消失实际上是以自我的统摄与占领为前提的。当主体的灌注与对象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也会遭遇对象的阻抗,使“物我同一”无法实现。“以我观物,外物皆著我之色彩。”(王国维语)投射机制是将“我”之影像附着于对象之上,尽管有些强制的色彩,但也可能实现一种“和谐的融洽”。“移情的出现是以一种预备好的主观心态或对客体的坚信不疑为条件的。它把主观的内容灌注到客体中,以便在主体和客体间产生一种和谐的融洽,这样便产生了主体的同化。”[1]145主体的同化是以对象的某种同质性和对主体的接纳、顺服为基础的,对象身上闪烁或折射出主体之光。
在艺术创作中,作家与作品,作家与笔下的人物、景物乃至整个世界都存在着“移情”的关系。这在自传体小说的创作中尤为明显,具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几乎是将作者植入作品之中。劳拉·阿德莱尔称杜拉斯为“自传专家”,从《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到《情人》,再到《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都是在讲述自己的生活。“在岁月的流逝中,她一直想要通过写作重建自己的生活,想要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一部传记。”[10]我生命的历史并不存在。……我青年时代的某一小段历史,我过去在书中或多或少曾经写到过,总之,我是想说,从那段历史我也隐约看到了这件事,在这里,我要讲的正是这样一段往事,就是关于渡河的那段故事。”[11]作者执着地讲述自己,是将自己的力比多能量灌注到作品和笔下的人物中去,小说中的人物就是作者影像的载体,自传体小说的核心,不是别人,正是“我”。杜拉斯虽然常常写自己的母亲,但她把首要的地位从母亲那里偷偷地拿了过来:“她不是我作品的主要人物,也不是出现得最多的人物。不是,出现得最多的人物是我。”[12]杜拉斯不相信有除却自身之外的故事,“虚构从来都不存在”[13]。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比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他将自己的爱与痛贯注其间,“使我感到切肤之痛的、迫使我进行创作的、导致产生《少年维特之烦恼》的那种心情,毋宁是一些直接关系到个人的情况。我像鹈鹕一样,是用自己的心血把那部作品哺育出来的。其中大量的出自我自己胸中的东西:大量的情感和思想。”[14]这些“直接关系到个人的情况”有着非同寻常的体验强度,表述出来也更真实,打动人心,这种“切肤之痛”不是想象出来的情感,而是在心灵上的烙印。又如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他将超越了母子之情的那种爱和绝望化成每一个字,连成每一页纸,这是一种他难以排遣和消化的东西,“今晚我的爱人似少女,可她已衰老。她枕边的辫子,不再是金色,却已花白,奇异的冰冷。她像一位年轻少女,因为她的眉毛光滑美丽,她的脸颊尤其圆润,她的双目紧锁,她依然睡得那么楚楚动人,那么安详,那么平静。 ”[15]而《追忆似水年华》更是将作者毕生之体验融入作者所创造的世界之中。尽管小说家与评论者始终强调小说中的 “我”并非作者本人,但移情的作用是显而易见、不可否认的。自传体小说具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魅力,因为这个经验是作者独有的,是从仅有一次的生命中萃取的爱与痛,它的震撼力与感染力是所谓“冷静的写作”所无法比拟的,所以许多作家的成名作都是他的自传,在小说中那饱满到近乎溢出的激情也大都受到读者的宽容。
自传体小说中作者对书中主角的移情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作者对小说中其他人物的移情。在这种情况下,作者看似在写别人,实则在写自己,作者甚至可以分裂成多个人物同台演绎,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很好的例子。他笔下的人物往往都是演说家、哲学家。我们常常可以看到长达几页的充满哲思冥想的内心独白或辩论,让我们为人物雄辩的才华和深邃的思想震惊,并且不管男女,脸上似乎都映照着歇斯底里症患者的红晕或情绪低潮时期的苍白。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他的小说给人的冲击感,那就是“痉挛”。这个“痉挛”的世界其实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内心写照,而每一个在发表高谈阔论的人实际上都是他自己,人物的存在只是为了传达他的思想。《卡拉玛佐夫兄弟》中“宗教大法官”的一章,伊凡、阿辽沙不是别人,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他的人格分裂出多个无法统一的自我,移情到了小说中不同的人物身上。
即使是在被罗兰·巴特誉为“零度写作”典范的加缪作品中,依然能发现作者的投影。加缪的小说《局外人》塑造了一个对他人和世界无动于衷的“局外人”莫尔索。莫尔索被塑造成为一个孤独的人,一个“拒绝玩游戏”的人,他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与他人生活的非本真(unauthentic)世界形成对照。莫尔索说,我独自一人,而他们却成群结队。这种态度隔绝了自我与他人,似乎却成为了加缪推崇的生活方式。但事实上莫尔索只是一个游手好闲者,没有精神生活,没有爱情,没有友谊,对任何人没有兴趣,对任何事没有信念,可悲甚至卑贱,但作者却似乎殚精竭虑留住、加剧这种境遇以向自己证明它是一种自由选择,于是莫尔索的人间地狱被理解成了天堂。莫尔索的形象不是一个凭空的创造,作家的境遇并未与之截然分离,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青年加缪的健康状况不太好,他还不是一个知名作家,也不确定将来是否会成名,于是他决定选择看不到任何出路的孤独和平庸。一个感觉到注定默默无闻和庸庸碌碌的年轻人被迫以漠然来应对社会的漠然,它反映了一种知识分子的骄傲和绝望。《局外人》并没有把作者的样子全部抹去,相反,我们看到了作者鲜明的姿态,以及他对其自身生存状态的论证与辩驳。由此可知,无论是多么谨慎的作家,移情的投射机制都在不知不觉中潜入到他的创作过程之中,不管他自称如何冷静和客观。
二、自居:成为我所向往之对象的愿望
自居(identification)在精神分析学中有多种翻译,如认同、仿同作用等。在《精神分析导论讲演新篇》中,自居是这样被定义的:“这个过程的基础是所谓的 ‘仿同作用’(identification)——即是说,一个自我同化于另一个自我之中(即一个自我逐渐相似于另一个自我),于是第一个自我在某些方面摹仿第二个自我,并像后者那样处理事务,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将后者吸收到自身之中。仿同作用不再不恰当地被比作用别人的人格来补充自己的结合行为,它是一种很重要的依恋他人的形式。”[16]在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中,自居作用被描述为:“一个人试图按照另一个作为模特儿的人的样子来塑造他自己的自我。”[17]113自居作用的基础是使自己处在与他人同样地位的愿望和可能性,在俄狄浦斯情结早期,一个小男孩会表现出对他的父亲有一种特殊的兴趣,他希望长得像父亲一样,在各个方面都代替他的父亲。我们可以简单地说,他把他的父亲作为自己的典范,但由于父亲是他和母亲之间的障碍,于是,他以父亲自居的行为中就带上了敌意,变成了要代替父亲的愿望。所以,自居作用是一种矛盾的情绪,它既能表现为对某人的认可,但也同样容易转化为要排除某人的愿望。[17]112自居作用有三个特点:第一,自居作用是与一个对象情感联系的原初形式;第二,自居作用通过退行的形式变成了一种力比多对象联系的替代者,就好像通过内向投射与移情相反将自我归入对象;第三,自居作用可能会随着对其他不是性本能对象的人也具有的共同性质的某种新的感觉而产生,这种共同性质愈重要,这种局部的自居作用也愈成功。如果说外射作用是将自我力比多外投,使对象身上具有我的特征,对象成为了自我的显现,自居作用则是以自己作为那个对象的替身,通过内向投射将它投入自我,从而使我具有了对象的特征,我成为了对象。
“自居作用”与谷鲁斯提出的“内摹仿”说有相似之处,所谓内摹仿是审美主体在内心摹仿外界事物精神上或物质上的特点,外射机制是由主体及对象,而自居作用则是内投机制,由对象及主体。谷鲁斯举例说:“例如一个人看跑马,这时真正的模仿当然不能实现,他不愿意放弃座位,而且还有许多其他理由不能去跟着马跑,所以他只心领神会地模仿马的跑动,享受这种内模仿的快感。这就是一种最简单,最基本也最纯粹的审美欣赏了。”[18]
移情包括了“自居”的含义,这种“移情”的形式。确切地说是一种“反移情”,即对象克服、吸纳了主体,在杨朔的《荔枝蜜》结尾有这样一个比喻:“仿佛我也成为了一只蜜蜂……”这被称为是“拟物”的手法,事实上是作者以蜜蜂自居了。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举了乔治·桑的例子,在她的《印象和回忆》中说:“我有时逃开自我,俨然变成一棵植物,我觉得自己是草,是飞鸟,是树顶,是云,是流水,是天地相接的那一条水平线,觉得自己是这种颜色或是那种形体,瞬息万变,去来无碍。……总而言之,我所栖息的天地仿佛全是由我自己伸张出来的。”[3]35
自居作用中也存在“物我同一”的现象,它是由对象统摄主体而达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主体彻底交出了自我之主权,因为这个对象并不是偶然的,它其实是主体心中的秘密,是“我未曾成为却渴望成为之对象”,这涉及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自我、理想自我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但在拉康那里,自我是他者之镜聚合起来的光影,自我本身并不存在,所以自我之形成只是从他人那里脱胎而出,那么“理想自我”也只不过是对他者的模仿。在这种意义上来说,拉康所谓的“自恋”实际上只是“他恋”。勒内·基拉尔的 《双重束缚》似乎深化了拉康的这一思想,作家会全然发现自己被弗洛伊德定义为一种过分自恋的人物。他说道:我们必须让作家来检视弗洛伊德在《关于自恋:导言》(On Narcissism:An Introduction)中提出的全然自恋的形象,吮吸期的婴儿和野兽,在被喂饱之后,这些生物看起来是那么安祥自足,对他者是多么无动于衷,以至于它们在弗洛伊德心中唤起了一种乡愁,据他观察也在所有那些通过成熟和责任感已然抛弃掉部分自恋的人们心中唤起了同样的感情。
整个自恋理论是否可能不过是这种欲望的一个投影?在弗氏那里,自恋只存在于他者中间,并且是从来没有被同等对待的他者,他们总有或多或少的人性弱点,在《关于自恋:导言》中隐喻在意义上总是被弄得要么有一点神圣要么有一点兽性——女人、孩子、作家。[19]有必要注意弗洛伊德是通过对纳西瑟斯神话一种无批判的解读,通过对这个神话表面意思进行一种全然的、简单的重写,发现和命名了“自恋”。这可能再次隐藏着对竞争者激烈的而又被激烈否认的相互作用,即未被辨识的摹仿性欲望机制,正是这种机制似乎正好被镜子主题象征着,从而也就被掩饰了。
基拉尔认为,除非通过他人做介体,没有人会对自己产生欲望,摹仿性欲望是根源,而自恋只是表象。在恋父情结中,由于父亲这个“介体”进入婴儿与母亲的关系之中,婴儿才开始意识到自身,而产生对父亲的摹仿,从而将父亲视为竞争的对象。摹仿欲望发展到最极端的方式就是杀死竞争者。而这在拉康论自恋中也谈到过,那就是,当自恋发展到极端就是谋杀,将那个现实中个体所认为自己所应该成为的那个人杀死,以确保自身的独一无二性。那么,到底是对象塑造了我,还是我创造了对象?帕慕克在《黑书》中触摸到了一些隐秘的线索:“我周围的景观宛如几何图案,而且精准到丝丝入扣的地步,我望着自己置身其中,当下意识到原来‘他’是被我创造出来的,但是对于自己是如何办到的,我却只有一点模糊的概念。从某些线索中我可以看出,‘他’淬取自我个人的生活材料和经验。‘他’(我想要成为的人),取材自我童年时看的漫画中的英雄……”[20]自我是在生活经验中搜寻点滴的材料,在心中确立英雄人物,然后向其逼近,但是,每个人搜寻的材料大相径庭,想成为的对象也截然不同。那么他的先天接受机制以及最终确定的选择不是个体独有的吗?如果说人有摹仿欲望,那么他是在摹仿与自己先天禀赋相契合的人,除非他的意识遭受社会的各种同化机能而失去了辨别力。那么,这个作为模仿的对象,即模体的出现的确是激发了这个主体的自我意识,但必须是他一眼就能认出这个模体,因为模体的特质与他的自我具有某些同质性。这样看来,人不是简单地接近模体,而是在模体出现时他先产生了移情或自居的作用。力比多的投注是先于摹仿欲望产生的。由此,自恋是摹仿欲望的原因,而并不是相反,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自居即“自恋认同”(Narcissistic identification)。当人以他所爱恋的那个人自居时,就是以“恋他”(与自恋之“自己爱自己”的情形相对应,本文以“他恋”来指代“别人爱自己”的情形,以“恋他”来指代“自己爱别人”的情形)的形式来完成自恋,使“恋他”转化为自恋——“由自居作用引起而流入自我的力比多带来了自我的继发性自恋。 ”[17]178
在小说创作中,投射和自居是往往交织在一起的,比如,前文所述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被视为投射作用的典型,但同样不乏自居作用。例如少年维特的自杀,是歌德想做却未做之事,他通过维特得以实现,在维特的身上,寄予了歌德本身所没有却渴望拥有的浪漫主义的决绝和将激情进行到底的勇气。前面分析的《局外人》,也存在着自居作用,莫尔索是这么一个人的画像或者漫画,这个人就是加缪年轻时从来不是,但曾发誓要成为的那个人,因为他害怕成不了别的样子。有一个细节极具启示性,莫尔索得到一次到巴黎出差的机会,并且有可能在那儿得到一份永久性的工作,但他不感兴趣,这个细节只有一个目的,即证明莫尔索完全没有任何野心,为什么任何喜欢日光浴的小职员都应该想调到冬季气候阴沉的巴黎?对于处于低层的莫尔索来说,阳光明媚的阿尔及利亚提供了和首都巴黎同样的晋升的机会,当莫尔索带着敌意的冷淡拒绝到圣日耳曼-德-佩街区生活,我们能听到加缪自己在声明自己没有文学野心。但自居作用中成为“我所向往之对象”,并不仅仅只在光明、善良、勇气等正面的意义上展开。弗洛伊德曾经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杀人者等罪犯的迷恋,对其无休止的同情,实际上只是一种自居作用,一种变换了形式的自恋。
在投射与自居的交互作用中,作家与作品发展出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于是卡夫卡说:整个故事就是我;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我”的经验与未成之愿望交织成一片光与影,或明或显地在作品中闪烁。倘若作品成为了“我”之精髓,作者的自我爱恋便在不知不觉之中转移到了作品之上。作品不仅是作品,它是有生命气息的另一个“我”,经过酝酿与改造,它已经滤去了现实之我的尘滓,更添了理想之我的丰满,此时,它便像是那喀索斯水中之影,让人心醉神迷。作家爱着他的作品,作品正是他的生命、他的本身。但作品也并非完全是他本身,因为移情的我只是镜中之我,作家对作品之爱实在是一种“恋他”。
三、感通:共鸣或神入
移情的第三种状态为感通(empathy),它指的是主体与他人、世界的情绪发生共鸣,理解他人的立场和感受的能力。有一种观点认为,“移情是对他人所处境遇以及心理状态在认知或想象层面上的理解,这其中并不包含对他人情感的实际体验”[21]。
移情是否可以体验到他人的真实情绪?这一点极其困难。《庄子·秋水》篇有这样一段故事:“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倏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本来每个人都只能直接地体验他自己的生命,对于他人是否有同样知觉、意志时,则全凭自己的经验而推断出来,对于他人的理解高度依赖于自己的直接体验。因此,对他人的理解及与他人的情感的沟通和统一,依赖于自己是否具有同样的体验,只有当他人的体验是自己所经历过的,理解才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自我经验的丰富,是移情的前提。主体要理解对象,就必须以过去的经验积淀为基础,当某一刻被唤醒时,人就会不由自主地用以往的经验作为衡量现实的参照。 胡塞尔的学生斯坦因在研究移情问题上颇有建树,她提出:我的外在感知活动与感知内容都是“原本的(primordial/originarer)”,而移情活动与移情内容则是对他人体验的再现(representation),因而是“非原本的”。但移情虽然是一种非原本经验,但它却指示着一个陌生的 “原本经验”,要理解充分这一点,我们还需来看看斯坦因对移情现象具体而微的描述:“当它(比如说我在他人脸上看到的悲伤)突然在我面前出现,它是作为一个对象出现的。但是当我思考它所包含的意图时(试图弄明白他的情绪给予我的是什么),这些内容却把我拖入其中,而它也不再是一个对象了。现在,我不再朝向那内容,而转向那内容的对象。而这时我就成了这个内容的主体,处在原本主体(original subject)的位置上。只有当我成功地进行了澄清,这些内容才又成了我的对象。”[22]10由此,斯坦因强调“如果我体验到他人的情感,那么这一情感就给予了我两次。一次是我自己的原本性体验,一次是对原本陌生体验的非原本性移情体验”[22]34。 虽然我的移情体验是非原本的,但是,他者的原本体验渗入了这个非原本的体验中,因而,移情是他者的原本体验在我的非原本体验中的自然呈现。
所以,即使是在“物我合一”的状态,“我”仍然存在,我作为感受他人的尺度而存在,作为原本性体验的给予者而存在。狄德罗曾说:“一个人即使天生是大演员,也只有当他积累了长期的经验,火热的情欲已经熄灭,头脑变得冷静,灵魂具备充分自制力的时候,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 ”[23]295假如“她继续动用感情,继续扮演自己,偏爱自然的有限本能而不是艺术的无限揣摩工夫,”[23]336那么“她们易动感情的天性把她们禁锢在狭小的范围内,而她们从未超出这个范围。”[23]336“长期的经验”包括表演经验、创作经验,也包括个体对生命的体验,狄德罗所谓 “不动情感”主义,并不表示表演者的忘我,而是他的存在不能损害角色本身的特性,以过度的带有个体欲望的投射和自居进行表演与创作。狄尔泰认为艺术体验具有普通性、深拓性和超越性。诗人的创造性活动的必要条件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个体自身的体验,二是对他人体验的领悟,三是由自身推导和深化的他人体验。诗人自身的生命体验是其认识世界的基础,同时也是个体由自我走向他者心灵途经的起点,因此,艺术的美感才得以获得主体间的交流和沟通。我们看到米兰·昆德拉对自传体小说的极力反对事实上是出于相同的原因,“小说产生于个人的激情,但是,只有当割断了与生活相联的脐带,并开始探寻生活本身而不是自己的生活时,小说才能充分发展。”[24]福楼拜曾说:“艺术家应该让后人以为他没有生活过”,莫泊桑则说:“一个人的私生活与他的脸不属于公众。”赫尔曼·布洛赫在谈到他自己、穆齐尔和卡夫卡时说:“我们三个,没有一个人有什么真正的生平。”纳博科夫说:“我厌恶去打听那些伟大作家的珍贵生活,永远没有一个传记作者可以揭起我私生活的一角。”所以,米兰·昆德拉认为:“一个真正的小说家的特征:不喜欢谈自己。”[25]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暗示了作家们的某种恐惧,即无法书写自身以外的东西,由于这种恐惧,他们急于撇清自己与作品的内在联系。因为局限于自我言说和个体经验的写作是封闭和狭隘的,作家们渴望寻找创作的神秘性、不可言说性,即作者在作品中隐匿或消亡,如荣格 《心理学与文学》中所指出的“幻觉型创作”,它超越了作者本身,是积存在心里的集体无意识通过个体的释放。不谈论自己并不能抹去自身的独特烙印,自我之体验是通往理解他者的必经之途,谁能跳跃而另辟蹊径呢?
在丰富自身体验的前提下,如何对他人之体验领悟呢?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中也有empathy的重要概念,它被翻译成“神入”,“神入在本质上定义了我们的观察领域,它不只是一种有用的方式,透过它我们得以接近人类的内在生活——如果我们没有透过替代的内省(vicarious introspection)而感知的能力,那么人类的内在生活的意念本身,以及复杂心理状态的心理学想法都是无法想象的。那么什么是人类的内在生活,它就是我们本身与其他人所思与所感。”[26]巴赫金认为,对他人的内在世界的体验,即同情性理解,无论对“他者”还是“我”的存在的完善都起着重要作用。“他者”和“我”的外在阻隔,提供了审视自身内在体验的新的意义,并不会造成人与人之间内在世界的不可跨越和沟通,反而我在他人身外,他人的体验被我再次体验,完全不同于他本人的痛苦和我本人的痛苦,对他人痛苦的再次体验是一种全新的存在性现象,是在一个新的世界层次上,为一个新的存在领域再造整个内在的人。
在移情的三种状态中,前两者“投射”和“自居”都没有真正摆脱自己,作者的意志覆盖了人物所具有的独立性。作品的人物或是作者真实经历的代言者,或是内心梦想的代言者,很难成为独立发展的生命。只有作者克服了自己主宰和支配人物的愿望,进入移情中的第三种状态 “感通”,力图摆脱满足自我的欲望,伟大的文学作品才有产生的可能。此时,让他者成为他者,作者与人物共鸣,并设身处地,力求使自己所思所想与描写对象重叠、吻合,用他的耳朵听,用他的眼睛看,用他的脑子思考,与他的心灵相通。这种状态作者既是在场的,又是隐匿的,突破了自身经验的局限性、狭隘性,展开了他者世界的丰富性、广阔性,将自传式写作提升到对人类心灵的幽微洞察,更冷静、更客观,同时却又更真实,更深刻地将自身的体验融入到对人类共同体验的探索之中。这种写作的方式,既不神秘不可触摸,也不空洞而冰冷,只是将大海的水滴在其波涛或浪尖上闪现其光泽,只是将幽闭的心灵敞开,让世界的美景在其中一一呈现。
[1]常若松.人类心灵的神话[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2]李斯托威尔.近代美学史述评[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43.
[3]朱光潜.文艺心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30.
[4]惠尚学,陈进波.文艺心理学通论[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27-28.
[5]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36.
[6]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70.
[7]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8]沃林格.抽象与移情[M].王才勇,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0:4.
[9]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一卷)[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261.
[10]劳拉·阿德莱尔.杜拉斯传[M].袁筱一,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4-5.
[11]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M].王道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9.
[12]布洛-拉巴雷尔.杜拉斯传[M].徐和瑾,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232.
[13]杜拉斯.外面的世界[M].袁筱一,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4.
[14]艾克曼.歌德谈话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18.
[15]理查德·奥尔丁顿.劳伦斯传[M].黄勇民,俞宝发,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99.
[16]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讲演新篇[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60.
[17]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G].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18]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616.
[19]勒内·基拉尔.双重束缚[M].刘舒,陈明珠,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86.
[20]奥尔罕·帕慕克.黑书[M].李佳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25.
[21]霍夫曼.移情与道德发展:关爱和公正的内涵[M].杨韶刚,万明,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84.
[22]Edith Stein.On the problem of empathy [M].Washington D.C :ICS publications,1989.
[23]狄德罗.狄德罗论美文选[M].张冠尧,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24]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论》编委会.小说的艺术——小说创作论述[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65.
[25]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183.
[26]Kohut H.The Restoration of the self[M].New York: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Inc.1977: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