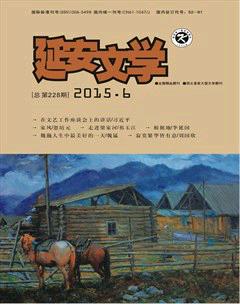黄金眼(外一篇)

刘云,陕西安康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十月》《飞天》《解放军文艺》《延河》《美文》等。出版诗集《劳动的歌者》,散文集《风吹过秦岭》《一生一个乡村》。曾获孙犁散文奖。
与植物之眼对视,往往是一件十分惊心的事。比如,我们久违了的大树,那种山野间有古气的大树,它们的气势不是来自于形态的高大或伟岸,是细小的枝叶,或斑驳身躯上那些不起眼的疤节、瘤生体,它们是树的眼睛。与树的眼睛对视,目不转睛的是树,而不是我们。从不同的年代、节令,看对视者,在树的眼里,我们可能是更小的树,所以山里人把古气的大树,称做大木,赋予其神气,不可侵犯。像我们称颂尊者为大人物。
在大人物的眼中,我们或许就是他眼中的草木。
白杨树不分南北,身躯上的月芽形眼睛,一律密集而有神。细分起来,南方的杨树之眼是丹凤眼,妩媚而有光润感。北方高原或平原地带的杨树的眼,应当称做虎眼,虎眼圆睁,雄性味十足。如果有机会让南方、北方的两种杨树见面,很容易从它们的眼形中分清籍自何方。它们当然是有自己的眼神的,一个反映北方,一个反映南方。其次是桦树,也以通灵见长,一身的心眼。这使它在树族中独有风姿。北方的白桦与南方高山地带的红桦,同样也有性别的差异:白桦是游牧部落的枪手或套马手,南方的红桦,多数做女儿态,形体、风中的姿态、晴空下如浴的恬静,都与南方的女儿有血统关系。白桦冷峻,红桦娇艳,它们都是树族中最光鲜的那个种族,与人近,与人情近,所以白桦、红桦承载了人类很多的情感。不仅因了它们漂亮的眼睛,几乎就是人的眼睛,有一种桦皮书,湮没于乡间深长的岁月之尘,可以当历史来读,用桦树制作的家什,离家最近,离男人女人的手最近。
最老的松树的油节,随着时间,往往长成眼睛的形状。那样的大眼睛,与神话中的生灵相关,沧桑而智慧。与其对视,看到松树内心空茫如大地的高度与宽度,看到我们小小的人在它的内心,只是一个小点,最多是松树脚下某个瘤生的植物的节芽。松树在树的民族之林,宛若帝国,或者是可以成为帝国的那类,它们往往通直,矗向云天,让白云的流苏挂满枝间。最成材的树就是松树,在人类生活的遗迹里,保存最久的是松树,它们以各样的造型存在于人类曾经或现世的时空中,依然泛着油光。琥珀生长在老气逼人的松树的垂荫下,为泥土掩没。琥珀以脂的形状存在,凝以时间的指纹,与虎有关,是虎的神与魂。我们不大可能想通一种来自树木本身的物质,最终成为石头,像矿那样被发现者雕琢,显示通灵。而我们不可能成为琥珀。也不可能成为化石。在考古意义上,你见过人的化石么?做它的一枚松针如何?那便已然是很高级的生命状态,因为面对老松之眼,人只能是文盲,失语者,连对话的机会都没有。
被赞颂最多的是松树。人因为赞颂而无法达到。这真是一个悖论。
几乎所有的植物,我们都不能了解,看似熟识的一部分,其实到了还不能通达它们的树性。比如对于植物来说,坚守、传承、浴火重生、杀伐与奉献,生机、蕴藏、老而弥坚,苦境、高拔、深扎、生生不息,这些相伴一生一世、一族一群的字眼,我们并不能深解。人创造这些激烈的词,依然是因为见识浅薄,无以体验,所有的词性只与人的寄托有关。比如果实,那些我们熟悉得如同家里一员的树们,它们用花朵与果实的丰丰歉歉暗示人世,懂得包忍,学会期待,拿起与放下几乎就是果树们最伟大的品质了。而我们人用欲望驯化结果子的树,事实上我们从未成功过。每到春天,那些花的眼睛、果蕾的眼睛,忽闪着时间和年成的暗示,我们从未读懂过,因此我们向上天祈祷,祈祷丰顺,和平,这几乎变成人类最自解的方案。秋天,果实与叶子落尽的树,以最简练的形态站立在天地间,它们读我们的村落,读我们欲望蓬勃的人,读大雪覆盖下时间的失忆期,与风一起拍打着手掌,用悲怆的歌声感叹人的不敏和麻木。树用蓬勃的努力暗示生活的丰满,或用秋冬的放弃告诉人们生活的高度,这些在我们有史之内还在思索、求解。而树从不用试错。试错是我们人的专利。
在植物之群面前,人选择退后,回到埋藏火种的屋檐下,用植物架屋建房,用植物制作梯子,以期达到某个高度;食用植物的种子,并努力复制新的种子,驯化果树并因此让它们与生活在一起;人用田土、水堰、池塘、篱笆,以及火种,与高大的植物分割,驯化植物的种子,把它们种得比自己矮小,人用庄稼这个词把自己紧裹,近而用村庄这样的状态,让自己与植物区分。看来,人总是喜欢活在自己的构思里。因此,我们知道人一直试图改变身边这个世界,从植物开始,将树木可能地驯化成果树,由野生变为家养。在果树的家族中,品种繁多,但几乎惊人一致的是,所有树上结出的果子,最后都变得与我们人类的口味相近,人能接受的味道,果子都能一一提供;那些不同于我们的味道,在早已然被排斥在家园之外,人用自己的心思,让树成为家常,无论被驯化千年万年,或是刚刚被人所接受,人用这个方式与树产生对话,甚或和解,取得战胜的快感。于是产生赞美,让自己在说的快感中成为树的主者。
事实是,树从未承认,不承认自己的驯化,自己的姿态最终与人无关。树承认天空,脚下的泥性,平地,陡地,山崖,或河岸,树承认这样的立地改变了自己。《病梅馆记》中的梅,是改变的梅吗?显然也远不是,它们仍然是梅,梅的心性和姿态。说人改变了梅,不如说梅自始如此,从来如此。是的,面对自然,也或整个大千世界,一切的变都尚无定论,仍然是我们的自话自说。我们所知晓的果实的味道,其实相当有限,我们用“发现”、“探索”这样的字眼解释无穷,这正好暴露我们的无知无依。一如那些我们不能接受的果实之味。
在蚂蚁眼中,一株小麦,可能就是它们世界的参天大树。
那么在蚂蚁眼中,我们“主宰”万物的人,也是参天大树吗?
我相当程度上怀疑我们人可能根本从未进入蚂蚁的法眼,它们匆匆忙碌着自己微小的生活,人与其何干?它们只关心天晴下雨。人甚至在它们的世界从未存在,它们只与细小的草木与伍,与细小的泥土与伍。
在老得无法用时间来形容的大树面前,人其实也是蚂蚁。我们常常用蝼蚁之类的凡小,来自嘲人类的无助。人显然不比果子更先生,也许人最初便是得到果子的蛊惑,比如众多神话中关于果子的神奇传说,人甘愿受到嘲弄、摆布,成为今天的模样。双脚双手,头颅,发肤,哪一样不是脱生于树木?人其实也只是时间之树上一枚果子而已,春生秋落,除此而外,人还能成为什么呢?!
面对森林,我们就是那些树脚下的叶子。曾经丰茂,经霜而萎,在树的脚下化为泥土。这样已经足够好了,至少我们在来年的春夏之际,可以攀上树上的枝头,再次成为叶子,从而看到更远的地方。
黄金眼,掌握在自然的手中,让树木、山崖、甚或大地,以眼睛的形态,观照这个时间视野中的一切。让树木接近人类,让人类与树木生活在一域,让树木以明白或暗示的形态读人,而让人永远不会读懂那些古老或年轻的树们举着的眼睛中流露的一切,让人在疯狂之后,面对它们陷入沉默。让人孤苦,看不透生生死死的一切。让人惶恐,永远有不能越过的地方。
包谷也叫玉米
包谷没来中国前,叫玉米。
玉米晓得与中国乡亲相处,是要入乡随俗的。它从名字变起,比如,在北地,或者叫玉茭,或者叫玉麦,包米,老玉米,玉蜀黍。到了南边,或叫包谷、珍珠米。南地也好,北地也好,玉米最难听的名儿怕是棒子了,包谷棒子。我家乡陕南山里,将土匪叫棒子,棒老二。叫棒子的玉米有些匪气了。
茭、麦、谷、黍、米都是中国地方品种,有着极分明的乡土劲,泥巴劲。比如关中专一长好麦子,玉米就成了玉麦。麦子养活秦人,秦人长成麦子色儿。临潼地下的兵马俑,一色麦子皮肤。陕南人与关中人站一起,都不吱声,看皮肤,一个水色,一个土色、麦子色,就分清了。关中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吃麦子。玉米来后,关中人用玉米面煮糊糊,还是就麦子主食,麦子做成面条、馍、饼,玉米粥稀如水,如汤,给麦子饭填空。
黄河边上长大的麦子,以及黄土高原长大的麦子,都带着北地尖利的劲道,很容易能化成血、化成筋、化成肉的。吃惯了北地的麦子,其它地方的麦都不是麦,甚至连粮食都算不上。比如我家乡汉江边上的麦子,简直算不上一料粮食,它们稀松平常,像家教不好的孩子,没有家传的优良,甚至是没有文化的。它们做成甚样的花色都不招人待见,面条?饼?馍?馒头?我看只能做浆糊,或者打成陕南人爱吃的酸菜拌汤,因为过人的酸菜,陕南的麦才略有些成色了。若是讲种麦,陕南不争不强,陕南有水稻,有包谷。
就好像麦子写成了秦地历史,玉米给历史勾勾边儿。秦人感谢麦子的养育之恩,顺带也给玉米一个地位,不拿玉米当外来户,用麦给玉米命名,玉麦,算是给它起了个中国名儿了。问题是,麦是包谷的名谱吗?
为什么把玉米叫成了棒子呢?玉米往中国地头一杵,个子高大,比所有的中国庄稼都高大,是外国洋马,大种马,像棵树,结的籽实,也比所有中国庄稼的籽实壮大,像纺棰,像棒子。另一个说法是,中国庄稼都秀气,东方气质,透着温良恭俭让,哪里像这外国来的玉米匪气?一个是小家碧玉,一个是粗汉子,棒子叫着贴切。
包谷长在中国的洼地里,它硬气,要长过洼地去。洼地的包谷因此在三分之二的时间里长个子,乡下人叫窜个子。窜个子的包谷当然不招农人待见,长个子的包谷有甚的用呢?就像一个壮娃儿,长到十六七岁了,还不承力,还不下地,大肚汉,一顿能造三个馍、三大碗干饭,可他就是不承力呀,不下地呀,这样的娃儿不招人待见,有甚的用呢!因此,只要留心,就能发现,中国乡亲不把包谷种在洼地里,他们总是把包谷种在高岗子上,种在坡地上,再不成,也是种在平地上,叫风够劲地吹,叫老太阳够劲地晒,叫夏日的暴雨够劲地淋,这样的包谷,结实,不倒伏。奇怪的就在这里,这样种着的包谷,于是身材日渐像了它的中国乡亲,壮矮,杆粗,叶片宽大,叶色发乌,腰里早早别上一株两株,甚或三株穗子,穗子已有了成熟的颜色,包谷的杆儿、叶子,还是青乌着。
在中国,乡亲们用自己的心思,磨难外来的玉米,比如把它矮化,用了奇怪的办法,让包谷合群,坐苗,在一片包谷地里,当它们还在儿童、少年阶段,就讲究齐齐地长,那些不小心窜高了个头的,会叫农人不怜惜地中耕锄了去:我好多年百思不得其解,为甚呢?那几株高个儿的包谷苗儿,看着出众,应当是结大包谷的嘛!可农人要将它们锄了去,就是这样,包谷地看着一抹儿平面就好,长得太高大了,必定锄去。这样的包谷,像早年间小娃儿上学,不蹲班,不留级,一二三,齐步走。这样的包谷,乡亲们不叫它格外结出三个四个穗子,一个就好了,大个头的,一个顶俩,万一结出三个穗子了,掰去一个,甚至两个,中国包谷,清一色独生子女。
好的包谷就是这样,中国式的矮个儿,却结实,腰里有劲儿。包谷关键腰里要有劲,腰是包谷最诱人的部位,好的腰,结出的穗子粗大,籽粒排列齐整,像齐整的牙,白包谷是白牙,黄包谷是黄牙,都好看。它们按大小排列,门牙,板牙,槽牙,不小心也长出几颗小虎牙,颇显淘气;不小心长出几颗花牙,便有些戾气哩,像乡下土气的有钱人,给自己安几颗金牙,好看而丑气。当然,这样的花牙,有时也可以想象成一个喜欢风骚的女子,她已然成婚多年,像是一块种熟透了的沥水的沙地,却还要做成早年年轻的样子,偏生长出些野草出来,喜欢招摇而羞涩的样子。乡下人看牲口,如牛的牙口,会说一句:是包谷牙么,好!在一口包谷牙和一口碎米牙之间,不管黄也好,白也好,长成包谷牙,才好。
一般来讲,中国乡下的白包谷,产量要比黄包谷高一些,白包谷以玉的颜色现身,颗粒粗大,在阳光下闪出瓷性之光。这样的包谷,非常工艺,常叫人疑心是用来观赏的,而不是下口的。白包谷浸在清清的水里,也如玉质那般,像珊瑚,轻易不敢触手去摸。而黄包谷,尽管也闪着金子般的光泽,更多的时候,叫人感觉着它只是铜,黄铜,红铜,这样的颜色凡常的生活中随处可见:老祖母睡房里银柜上的铜锁,老祖父用了若干年的铜烟锅,妗子的铜戒指,小娃儿的长命锁,传了几代人的铜油灯,还有什么呢,讲究的乡下人老宅子堂屋神龛上敬祖先的铜烛台。不晓得玉米初来中国的样子,是否就分白玉米、黄玉米的?我更相信是中国乡亲的改良,黄玉米揉进了中国的审美成色,黄的土地,黄的肤色,黄的龙脉,黄的尊贵,甚或金黄金黄的传家的心思。我喜欢雪白的大米与金黄的包谷珍儿一起合伙做成的金银饭,我图那雪白的陪衬下的金黄,温暖、朴实、高贵而典雅!
在乡下,白包谷用来熬粥,它可以熬出水米的风度,糯软而粘牙。在讲究的春天,或干热的夏天,这样糯而软的粥,可以就饼子吃,可以就春天的白菜苔儿吃,用来下火去躁。而黄包谷,我以为是中国乡下最家常的主食,干稀不论,随心思吃用,如果做干饭呢,那会有一个好名字,黄饭;如果煎饼子呢,叫黄叶子。吃过白包谷与黄包谷合伙蒸出的干饭,名字叫金银饭。我喝过白包谷米煮成的甜米酒,虽说没有糯米甜酒香软,喝在口里有沙粒的感觉,也算很好了,颇多野性的疯张。在乡下长长的岁月里,间或有一碗白包谷米酒吃吃,蛮兴致。
很长时间对包谷并无特别的感觉,以为它就是乡下的一种庄稼,粗放地生长,粗放地收获,好年成,它叫粗粮。或许更多成为牲口的精饲。遇上荒年了,也不能算正经地金贵,糊口救命而已。我对包谷有感觉,是上了年岁了,一个词经常涌进心头:青纱帐。包谷在中国平原地带,真如帐幔一般,遮住了平旷的大地,遮住了平原的天际,那里面故事万千,每一个都惊心动魄。在中国,包谷才有这样伟大的际遇,参与历史,制造历史,中国化的包谷,见证中国土地上的风风雨雨。什么样的中国大地上生发的卓绝故事,没有青纱帐的注脚呢!而长在中国北方也好、南方也好,山岗上的包谷,乡亲们喜欢用包谷林称呼。它当然是包谷林了,像中国乡下活过一个又一个年头的树木一样,包谷林子,像树木那样有气势。
我老家陕南乡下的高山地方,把成片种植的包谷地,叫包谷扒。乡亲们把长得古气的树林叫扒,老扒,黑老扒,大老扒。叫老扒的林子有神气,人不能久呆,久了会恍惚。老扒的气息在于叫你在迷糊的时段里,会见到众多你并不熟悉的祖先。他们穿越时空,从巨大的树干后面闪现,或直接幻化自一片浓密的枝叶,或就是一棵现出眉眼的老树,他们会以各样的神色与你见面,说一些古古的方言,文言,用奇怪的修辞、比喻,或隐喻,或吟唱般的语调,说出你弄不明白的事理。这些文字、语言、事理你都不明白,仿佛早已过时,但在黑老扒的奇遇,会从此影响你的一生。叫着包谷扒的长势汹涌的包谷地里会遇见祖先吗?没有人告诉我。那些矮壮的包谷杆、或乌黑宽大的叶片、或血红的包谷缨絮,都不能向我透露祖先的信息。
日子好过以后,我们要经常吃一些粗粮。粗粮,这个词,近些年特别打动人心。我记得在早吃长饭的年月,粮食就是粮食,像一家的精神支柱,永远那么贵重,在一个家里占据主题,哪怕是不小心在饭桌上掉落的一小粒米,都不能被忽略。经常做梦睡在粮食堆里,吃用不愁。在乡下秋天高远的晴空下,那些收去籽实的包谷秆儿,稻草把子,黄豆棵子里,都曾躲藏过童年饥饿的梦,甚或青春期那如新粮食一般清香的躁动。在不可示人的月光下,在秸秆堆里的那些怀想,在以后年代岁月里以酒曲的形式存活,在呼吸里渗透。怀念粗粮,我以为是遥远的心思的复活,在早年那真实的生命中的曲菌,其实一直未死去。
茭,麦,谷,黍,米,这些名姓,像乡亲们一样,时常想起,经常光顾我们惊慌一瞥的往事,显出温暖。也许是偏好,对包谷的记忆,永是高过麦子、大米,和其它那些光彩的粮食。在我吃过的粮食中,包谷占据了我生命成长中的主要时间与岁月,它让我对食物期待不高,只要有一碗包谷饭,哪管是稀的、稠的、干的,有盐的有油的,无盐无油的,都会让我的灵魂安妥。我在吃长饭的年月,包谷是疼爱我的父母、祖父祖母,是那些至今还来往的亲戚。他们真实,睁眼可见,无欲无求,给我安静的心情。
包谷也叫玉米。我只是更喜欢包谷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