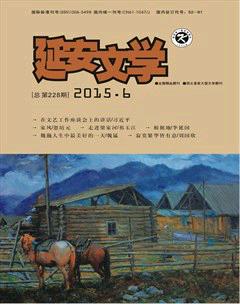借嘴
吴忠民,陕西商州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延安文学》《延河》《青海湖》等。
雨不大,却下得不停。四宝身边来过一只芦花鸡,把湿软的地面啄几下,瞅一眼在檐下躲雨的四宝,走了。来过一个披浅蓝碎花雨衣的人,进院子办完什么事,也走了。院子里边,出来过两个人,被四宝三言两语打发了。
被四宝打发掉的第一个人,搭眼看去涉世不深,眸子清亮。她劝四宝回去,说,管事的不在,有啥事我可以给你带话,蹲这儿不吱声不是办法。四宝不忍拂她好意说,女娃娃不要管我,忙你的去。这女娃娃瞪大眼睛怔了一下,扭身折回院子。时晌不大,院子里出来第二个人,温吞吞走到四宝身旁。他只拍到了四宝的肩,还未及开口,四宝就火了。四宝斜眼瞅了瞅来到他面前的那一双花花搭搭沾了泥的皮鞋,是不是也要劝我回去?你晓得我有什么事,你晓得我要找谁?肩头轻轻一筛,那只手跌落下去,四宝就苫眉搭眼望向了远方。四宝偏过脑袋啐了口唾沫星子,懒得搭理他们这些不顶用的闲人。
事实上,四宝已经感觉腿肚子涨疼,小腿杆子发怵。看到一个干部进了大门,四宝准备站起身的那一刻,已经有些力不从心——蹲的时间太长了。吃罢早饭四宝就早早赶到镇上,一直蹲在大门侧边屋檐下抽旱烟。正往大门里走的这个人,个子不高,一身洗旧的西装,鼻梁上架了副度数不低的厚眼镜。四宝打听过了,这人应该就是镇上信访办主任。
四宝跟那人进了信访室,张口央求青天大老爷给他作主。四宝说他们村上要在向阳川口修尾矿库,那大坝离住户太近,溃坝了会死人的,将来提炼矿渣时粉尘漫天,庄稼会呛死。还有,建这个大坝得征地得迁坟,四宝他们祖上的诸多坟墓,他爷爷,爷爷的爷爷,躺了百十年还得爬起来给人家腾地方。四宝抚一把胡子拉碴的嘴巴说,主任,我不知道你是啥级别啥番号,我就知道这事归你管。话毕,径自拽一把椅子安在主任办公室当门口,一屁股坐下:你看着办吧,活人没法生活,死人不得安生,如今这世道,给谁生下亲孙子了还是咋的?
信访办主任自打第一眼看到四宝,就看出面前这个老头是一块滚刀肉。主任一直微微笑着听四宝讲这件事的根根筋筋。听完。主任问,真有这事?四宝扯起脖子反问主任,风不吹树不摇,咋没这事?主任不愠不火劝四宝先回家,他说四宝反映的情况他知道了,回头认真过问,真像四宝说的那样,镇上一定出面解决。主任这样的态度和四宝的心思对上了铆。面对主任体恤,四宝觉得还端在手里的烟锅子横在胸前,有点做作,把长长的烟杆子朝上举了一些,噙到嘴里。噙嘴里又似觉不妥,复又端在手中。最后还是瞄了一个地方,把烟锅子放到身旁的桌上,再把主任那堆文件轻轻往里推了推。主任的话虽说得好听,四宝哪能就这样给糊弄过去。放妥烟锅,四宝扭身向主任做了必要的补充。四宝说,无利不起早哇,把外地的矿渣大老远运到我们村,他们是在借别人的大腿搓绳子,没有村干部支持,修尾矿坝的几个能人成不起事情。主任说,都知道,知道。掰开饽饽说到馅,不还是那些事。甭黏糊了,话头多了,你我心里都瞀乱,回吧。四宝把两条腿叉在当门口,回?不能就这样回去。三句好话当钱使,他们空口白牙的话他听得多了。信访办主任弯下腰,拍了拍四宝肩膀,老哥哥,回吧。又拍了拍自己腔子,都在这儿给你记着呢,一定给你个说法。四宝觉得这下差不多了,他相信这个“一定”。四宝起身,上一眼下一眼瞧着主任,又偏转脑袋细细打量了一番镇政府院落。一缕阳光费劲地顶出厚厚的云层,渐渐渲染了周边的颜色。四宝长吁一口气,心下说,蹦跶吧,看你们还张狂不。
四宝没说瞎话,村上确实已经着手和村民谈判了。向阳川口有耕地的,有祖坟的,有核桃树的,好多人架不住村干部劝说,有的顶不住声色俱厉的压力,更有不少人担心失去享受已久的低保,悄悄和村上签了协议。村委会找过四宝。那天,村长他们告诉四宝可能要迁四宝家的祖坟,被四宝堵在家门外。四宝说,如果是国家重点项目,或者比如说修学校,办敬老院,建土产加工厂,搞一两件村里人都能受益的事,我支持。少数人发财,祸害了庄稼空气,没门。村长隐藏了皮肉下的内容,腆着笑呵呵的一张茄子脸说,你个老叔,还是这么犟。
四宝从镇政府回来,走路一冲一冲,两只八字脚踏得咚咚有声,口里噙着的旱烟锅子,老掉牙的火车头般,沿路释放出随走随散的烟雾。村口,四宝看见了善伯。正是午饭后的空闲,善伯坐在楼门洞那里的青石板上,和五叔下棋。五叔炮二平五,欲借炮坐当头的威力,掏吃善伯的象。善伯停下抠脚趾缝的手,他嗅到了脚臭,也嗅到了面前二指宽界河畔的危险。善伯对五叔的意图有所觉察,却一时找不下破解的法子。四宝站在身后,哧哧笑了:只吃碗里,不盯锅里,哪有这样下棋的。皇上着急,哪知太监更急。跳马!四宝一声断喝。五叔一惊,眼珠子盯在棋盘上挪不开,却点了点头,腾出手,拿食指和中指作剪刀状,把马推到了二杆上。一招正当其时的卧槽马,反转乾坤,输赢已成定势。厮杀结束,四宝给烟锅里摁满了金黄烟丝,朝下棋的二人递了上去。
四宝年纪不小,在村里的辈分却低得可怜,孝敬长辈子抽口烟是很顺茬的事。善伯笑嘻嘻调侃五叔的臭棋,二人轮换吃了几锅烟,四宝见缝插针问善伯,这几天你老人家就没听到村上有啥动静?善伯拉长声音悠悠地“啊”了几下,并没有下文。叹息一声,人矮下去了一截。磕巴磕巴烟锅子,善伯把棋子往盒里盛,准备散摊。四宝没挪窝,还想再聊聊。善伯和五叔急着起身。他们说比不得四宝,四宝的儿女在南方办企业发了家,如今过的是神仙日子。他们俩个却要靠吃低保接济,眼前的农活不干不行,瞎子背跛子往前混呗。话毕,善伯拿手掌心旋着抹一把烟嘴,递还与四宝。四宝心下不乐意,没接。转而追问善伯:村上要修尾矿坝,就由着他们?五叔接话茬说,那还能咋地。四宝问,有钱人搞矿粉加工,在咱村里排毒气搅浑水,咱老了,村里的后生也都不过日子了?善伯没作声。五叔一拳头砸进自己的巴掌说:对,祸害乡亲的事,伤天害理。四宝见五叔有了响应,垮下脸告诉他们:我今儿把村上告下了。这话一出口,善伯像被烟头的明火烫到了舌尖,牙痛般“咝”了一下,猝然有了警惕。善伯觑五叔一眼,五叔已被骇得变了脸色。就像弹出了一枚旋转的游戏币,四宝把捂着的手挪开,竟然出现了亮光闪闪的国徽麦穗图案。短暂的沉寂过后,善伯讪讪笑了,胡乱指了一指村子北头说,我俩相跟着去地里看看庄稼,趁墒补补苗。五叔见状也赶忙起身应声,栽晚了缓不过劲哩。四宝看清了,用人的时候掉链子,关键时刻弯了脊梁骨。村上的事,他们说一句硬气话也不敢,就更别指望他们站在自己这边了。四宝杵那儿看着他俩背影走出去老远。四宝不把村上的决策当回事,在向阳川口有地有树有坟的其他人家,敢这般大胆的,却没有几个人。
转天晚上,百忍哥来四宝家借锯子。油锯拧了马达呜呜响,伐树利落。
百忍的意思是,正二月里他就想伐屋后那几颗杨树,一直腾不开手脚。那几颗大白杨长了二十多年,比屋顶高出了不少,落叶沤得屋瓦都漏哩。趁这几天春闲,伐了它。听得百忍的话,四宝歪噙着烟杆子,话里拌着唾液声和烟屎味,拿半边嘴对百忍说,锯子借给老哥用,随便扛走。你伐了屋后的杨树,是不是也要伐川口那几颗核桃树,给人家腾地方?我知道,村上找你好几回了。百忍家有七八棵核桃树,全都长在村上要建坝的大田里。这些树确实很让他闹心。凳子还没坐热的百忍对四宝的话有所不满,“呼”地站了起来,他不认同四宝对他的判断:别说你四宝是个人精,这回你却没摸准我的心思,屋后的杨树,我真要伐。修尾矿坝占地,我那些核桃树伐不伐,还看你的主意正不正,你敢扛着,我就随你。四宝仰脸说,百忍老哥,人穷志不短,咱不能和村干部一般模样,让老板们一个个牵着鼻子走。晓得不,他们修尾矿坝是私下里搞的,上不了桌面子。一来上边没批项目,二来没开社员大会,再说,下游住了那么多人家,能有多少人答应他们?我铁了心要跟他们干到底。百忍说,你不怕,那我就不怕。百忍把油锯扛上肩,很有内容地笑了说,总算探到了你的口风。四宝没接话茬,拿大拇指摁灭了烟锅,嘱咐百忍帮他办一件重要的事。他让百忍去凤镇赶场子时,顺便捎买几包老鼠药。四宝说,敢强征强建,我死给他们看。
百忍早年死了父母,一生没成起家,打小爱唱陕南民歌。年轻时的百忍,唱歌习惯于右手托腮,向左歪了脑袋,让人怀疑他总是在牙疼。由于他一副与众不同的歌手范儿,不辨音色,老远就能从吃饭的人堆里,认出那是百忍在唱歌。百忍唱采茶歌,唱十爱姐,唱摘黄瓜,很多歌是有点黄的,曲调甜甜,歌词酸酸,听着催人亢奋,让人脸烧。大人们不许未出阁的女孩子听百忍唱歌。年轻小媳妇,却把脸藏在硕大的老碗后,人藏在门后,支起耳朵偷偷地听。他们那里人人都能哼唱一两段民歌,可是天生一副好嗓子,能入辙入韵唱出全本歌子的,十里八乡却只百忍一人。如此说来,百忍算是土生土长的一名艺人,也可以归为乡土文化人了。文化人有文化人的糙毛病。百忍就有爱说嗑的毛病,谁有不对的地方,说得说不得,他都说。谁家有好事丑事,传得传不得,他都传。眼看百忍七十岁了,日了过得买葱还想饶头蒜。村里照顾他伶仃一人,村长倡议全村集资给他打造了墓坑,箍了墓前财神爷寿星佬坐镇的漂亮门面,给他办了低保。尽管村上百般照顾,可百忍还是缺钱花,时常去凤镇赶场子,靠唱歌,挣一点儿人家打赏的零花钱。有时也上山挖葛藤根当药卖,或帮人砌石修堤,搞点零碎银钱贴补家用。苦于没有婆娘顾惜热冷,百忍身体不好,挣两个钱吧,老鼠给猫攒家当,进一次医院就花成了光腚。百忍知道,要不是村上帮衬他,给他垫了好几次医药费,他百忍活不到今天。
油锯的金属光亮在月地里一闪,百忍身影隐没在门前树荫里。四宝心下对自己说,百忍老哥哥,对不住了。今晚,百忍借四宝的一台油锯来伐树,四宝却要借百忍的一张嘴,打得窗子叫门听。四宝得在棋盘上安置一枚安如磐石的重要棋子——卧槽马,他需要通过百忍的嘴,让村长晓得,当然也应该让所有人晓得:胆敢再逼着迁坟建坝,他四宝会在关键时刻,恰到好处的拿老命来拼一拼的。
经历了夏收,金灿灿的麦浪刚褪尽,不几天功夫长起满地绿盈盈的豆苗,风吹来,松蓬蓬的豆叶婆娑轻摇,一波赶一波地绿浪涌向远方,豆杆上还未结出嫩荚,村庄的旮旮旯旯却好像早已弥漫起了好闻的豆香。仔细嗅来,村子中间百忍家的两间土坯房里,却飘出了焦苦、酸沤的中药气味。悖运如树,会长出许多枝叶,无端地伸进寡味的日子。不知是劳作苦累还是心理负担太重,多年的老病又一次缠上了百忍。
这天后晌,四宝找百忍,问起托他买老鼠药的事。百忍比上次更显得不好意思,说哎呀呀又忘记买了。四宝提醒他,应人事小,误人事大。镇上的信访办主任,好像并没把四宝反映的事当个事,村上还照样在一逼二逼要征地,要伐树,要迁坟。听说风声又紧了,不少人自己动手把树伐了。四宝只敢轻轻催一催买老鼠药的事。至于他让百忍带的话,传到了哪一层,哪些范围,他不能多问。问急了,依百忍的性子,或许他会自作主张,闹出没法收拾的乱子来。四宝就像在使一台老掉牙的播放机,声大点儿吧,怕震坏了机子,声音控制小点儿吧,又怕传不到该听的人的耳朵。上了年纪的百忍又不是一个特别能控制得住自己的人,四宝担心他的话要是说过了头,村上那些人肯定会找他百忍的茬,那样的重压,恐怕百忍一个人应承不下。百忍叫四宝放心,住院之前一定把那能毒死四宝的药给买回来。
去凤镇赶场子唱歌的时候,百忍一直惦记着四宝交待的事。有那么两三次,百忍踏进日杂商店,眼盯着老鼠药,自己却像是在做贼。人家问他要买什么,他心虚,问一问绿瓶太白酒卖几块钱,问一问还有没有新上市的甘蓝菜籽,悄悄顺门边溜走了。还有那么一次,百忍把钱递给了卖老鼠药那胖胖的小伙子,却又把钱讨要了回来。依百忍几十年走南闯北的经验,他估计四宝干不倒村长和那几个老板。百忍有些怕,要是四宝想不开,真的服了药,他百忍可就是罪人了。哪有看着别人想死,自己赶忙上去递刀的。
判定四宝确实铁了心要和村上抗争,百忍悄没声地干了一件朗然率性的事。百忍自有主张。
百忍与村上的正面交锋打了个平手。那天下午,村长找百忍到村办公室谈话,村长他们和百忍一起喝了些茶水,把百忍的嘴巴赞扬了一番,然后他们关心了一下他的病,关心了一下他最近的生活。话锋一转,村长问百忍,实话说,村上对你怎么样。百忍不解地回答,挺好。村长说,那么,村里最近要修尾矿坝,你得帮着做些工作,给大伙多做解释。村长复说,你的嘴巴不是挺能说能唱的嘛,应该不是多大个事吧。百忍一时没言语,半晌扔出一句:我的嘴,良心管着,我自个做不了主。百忍歌子唱得好,在处理村里大事上却还显嫩,不晓得分毫深浅。这是什么话。村长听罢,很严厉地批评了他。接着文书他们几个哼哼唧唧夹枪带棒轮番把百忍数落了一通。村上批评百忍,没有像对四宝那么客气。村长斥责他的大意是这样的,老得快进土的人了,管不住自己一张臭嘴,人家那尾矿坝项目,是上头批了的,是上头领导包抓的重点项目。目前修坝只是头一炮,听响声还在后头呢。你百忍以为自己是谁,啥时见过茶盅大过茶壶。谣言惑众,胳膊能扭过大腿?说什么修坝是私人开发,说什么村干部与老板之间不干净,说什么敢逼着迁坟会闹出人命,惹急了四宝会喝老鼠药一死了之。都是些什么屁话,小心风大删了舌头。百忍被逼急了,说,村长你不要拿大帽子来压我,既然是上头批下来的项目,拿文件我看看。半缸子茶水被村长重重蹲在桌上,溅出来不少。村长说,看文件你还没到那一格。百忍手托右腮,眼里布满荫翳,问,非修不可?村长说,没有退路。问,当真硬上?村长说,软硬不必你操心,没有我弄不成的事。百忍声音不大,说,要硬来?咱走着瞧。村长和坐桌旁的人哄然笑了。村长的掌心很爱惜地轻捋了一下头发说,还真没看出,病怏怏的百忍有这两下子。有能耐,自己的事自己想办法,所有事情自己办。真是长本事了,村上还管不了你。
村长的话,准确地戳中了百忍的命门。村上动不动就拿低保来敲打,针针不离穴。病了得医,住院得花钱,看完病肯定又得欠下老大一笔窟窿债。医疗保险解决不了全部问题,村上以后若不帮他筹钱看病,不给他争取困难补助,他的日子如何过得下去。这么一说,百忍硬生生拒绝了村上的要求,算是小胜,可今后村上肯定不再支持他,甚至刁难他,却让百忍处在败下阵来的地位。看似平手的交锋,其实明摆着以百忍的个人失败而告终。莫非村上照顾了他,他就得把自己卖了不成。百忍似乎被他们剜心戳肺,心尖尖疼得打颤,比小时候死了爹妈要难受得多。摔了村办公室门,百忍厉声吼道,老子不信那邪,嘴巴还不由自己了。
今年有老天爷照应,村子地势朝阳,遍野都是熟透了的黄橙橙的豆苗。饱晒了一上午的豆杆梆梆脆,四宝“咔嚓”一声就把豆杆拽在了手里,往地上归拢的堆里扔去,豆粒在干豆荚里摇得叮铃作响。路过善伯家的时候,四宝被站在门口的善伯叫住了。善伯在门前等了好一会子了。善伯是这么说的:来来来,宝娃子,喝点啤酒下下火。四宝推让了一番,不好拂了长辈脸面,放下肩上的一大捆豆杆,随善伯进了屋子。却不料,堂屋小桌旁,村长摇动蒲扇,海怀敞腔,扇得正欢。四宝止了步。拧身走,不好。坐下与半只眼睛也见不得的人喝酒,也不好。愣怔间,村长热见着让四宝快坐。村长笑让四宝说,老叔,小半年没在一块坐坐了,门杯四个,喝起,爷俩再划两拳。四宝没吭气,目光从善伯脸上滑过,陷落在门后。四宝从铁丝上扯下一条毛巾,在凉水盆里涮了,拧干,绽开,擦脸。擦完脸擦胳膊。忙活一阵子,觉得冷落够了,坐在旁边凳子上。四杯啤酒进肚,四宝起身便要走。善伯扯起四宝袖子,拽进了小房。善伯说,今天,你不看佛面,却要看僧面。今儿你从我门里出去,伯的脸面在哪里,以后咋在村里做人?他们这里喝酒,一种是用大杯匀了闷喝,谁不借谁的,喝完为止。一种是猜拳行令,搞点热闹气氛。气氛一搞出来,像村长这样有身份的人物在谁家喝酒,满村人都知道了,裤腰粗的脸面也就有了。这第二种喝法,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拉拉手,划划拳,就成了不大对路的两个人之间的粘合剂,豪情涨起,几条河里的水就都汇到一起来了。今天他们是第二种喝法。照这架式看,今天四宝必须赢了村长,他计划在预定的几招内,定要给村长难堪。几个回合下来,却不料四宝的手指头不争气,村长赢了。四宝连喝了好几杯,心下忿忿说,你村长这点手段算什么,到时候叫你见见真章。咱没别的,爹娘给的身板,是由得了自己的。这回,四宝没有再理会善伯的劝阻,一甩袖到了屋檐下。
四宝把黄豆杆扛上肩,村长从屋里赶出来,绕到四宝面前。村长翘起大拇指,越过肩头指向身后,对四宝说,叔啊,村里不修大坝了。这个决定呢,是上头的意思。眼下咱大河里的水成了省城人的吃水源头,谁也不敢往那枪口上撞,环境保护,晓得不。这消息来得突兀,是谁也未曾料想到的。四宝问,不修坝了,这事全村人都知道?村长说过几天开组长会就通知下去,到时候全村都知道了。凭啥相信你的话,四宝问。善伯在旁边一片好心地悄声嗔怪四宝,真是的,你这孩子,要是还修大坝,我能好意思请村长喝酒?是镇上干部昨天亲自讲的。四宝明白了,村长今天是在给四宝开小灶,叫他不要领头再跑再闹了。四宝不领这个情,他提高了调门说,不修了好啊,修一个能让大伙致富的厂子才显你娃的能耐。这话,让村长很不好转弯。村长对四宝讲,当干部的,也难。以前老侄有对不住你的地方,多多担待。四宝撂下脸子谁也没搭理。站在场院塄坎边的村长,手里的扇子摇得一下慢过一下。
他们那里午饭时间在三四点钟,正是一天里阳光最盛的时候。知了抓住秋的尾巴,隐蔽在浓密的树叶里吼命般嘶叫,炸开荚的黄豆杆,蓬松松铺满场圃。有人端起碗扒拉几下,趁着焦火的日头,拿木叉翻挑快晒干的豆杆。有人额上裹了包头,抡起连枷,进一步身一趋,一茬压一茬打豆荚,吱扭吱扭,噼啪有声。晌午饭快结束的时候,细心的人发现,百忍没有像以往那样,大拇指扣碗沿,四个指头托碗底,晃着身子,摇嗑着嘴皮,来大碾盘子边上吃饭。百忍莫不是病倒了?推门一看,百忍已经倒在了自家炕头。百忍喝药了。给四宝买回的老鼠药,百忍尝了鲜。
只有轻生的人喝了毒药,他们那里才叫做:谁谁喝药了。
四宝挑起大大一筷子面条,油汪汪地,挂着辣椒葱花大蒜屑,面条没填进嘴里,跑进院里的小伙子告诉他百忍喝药了。四宝愣怔了一下,哧溜溜,缠绕在筷子上的面条跌落碗里。四宝拿筷子点一下报信的人,谁,喝药了?小伙子把刚才的话又说了一遍。四宝把筷子啪地一扣,走,喊人。消息传开,村邻乡亲围了一大堆,村上干部们也来了。有人说赶快熬点绿豆汤解毒,有人说按这情况一定要喝肥皂水洗胃,急性子的催腰里别手机的人快打急救电话。不知哪里冒出了一句提醒,沸沸扬扬的场面冷了下来:村上已经来人了,最好看看村长的意思。这下,多数人醒悟开来。送医院去,百忍住院的花销谁来出,目下敢不敢送医院,这确实是件不好说的事情。众人眼睛齐唰唰聚向村长的脸。村长痛恨这些不识时务的东西,沉了脸子嚷,啥时辰了还敢耽搁,救活百忍,就是村上目前最大的事。
四宝一把抓住担架,稳稳抬起百忍。他真的很担心,干了傻事的百忍哥,能不能挺过这一关。四宝埋怨躺在担架里瘪塌塌的百忍,老哥哥,糊涂呀,谁让你直接和他们干上架的。
百忍老哥哥,能说善辨的嘴,半张着僵在那里,肚皮一歙一鼓。他可能没有听到四宝的话。
责任编辑:高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