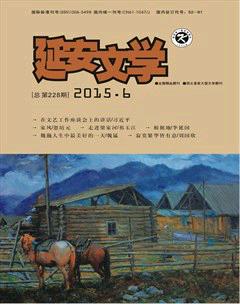瓜滚在园里
王卫民,陕西商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发表于《延河》《西北军事文学》《延安文学》等。出版小说集《风雪阿尔泰》。
……噢……我知道不容易,可村上的断头路就指望你这些瓜说事哩,政府要来调研,你不是我哥,你是我爷,求爷爷再等几天出园……
村长这是第一百次电话给他了。
村长是从县城给他打的,而他就在瓜棚里。
瓜棚又叫做庵子,是金凤山一带庄稼人看秋的窝棚,木椽架子蓬上茅草,外边四周刨些水沟,就算成了,纳凉歇脚夜里看贼。有这个庵子,秋田苞米和红薯就能放心地疯长。“噼哧”一声,绵绵的苞米裂开身,籽儿从苞衣中露出来,把脸笑成金子似的。小小茅草庵,白日遮荫,夜里隔寒,拿来钢丝床,放平了人躺上去,听田野蝉鸣,看蝴蝶飞舞,偶尔一只草蚂蚱图凉钻进来,“吱—吱—”,那份情趣要多惬意有多惬意。
此时的宫元没有那份心情。
他和村长是本家平辈,骂不成娘。挂了电话,跨出庵子,仰头太阳有些刺眼。他眯着眼,蹦起来恶狠骂了一句,“宫常章,我日你婆娘。”
骂是骂了,可他仍不解愤懑,提起脚下一窝香瓜,连瓜带蔓齐根儿拔断,气极败坏地扔到地坎下。瓜被摔得粉碎,瓜汁四溅,瓜气又迅速弥漫到瓜田。
宫元很心疼,又后悔,一头倒在庵子里竟呜呜地哭起了起来。
今年雨水少,宫元的这片香瓜田从长苗时,靠他一截儿一截刨出毛水渠,把蝎子沟那股山溪引到地里。地不亏人,今年遇上了好价钱,但必须是宫元把瓜送到大路边上。尽管村上的断头路有三四里连人力车也去不了,可山坳坳人或背或挑还是能送到断头路的那头。搭庵子过去住是防贼,现在贼不在庄稼地里瞅,嫌脚重。就剩下防野猪,野猪糟害人那才叫狠,金凤山一带的庄户人家差不多都领教过。
正在他喜上眉梢的时候,村长来找他,要他别急着卸瓜出园。
他说,瓜熟自落,人挡不住。
村长说瓜滚在园里。
“那是大半年的血汗啊,你忍心吗?”宫元几乎在吼问村长。
宫常章面对宫元的吼问和不恭并没有急燥,宫村长用手指了指宫村上的炊烟,慢条斯理地说,断头路这回再不修,宫村的烟火会一年少出一年,有一天就断烟绝户了。
宫元说几十亩的瓜园能留住烟火?
能,能留住。村长回答着宫元的同时,又似乎在自语着,狗日的,看今次还怎么说。
宫元知道这是在骂谁,更知道为这断头路,村长到政府求人时只差叫爷。更要命的是宫村这条路能不能修好,事关宫村在县级地图上还能不能有名字的大事。
话还得从四年前说起。
那一年,宫村的通村路眼看就到头了,一夜之间机械撤走,连最后两斗子浆灰也被工人在地上堆成一疙瘩。宫常章去了县上才得知,政府在口镇建了几千套楼房没人住,才决定把宫村也纳入移民对象,过城里人的日子。宫村将不存在,修通村路何用。
宫村长觉得突然,宫村人却说是村长把宫村人给卖了。再后来只有不到十户去口镇住楼了,没一年又回村住。宫村人说,几百年不通路的宫村人没饿死,政府不能把宫村人一个一个背上楼,路就断着。镇上、县上把宫村低保给取消了,民政局救济减了,宫村人就是不去。后来省上某个领导视察口镇移民点,批评说是堵了河道。
政府忘了宫村的断头路。宫村长找政府,他说,村民害急症下不了山,瓜熟出不了园,猪养肥了变不成钱,政府就决定来宫村调研。
宫元这才记起春天村长为啥劝他种瓜哩,还说上边有补贴,原来他自己掏腰包,蓄谋已久啊。
手机响了,是瓜贩子打来的,叫他明天无论如何也要把瓜送去,差一天就要少价,差两天要退订单。宫元满口答应,因为按日期已推后三天了。
宫元卸一笼香瓜带在摩托上,他要回村逐家逐户请人明天帮他卸园子,再送到路上,少不了给人家留两三个瓜尝尝鲜。并言妥了帮工的工价,瓜尽饱吃,中午地头有屋里的送饭,豉豆包子绿豆汤。
盛夏的宫村,青藤绿树,山高水长,村邻三五一伙倚荫戏水的乘着凉,接过了宫元的瓜,一番夸奖。当说到明天卸园子帮工时,却吱吱唔唔,阴阴阳阳不是要去口镇,就是红苕要翻蔓或苞米要薅拔藜子草。
突然,乡邻如狐一般,宫元觉得有些怪。
宫元把香瓜送完天已暗下来,急匆匆回家,屋里的叫桂桂。此时桂桂正忙着上屉蒸馍,揉碱。男人决定明天卸瓜出园,电话打回来有些迟,面和好,发酵占了时间。她一边揉着面,一边对男人说,趁空去看看二大大,他摔腿了拄着双拐,四娘娘闪了腰在炕上几天了,还听说兰婆犯了心脏病。宫元有些莫明其妙,这几天村里尽是破事儿,撞着哪路小鬼了。桂桂还说,反正有些怪,平日身子硬朗的只要村长去了他家,他就得有事。听说毛毛屋里的,活蹦乱跳的,一个后晌和村长说着话就有了颈椎。宫元说,不是有了颈椎,是有了颈椎病。
桂桂说,还不是和咱那些香瓜不能出园一样,坟头唱戏哄鬼哩。
说话间桂桂已将一笼鼓豆包子上了锅。宫元胡乱吃了东西就要走,他给桂桂说,野虫精哩,瞅着没人钻进瓜园可不得了,那可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桂桂又说,村长说考验宫村人的时候到了,不就是修个断头路噻,打仗似的兴师动众。
宫元把屋里人的话囫囫囵囵地听着,推碗折身出门,融进青幕深沉夜色中。
“立秋十八天,寸草结籽。”这话说的好,在这段日子,宫村的田野一片丰收气象,更重要的是没有多少地里活,是犁耙高挂的一段时间。
村长为了那截断头路,给政府好说歹说。昨日进城又说村上有人病了,跌断了筋骨,路不通,看不了病。尤其是几百亩“白兔娃”香瓜出园下不了山,进不了城。谁也不知道政府咋答复,反正他是城里宫村来回地跑,没他闲着的半点时间。
黎明前,宫村还沉浸在睡梦里,夜莺还没归林,有一声没一声在村中啁啾,尖唳的猪嚎一声紧一声地划破夜空,在宫村回荡。按说庄户人家,像类似猪叫狗吠猫叫春是正常不过的事。可宫村长不行。他知道村头宫正家有六头猪,金苗苗家有十多头猪,都滚圆溜肥,半月前就该出栏卖杀房了。是他亲自上门给他俩都叮咛过,猪不能卖,当然,理由仍与断头路有关,说是非常时期,必须步调一致,认识统一。宫正指着猪说,我听村长话能行,猪不听。它每天要吃要喝要长膘,超过斤两光长膘,膘厚了杀房不是拒收就是压价。
村长瞅着猪,又瞅瞅宫正,找不出更有说服力的词,说一句,我不答应卖不成,除非你不走通村路。他气呼呼又去见金苗苗,还是那一句话。金苗苗说,该有个准日子哩。村长说准不了,要准你找政府去。金苗儿知道村长唱的哪一出,故意道,我立马就问,宫村长顿觉失口,忙不迭改口说,苗苗爷爷你饶了我吧,就这个断头路咱们落后几十年都不止。宫村长看上去憔悴焦虑,竟有几分可怜。
确实有人建议过,集资把路修了。宫村长把一只手竖起来,压倒一个指头说,一,从县城到宫村四十公里,人又不多,这“村村通”班车政府发不发。“村村通”每辆每趟政府有补贴。他又压倒一个指头说,二,遇上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路是宫村自己修的,补坑垫壕的宫村人自己掏钱吗?三,他又压下一个指头,谁修路,谁就把村前村后一公里内的路灯竖起来……他把一个手的指头压完了,在场的村民异口同声说村长,你定夺。
猪的嚎叫把宫村长从粘腻腻的梦中嚎叫起来。
宫村长和宫元,金苗苗吵吵着往宫元的瓜园而来。
这时太阳刚刚露脸,宫村的树梢上披上一层金光,家家户户门前的豆荚花、丝瓜花正迎着晨光绽放。
宫元早就做好准备,却不见帮工的影子,正准备回村时,村长领着两个养猪的,宫元一头雾水。他看看村长又看看宫正和金苗苗三个人没一个好脸色。
宫村长指着瓜园说,你俩看这瓜早该出园了,就是元元哥从大局出发,等政府来调研。你说是不是,他把头转向宫元,宫元只好点着头。
“瓜卖了,猪卖了,金科爷他们没病了,政府看屎去。”宫村长说着见他们三个肉脸对肉脸,不由心生悲悯。且不说宫元的香瓜烂了滚了,低价能卖。大热天,肥猪热死三五头是常事。牲口自己犯忌,会连窝儿接着死。有这一丝侧隐,他咬牙期许说,明天吧,政府说的。
再说金科爷卧床有些日子,该进城看医生住院的,他劝大热天就别去了,村医暂时给挂了水。真的他要断丝了,碰上政府来调查,那真叫瞌睡遇上枕头,多好的说道,“路不通,群众看病难就医难,一个老人硬是病死在床……”。正这么想着,宫元屋里的电话给宫元说蒸了几笼馍,一大锅绿豆糁子,没人吃。他回答说,定的三轮车来了又走了,拉不了瓜往返费一分也没少哩。
“都是村长在捣鬼,谁帮工扣谁的地膜补贴,啥怂东西……”宫元摁了一下手机,电话挂断,宫村长听的仔细,却什么也没发作,勉强挂一丝苦笑。
离开瓜园前,宫元蹲下去,用右手中指十分内行地在瓜上“嘣嘣”的弹着,村长他们三人住了脚,也知道宫元要干啥。搭庵子不防贼,确实没人偷,谁馋了不论庵子有人没人,随手掳一个两个不是啥大事。加之这种叫“白兔娃”的香瓜自从花中露出时就是浑身通白,日渐长大简直就像卧了一地的小白兔。少几只兔子宫元是数不清的。既然村长领人来园子说话,他送几只瓜正常不过了。
刚才还气咻咻怒不可遏的宫正和金苗苗接了瓜放在掌中双手只轻轻一拍“嘭”一声,瓜汁喷涌,青黄色的粘液从指缝儿往下流,宫正和村长干脆把脸埋进去吮吸,瓜园和香瓜让四个人都醉了。宫元从瓜汁喷涌四溢和开瓜的响声判断,如果两天不卸瓜,就可能赔大发了。那个村长却粘粘腻腻地说瓜还行。当各自回家时被宫元一把扯住了,他说,吃了瓜就要走,没那么轻松,村长他们突然愣了一下,宫元说,几笼包子,一大锅绿豆糁子,你都不吃,我敬神都没香炉,走,桂桂把桌子摆好了。
村长如梦初醒才怨自己早该给宫元把事说明白,免得宫元屋里的张罗了一夜到明。他转脸向宫正和金苗苗道,咱们撑死也吃不完。又看看宫元,宫元一脸的无奈。
稍倾,村长计上心来一样,推宫正和金苗苗一把道,你俩先去,给我盛碗糁子先凉着,我就来。
宫元又一脸茫然,不明白这个宫常章宫村长又搞啥名堂,再出啥臭点子,他真要上吊了。一咬牙一左一右拽住两人手腕进了院子。
桂桂正泪巴巴在院子呆呆地站着,糁子绿豆汤,鼓豆大包把院子暄染得热气蒸腾,碗筷干干净净摆着。见来了人,桂桂抹了泪,装出几分笑脸,让过凳子,片刻一盘包子端了上来。宫正、金苗苗早就没了气愤,还没坐定,手刚伸向包子,那棵大槐树上喇叭起来,是宫村长那带着几分嘶哑而又被村民既讨厌又权威的声音:凡被宫元请了帮工的村民,听到广播后,请立即去宫元家吃饭,这是任务。饭是绿豆糁子汤,豉豆大包子……
宫村这个早晨,四山遍野里久久回荡着包子、包子、包子……的声音。
村文书石柏树在这几天成了导演的角色。
在政府下来之前,宫村的前期准备是关键。这是镇上安排的,要有形式,有内容,要将政府打动、感动。所有这些,宫村人认为很有必要。地里的瓜、圈里的猪、炕上的金科爷,村上旮旯里有拖着拐杖的二大大,双手捂着腰的四娘娘,手捂在心口的兰婆,梗着脖子,斜眼看人毛毛屋里的。石柏树说,政府肯定会被感动得死去活来,别说一条断头路才几公里,就是重修一条都对不起宫村人。
他给二大大说,折了腿的拐杖杵在地上,应该有坑儿的,即使没坑也能留下重重的痕迹,不能刺喇着拐杖走。闪了腰的四娘娘要回忆临到炕上时,怀娃婆是咋走路的,双手从后扶着腰嘛,还有……夹道欢迎不兴不许了,一桌工作餐应该有,不显侈奢,又能表示出宫村人好客热情,更重要的是从干部到群众对修路是如何如何望眼欲穿,梦寐以求,或嗷嗷待哺,还有……反正石柏树和宫村长俩坐在挂着大喇叭的古槐下说起来就没完没了。
生在宫村,长在宫村,多么无忧无虑,城里人乘凉散步,谈论最多的是菜又涨价了,宫村人随便一个地坎、地边,大小青菜豆夹儿、韭菜啥的,经从后山过来的那汩泉水濯洗,生吃都是脆儿甜。午后他们从宫村长口中得知政府明天一定要来了。过了明日,紧张了多日的他们就会闲下来,尤其兰婆、四娘娘、毛毛屋里的。装模作样,装神弄鬼,真不是人干的活。毛毛屋的这几天不错,梗脖子斜眼还真像哩,四娘娘倒喜滋滋的,她说真的要是一不小心携了崽,多美。
因而,宫村人一擦墨赶鸡入窝,赶羊入栏,看几眼电视,带着梦,进入只有属于宫村人自己那份凉爽惬意的梦乡。
宫村长和石柏树低声絮语了许久,竟陪着月亮枕在了西山墙。他俩议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宫元的瓜过了明天真的会烂在地里吗?
早晨他俩都在宫元家里“吃大户”时,有瓜客电话给宫元说,明天市场上没有外来的瓜,要是能送去,每斤加一块伍。宫元摁了免提,在场人都听清了。
“村上陪不起的。”石柏树轻轻提醒村长。
“政府说来,一定会来,他们前脚走,后脚把人轰到园里卸瓜。”宫村长说。
“早晌来就好了,要是后晌来就……”
宫村长接过石柏树话茬儿说,“就接线挂灯,连夜卸瓜。”
因万事俱备,宫村长和石柏树都感到宫村此刻安详而亲切。风调雨顺,是老天爷的事,国泰民安是大人物的事。宫村人的发达、贫穷、文明或落后就是他俩的事。政府曾经喊“村路通百业兴”,这几年又喊,“要脱贫先移民”,“奔小康住楼房”。宫村人不赶时尚。宫村人有老祖先留下的大片大片山地台田,有成片的药籽林,添树林,林中有五味子,有参天古树上结的大如蚕豆的松籽。只要勤快,别说什么小康,甚至能赶上西方。
断头路一日不断头了,每日里的班车,来来去去,夜里路灯明明亮亮,夜里窜门不用打手电,那些野虫也见不得光亮的,特别是野猪、羊鹿不再进村嚇人。
那一夜,月亮把自己一翻打扮,光辉已走在天上,宫元打过锣之后瓜地一片静谧,瓜香在青幕中弥漫。累了一天的宫元“咣”地将锣扔在地上,无奈的一声叹息。许久,庵子里才传出鼾声。
宫村长蹑手蹑足到瓜地中间卸下两个瓜,又猫腰出地。他不是做贼,却像贼一样,真怕宫元突然醒来发现自己。其实偌大一片瓜地里,狗尾巴草在月光下和一个人猫着的影子差不多,从远处谁也看不准。加之还有些夜风,蛐蛐、秋虫、土蚂蚱合凑着无比美妙的“秋夜曲”鬼也猜不着宫村长能到瓜田里偷瓜。
宫村长象个巫婆闭上双眼,把瓜掬着,口中念念有词,乞求老天保佑,只要瓜瓤儿不成清水和有醋酸味,就说明瓜熟过了,还不到将烂的时候。凭他卸瓜的感觉,瓜蒂儿已不那么水灵,已开始发蔫。真要是一地瓜烂了,宫元不打断自己腿才怪。他念叨够了,却没勇气把瓜打开。远处的狗吠、近处的莹火虫、黑魆魆的树影像魔鬼在吞噬着自己,像不敢打开潘多拉的盒子一样把瓜打开,一扬手两只小白兔一跃钻进葳蕤的野草丛里。
金科爷在ICU插氧,挂水,金苗苗办的手续。每当他出出进进,恨不能把宫村长咬两口,都是他不让爷爷进城,说老年病不要命。他以为宫村长纯是和他过不去。猪不能卖认了,爷爷前几天就该住院了,夜里发病差点把他吓个半死。
金科爷发病时,宫村长和石柏树还没散开,村长判断就是那一阵急促的狗吠时候。苗苗叫绑斗子抬爷爷。有帮忙的邻人撺掇金苗苗说,给宫村长说一声,让他也来遭遭罪,黑天夜地,抬着老人,享福啊。金苗苗不同意。他说为断头路村长几乎都要疯了。也不怪村长的,移民搬迁楼一幢一幢空着没人住,政府说群众不赏脸,恨不得把人用鞭子赶上去。这次能把政府说通来调研,亏他为宫村人积了大德。万一宫常章硬着心肠不让送爷爷住院,殁了爷爷,忤逆不孝的恶名还不背在他金苗苗身上。
宫村夜静谧而安详,那一刻月亮刚刚隐去,四抬斗子,走在黑魆魆的村道上,不是磕碰就是颠簸。摩托车倒方便,有人建议金苗苗说,找个人抱上病人,坐上去和苗苗用带子捆上,去城里快当。金苗苗说黑灯瞎火捆在一起,一出事是三条命,使不得,就找来一个藤编圈椅,用两根细抬杠绑好。就这,金科爷还一路大呻小唤的,到了断头路的那一头,120急救车已在等候了。
是金苗苗给宫村长拨的电话,话语里能把村长千刀万剐都是轻的。
接到电话时,宫村长和石柏树分手后刚进门。他骑着摩托赶来。金科爷年岁大,阎王请一回又一回。要是夜里不发病,政府调研的当口去医院,那该多好,活灵活现,何其感人。社会如此文明了,还用滑竿抬人。不把政府感动才是怪事。然后,金科爷在半道儿或刚到医院就丝断了。
可这过程和结局不是他能设定。
他身上就装了几千元,毕竟是为村上的事误了老人家,掏钱给金苗苗时,金苗苗瞅也不瞅一眼。
他找到医生,说了床号,询问病情。医生说正好要找陪人,他说“我就是。”医生说,你们村的村长真不是个东西,你老人病成这样竟不让送医院,想用一个病老汉换同情,修村道,荒唐,医生抬起头看了看他继续说,回去给你们村长捎个话,必要时,我这里可以开个证明,就说你们宫村的病人凡来医院都是延误了最佳治疗时间。医生边说边写,同时撕下两个单子,转院和病危通知。
他瞅着墙上红彤彤的“静”字,一时竟茫然不知何往,回到病房金科爷气若游丝,金苗苗如临仇敌,不回病房那这转院和病危通知呢?踌躇和犹豫中,金苗苗持手机从ICU室出来,把手机摁到免提上,是一个女人哭丧似的声音。“……只有出来气,没有回去气,怕是不行了。呜呜……”宫村长狐疑片刻,从金苗苗手中接过手机,回答说,我就在旁边,没有那样重。手机里女人说“已经开始吐白沫了。”他就在ICU门口,眼看着金科爷平静地躺上,氧气泛的泡儿均匀无异,并未吐白沫啊。“趁有一口气,叫屠夫杀了,还能卖些钱的。”宫村长越听越是一头雾水,毛骨悚然,他也听出是苗苗的女人。大白天遇上鬼来了。
还是金苗苗从村长手上夺了手机,先是对村长说,是那几头猪害瘟了,又对手机里的女人说,先烧烫猪水,我这就电话找屠夫。
村长这才完全明白过来。他冷静地对金苗苗说医院这里他先招呼,几头大肥猪也算大事情,用刀子先捅了,血放过,还值几个钱的。
这时他的手机响了。也没看清来电号码,只听到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说,今天政府派人调研宫村断头路修复的事,要宫村长做好准备。
短短的一个早晌,接连不断的坏事坏消息,哪个都是要命的,可仅仅这一个好消息就抵消了坏消息,如果用秤称,还能称出多余的来。
宫村长觉得划算,觉得值。
他对还在医院过道上帮金苗苗抬金科爷的几个村邻说,他要回去准备迎接政府调研,事关重大,不能在医院。要他们几个留在医院,村上付工资。
宫常章人生路上平坦,或坎坷,作为农家孩子,自幼在宫村长大,踏遍了金凤山的沟沟岔岔,去南方几年,也经历了一些人间冷暖,世事的艰难,可今次为村修通道这个坎太大了。守住祖先留下的家园还要政府认可,却非要摊上宫村人。是命,不遇坎儿,这个村长还算可以,比如应酬镇上的县上的,有时也溜几句洋腔,说个段子。今次才发现自己无能、无才、无算计。他也曾三番五次讨教人,比如去敲谁的门,拎上特产,特产下压上红包儿,或故意放开自己,疯颠颠地吆喝去泡脚耍牌,准备输三五千。可是形势不对了,到谁家连门也不让进。“有话去办公室说”成了新形势下的新气象。稍有动作,那谁会板起脸或恼怒道“你不是来给村上办事,你是逞心来害人的”。他一次次被拒之门外,一次次在尴尬和窘迫中退出来。也想过放弃,可是断头路像巨石压在身上。眼下可以不说,自他放话要把路修通以来,那些打工在外的孩子们高兴得发疯,说他们要把小车从深圳从南宁开到宫村。宫正的儿子说有一个客商来查看了宫村人饮用的那眼山泉水,终在金凤山一个半山岩根下找到来源,竟是地下河涌出来,回到南方检测说水质纯天然度达到直接饮用标准。如果头一天通路,第二天就来办瓶装水厂,到时宫村人还不够用哩。
宫村长摩托飞驰到断头才放慢了车速,太阳又赤裸裸开始发威,当它的光茫在密扎扎的林子穿过时,就很没有底气,林梢间细碎的光斑显得萎琐而无力。
断头路就在林子中间,乱石中垫着砂石,溪水从林下的青苔中渗出,宫村人来来去去踩碎了青苔,于是溪水在这一块潺潺作响。
摩托车、人力车在这里本来勉强可以通过,是他指挥人把村邻垫的砂石挖了。现在只有嶙峋的怪石无序而狰狞地躺着,摩托车从中拐来拐去十分费力。
石柏树电话中兴奋地给他汇报说,宫元卸了两笼瓜,金苗苗的两头大肥猪已杀的挂在架子上,村委会门前场院里摆好桌子,二大大、四娘娘们都到了……
村长一手拿着电话,一手推着摩托,听石柏树的汇报,突然意识到不用他赶回去,应该把迎政府的地点就放在这断头路上,应该有一大群乡邻跪一长行,应该……
摩托倒下去,压着他,又把他推下石坎,摩托没离开他,很忠实很实在的把他压在下面。在那一瞬,金凤山在旋转,林子在旋转,接着是一群大肥猪向他扑过来,他刚刚闪过身子,又是铺天盖地的小白兔从林子窜出把他再次扑倒,他挣扎着直起腰,又是二大大的拐杖、四娘娘的拳头,还有瓜客举着秤砣劈头盖脑地向他砸来,天暗下来,一片漆黑……
许久,许久,手机在一个石头缝中响了,十分悦耳,他在黑暗中摸到手机,是宫元的电话,宫元说的啥他听不清。
他睁不开眼,任宫元骂他八辈祖宗,一笔也写不了两个宫字,尽他去骂。
镇长的电话来了,说政府调研今日又不来了……
他十分艰难从牙缝蹦出一句“瓜都……”
镇长说,瓜滚在园里。
责任编辑:魏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