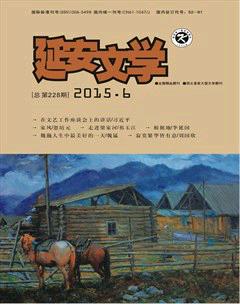拐点
王哲珠,女,80后。广东揭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中国作家》《作品》《广州文艺》等。有小说被《中华文学选刊》和《小说月报》转载。有小说入选《2012中国中篇小说年选》。出版长篇小说《老寨》。
母亲又来电话了,这已经是第三个电话。
手机就在我手上,我看它在掌中不停地歌唱。一首歌将唱完的时候,我按了接听键。我知道,就是不按,歌声暂时停了,还会第四次,第五次地响起。
“有没有空?是不是在开会?”母亲问。每次电话,母亲总要问这两句,怕耽误我的工作,在她看来,我的工作全是大工作。特别是开会,更是我工作中的大事,一点也扰不得的。她和父亲的电话从来是掐着我的下班时间打。偶尔碰上我临时有采访任务或临时会议,我只对着话筒低低说一声,忙着。那边便一连串说好好好。挂了电话,像犯了什么错。
现在,我说:“没事,下班了,正看电视。”
母亲说开了:“后天就是中秋了,有放假吧?会回家的吧?怎么还没消息?”
今年确实晚了。大姐二姐远嫁,我还单身,这几年的中秋都是我回家团圆,大姐二姐至多匆匆回一趟,吃顿饭就走。中秋夜的月娘是要我和父亲母亲一起拜的。就是中秋没放假,我也尽量先请好假,对父亲母亲只说是例行放假。往年,我会提前几天给家里电话。我一交代回家,父亲母亲的中秋节就开始了,我提前几天交代,他们的节日就拉长几天。
我知道该说,回,明天就回。接着,我会在电话里听见母亲在那边对父亲喊,阿平明天就回。然后,母亲再转身对我交代一堆关于路上小心的话。如果我愿意,多请两天假不是问题,特别这大半年来我写了那一系列报道之后,必须承认,领导是给了我许多优待的。
这时,我看见父亲看住我的眼问,写好了吗?我的舌头就打了卷,对着手机里的母亲说:“忙……这两天忙,后,后天回。”
我听见母亲的声音拐了一下,像什么东西掉在地上,又匆匆捡起。她说:“那好,后天是中秋,你起早一点,早点到家。用不用到时去个电话喊醒你?”
“不用,我手机设闹钟。”我说,匆匆挂了电话。我听到父亲在那边问母亲:“后天?今年这么迟。”我怕父亲会接过电话,要和我说几句。要是父亲接电话,我保不准自己会改口,说自己其实很忙,抽时间回家会赶得很急,回城车票将会很紧。父亲或许让我干脆别回,说做好工作重要,然后他会去劝说母亲。那些话或许又可以拖一拖。
我知道,那些话终归要说的。春节总逃不掉吧,就是不面对父亲,父亲的眼光也如影随形。
父亲果然又问了。
我凌晨三点的车,将近中午到的家。吃着午饭,父亲就问:“阿平,那事写了么?”我一口饭含在嘴里,吱吱唔唔的。父亲坐在桌对面,停住筷子,认真地看我。
我用力吞着饭,以掩饰脸上的红涨。果然,母亲说:“慢点吃,吃了再说。”
父亲仍然看我。我说:“开,开个头了。这一段赶其它的报道,又开会……”
父亲点点头,深信不疑的样子:“你先忙好你的事,不过,也赶紧点,金河大路的草都长高了。”
我点点头,心烦意乱地吹汤,这汤怎么这样烫。
母亲说:“别睬你阿爸,事不是都处理好了?金河大路不是顺顺畅畅的?屋后那屁大的地和两棵黄皮树不是好好的?你爸就是木头脑筋,不会开窍,不会拐弯。”
“你懂什么?事是处理好的?那是巧合,是碍了大人物。理就是理,占着理哪能不说清?”父亲放下筷子,对母亲也对我,一板一眼地说。他一直这样,每次说都是认认真真的,反复地说。
母亲说:“好了,好了,又是你那一套。吃饭,听都听烦了,你也说不烦。”
“这是正经道理,能不说通。”父亲说,又看看我。
我猛地低下头,清楚这件事对父亲总归得有个交代。大半年前,接到父亲的电话时,我就知道,事没那么容易。
那次,手机响的时候,我听到的不是母亲而是父亲的声音。父亲开口就说:“阿平,你看能不能请个假,回家一趟。”
我胸口一沉。
父亲又说:“家里的地要让人占了。”
我就有些莫名其妙。家里的田除了父亲闲里侍弄一点,其它的早荒了,白给人种都没人要,还有什么好占的。我说:“爸,你别急,慢慢说。”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感觉极好。突然想起小时候,我弄坏了什么东西,或碰上什么难事,便走到父亲面前,无措地喊:“阿爸——”然后,事就不成事了。从小到大,似乎没有父亲解决不了的事。自大学毕业后,我再没有对父亲说过什么难事。倒是父亲常来电话让我拿主意,比如重新修厕所,比如电视机买什么牌子,再比如要不要买医保。现在,父亲在电话里喊:“阿平,你回来一趟。”
父亲说要被占的是屋后的地。我想起家里那座下山虎 ,屋后是一小片长条形的地,两头是两棵黄皮树,中间一向种着两畦菜,菜地边是条田间小路。要那点地做什么。父亲说是修路,不是村村通公路么。我想修路是好事,如果家里的地确实在规划内,没什么好说的。父亲一向明理,会想不通这点事?再想想又不对,屋后长条形的地紧靠我家的墙根延伸出去,宽不到三米,路就修在墙根下?
和父亲站在屋后,我明白了。屋后那片田地大多荒着,那条田间小路被踩宽了,路那边开了家杂货店,兼卖肉菜,隔着路,正对着我家后墙。将要修的金河路从西寨、东寨中间直穿过来,正好横过杂货店,直连到西寨、外寨,是整个乡“村村通公路”规划中最重要的主干道。
父亲说:“杂货店是老乌家的,刚建了一年,在四乡八寨的中心,开店后,生意好得像着了火,是舍不得拆。可在规则内,有什么办法。”
我不太明白父亲为什么说这些,只说:“既然路从这横过,店当然得让路,和我们屋后的地有什么相干。”
“问题是店不肯让路。”父亲指住那家店,指头愤愤地一点一点,“金河大路修在原来小路的路基上,沿路就占那些荒掉的地和几间旧牛棚,单单穿过这家店,人家就不肯挪地。”
“哪有这样的理,嗯?”父亲对我发问,连连地问。我哑口无言。是没这样的理,可有这样的事。
杂货店的老五早想好了,修路是大事,不敢阻。他让路拐个弯,绕过杂货店,顺着我家的屋墙,从我家的地横过去。我的语气也激动了:“这像什么话?”
父亲说老五的叔伯兄弟在乡里当干部,老五的妻舅在镇政府做事,老五早把这事走通了。这段时间还在杂货店一边修了水池,准备卖鱼哪。金河路早在老五心里拐着弯,绕开他的杂货店了。这是仗势欺人了。
我真正明白父亲让我回来的原因了。我知道这是仗势欺人,可我涌动的气愤已经被一股说不清的烦躁所替代,嘴上不再煽动父亲的愤怒了。
父亲说:“阿平,你去和乡里的干部好好说说,不行就到镇上去说。”
母亲说:“别听你爸的,一个月前路要拐弯的事一传,你阿爸就闹开了,到村干部那里闹,闹不成,又去了乡里。有人睬他么?人家表面笑笑的,应付几句,瘟神一样把他送走,老脸都丢尽了——如今,又要阿平去丢脸?”
“什么丢脸?”父亲的声调高了,“理都在我家这边,我不是闹事,是让阿平去讲理——阿平,你是走过大地方的,能讲出一二三四来,你去乡里好好说,直通通一条路,在我家屋后这么一拐,像什么话。再不行,直接上镇子,我就不信,没人管得了这事。”
“试试吧。”我应着,目光躲闪父亲的目光,和语气一样吱吱唔唔的。我开始想象去和那些村干部、乡干部打交道,想象怎样软了口气和那些人说话,怎么用“道理”去谈论那条将会拐弯的路。所有的想象都似是而非,又荒唐又合理。这些想象将还未行动的我弄得筋疲力尽。
“我们不是走关系,是说理。”父亲说,把每个字咬得很清楚。
“你不是去说过了,说出什么了结果?”母亲说。我的为难,她一定看得很清楚。
父亲说:“那不一样,我有理吐不出,颠来倒去说不出新话。那些干部话说得好听,可听得出不想理这事,嘴上不提老五,可事事偏向老五,我没法不冒气,气一冲,话就不好听。阿平肚里有墨水,墨水能把道理洗得光亮亮,管教那些干部无话可说——阿平,有些法律肯定说到了这些道理,你肯定知道,你就按那个去说,我不相信他们还真敢违法了。”
父亲这样说,我知道,自己无论如何得走一趟。
母亲脸色变得难看:“阿平事够忙了,你专门把他叫回来奔走这点破事。照我看,这事就别去管了。屋后那点地算什么,要种菜坡子山边有的是田地。三婶几个月前去城里带孙子,让我把她的菜园种下去,我都没点头,那可真是块好地。”
说实话,我觉得母亲的话有道理,家里这座下山虎虽有些旧,还是干净的。只住父亲母亲两人,大姐二姐是在外安了家的,我也不可能回来住,单就屋子来说,已经太宽,宽到有些空。田也早不种的,屋后那点有什么要紧的,像天井里那个时常漏气的摇井,我让父亲安上抽水机后,就变得可有可无了。
我没说,只对父亲说:“午饭后我找他们说说。”
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看出了我的意思,他把竹椅往我面前拉,说:“不单单是那块地的事,按你阿妈说的,那点地现在能做什么。如果正经在上头的规划里,路本该在我家的地上穿过,就是几十年前地最金贵的时候,我也不二话的。现在弄的是什么事,整条巷八九座下山虎屋后都留出那么宽的地,到我们家就拐进来了,像什么话?以后我都不敢往屋子后去了。金河路拐出的这个弯就是我们家的笑话。”
我看见父亲的眼光在抖,和声调一样急促地往上扬。父亲的意思我明白,我半垂下头,按住父亲的手背,一时无话可说。我猛地觉自己往小里缩,缩到童年那么大,父亲比年轻时更有力,我坐在他面前,用心听着他的训诲。
我去了村干部家。自高中考进县重点中学后,一直到大学毕业,我便极少回家了。有时,连假期都去大姐二姐所在的城市,或闲逛,或勤工俭学。毕业后在大学所在的城市找到工作,更难得回家了。同个寨子的村干部对我来说陌生又模糊。再说,村干部算是我的长辈,我将怎么开口。我摸摸衬衣口袋里的证件——出门之前,父亲一直交代我带这个,说有时得给他们这帮人试点硬东西——我问自己,想找麻烦吗?答案是否定的。这样一来,摸口袋就显得滑稽了。按母亲说的,用软的么?我知道这也许有用得多,我从城里带回的好东西不少,就堆在桌子上,随便选一两样,在农村也是相当显眼的。但我在父亲的目光中走出来,用他的话说,我是该挺着腰背说话的,于是我两手空空出门。后来,是母亲偷偷追上我,提了两盒东西。母亲没我那样酸文假醋,她说:“礼多人不怪,再说,都是长辈,你难得回一次,没事都得走走的。”现在,这东西就在我手里,我这样提着进去,然后说那件事么?
我心烦气躁,暗暗咒骂屋后两畦烂菜地,咒骂它们把我好好的中秋弄得像团乱麻。我在村干部家附近来回走、转圈,意识到自己的胡思乱想泛滥成灾,犹豫的时间实在太长。所有的行动未曾开始,我已经被想象里的麻烦弄坏了头脑。
我进去了。客套、喝茶、提那件事,再客套、喝茶。然后,我站起身道别。走出门口的时候,我抬手看了下表,时间短得让我怀疑表的指针,比刚刚在门外犹豫的时间快多了。
趁着一股气,我把摩托车直接开向乡里,车头挂着剩下的一个礼品盒。找乡干部几乎重复了找村干部的情景,只是少了在附近转圈的时间。
回家的路上,我无比轻松,所有乱麻一样的麻烦似乎统统解开了。我想,我是尽了力的。我找了寨里、乡里管这事的最要紧的人,该客气的客气了,该讲的道理应该讲透了,作为一个晚辈该尽的礼数尽了。在乡干部那里,我甚至在掏烟时有意地让工作证无意地露出来。我没想到那乡干部会如此聪明,他即刻半立起身,把一杯茶直端到我手边,开始倾诉基层工作的琐碎和复杂,抱怨对上交代对下执行的为难,赞赏我作为一个城市人对大形势的了解和一个大地方人该有的胸怀。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成了来自大地方的城市人,但他让我觉得,再提那片长条形的地,就显得小气了。他甚至让我感觉到他对我那个工作证过份的敬畏,这份做作的敬畏让我敏感,让我莫名其妙地深究起自己露出工作证的用意,好像我的理不直气不壮,需要那个证。到头来,我倒像成了没理的。现在回想起来,我出门时,在他的客气里甚至有些灰溜溜。
不管怎样,我是尽力了。我反复对自己说这句话。对于父亲,我算有个交代了。我对这件事已经用了心。可愈近家门,这份轻松愈显得含糊,渐渐地有了重量,到了家门口,已经变成灰色的沉重,压得我迈进大门门槛时几乎提不起脚。
父亲立在厅里,眉眼欣喜,满脸天真地看着我。是的,我确定是天真,父亲腰已经微驼,皱纹在双颊交错,可他那份天真依然澄澈如水。我呢,我的天真早不在了,我未老先衰,早已污浊不堪。
我的脖颈向下弯软,拖着步子朝父亲走去。父亲看了我一会,往后退,在藤椅坐下。说实话,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想好怎么对父亲开口。我忘了走访的两级干部是怎么说的了,他们含糊而客气,不点头不摇头,不说对不说错,只是把我送走。对,把我哄出大门。
我坐在父亲面前,像多年前偷了人家的甘蔗被扭送回家,无可名状地羞愧和忐忑。
母亲不在,大概又为我的晚饭准备了。厅里太静了,只有父亲吐出烟雾是动着的。极静之中,我莫名其妙地听到自己儿时的一句话:阿爸,等我大了,把这些人都抓住。当时,我说这句话时,手插着腰,小小的脑袋仰着,感觉所有的东西都踩在自己脚下。
儿时的我,粘在邻居的黑白电视机前,一头扎在战斗片和警匪片里,满脑的军人梦和警察梦。我扬着竹枝做的手枪,满天满地地跑,在想象里纵横世界,伸张正义。一天,父亲挑了一担蕃薯上镇子,一辆拖拉机勾住了父亲的竹筐,把他带倒后扬长而去。父亲脚受了伤,半跪着捡回散落的蕃薯后,被一个熟人带回家,一直包扎了大半个月。每天,我蹲在厅里看大姐和阿妈给阿爸换药,就发誓要找到那个坏人,把他的手扭到背后,像电视里那样。我说长大后要当个解放军,骑着自行车到处去,把这些人都抓住,抓得干干净净。大姐笑得手里的药抖落在地,我不满地瞪她,觉得她没用。父亲看着我,认真地听我说,然后认真地对我说:“阿平的话比药好,你会抓住那个人的。”当时,我深信不疑,包括父亲的话,包括很多东西。
现在,我几乎找不到深信不疑的东西。儿时踩在脚下的东西轻了,往上浮,顶在我的头上,让我的眼前灰蒙蒙,把我的脖子压弯了。
我就那么弯着脖子,顺其自然的模样。
“去镇长那里告。”父亲突然说,声音又突兀又高扬,在客厅四壁间来回碰撞。
我吃惊地抬起头,父亲脸上闪着一层光,质地坚硬。
父亲说:“陈镇长不是你的朋友么?找他,告这些无理无法的人!”
我思维才转过弯,陈生泰算是我的朋友,也念过县重点高中,比我高两届。我高一他高三时,周末常一起回家,再一起回校。可上大学后我们极少联系,再说,他只是副镇长。再说,他管到这种事?再说,我怎么开口……
“你放心,我们有理,是去反映下边的情况,不是去求人。”父亲对我的勉强似乎一清二楚。
我怎么能对父亲说,反映情况也是求人,随便一个人都能反映情况,或者说去告么?
父亲说:“把事透透地说给镇长听,看他怎么说。让他知道下边有这种事。”
我怎么能对父亲说,下边的情况,镇长或许比我们更了解。我只对父亲点点头:“我试试。”
陈生泰许久不说话,打手势请我喝茶。
我说:“主要是我阿爸,老人家想不通。”
陈生泰说这事其实不直接由他管,转口又说他得好好想个法。
我许久不说话。
陈生泰知道我衬衫袋里的证件,知道我难得开一次口。
我知道我那个城市的遥远,知道陈生泰要转的毕竟是金河镇的天地。
所以,我们沉默极长。他在想法,我在等待。
后来,陈生泰问了我家那座下山虎的位置和屋子四周的情况,然后说,给他点时间。
陈生泰隔天就给我来电话,让我去镇上见个面。
他一说出想法,我就知道他对这件事是用了心的,用得恰到好处。他拿出一张纸,画下我家的下山虎和周围的情况。
我家的下山虎在巷子第一座,一侧靠大强家的屋子,一侧是一段小路和半面斜坡。陈生泰的笔圈住那段小路和半面斜坡。都说好了,这一段小路和两边的草地平整出来,也是长形的一片,和屋后那片地差不多大,算我家的。随我家怎么用。另外旁边的斜坡削平整好,重新修出一段路面。平斜坡修路的工钱老五会出。
我抬起脸,看住陈生泰,如果可以的话,我真想把“刮目相看”好好表示出来。
除了最后一句话我不喜欢,其它的不用多说什么了。父亲可以把屋后的菜和黄皮树移到屋子侧面,甚至可以靠着自家的侧墙再搭出一间房,放杂物或者停车。
对父亲,我可以给个真正的交代了。因此,进门的时候,我头是扬着的,母亲迎出来时愣了一下,小声问:“真说通了?”
我不答,只是笑着往里走。
父亲从藤椅站起身问:“成了?”
我拉了父亲,走出门,来到房子侧面那段小路。我拿出自己掌握文字的功力,描述将会出现的那片地,描述将会搭建起来的那间房。我在自己的描述里兴致勃勃,是捡了大便宜的语气。
等我停下话,往喉头咽口水的时候,才意识到不对头。在我的一大段滔滔中,父亲不出一言,沉默如石。我疑惑地看看父亲。父亲问:“你答应了?”
他的语气不对,我的回答一下子带了怯意:“这样不是挺好?地在屋子侧面更方便,老五的店也没必要挪。”
“我要的是老五挪店?我要的是地?”父亲的话严厉了,我工作以来从未听过的严厉。
我呆呆看着父亲,发现自己确实弄错了他的意思。我觉得无法可想,突然想,或许前两天我应该说很忙,忙得抽不开身,远远躲开这事。
父亲说:“是拐弯的事,要紧的是拐弯。”
晚饭时,母亲对父亲说:“你还要怎么样,让一家人缠在那长条地上!”
“我说了,不是地的事!”我们都没想到父亲的声音会那么大。
“阿平,别管他,回城做你的事。他死脑壳,死目光,说不通的。路都能拐弯,他是拐不了弯的。”母亲不看父亲,看我。
父亲就在这时候想出了新主意:“对了,阿平,你还有你的笔,我怎么没想到。”
我惊恐地看着父亲。
父亲沉浸在他的激情里:“你是记者,城里的记者。把这事写下来,让大家看看,说说,公理自在人心。我知道,这种事,不单是我们屋后一件,也不单我们寨里有,其它乡寨,其它镇子肯定也有,肯定也有人没处说理。说得多好听,村村通公路,可做出来又全不一样了。阿平,写出来,也替他们说说话。”父亲放下碗筷,在厅里转圈,扬手,好像在谴责那些办事不公的人,又好像为受了委屈的一群人鼓劲。他说,“阿平,听说你在的那家报纸是大报,正好,看的人多,知道的人就多。”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父亲,再转头看母亲。我想,我的眼神里一定充满求援,母亲扯父亲坐下:“不能好好说话?”
我回城了,在车上,我努力合上眼睛,让自己入睡,但思绪极清醒。父亲的目光在脑里晃,静静观察着我的思绪,这让我不自在。父亲或许是看透我了,我是他儿子。我当得了他的儿子么?我不敢让这个问题在脑里停留太久。我想,父亲终究还是没看透我,他怎么想得到,儿子已不是敢把所有东西踩在脚下的那个了。
我知道,照父亲说的去写,我的笔管里肯定有血在奔流,那样笔下的文字肯定有灵魂在跳舞。可父亲哪里知道,我不愿让笔流血,宁愿让它欢快地歌唱,为我的生活唱出一层光鲜灿烂的外表。
我是胆小鬼,胆小到似是而非。
出发前,父亲又再三交代:“阿平,回到城里就写。”我喉头发出些含含糊糊的声音,弯下腰身提行李,让自己也弄不清是在点头还是在摇头。
回城后那段日子,我一直恍恍惚惚。我害怕听到手机响,好像手机的铃声便是父亲的催促,几乎到了神经质的地步。我惊恐地发现,自己已经脆弱到如此境地。偶尔,我稍稍冷静,想想就是写出来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是想象中的严重。但我已被损坏,我身上某些东西不单失去了,甚至走向另一个极端,已弱得夸张了。
父亲来了几次电话。我对自己能敷衍过去感到吃惊。后来,父亲的问话就简单了,只问写了么?说写了念他听听,报纸寄回家给他看。
我开始想办法,让父亲忘掉这件事。
我珍惜这份工作,毕业后靠着我的笔考进这家单位,靠着笔一点点让领导看见我,对我这种凡常的农家子弟来说,我已属于上天的宠儿。我的工作不错,不算低的收入,不算低的补贴,不算少的出差机会,进了这家单位的人有不算差的名声。我把前面的路安排得好好的,按揭一套中档的房子,向那个适合我的女孩谈谈结婚的事,用笔好好在单位打基础。一步一步,又踏实又清晰,我将在这城市拥有一席之地,这将是我的城。至今为止,我的笔没出过一点偏差。现在父亲要我写这个东西——也许是没什么的,可我不得不小心,日子不能出一点差错的。
让父亲忘掉的办法是让他离开。我想接父亲进城住,虽然按揭的房子还没有着落,但我单位的宿舍已足够宽敞。让父亲在城里逛逛,看看外面的精彩,屋后那长条的地算什么呢?那个弯拐出来没什么大不了的。到时,我打电话给大姐、二姐,让父亲去她们那里也走走。如果父亲愿意留在城里,最好。如果不愿意,到那个时候,屋后的路已经修好了。
我打电话回家,破例的不是母亲接,父亲像守在电话机边,一声铃音后,就听到他的声音:“写好了?”
我兴冲冲的声音顿了一下,提自己的想法时说得吞吞吞吐吐。
父亲说:“好好的,我去城里做什么。”
我提起那个适合我的女孩,我知道在屋后那条路出现之前,这是父亲母亲最关心的事。我说想让他们看看这女孩,是不是真的适合我,能不能把正事办了。我们都忙,没时间回去,让他们进城。
父亲很高兴,但他说:“让你阿妈去看,她晓得这个,她说行就是不差的。这一段我先不走开,屋后的路就要修了,我倒要看看是怎么拐弯的。”
我的头胀了,扣着手机的耳朵嗡嗡响。接着,我听到母亲的声音,那声音兴奋得一跳一跳的,她问:“真谈成了?多大年龄?性子怎么样?有没有生辰八字?我这两天就进城?”
我有气无力地说:“缓一缓,她这个星期出差。不在。”
我又害怕看到家里的电话号码,终究还是来了。是母亲的声音,我揪紧的喉头松了一松。
母亲说:“成了,成了,事过了。”
“什么事?”
“路的事,杂货店要拆了,路按先的方向走,不用拐弯。”母亲说。
我握着手机,立直身子,父亲又去闹了?
“不关我们家的事。”母亲微微叹口气。金河路本是金河镇最有声望的企业家刘正明要捐建的,开工前他看了图纸,又专门沿路走过,看到了那个拐弯,当场发脾气,说他为乡里建的这条路本是如何的顺畅平直,突突兀兀拐个弯像什么样?要这么拐的话,路不如不修了。那个拐弯就在刘正明的脾气里捋直了。母亲说到最后,止不住庆幸:“早知这样,也不用乱操心了。大人物一句话顶千斤哪。”
我涌起莫名的羞愧,但还是欣喜的,这事总算是过了,父亲该安心了。我让父亲听电话。
母亲说:“他在里屋,你让他听做什么,说不通的人。”
父亲还是来了。我说:“阿爸,路不用再拐弯,按正经的路线走了。”
我没想到父亲的声音那么低哑,他说:“说理说不通,人家一句话路就直了。这算什么事,儿戏一样。村干部乡干部就是这么办事的。”
我沉默。除了沉默,我还能做什么。
父亲不沉默,他说:“阿平,一定要写,把这事的曲曲弯弯写清楚,让人看看,这些干部就是这么讲理的。路看起来是直了,实际上弯得很,里面不知绕着几个圈子哪。”
啊?我的手机差点掉在地上。
我对父亲陈述接下来单位有大活动,报纸要跟踪,我有很多的任务要完成,很多的稿子要赶,会费很长时间。
父亲说:“那等你忙过这一段,有空了就写,反正那个弯在我心里绕着呢。你要写的时候,有什么不清楚的就给我打电话。”
这事就这么拖着,一直拖,大半年了,我还未给父亲一个交代。现在,我回家了,坐在父亲面前,要怎么说。
其实,关于路的事,我是写了的,早就写了。可我没法对父亲开口。
大半年前回城时就动笔了。当时,“新农村建设”成为一朵新鲜的花,绚丽地开放于各大报纸。以几年来培养的嗅觉和敏感,我知道,机会在眼前,只要我愿意,我的笔可以唱出最合适的歌。
我以回乡为主线,讲述了屋后即将拐弯又被捋直的路。当然,在我的报道里,拐弯是因为落后村民的目光短浅以及蛮不讲理的固执;捋直是因为基层干部的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因为爱乡企业家的深明大义,多项优待。我夹叙夹议,情真意切,饱含激情。在我的报道里,“新农村建设”是逐渐空落荒废的乡村的活水,基层干部和爱乡爱民的企业家在引水、播种,凋零的乡村再次灿烂出鲜花,也必将会硕果累累。
报道写完后,我回头重看的时候,后背冒汗,双腿发软,不敢再细读。
领导读完报道,拍桌赞赏。“以小见大,大而不空,令人感动。”他这样说,几近苟刻的他当着我的面这样说,我每个字记得清清楚楚。
我一发不可收拾,由修路写到路灯写到开渠引水写到自来水进村写到绿化写到农村新项目……我的笔放开了歌喉,处于极好的状态。我来自农村,对农村了如指掌,这有助于我“注入感情”。我写出一个系列,在我的笔下,真真是“幸福之花处处开放。”
单位受到上级的表扬,我受到单位的奖励,物质的和精神的。物质的对我那套将要按揭的房子有着很大的帮助,精神的让我看到脚下的路子发着灿烂的光芒。
我不知道这有什么不好,我尽自己的能力把日子安排得如此完美。只要不想起父亲和他那份交代,我真想对日子歌唱。
现在,父亲说,路在他心里弯着。
我低下头,想,我该怎么把头抬起来?
责任编辑:张天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