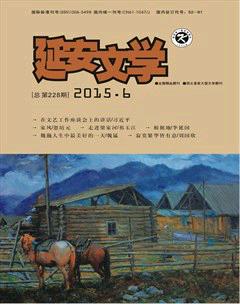水巷口


张品成,湖南浏阳人。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赤色小子》《永远的哨兵》,长篇小说《红刃》《红药》等。曾获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第十四届冰心文学奖等。
第一章
沙堆后面有一排脑袋,是一些少年,他们趴在沙上往海峡那边望。
远处的海面上泊了些大船,海上风平浪静。那时候海在睡觉,潮不起也不落。天上缀了些白云,天蓝得透亮,白蓝分明。有一些鸥鸟觅食,忽高忽低在那么飞,突然就箭一样射入水里。然后又蹿飞至半空。潘庆他们知道,鸥鸟在叼食小鱼,那时它已经得手。
往常潘庆他们爱看鸟观云,然后踏浪戏水,沙滩上有小小沙蟹,孩童们与那些小生灵追逐,锐声地叫喊,突然就猛地驻足,因为那有一些小小的洞穴。他们观察那些洞洞,他们知道那些沙蟹就是遁于那些沙洞里。然后,他们掘沙,弄得沙尘飞扬。手里各捏有战利品,一只两只沙蟹。他们玩沙蟹,用细绳将两只爪钳绑了,看他们在沙滩上蠕动样子,平常蟹梭走得飞快,浪走浪奔。现在各有各的主意,钳爪运作不能统一,在沙上画出一些“符”或者“图”来。孩童们就久久看那些线条,把各自的“符”和“图”发挥想像,说出许多道道,最后都笑着闹着跳入海里搏浪戏水,玩得疲了累了就回家。
海滩和大海,是海边孩童的乐园。
但这些日子他们乐不起来。
有一天,孩童们突然发现海面是多了些舰船,他们看,大海里,那些舰船火柴盒儿一样在海面漂泊。他们跑回家,“哎哎!”他们朝大人们叫着嚷着,他们觉得有了新发现,神情亢奋。可大人们的表情迥然不同。他们阴沉着脸,他们还伴有叹息。
潘庆记得那天的情形,他兴高采烈地和家里兄弟说这事情,潘家五兄弟,潘庆排行第三。他说:“海上有大船哟,铁壳大船,还时不时喘气,一气就呜呜叫着吐黑烟。”
父亲阴沉了脸说:“都看见了的。”
“那么多的船,那么多……”
娘叹了口气,潘庆不知道娘为什么要叹气,潘庆父亲在这个镇子上教书,家境算不错,娘也是个开朗的人,潘庆鲜有见娘叹气。
后来,潘庆听到大人们说到三个字:日本人。
后来,孩童们就都趴在了沙堆后面,他们往海上看。
“那是日本人的船。”小五子说。
“日本人的船怎么了?”潘庆说。
“日本人要来了”南生说。
“日本人来了怎么了?”潘庆依然直了眼睛说。
“不是船,我爸说那是炮舰。”南生说。
“那是炮舰怎么了?”潘庆说。
“看你说的?!”南生说,“日本人来了,要交火了,炮舰上都是炮,一交火他们会往镇子上开炮……”
潘庆说:“那又怎么样,我们的人不是也往海堤上架炮了吗?我看见他们架炮了……”
“我也看见了。”
“那你还说?”
“我说要交火……”
“交火交火呗,枪炮交火放炮仗样……”
“那很热闹吧?”
“当然热闹。”
孩童们很快就抛去了被父兄们沉郁表情所影响到的那点什么,他们想像了交火的样子,觉得很新鲜。想像了海里和岸上两军对垒的情形,觉得很刺激。他们喊着叫着,在沙滩上跑。
阿成伯在整理他的渔具,日本人的船泊海上,没法出海打鱼,镇子上的渔船都在港湾泊了。阿成伯抬头看了看疯张的孩童摇了摇头。但潘庆他们仍然欢着。终于阿成伯吼了一声。
“热闹你个鬼哟,炮弹枪子不长眼睛,谁挨着血肉横飞,做个孤魂野鬼。”他说。
孩童们怯了,笑声叫声偃旗息鼓,表情蔫蔫。心上和天一样,黑了一截。
镇子和家里也失去往日光彩,大人的脸像没抖干净的米袋,阴沉得难看。
大半天的没有人说话,一屋老小时不时往祖父的脸上睃望。
祖父不说话,眯了眼长久吸烟,样子有些神秘。吃饭时光听得碗碟响,没人出声。到傍晚时候,祖父咳了一声。大家支了耳朵,他们想,老太爷要发话了。
果然,祖父说话了。
祖父说:“香火不能灭了……”
大家在昏暗里点着头,他们想,这是当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祖父说:“潘家到我手上一线单传,好不容易我儿争气……在你手上花开五枝,不能让日本人给毁了潘家香火……”
祖父的主意是,五个孙子放五个地方。
祖父说:“狡兔还三窟哩,难道人还不如兔子?我花开五枝,任你风任你雨总有一朵两朵在的哟……”
“万一真有什么情况,东方不亮西方亮。潘家不会绝了香火。”祖父说。
然后是抓阄。“一切天定哟。”祖父说。
他伸出握拳的右手,然后张开五指。
掌心里有五只纸团。每张纸上写了一个不同的地名,那是岛里有可靠亲友的地方,把子嗣寄养在那放心。
潘庆五兄弟。依次小的先拈,潘庆排行老三,怎么的都是他第三个拈。大弟二弟拈了,不敢打开纸团,怯怯地盯了大人看。潘庆拈了,他没觉得有什么。他打开纸团看了一眼,那有两个的字,跳到他眼眶里,心上莫名涌上些欣喜。后来大哥二哥也拈了,大哥不仅打开纸团看,还大了喉咙读出纸团上地名。“八所……”
大哥说出的当然是个地名。除了最小的弟弟留在了爷爷身边,其它四兄弟都将离家暂寄别处。
潘庆惦记的是海口,那是个大地方。潘家几兄弟一直想去那地方,那是他们外婆家,但他们兄弟五人,谁也没去过。
铺子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铺前,其实是个渔港,自古来打渔的船只在那来来往往,就有了一家两家的铺子,后人随口就把地名叫做铺前。
潘庆家的铺子也开在铺前,那是爷爷的爷爷辈上的事了。当然铺前的镇名不是由潘家的铺子而得名,那时候铺前已经有几十家铺子了。
潘家做绳的营生,潘家先人是个编绳的外地匠人。祖宗打的绳粗细不一,但特点是耐用。一根绳其实也有很大讲究,在于用料。用过潘家先人绳的人就纳闷,问:怎么同是绳潘家的就耐用?潘家先人当然不说,他用几种料,绳就经磨耐蚀了。船走海上,需要各种绳子,抛缆要缆绳,拉网要网绳。还有船上各种用途的绳,一条船,其实粗粗细细绳呀缆呀什么的到处都是。铺前是个渔港,所以,潘家绳的生意奇好,渐就做大,成了铺前富户。
到潘庆父亲手上,祖父就不想儿子继续这门手艺,你读书,你脑子灵活,你是读书的料。祖父说。读书做官。祖父说。父亲也不想编绳,他想读书。然后就去了海口求学。
父亲就是在那遇上母亲的。
他们恋爱的事让外公知道了,外公说:“要我同意这门亲事比上天还难,我们韦家东南亚都赫赫有名,韦家的千金怎么可能下嫁个编绳的人家?”
潘庆妈哭了数天,一双眼睛红肿得吓人。
外公视而不见,丢下一句狠话:“你要真跟那个姓潘的小子,你永远不要进韦家的门。”
消息传到铺前潘家,老太爷也恼了火了。“他们韦家不是看不起潘家吗?我们潘家在前铺也算有名望的家族,韦家要给我们脸色,我还看不上他们哩。”
他敲着祖宗的灵位跟儿子说,“你回来!你要是倒插门去了韦家你就不是潘家的人。”
但父亲做好牺牲一切的准备。
父亲没倒插门,海口韦家也真没把前铺的潘家放眼里。他们当然把外公的话当圣旨,跟三小姐申明,真跟那个姓潘的小子,你永远不要进韦家的门。
那个夜晚,潘源远牵了潘庆娘的手,说:“韦美珍,事情由你决定,你是依了你父亲还是依了我。”
潘庆娘很坚决地说:“我跟你走!”
一对男女回到了前铺,父亲没按祖父的意思去做绳铺的掌柜,父亲去了镇上的学校教书。祖父有些生气,但儿媳给他生下个孙子,气就烟消云散了。后来又接连生了几个,更是喜上眉梢。
娘嫁到前铺就再也没回过海口的家。她当然想回,但外公是个倔性子,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收不回。外婆也想女儿,常常由大舅带了来前铺。外婆和大舅来时总要给五个外甥带许多点心。潘庆很喜欢那些点心,有一种特殊的清香,他对外婆家所在的那个城市的最初印象就是点心的香味。
外公不让他女儿女婿进家门,但没说不让外孙进。外孙身上有韦家的血脉,叫外孙但绝对不是外人。潘庆弟兄五个都去过海口外婆家,那条街叫水巷口,外婆家挂的是6号门牌。那是个深宅大院。第一次进那豪宅,潘庆猛吸鼻子。那时候正是秋天,他真的闻到那种点心的清香。其实不是来自点心,来自院里的那棵桂花树。潘庆那时才明白,花是可以作点心的佐料的。他回前铺后和娘说起那棵桂花树,牵动娘那根心弦,泪水就下来了。
但直到外公病重,娘才回了海口家里,看见外公时那个老人已经神志不清,嘴里只会叨叨了含糊不清的什么。然而,他说什么已经不重要了,捱了几天,外公过世了。
外公过世后两个月,潘庆却因为那个纸团,要来外婆家度过他人生中的最重要的时光。
外婆托人捎信到铺前,说你们来海口过小年。
娘看了信没说二话就收拾了准备带了老公儿子一大群回了海口的家。娘给外婆写信,娘说:“多好呀多好呀好些年没跟娘一起过年节了。”
一家人欢天喜地了,兄弟五个更是亢奋,他们从没到过海口,他们听说过海口,他们知道这有繁荣的街市也有很多人还有一家亲戚,但他们从来没来过。大的小的都很妒忌潘庆,怎么就他拈到那只纸团儿?
娘在信里说:“在海口过小年,在前铺过年,这才让我心安呀……”她抹了一下眼睛,眼睛那早已湿湿,那信笺也沾上了泪痕。“到正月我就把庆儿带来妈还有哥你们帮我管教好他哟。”娘在信中这么写。
腊月二十,娘就带了潘家兄弟五个来到水巷口6号。五兄弟欢天喜地了,海口到底是大地方呀,街多。除了水巷口,他们喜欢在那八条街子里蹿走,八条街都沾了个“兴”字,除义兴街外,还有大兴、福兴、彰兴、同兴、永兴、新兴、振兴。还有得胜沙中山路。不像铺前,就那么一条窄街,几间铺子。海口街多得很,铺子就更不用说,串一天你也串不完。得胜沙还有五层楼。那是潘庆来到这个世界看到的最高的楼房了。潘庆想,小年那天要疯玩个痛快。外婆已经给了这五个外孙期望,外婆说:“小年那天让大舅带你们去街上走,喜欢什么买什么,想去哪就去哪。”
但日本人没让人过好小年。也是小年那一天,从早就一直响着的爆竹,掩盖了西边那些轰轰炮声。直到前方撤退的国军士兵怆惶地从街子跑过,人们才知道小年过不成了,日本人的舰船在澄迈的什么地方泊岸,日本兵蚁虫样往海滩上涌。
日本人当然也不想让人过个好年,更多的是想利用国人过小年这么个时机。中国人对过年很有讲究,小年是一场“演习”,他们全力投入。中国的守军也一样有这种小年情怀,要比平常松懈很多。所以,这是个机会。
日本人选择在小年的前一天登上了这个岛子。没像祖父分析的那样,祖父说:日本人鬼精的很,他们舰船是虚张声势,显而易见,他们玩得是古兵法上的那一招,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哟。他们会找个偏远的港口进攻。
日本人没有选择偏远的海港,而是不可一世地直接由澄迈登陆进攻海口。澄迈紧挨海口,也就几十公里的距离。他们剑走偏锋,他们出其不意。
海口和其它地方一样,那时候家家正在准备年货,那时候街巷里张灯结彩,人人脸上张扬了喜气,没人想到日本人那么缺德那么阴险,挑了这日子来了。
家家户户都关门闭户,孩童们好奇,他们支了耳朵听,先听到“噼啪”喧嚣。他们扒开门缝看,硝烟漫起,然而那时候什么也没有,那些是街上人家放的爆竹。黄昏的时候他们才听到零星的枪炮声,不仅零星也并没有持久。门缝里看到街子上日本兵整齐地列队走着,踏得街石振动。
晚上,街上静得像坟场。外婆和娘挤一张床,他们睡不着,说着话。潘庆支了耳朵听。
外婆说:“我嫁来海口几十年了,腊月里从来没这么静过,什么声音都没了,就听得咚咚的心跳。”
潘庆听得娘说:“妈,静就静点,只要不交火就是菩萨保佑的了……交火总热闹吧?那是要死人的事。”
外婆说:“家里离天后宫近,我连了半年给天后娘娘上香哩。”
娘说:“我明天带了庆儿他们回澄迈。”娘是想,既然日本人来了没像先前传闻的那样两军生死交火,潘庆也就没必要呆在海口了。
外婆不干,外婆说:“你把庆儿留下来。”
娘说:“又没交火,又没枪子炮弹漫天飞……”
外婆说:“你让庆儿留下来。”
娘还想说什么,但外婆打断她的话没让她说,外婆说:“你离家这些年,只把娘抛在家。现在娘需要有个人在身边,你哥你弟都成天在外面忙……你就依了娘。”
娘没说什么,娘的声音哽咽了,“都是命!”她说了三个字。
娘跟外婆说:“妈,正月十五我一定把庆儿送过来!”
第二天,街上有人开门,后来大家都开了门,毕竟是小年呀,不能关门闭户的,打开门招财进宝,关门闭户的不吉利呀。他们试了开窗,没什么异样;然后就开门,也如往常,继而就小心地迈步出门,他们四下里看,好像一切都没有什么异常。一个两个的就试了出来,十个八个的就相跟了。平安无事,然后,街上又热闹起来人来人往。
潘庆欢天喜地,他当然愿意留下来,五兄弟都没进过五层楼,他们想进那地方。他们说那地方像给潘家的五兄弟盖的哟,一人一层。潘庆排行老三,当然是三层。他想像着在五层楼的第三层看海时的情形。五层楼正对了南渡江的出海口,看得到港口船进船出,也看得见西边出海口辽阔的海面。
日本人征用了五层楼,那是这座小城最高的楼,也是整个海岛最高的楼。
潘家兄弟没能进那张门,日本人占了那地方,当作了日本的宪兵司令部。他们也觉得那是个好地方,凡是好地方他们都想归为已有,不然,这些日本人来这个岛子干什么?不然这些日本人枪呀炮的攻城掠地为个什么?就是要把世界上的好东西归为已有。
日本兵荷枪实弹地在那布哨站岗。潘家五兄弟和街上的伙伴去了得胜沙,但看见日本的枯叶一样的冷脸汹汹目光和寒光逼人的刺刀,早早地收住了脚,在街角往这边看了几眼就没再敢往前迈一步,他们更没能登上五层楼。
总有一天我要进这门的。潘庆想。
第二章
正月十五一过,外婆就叫大舅去前铺接女儿女婿走娘家。当然更重要的事情是把潘庆接去海口。
大舅穿着身黑衣服,他好像一直穿的是黑色衣服,戴了顶礼帽。前铺的钱家阿公在榕树凿木头做龙骨,听得“突突”的声响。抬头,看见一艘小洋艇驶近码头。那艘小艇靠了岸,一个男人从舷窗里探出个头来,捏了礼帽神彩飞扬地朝那棵大榕树挥了挥手。那人就是大舅。大榕树下站着潘庆的父母和潘庆。父亲眉头皱了一下,他一向不喜欢这个穿黑衫的男人,但毕竟算是一家人。父亲挤了眼睛笑了一下。
大舅说:“我接你们去海口,正好运批货。”
父亲说:“日本人封锁了海面呀。”
大舅笑了一下,“我有通行证嘛,我运的就是他们需要的货。”
父亲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晚上吃饭的时候突然搁下碗问,“你给日本人做事?”
大舅眨巴了眼看了父亲好一会,“宏飞跟你说的吧?”宏飞是小舅的名字。
“很多人都在说哩。”
“怎么了?!说什么哩?”
“他们说你帮日本人做事?”
“帮谁做事不是做事?”
“可是……”父亲想说,可是那是日本人,是侵略者。但大舅没让他说出来。
“我是个生意人,这么一大家人要吃饭……日本人把住了生意,你不跟他们做就会饿死。”大舅说。
“街子上那些人是妒嫉我了。我在东洋呆过,学会了日本话。我和日本人做生意他们做不了,他们就说我汉奸卖国贼……”大舅说。
“是不是汉奸卖国贼我自己心里最清楚,日本人来了人还得穿衣吧还得吃饭吧?那各样生意还得做吧?日本来了谁家把店铺关过了?都开门揽客哩……这些人眼红我生意做得好指戳我骂我汉奸……”大舅说。
父亲还想说什么,母亲用眼色制止了他。母亲把话题转向了别处。她问外婆:“宏飞呢?”
外婆说:“初三就离家了,一直没见回来。”
母亲说:“大过年的,还东跑西跑的……”
大舅突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脸上神情暗淡下去。
潘庆觉得大人们的神情有些诡秘,这个春节不同往常,往常大家们的脸堆满了笑,一屋子的喜气绕梁而拥。今年像似有笑在,但笑里有着什么。
是什么?潘庆说不清。
父亲和娘在外婆家住了几天就走了,父亲说年一过,就要开学了,那边学校事多。父亲不想潘庆留在海口,他隐约为儿子潘庆担忧。但外婆却不肯,外婆说:“我舍不得离开庆子了,我也活不多长了,你把他留些日子吧。”
大舅也说:“现在海口一切都好,你倒要接走他,至少这里学校比那地方的要好哟。”
父亲说:“庆儿,你说是去是留?”
潘庆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他不知道该怎么说。他喜欢海口,这地方热闹,外婆和大舅及舅妈都对他挺好,他想留下来。但父亲母亲心思他是知道的,永远觉得自己的孩子在身边才放心,他看到他娘他爸的眼神,好像逼了自己表态。他吭嗤吭嗤了好一会儿,突然就从嘴里跳出几个字。
“我想留下来!”潘庆说。
父亲说得对,年一过,学校的门就大张了的嘴,那些孩童,饭粒一样涌进了学校,填满了每一个教室。
潘庆去的是一小。一小离家近,就在博爱北路路口,离水巷口一步之遥。
舅妈给他缝了只书包,大舅亲自送他去的学校。潘庆插班进了三年级,其实一年级三年级无所谓,日本人来了,开设了一门新课,他们要学日语,大家都得从头开始学。
大舅很那个,对什么都不是太放心,带了潘庆去报到注册,交费自然是大舅,还领了课本作业本。然后还带着外甥校长室呀督学室呀校监室呀地走了一遭,见人就说:这是我家外甥哩。潘庆理解大舅的心思,他是想今后让潘庆多受点关照。督学室里坐着两个日本人,大舅哇啦哇啦地和他们说了一番。看去他们很熟的样子。那是潘庆第一次听大舅说日本话。
走廊一角,潘庆扯了大舅的廨说:“原来你还会日本话呀?!”
大舅说:“当然呀,要不然日本人怎么叫我做商会会长?”大舅说这话时有点小小的得意,“所以说要多学点技艺,艺不压身嘛,多门技术多条路……庆儿你好好读书哟。”然后,大舅肥厚的巴掌抚摸潘庆的后脑。潘庆感觉很温暖,他喜欢被人这么抚摸。
潘庆进了一小,他读三年级。每天,他都要和马起方一起,从水巷口出发穿过一些细小的巷子去上学。马起方也住在水巷口,马家和潘庆外婆家一墙之隔,他们是邻居。马起方也读三年级,他们在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班。他们上学放学都一同穿街走巷。
巷子羊肠一样,马起方从小在那长大,熟悉那些迷宫一样的巷子。每回潘庆走走就迷路了,困在巷子里走不出去。潘庆喜欢捉迷藏,他让马起方找他,可到后都是他找不着马起方,躲躲潘庆就把自己躲丢了。马起方总是适时地出现,将他带出那些迷宫一样的窄巷。那以后,躲躲,躲丢了他也不急,他知道马起方救星样迟早会出现在他的面前。他从容地在那些变街曲巷里走,看那些榕树。他喜欢看墙壁上的树。海南这地方,老房子你常看见这么个景象,墙上长着树。外来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是谁把树种到墙上了?不是人种的那怎么就长出一簇两簇的榕树来了?其实很简单,鸟吃了榕果,就把榕子弄在鸟屎里了。鸟到处飞,飞飞就栖在老屋的瓦檐上了,挤出一粒两粒的鸟粪来,掉在墙缝里。雨落下来,顺了墙淌,那粒榕子得到滋润,就萌了根发了芽,天长日久,在壁上长成一棵榕。铺前也有壁上之榕,但没像海口那样,一长溜的墙都长了榕树,像壁上的森林。潘庆看老墙上榕树看得痴迷,也忘了来路,迷路是注定了。他怎么走都走不出那迷宫一样的巷道。
每到那时候,马起方总能幽灵一样出现在他面前,所以他很佩服马起方。潘庆说:“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
马起方笑了:“也没什么奇怪的,我早先这条巷子要迷路一准是在这……你多迷几回就不会迷了。”
果然如马起方所说,过不久,潘庆把那些巷子跑得烂熟,就从不迷路了。
几个月很快就过去了。父亲不放心潘庆,来过几次海口。父亲问起学校,潘庆说:“很好,很好呀。”父亲说:“和前铺学堂不一样吧?”潘庆说:“不一样不一样,怎么能跟那地方的一个样呢?”父亲哦了一声,说:“看样子你还是喜欢学校的,喜欢就好。”潘庆知道父亲的来意,他担心自己的学习。父亲把读书看得高于一切。但潘庆说的不一样不是父亲所想,这里的学校和在铺前完全不一样,在铺前,小学校里人不多,父亲在那当校长,对潘庆几兄弟的管教就格外的严。校长的儿子不守规矩,德行操守不如人,那父亲这个校长怎么做?五个小子,个个都顽劣调皮,是那种无事生事,有事翻天的角色。家里守族规有祖父管教,学校守校规有父亲管教。所以,在学校父亲成天对他们板了张脸,在家里祖父也成天板着张脸。他们家里学校里都做缩头乌龟。但潘庆来了海口,总算解脱了。“喜欢加用心,读书才能有长进。”父亲说。
父亲来的那天,小舅正好从外地回来了。小舅对那个叫姐夫的男人说:“光晓得读书,装一肚子诗文有什么用?国将不国了哟……”小舅一脸不屑的蔑视神情。除了看外婆有笑脸,看谁都像借了他的米还的是糠。
大舅对妹夫说:“你别理他,他就那么样。”
和小舅不一样,大舅看谁都一副笑脸,何况他还长了张菩萨脸,眼睛鼻子全那么协调,就是胖也胖得恰到好处。那张脸讨人喜欢,那张嘴更是讨人喜欢,能说会道不说了,声音轻柔,神态舒缓,举手投足全一副大家气度。别人说日本人找大舅做事,可能就是缘于这些原因。日本人要“维持”治安,找的就是人缘好,遇事能服众的人。
如果说潘庆不喜欢小舅,那可能事出有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小舅似乎不喜欢他。整天绷着脸的小舅从来不主动跟潘庆说话,这让潘庆感觉很不好。他不知道为什么小舅整天绷了脸,他也弄不明白只要大舅小舅两个亲兄弟坐在一起总是水火不容。在潘庆看来,责任来自小舅,小舅总要凶巴巴地和大舅说话,而大舅总是笑而不语,或者简单轻柔地地低声说一句两句,一忍再忍,总是笑脸。何况小舅总是行踪诡秘。做贼才那么个样子呀。潘庆常常这么想。昼伏夜出,神密莫测,总是弄出一种神神鬼鬼的样子,实在让人喜欢不起来。
有时间小舅也会对潘庆温柔一下,摸摸潘庆的头,然后大眼睛一动不动看了潘庆,那么叫一声“庆儿!”,可是那时潘庆心里已经对小舅有了成见,因此回避了小舅某种目光,那种成见在潘庆内心根深蒂固。不过,那种时间很少,小舅总是来去匆匆,就是见了外婆,也是那么几句常规客套的话。
不过在潘庆看来,喜不喜欢小舅在他并不重要,因为小舅不常在家,他似乎只是韦家的一个客人,隔不多处会上门一下。潘庆关注的最多的是他的学校,与他生活和成长息息想关的是他的学校。
可是,潘庆很快就不喜欢学校了。学校新是新,但新得离奇。每天进学校大门,就要给那面太阳旗行礼,还得给老师校长和高年级的同学行礼。繁琐得很不说,还不能马虎。行礼时,双手自然下垂,双脚并拢,手指并拢,随着腰部的弯曲,身体向前倾。给校长行礼和有身份的贵客行礼时还格外不一样,那叫大礼,腰须弯到脸部几乎与膝盖齐平的程度,然后缓慢直起身子。不能太快,太快了说你心不诚;也不能太慢,太慢了你腰就挺不直了。每天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做这个动作,学校要求在家也要跟父母行大礼,出门行礼,进门行礼。当然,潘庆他们一进家门就不管那一套了。礼是中国人最起码的做人规矩,但到日本人那,就夸张了,弄得成了一种形式,假模假样的。
校长是个日本人,不常来学校,每周一来训一次话,一口的中国话,让人一时想不起,他是个日本人。校长一来,大家都要给他行大礼。那时候,督学那双眼睛就在队列中扫,谁要是动作做得不到位,他记得一清二楚。放学时会叫到惩戒室训话,然后让你“长见识”。让你挨竹片或是抽脸,其实就是体罚。
其实学校的日常管理,就掌握在几个督学手上。
督学也没什么好的办法,他们依赖惩戒室。其实可能会有很多种办法开导和训育学生,但他们不愿意用更多的办法。他们觉得惩戒室很管用。
惩戒室里名堂花招不少,主要有两样,一是单个一人犯错时,督学罚做一百下俯卧撑。别看那动作简单,但要真做下来其苦不堪。两个人以上,那就是立下了互相扇耳光。扇一下嘴里还要伴有喊声,眼睛不能斜视,要专著了看对方的眼睛。
督学不止一个。
督学中的一个是个台湾人,人长得瘦瘦长长,却也一脸的斯文,戴一副眼镜,看去像只螳螂。虽然是台湾人,但一板一眼照日本人那套做,撸起人来凶得很。他名叫吴善萨。学生背面都叫他散沙,后来就引申叫沙皮。据说那些来岛子上的日本军队中大多是台湾人,这让学生和大多居民都难理解。台湾不是中国的吗?那些人怎么穿一身日本人的衣服?端了日本的枪举了日本的旗杀自己的同胞?那些台湾人见了日本人还低三下四的。他们想了很久,想不通。他们想,大概是被逼了来的吧,但看上去却不像。小舅说:“这有什么?做了亡国奴,有一天你们都会这么个样子,成了人家的一群狗!”大舅却说:“话不要说得那么难听,台湾是台湾海南是海南……”小舅却双眼通红,大了喉咙说:“不把他们赶出海岛赶出中国迟早全国人一个样!”他们吵起来,直到外婆出现,兄弟俩才住了声。
潘庆那时弄不明白他们吵个什么,但在学校看到那个台湾人不舒服。不仅他,学生们都不喜欢吴善萨。
“沙皮!沙皮!”有一天督学吴善萨从大家面前过,谭浩飞冲了那背影喊了两声。潘庆歪了头疑惑地看着谭浩飞。
谭浩飞只是笑,“就是呀,叫沙皮……”
有人点拨潘庆,“不是有种狗叫沙皮的吗?”
潘庆也笑了,“是哟是哟……可他更像螳螂的呀,不过应该叫他沙皮……”
谭浩飞坐教室最后一排,因为个头高。在班上能做孩子王却不是因为他个头,是因为他家在老街上卖凉茶,是大家夏天喝的那种消暑茶。也是怪了,老街上做什么生意的都有,药铺当铺南货店绸布店……那些看去都是赚大钱的生意呀。可谭浩飞家卖茶水卖了几代人,靠那一杯黑黑的凉茶发了家在老街上置地建屋,那杯茶能做出名堂真是让人百思不解。人家说谭家有神灵扶佐,不然那么一杯清茶能发家?但老辈人不那么说,老辈人说,你制一碗茶试试?苦是苦,但喝后苦尽甘来,舌面久久津甜不绝,不仅消暑解渴,还泄火。说起功效。街上人说起来头头是道:清肝明目,益胃健脾;散瘀消肿,利湿退黄……还哪是茶哟,就是一味神药。其实街子上人还真就将其当作药,家里有人遭风寒感冒,说,去谭家茶摊喝凉茶去。连喝两天,热退了鼻子通畅了四肢也不酸胀了……
谭浩飞常带了班上同学去他家喝凉茶。他爸很大方,凡谭浩飞带去的人喝茶不收钱。谭浩飞的威信就是因他家的茶树立起来的。没人不对他家的茶馋,就是日本人在海南最高指挥官太田奉汤佟也对那茶衷情,不然怎么成天板着的那张脸一到谭家茶铺前就松驰了,小眼睛眯了笑。“大大的好。”他朝谭浩飞的爸翘拇指。第一回谭掌柜还不知所措,搓揉了一双手,嘿嘿了。司令官向他行个礼,谭掌柜也跟样回了个礼。“大大的好!”日本人说。谭浩飞的爸说:“好……好。”他们成了朋友,人们见那个叫太田奉汤佟常常坐在茶铺的那张竹椅上和谭浩飞的爸聊天喝茶。长官常去,那些日本人也都三五成群地去。有人不知道具体来路,觉得谭家势力真大,有日本人撑腰。所以,谭家的名声更加大了,生意也越来越好。
也因此,谭浩飞在学校很放肆,督学和老师对他常常网开一面。
他给督学起了个外号叫“沙皮”,而且时不时指戳了督学吴善萨的背影做着鬼脸,“沙皮沙皮”那么叫,常常引一大片的哄笑。
很长时间,督学总觉得自己身后的笑声有些放浪且有所指,但听不出所以然。
那天,他又听到“沙皮”两字,然后是一大片的笑声。
他摇摆了瘦长的身子走到潘庆他们身边,伸长脖子瞪大小眼往每个人脸上那么看。
“沙皮?!”他那么说出两个字来。
潘庆有点紧张,那些学生除谭浩飞外都有点紧张。他们偷偷往谭浩飞脸上瞄。谭浩飞笑笑,朝督学吴善萨有模有样的行了个礼,说:“是个老师,我们在说英文哩。SharPei,怎么样?我发音还可以吧?”
督学吴善萨是日文老师,他不懂英文。他看了看大家,带一脸的茫然走开。他支了耳朵,想捕抓那些放肆而开怀的笑,却没有。待他拐进巷子,才感觉后颈和肩背地方精灵样一些东西在跳,那些笑终于拐着弯扑到了他的身上。
第三章
潘庆最喜欢上的是生物课,生物课常常走出课堂到野外去这是一个原因,最重要的是老师。
教生物的老师也是日本人,叫原田志乃。潘庆和大多数同学开始也不喜欢这个老师,凡日本老师,他们都本能地抵触。何况原田志乃先生长得小眼睛大鼻梁那张嘴嘴角还有些歪斜,就是说长相很丑,人都不喜欢那张脸。再说,人丑点其实没什么,笑就像花,丑脸上多挂些花呀。原田脸上什么时候都一副刻板表情,眼珠儿也少有蠕动时候。只有看见小虫小草,只有到了野外看见花草树木,原田的眼睛才灵动起来。原田一口标准的国语,他和你说中国话你根本看不出他是日本人。原田身后还常常跟了个尾巴,是个日本男孩,据说是从大洋那边带来的。男孩瘦瘦小小,但和潘庆他们一般大,也正读三年级。这个日本男孩叫青木未央。原田叫他青木央,同学们却在后面加了个字叫他青木央央,其实不是央而是秧。秧秧是指小苗苗,意思是这个日本男孩就是根不起眼的嫩苗苗。
他们都不怀恶意地在那个日本男孩后面喊:“青木秧秧……青木秧秧……”但青木未央少有回应,那是个寡言少语的男孩,整天跟屁虫儿一样跟在原田先生的后面,就像原田的一只影子。
谭浩飞说:“原田先生,这是你家公子吗?”
原田笑着,说:“你觉得呢?”
谭浩飞说:“我觉得像,不然我怎么会问起你呢?”
原田说:“你也不看看两个人的姓,中国人也讲姓氏的呀。”
谭浩飞说:“那也不一定的呀,万一是拖油瓶呢?”
原田的中文不错,可他却不懂拖油瓶是什么意思。女人没了老公改嫁带了孩子过夫家,孩子就叫拖油瓶。起先大家以为是原田的儿子,可名字却看出端倪,就猜想原田老婆一定是个改嫁到原田家来的女人,连了前夫的儿子一起入门了。原田是个继父。后来大家知道,其实什么都不是,青木未央是原田在日本收养的一个孤儿。原田要来中国,也就把青木央央带了来。
秧秧读书很认真刻苦,但学习成绩却平平,不只是平平的事了,常常在班上属倒数一二。他最好的功课就是日语,但他不能因此平衡呀。日语他娘肚子里一直学着的,是他母语,在一大群初涉日语的中国少年里,他当然优势显著,鹤立鸡群。但除此外,别的功课大多平平,很符合他个头长相,属班上最未最后。
但秧秧对荣辱似乎无所谓。对来自任何人任何方向的指戳眼色均反应平平,甚至有几分呆滞。没人跟他玩,他也不愿跟人玩,除了教室,他多呆在西苑里那间小屋子里。西苑不是花园,是几栋日式的小屋子组成的院子,有一处花园包拥,小花园又为院墙包拥。地处学校的西面,日本人给起了个名叫“西苑”。院墙和屋墙,用的是火山石,那种石头看去坚硬而阴冷。那是学校专为那几个日本藉教师修建的。
那种屋子潘庆他们没见过,据说里面也和海口民居的摆设大不相同。有种叫榻榻米的东西。潘庆和同学真以为是个什么物件,比如类似桌椅锅盒什么的日常用品。他们很好奇。学校规定中国学生不能轻易去日本老师的住所,有事情就去老师办公室不能去西苑。
潘庆几个总在西苑那探头探脑,沙皮见了,总是喝斥,“看什么看,贼一样哟!”只有原田朝他们微笑。
“你们看什么呢?”
有胆大的就回答原田,“他们说里面有榻榻米,我们想看看榻榻米……”
原田笑了笑,朝他们挥了挥手,“来吧,你们看个够。”
他们就进了西苑,然后看见了榻榻米。
“那没什么嘛,不就是一垫子?”有人说。
“就是就是!”大家说。
然后,原田没说生物,他给他的学生说榻榻米。
“就是就是,就一垫子你们没说错。”
他说榻榻米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就是房间里供人坐或卧的一种家具。是盛唐传统房间“和室”铺设地面的材料,传至日本后演变成为其传统房间内铺设地板的材料,成为日本家庭用于睡觉的地方,即日本人的床。
从原田的嘴里他们知道,传统的日本房间没有床,也不使用桌椅板凳之类。就只榻榻米,晚上在上面睡觉,白天把被褥收起,在上面吃饭和进行各种活动。客人来了,坐在上面喝茶交谈。所以,一进日本人的家,一定要脱鞋。不脱鞋就如穿鞋踏在我们中国人的床上一样。日本人十分喜欢“榻榻米”。
他们说原来榻榻米就是日本人的床呀!
他们说原田老师你真好。
开学之初,大家对原田没什么好感。不仅原田,对大多日本老师都没什么好感。那是入侵者,他们占我们的城池,杀我们的同胞,能好感得起来?
潘庆生物课的第一天,就给原田老师弄了点事。
他把那只铁盒子放课桌一角,是药店里装丸子的那种小铁盒。这没什么异样,他们常常用这种盒子装铅笔橡皮什么的。潘庆前面坐的是蔡其伟,是老街上“泰昌隆”家的公子。“泰昌隆”是家旅店,蔡家财大气粗,但这个蔡家后人却很柔弱老实,常常是人欺负的料。但蔡其伟却是个逆来顺受的人,什么事都笑呵呵的。他还有个毛病,好动,平常手脚不安分。你说一个柔弱的小人儿,手脚老那么动着干什么?不是常常莫名惹事端吗?他不在乎,似乎惹了事端就惹人注意了,在人眼里了,不然,他怎么老笑?
开始督学老找他“麻烦”,拉去惩戒室“教训”。他依然是那么种不以为然。“沙皮”曾火冒三丈,亲自动手狠抽了他几个耳光,一边脸都打肿了。
蔡其伟他爸找到学校,他算是个有身份的人,所以校方很慎重。校方说,这事由善萨督学跟你谈吧。
沙皮就把蔡其伟他爸领到一间大屋子里。屋子空空荡荡,有些幽暗,窗子被掩了厚厚的帘子。海南是一年皆夏,一雨成秋的地方,整天的晌晴曝日,怎么就闭门掩窗的?弄得奇热难当,还有那么点阴森森感觉?那就是学校的惩戒室。沙皮别出心裁,把蔡其伟他爸带到这地方来,首先让对方心理上被影响。
沙皮跟蔡其伟他爸说你家儿子如何如何……
蔡掌柜说:“我都知道,他天生中了邪魔……就是人说的鬼上身驱不去,整天都那样……你总不能把他杀了吧……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哟……”边说眼泪边在那双老眼里打滚。
沙皮说:“原来是好动症呀,你们没请郎中看看。”
蔡其伟他爸说:“请了怎么没请?郎中给了药,吃了没用。叫神婆也来过,神婆说就是中邪了。邪魔附体附个紧,要个三五年才能挣脱哩。”
沙皮说:“哦哦……那就只有这样了,顺其自然。”
他们的谈话以这种结论结束了。于是,很多老师对蔡其伟的好动视而不见。
蔡其伟再也没挨训也没挨抽。
就是上课蔡其伟也难得安分,前面的同学戳戳,没人理他他依然不停有动作。趁老师回身写黑板,蔡其伟老回身弄事,说借个笔呀借个什么的。
今天当然也不例外,果然动了动了就回过头来,蔡其伟的手就伸向那只盒子。潘庆装了没看见,其实盒子里今天装的不是文具,盒子里装着的是只毛虫。
很快就听到蔡其伟的惊叫声。他最怕的就是毛虫。
课上不成了,同学都站了起来往蔡其伟那边看,看不见什么,他们眼里都是惊疑,一片嘈杂。
潘庆往原田先生那边看,原田推了推眼镜走了过来。他小心地从盒子里拈出那只毛虫,周边响起一片嘘声。原田那脸依然那副表情,他摆了一下手,示意大家坐下来。大家重又坐回坐位上,教室也安静了。
原田站回到讲台上,他举了那只毛虫。潘庆以为会有风暴,但风平浪静。
“一只毛虫。”他说。
“好!好!正好过几天我们要讲到这个……”他说。
他叫人找来只罐头瓶子,然后一节课上成了玩耍。他到学校的园子里摘了些树叶草叶,把虫和那些叶儿都放进了瓶子里,瓶口用一块透风的纱布蒙了。谁也没明白这个日本人玩个什么名堂,他竟然找来根绳,把那只瓶子不高不低在悬在黑板上。
潘庆没弄成事让那个日本人尴尬,倒像是被那个叫原田的老师把大家都捉弄了。
潘庆他们的心思都在那只瓶子上了,那些天,进出教室谁都踮了脚往那看。
有人说:“虫子好像吃草叶哩”
“哟是哟是哟!”
“毛虫长肥了你们看是不?”
过两天又有人喊:“毛虫不见了你们看是不?!”
还真不见了,那瓶里出现的是一截棕色的硬壳,但依然在里蠕动,嘴里似乎不断地吐了丝丝,那些丝丝把自己缠了。
原田终于讲毛虫了,他说:“今天我们说说毛虫的一生。”
没人吭声了,大家都被那个丑模样的老师吸引,“你看它现在成为蛹,蛹不吃也不动,但在壳内发生着剧烈的体态变化。”
“你们过几天后看看它会是什么样?”
有悬念留在那些孩童心里了,那些天他们谈论的都是这桩事。进出教室都齐心往那只瓶子里看。他们又惊惊诧诧地喊着叫着。
“看喽看喽……看到那薄薄的丝破了喂……”
大家就看,那棕色的壳儿真破了,拱捅有东西。折叠的湿润的纸片一样的东西,后来就全展开了,成了张有彩色画纹的“薄纸”,后来他们都看出来,那是两片翅膀,那是只蝴蝶。
原田又来讲课了。
他说:“你们都看到了,你们也都参与其中了,虫子的一生大致都是这样一个蜕变的过程。”
他将瓶口纱布解下,用指尖小心地拈了蝴蝶,放在自己眼前看了好一会,又走到大家中间,让大家看个明白,然后原田把那只蝴蝶放在巴掌中间。所有的人都屏息静气,教室很安静,安静得掉根针都能听得到,他们视线绳儿样拴在那只蝴蝶上。
那只蝴蝶在原田的掌心挣扎了,扑扇了几下翅膀,翩翩飞舞了起来。在教室里绕了两圈,飞飞就飞出了窗子,飞向那片绿色。
教室里众人齐齐地“吁”出了一声。
原田说这课就上到这了,你们写点你们想说的话吧。
又是异口同声地一声“吁”,潘庆他们就大眼小眼地瞪了台上的先生。这就叫上课?你也没讲几句话呀。他们想。
那天,潘庆写满了两张纸,他从没写那么多字。大舅那天看了潘庆写的东西,一脸的惊诧看了外甥好一会,“哦哦!庆儿真有长进了哟,看来到海口读书真没白来……”
还有,蔡其伟竟然安分了,手脚没那么动来动去的。潘庆想了想,这几天上生物课,蔡其伟就没乱动过。
潘庆他们虽然不喜欢日本老师,但却有个例外。其实在原田之前,他们最初却很仰慕一个叫牧野的日本督学。
开学之初,早操时草坪里站满了人,学生排了整齐的队伍,那边老师就过来了。只要牧野一出现,学生那整齐的队伍必定会有些乱,大家都把头偏向那个方向。有人嘴里不由自主就发出“啧啧”声。开始潘庆他们不知道那个日本人脸上有什么东西吸引他们。是牧野脸上线条特别?那是,呈一脸的英俊不说,还透现刚毅。可想想,又觉得不是。是他的头发?头发确实有特色,一般情况下牧野都戴了一顶军帽,看不见他的头发,可他摘了帽,那头头发则让人眼睛一亮。寸长的头发油黑发亮。发式特殊?想想,也不是。牧野喜欢穿一身军装,天再热也要把上衣的每一粒纽扣都扣个妥贴,脚上还套了双军靴,这军装也确让人精神。可潘庆他们想想,也不对呀,满大街都是日本兵,怎么那些人穿了同样的军服没有让人侧目的呢?
潘庆观察了很久也想了很久,后来想出点眉目,是因为牧野身上某种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吸引大家。
大舅有次问潘庆,“喜欢你们的老师吗?”
潘庆摇了摇头。
大舅说:“总有喜欢的吧?”
潘庆想了想,终于点了点头。
“谁呀!”
潘庆说出了牧野的名字。牧野不知道是因为外貌或者说身上的什么东西,在小小的海口显得很特别,是经常被人说到的人。大舅小舅都知道他。
小舅听了潘庆的话,猛地跳了起来,“怎么可能?!你怎么会喜欢这么个人?你怎么能喜欢上这么个人?!”小舅的嗓门很大,这举止让潘庆吓了一跳。
潘庆怯怯的,看了看小舅,不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大舅外婆也很诧异。
小舅愤愤也汹汹,“狗东西,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你看庆儿他们都接受了什么哟?”
潘庆依然很茫然,连大舅也一脸的茫然,外婆则不住地摇头。
小舅说:“那畜牲身上的武士道精神还有那身狗皮欺骗了你们哟……庆儿,我看这学不上也罢哟,在那种学校会越学越坏的!”
外婆说话了。外婆脸都气歪了,“鬼话!自古来哪有不读书的?!进学堂知书达理开智晓事,哪有叫后人不读书的?!”
小舅说:“我没说不读书,只说不要读害国害人的书。”
外婆说:“什么叫害国害民?!识文断字是本事,你看你个宏飞哟,你不安份读书,你还让你家外甥也不好好读,难道都像你这样成天在外晃荡,也不知道做些什么事情游手好闲……”
小舅说:“妈,我是你生的儿子,不会让你丢脸,我做的事为国为民光明正大。”
“你要是有你哥一半就好了,妈也放心了。”
“他算个什么?听听外面都说他些啥哟……我都替他丢脸……”
外婆哭起来,外婆挥了挥手示意小舅离开她身边。
学校还设有柔道和剑术,教授这两门的也是牧野。每到这时,牧野总是格外的亢奋。因为柔道和剑术,他都学有专长,曾经在某个级别的比赛中拿过冠军。所以,他一进入那种场所,更是显得神采奕奕,更是吸引了潘庆他们的目光。而那些来自学生的倾慕神情,也更让牧野精神焕发。
柔道和剑术,每一堂课都上得很精神。牧野很得意,一切都在按他的意愿进行着。他跟原田说:“我们在支那办教育,最核心的是要把支那人驯服,让他们的后人绝对忠于天皇,永远为大日本帝国所用,造就精英式的良民。”原田显然对这话不怎么认可,总是淡淡一笑:“是吗?”他说。
“怎么?!”
“你是想把他们驯化成战争机器……”
“怎么?原田先生,这有错吗?”
“到那一天,战争也就结束了,世界大同,都是大日本帝国的天下了,不会再有战争,要的只是科学……”
牧野无语以对。天皇要的就是这目标,天皇旨意里也有这说法。他不能说原田说得不对,你看军队势如破竹,看情形不出半年,整个亚洲全在大日本之手。到时候还真用不了军队了。
可他对原田的存在很不满,甚至有点恨意。
但牧野很长时间都是潘庆他们的偶像,要不是原田,可能一直是他们的偶像。
那是后来的事。
(本文为同名小说的前三章。)
责任编辑:魏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