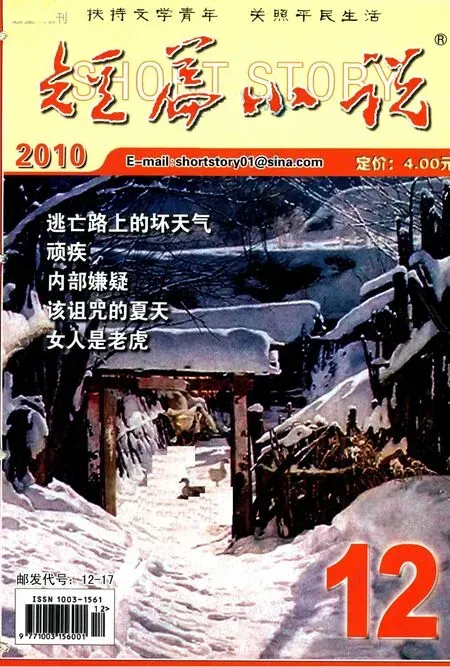三叔那些事
◎刘学兵
三叔那些事
◎刘学兵

多年以前的一个凌晨,父亲打来电话,说三叔走了。
我听了电话,心里没有一丝悲戚,也没有某种失落,好像一个完全和我不相干的人从这个世界消失一样。
父亲在电话里催得很紧。让我们尽快回家。
我看看时间,都快一点半了。我说,是现在吗?
父亲说,就是现在。立即,马上,火速。
我说,哪里去找车?
父亲说,打出租。说完便撂下了电话。
放下手机,我怔怔地说不出话来。三叔这个人,怎么说呢?一向,他是很多人眼里的英雄,可是也有人叫他流氓,说他生活作风有问题,道德败坏。总之,三两句话说不完。我和他谈不上有很深的感情,在我没有外出打工之前,为了他那个商店的事情,我和他还吵过一架,有一次甚至还差点动了手。那时他已经快五十岁了,而我还正年轻,我相信他不是我的对手。尽管他是英雄,但已是英雄迟暮。坦率地说,三叔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个人,他独身一人,却养了一大群鸡,一大群鸭子,他既要张罗他的商店,又喂了四头肥猪,既要给一个面粉厂销售挂面,又要种地里的庄稼。他的每一天都是在忙碌中度过的。有时候到了深夜,我还能听见他在唱歌。那些年,我好像从来就没有感觉到他有什么忧愁。即使是他最喜欢的手表,被和他睡觉的女人顺手拿走,他也没有去计较过,沉默着,任由那女人戴在手上炫耀。他生性豪爽耿直,为朋友不惜拍胸脯,事发东窗也不会拍屁股逃之夭夭。他喜欢喝酒,经常酩酊大醉,倒在路边一直睡到月上树梢,才跌跌撞撞地回家。他一生经历了无数的女人,却没有一个和他血肉相连、息息相关的女人。也没有一个女人真正属于他。
时值寒冬,我和爱人站在大街上等车。爱人禁不住浑身直哆嗦,也不知道是由于太冷,还是由于害怕。站在大街昏黄的灯光下,我们嘴里哈着寒气,等着出租车载上我们赶回老家,赶回遥远的乡村,去送三叔在人世间的最后一程。
我的三叔名叫刘志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用现在的话来说叫牛逼。人们不叫他刘志荣。都叫他大刘。大刘长大刘短的,后来干脆叫成了大牛。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这么叫。在家里,爷爷,大伯和父亲也这么叫他。
三叔在全村人的记忆里是以英雄的身分出现的。
在没有成为英雄之前,三叔其实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小混混,好吃懒做,好逸恶劳,经常和爷爷唱对台戏,爷爷叫往东,他偏要往西,爷爷要向上,他偏要往下。一个钉子一个眼。气得爷爷开口闭口都是对他的臭骂。三叔和大队那帮知青打得火热,经常出去偷人家的鸡、鸭、鹅来改善生活。有时候甚至连狗、猫也偷。三叔能当英雄,完全是一个偶然。那天三叔和几个知青偷吃了人家的一条狗,回家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那是一个月圆之夜,月光在四周铺了白茫茫的一片,雾气已经开始四散流淌,草丛里的虫儿也叫累了,打着哈欠进入了梦乡,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三叔摸了一下肚子,心里就想,叫吧,下一个就是你。然后,三叔打着饱嗝,用指尖在黑暗中剔着牙缝里的狗肉,心满意足地往家里。一边走,一边还冥思苦想,如何在爷爷开门的时候编造一个谎言来瞒天过海,逃过爷爷的责骂。在经过一片树林的时候,三叔听见了砍树的声音。三叔悄悄地走过去,发现一个人正紧张地挥动着柴刀砍着一棵柏树,飞舞的木屑惨然遗落在脚下的草丛里。地下,静静地倒着几根还未除去枝桠的树木。
那一年,三叔二十一岁。
那一年,偷树的秦德才遇到了偷吃狗肉后回家的三叔。虽然都是偷,但是性质不一样,这就注定该秦德才倒霉。三叔年轻气盛,又刚刚补充了粮草,正义的力量遍布在三叔的全身。他跳出来一声大吼,就和秦德才扭到了一起。秦德才不是对手。慌乱中,秦德才的柴刀把三叔的屁股划了一个口子,鲜血直流,片刻就湿透了三叔的裤子。可是,三叔并没有退缩,他像一头受伤的雄狮,疼痛激发了他的斗志和豪气。三叔咬着牙夺下了秦德才的柴刀,把他摁倒在一个水沟里成了落水狗。
三叔从小的理想是当兵。他喜欢唱再见吧妈妈,再见吧妈妈,军号已吹响,钢枪已擦亮……常常唱得如痴如醉。他最佩服的英雄就是王成,想象着自己有一天也做一个像王成那样的英雄。有时候做梦三叔都在叫向我开炮向我开炮,悲壮而豪迈。可是,三叔愿望没能够实现。那年大队的新兵名额被精明的大伯抢走了。大伯戴着大红花,昂起头,脸上的笑容比地里的豌豆花开得还要鲜艳,比稻田里沉甸甸的谷穗还要稳重。他胸挺得老高,从三叔身边走过去的时候,明显地带有一股霸气,让人顿生敬畏。三叔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稀里哗啦地流了一脸,然后砸到脚上,打湿了三叔的布鞋。大伯当兵的地方是西藏,他在信里每次都提到西藏的山有多么多么高,天空有多么多么蓝,白云有多么多么的白,就像地上的羊群,从身边一直铺向远方,说眼睛都看痛了,都看不到边。看着大伯的信,三叔越发懊恼。他发誓说,这辈子当不了兵,但一定要摸一摸枪。
现在,三叔终于摸到枪了。
在批斗秦德才的大会上,三叔英姿勃发,风光无限。他的肩上挎着一支步枪。整个大会上,只有三叔一个人肩上挎着枪。那支步枪很长,三叔挎着枪的时候,枪托都差点掉到了地上。我还看见枪的上面有刺刀。那一天阳光夺目,三叔枪上的刺刀在夺目的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在铺天盖地的口号声中,三叔手里的绳子像蛇一样敏捷地游动着,不一会儿便把秦德才五花大绑了。秦德才的头始终低着,头发很长,我看不到他的脸,我只是看见绳子深深地勒进了他手臂上的肌肉里。这个样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于在以后的好多年里,强盗小偷在我的心里就是那副长头发、深深地低着头的样子。
秦德才因为偷集体的树木,被判了三年徒刑。而三叔呢,从此便风光起来,比大伯当兵戴大红花的时候还要神气。
每次三叔从外面回来,爷爷都会指着三叔破口大骂一通,把满腔的怒气和一口的酒气撒到三叔身上。但是,三叔在人们的眼里却是英雄,因为他抓住过坏人,还因为他挎过枪。所以全村唯一的商店毫无争议就落到了三叔的手里。大队书记说,一个可以用鲜血和生命保护集体财产的人,他一样可以用鲜血和生命来保护集体的商店。于是,以大队长女儿为首的一帮姑娘不得不打消了念头,只得老老实实下地干活儿。
这是个美差。
首先是轻松,不用下地,不用肩挑背磨,不用日晒雨淋,整天只管坐在商店里,卖多卖少不管,能不能赚到钱,可以忽略不计,报酬更是令人垂涎三尺,每天记五个工分,每月补助四元。这个美差像绳子一样拴住了三叔。他每天都老老实实呆在商店里。
三叔的好日子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那段时间城里流行一种款式的裤子,叫喇叭裤。按当时人们的说法,穿喇叭裤的人都是流氓。然而三叔却是全大队第一个穿喇叭裤的人,裤脚罩下来,几乎罩住了鞋,走起路来一扫一扫的,扫得地面上尘土飞扬。那个喇叭裤还是花格子每个格子一种颜色,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在那个时候简直是惊世骇俗。花衣花裤是女人的专利,对于男人来说,那就是异类。人们能够接受三叔是异类,却不容忍别人这么穿。三叔是英雄,为集体流过血,敢于流血的英雄都是与众不同的。于是经常就有人看见三叔穿着花花绿绿的裤子衣服站在商店门口东张西望。后来,三叔告诉过我,他说他是在望秦多多。在全大队,三叔还是第一个戴手表的人。这让所有的人比看到他穿花花绿绿的喇叭裤更令人惊讶。那块手表很精致,在手腕上很扎眼,仿佛那只手也越发地显得珍贵起来。我至今记得,那是一块山城牌的手表。我常常摘下他的手表,放在耳边,听那秒针转动时滴答滴答的声音,悦耳极了。他生怕我不小心掉在地上给他摔坏了,把手表递到我手上的时候,还把我的手连同手表紧紧地握一下。说,拿稳。我说拿稳了。他说,你说,这手表,多少钱?
我不知道一块手表到底值多少钱,手表和钱的概念在我的脑海里是模糊的。在我的眼里,十元钱就是天文数字了。为了不使三叔失望,我还是尽量往天文数字上靠。
我说,九元吧?
我的口气一半是猜测,却又带了一半的肯定。
三叔哈哈哈地笑了。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少了。他轻描淡写地说,然后,他走了。两只裤脚在地上扫起一片灰尘。
后来我才在父亲那里打听到,三叔那块手表价值六十多元。我还感觉到父亲的口气里也充满了羡慕。
但是我更多的却是不解。不就是时间嘛,早上太阳把大树拉得长长的,中午太阳把大树揉成一团,像揉一堆面团,晚上太阳又把大树拉得长长的,太阳和大树就是时间啊,何苦花六十多元来把时间看得那么清楚呢。
爷爷似乎总是对三叔有成见,见到三叔就会没来由地发火。在他的眼中,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儿子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爷爷的火气很旺,他直拍桌子,眼睛里好像要喷出火来,胡子一根一根地颤抖着。大牛!刘志荣!再过十年,再过十年我要是不死……再过十年……
三叔在旁边的时候,爷爷的话都是留着不会说完,等三叔离开后,他才咬着牙把后面的半句话狠狠地吐出来,再过十年,我要是不死,就能看到你还有没有今天风光!
事实上十年之后三叔依然很风光,而且把生命活得奇迹般的辉煌。
爷爷没有看到三叔的衰败和落魄,就无奈地去世了,咽气的时候还没有忘记直起身子说最后一句话。
算你龟儿狠……
三叔在我眼里是不可思议的,他把自己的房间布置得如天堂般华丽无比。尽管这个房间的外表斑驳,甚至刮风的时候还能从墙缝里透进来丝丝凉意,根本无法和现在的小洋楼同日而语。但是,屋里面的摆设却令人惊讶,令人羡慕,令人流连忘返。我终于知道秦多多为什么走进三叔那间屋里不肯离开了,那间屋子里有魔力呢。有一次,我听见他们在屋里说话,我一头冲进去,发现他们抱在一起,鼻子对鼻子,眼睛对眼睛。原来男人和女人还可以这么抱在一起啊。我说,三叔你抱秦多多啊。秦多多说,不许乱说。我说,就是抱了嘛。三叔说,抱了我也不怕。我说,我也要抱秦多多。三叔就笑。说,你抱不动。秦多多推开三叔。说,让他来抱。我屁颠屁颠凑过去,秦多多的脸微微有些发红。她俯下身来,我的嘴刚刚凑到她雪白的脖子上,便闻到一股好闻的香味儿。我说,秦多多你好香啊。这句话让秦多多中途变卦,她踹了我一脚,愠怒。小流氓,滚远点!
我落荒而逃,边逃边喊秦多多好香,秦多多好香。秦多多追出来。小流氓!再叫我撕烂你的嘴!我生怕她追上来撕烂我的嘴,跑得更快。却不想一头撞在另一个人的怀里。抬头一看,是秦德才,更加惊恐。强……强盗。我哇的一声,吓得大哭起来,哆哆嗦嗦地站在那里,怎么也迈不开腿。
秦多多一看秦德才来了,怯怯地叫了一声,爸。
秦德才说,还不滚回去。
秦多多还想说什么,秦德才又说了一个字。滚!他拉着秦多多就走,边走边说对三叔说,男人都死完了,我也不会把多多嫁给你。三叔倚在那漂亮的写字台边,看着秦德才拉着秦多多急匆匆地走了。微风吹过来,送来秦德才对秦多多的几句怒骂。
全家唯一的一张写字台属于三叔的,他在上面铺上了漂亮的桌布。这在当时的农村来说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就是放在今天,一个相当富有的农村家庭也未必在写字台上铺桌布,不是铺不起,而是没那个心思,没那么讲究……高柜和写字台都用红漆刷过,闪着光,能照出人影来。写字台上有花瓶,花瓶里插着相当逼真的塑料花,用很透明的薄膜罩着,旁边还有精致的瓷器、奔马、观音菩萨……其中有一尊笑容可掬的弥勒佛尤其令我着迷,时常抱在怀里玩耍。我觉得他的笑容就像三叔的日子那样灿烂。
我不知道三叔哪里来那么多的钱。
我发现三叔很少洗衣服,后来才明白,原来是有人偷偷帮他洗。来的次数最多的当然要算秦多多,也有其他的年轻女孩。其中还有一个长得特别漂亮的女知青。我一直认为秦多多只是身材好,如果要说漂亮,还得算那个女知青。我不知道那些女孩子为什么要来给三叔洗衣服,来给三叔做屋里的清洁,把那些塑料花清洗得干干净净,看上去跟真的花一样。她们还把那些陶瓷观音陶瓷弥勒陶瓷奔马用湿布抹得一尘不染。她们有时候还争着抢着给三叔洗衣服,到三叔屋里做清洁。看她们的样子,一个个都迫不及待,巴不得三叔今天换了衣服明天又接着换衣服。甚至连结了婚的女人也喜欢站在那里和三叔说一阵子话。她们轻启朱唇,声音婉转。那身材更是令人着迷,一个个显山露水,走起路来花摇柳颤。三叔一律来者不拒,不动声色,不表明态度。一时间,女孩子们个个都感觉有希望,可谁都没有把握,想丢,丢不下,放手又舍不得。三叔脚踩几只船,就在众女子中穿行自如,迎俏接丽,春风满面。

有人找到三叔,说,大牛,给你介绍个对象,要不要?三叔说要。如此这般一说,就谈到了怎么见面的问题。见面的时候如果是冬天,三叔就穿着红色的秋裤,趿拉着一双拖鞋去见女孩子,要是遇到夏天,三叔就穿一条短裤,依然趿拉着一双拖鞋。不管是女孩子,还是女孩子的父母,都被三叔的这身打扮惊得目瞪口呆。接着奇怪的现象出现了。所有女孩子的父母不愿意自己的女儿和三叔交往,而所有的女孩子都喜不自禁,争着要和三叔一起去看电影,都争着来给三叔洗衣服。
秦多多长得不算漂亮,可是,脸上的鼻子和眼睛摆放得很匀称,就像她父母商量好了似的,鼻子摆放得好,眼睛再拿去嵌上,就很好看。这也就罢了,偏偏这姑娘小嘴儿甜,见着谁都爱打招呼,口一开,笑容也挂在脸上。经她的嘴说出的话,温柔得很,听着特别爽心。惹得周围的人一个劲儿地夸奖,说三叔好福气,说秦多多好福气。唯一不足的是,秦多多的嘴巴有些大。这也许是她喜欢叫人的原因。三叔好像不在乎,和秦多多的关系越走越近,有点如漆似胶的意思。
然而三叔和秦多多最终没有走到一起。
事情还得从三叔的干妈说起。
三叔的干妈是我们大队的大队长夫人。虽然没有一官半职,但是那气势跟大队长差不多,精明强悍,一副舍我其谁的样子。干妈对三叔说,大牛你怎么就看上秦多多呢,你也不想想,她配得上你吗?你看她那张嘴,能把一个人吞到肚子里。女人家,嘴大吃四方,你是养不起的。
这真是十个说客不敌一个夺客。就这一竹竿,把一艘即将驶入港湾的航船撑得老远。一段即将圆满的姻缘,就这样惨遭扼杀,无疾而终。三叔信了干妈的话,和秦多多断绝了关系。后来我还看见秦多多来过几次,她不声不响地洗衣服,不声不响地做屋里的清洁,还主动约三叔一起去看电影。但三叔总是对她不冷不热,有时半天也不吱声。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三叔和秦多多抱在一起,鼻子对鼻子,眼睛对眼睛,叽叽咕咕地说话了。
太和医院急诊科临床一线的医师、护士,自发在2008年成立“星星急救科普志愿服务队”。他们利用各种时间,走街串巷宣讲,希望将医疗急救专业知识向公众普及,从而提高民众的急救意识和技能。一旦接受培训的民众达到一定规模,将会为送医不及时的特殊患者争取急救时间,这也是发挥医院救死扶伤社会功能的一种有益途径。
三叔是鼓起极大的勇气才提出分手的。秦多多眼睛里露出的笑容渐渐地凝固了,变成了一种平静残留在她的脸上。她听着三叔的话,沉默着。沉默像冬夜的寒风撕裂着三叔的心。三叔的话还没有说完,额头已经渗出了一层细汗。他感觉和秦多多说这样的话很吃力,很艰难,比他做英雄还要艰难千倍万倍。秦多多没有哭。她始终弄不明白,前天好好的,昨天好好的,很久以前都是好好的,一直这么好过来,为什么今天说分手就分手。她转身,磨磨蹭蹭地离开。三叔看着秦多多的背影,站了一会儿,也转身想走。突然,秦多多站住,回头。
大牛。
三叔站住。
不敢回头望秦多多。
秦多多跺了一下脚。说,你混蛋。
地抖了一下,三叔的心也跟着抖了一下。
三叔果断地和秦多多断了来往,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对三妹有点意思。三妹是三叔干妈的三女儿。干妈想生儿子,却一口气生出四个女儿,为此还差点让三叔的干爹丢了乌纱帽。这四个女儿生得一个比一个水灵。在这四个女孩子中,三叔对三妹心有所动。三妹是高中毕业生,听说大队长正托关系把她招进县种子公司上班,以后就有可能是吃皇粮的国家干部。干妈对这个女儿也是宠爱有加,从小哄着捧着,受不得半点委屈。别的女孩子都有事无事往三叔的身边凑,唯独这个三妹,小公主一样盛气凌人,从来不拿正眼瞧一下三叔。这让三叔多少缺了一点自信。三叔不止一次梦到三妹。梦到她面带微笑,沐浴在清晨的阳光里,踏着挂满露水的青草向自己飞奔而来。梦到三妹和自己手拉着手,行走在县城宽阔的大街上。越是这样,三叔对三妹就越发地想入非非,不说得到,就是听到三妹的消息,也妙不可言。可是,从梦里醒过来,三叔满脑子都是秦多多长长的辫子,乌黑的大眼睛,还有那张大得有点离谱的嘴。
干妈这么邪乎冲出来,明确要求三叔断绝和秦多多的关系,让三叔感觉到干妈似乎在暗示什么。后来,干妈的四个女儿陆续都出嫁了。三妹是最后出嫁的,她嫁给了县种子公司的一个经理。三叔这才明白,干妈的话里并没有什么弦外之音,更没有什么暗示,是三叔自己想多了。
更令三叔失落的是,在最后一次和三叔见面过后,秦多多依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带着一种绝望,草草地把自己嫁了出去。
那以后的很多个夜晚,三叔从商店回到家里,张罗他那几头肥猪的时候,我都听见三叔在唱歌:妹妹找哥泪花流,不见哥哥心忧愁,心忧愁,望穿双眼盼亲人,花开花落几春秋……尽管有鸭拖长声音嘎嘎地叫,有鸡咯咯地往圈里拥挤,有猪嗷嗷地打闹,一切都是那么忙而不乱,有条不紊,甚至灯火通明,但我依然能感觉出一种透彻骨髓的冷清。而三叔唱歌的声音嘶哑,时断时续,总带着一种凄凄惨惨戚戚。
英雄三叔的光辉岁月到这里似乎该结束了。可是事情往往就没有那么简单。秦多多带着绝望,心不甘情不愿把自己嫁出去了。秦德才心里憋屈,他认为三叔不仅让他蹲了三年监狱,还玩弄了秦多多。不以婚姻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他刘志荣就是一个流氓。秦德才经常在别人面前,满含愤怒地控诉我们一家人,说我爷爷是老流氓,三叔是大流氓,我们是小流氓。
秦德才外号一根筋。此人仗着读了几本古书,喜欢谈天说地,更喜欢和人家争长论短。什么事情都认死理,弯弯道理他都要脸红脖子粗地讲直,不撞南墙不回头,撞到了南墙也不回头。要为自己出气,为女儿秦多多争气。这事要是换了别人,兴许这一辈子就认了,不去指望了。可是一根筋秦德才不。他读过古书。他讲究策略。虽然成天唯唯诺诺,可那是蓄势待发。不就是砍两根树嘛,你大牛成就一世英名,我那三年监狱岂能可以白蹲?多多还是个黄花闺女呢,岂能让你大牛说玩儿就玩儿,说丢就丢?
一根筋报复三叔的方法真是出人意料。他居然也开了一个商店。开张那天,他噼里啪啦放了几挂鞭炮,还在店门口摆了几篮鲜花,同时邀请几个亲戚到店里为生意开张。最妙的是,一根筋的商店就在三叔商店的隔壁。这可真是个为秦多多出气的好办法。三叔商店的生意顿时就垮了一大半。想来,也在情理之中。读书人,读过古书的人,怎能让满脑子的古书白读?
那个时候供销社已是一派日落西山的景象,大队也不叫大队了,改成了行政村。原来供销社在村里的代销店经过一番运作后,变成了三叔的私人商店了。仿佛就在一夜之间,村里冒出了好多家商店,一家比一家气派,货物一家比一家齐全,家底一个比一个殷实。
眼瞅着生意支撑不下去了,三叔拓展了业务范围。他首先帮一家挂面厂销售挂面,然后自己在家里又喂了四头猪,喂了一大群鸡,他还没有荒废掉划分给自己的地,春播秋收的时候,总能看见他在自己的地里挥汗如雨地劳作。这期间,三叔传出了一些绯闻,说是三叔睡了村里某某某的女人,连手表都睡丢了。三叔睡人家的女人我想应该是真的,有一次我就看见一个女人从他屋里走出来,正扣着衣服上的最后一颗纽扣,脸色粉红,然后用手整理着有些凌乱的头发,匆匆而去。至于三叔那块精致的手表,我有好久都没看见了,差不多已经忘记了那秒针走动时悦耳动听的声音了。
再说三叔的生意。
清淡得简直如同一杯白开水。三叔思前想后,觉得还是应该在商店上做文章,以此来改变自己的一切。一个晚上他提了两瓶啤酒,揣了两包好烟,来到隔壁一根筋的商店里。灯光有些昏暗,微微闪烁,仿佛一不留意刺的一声就会灭掉。一只蝙蝠闯进来,绕着屋子飞了几圈儿,张着丑陋的脸,好像是来看他们的笑话,然后又不知在屋里什么地方转了一圈儿,向门口飞去,一头撞进黑暗里,再也没有飞回来。三叔赔着笑脸,大伯长,大伯短地叫着。三叔和秦多多呆了一段时间,别的没有学到,倒是学会了怎么和人打招呼。以前是很难看到他如此卑微地在一个人面前低声下气的。他把一根筋儿拉到桌子上,撕开一包花生,再递上一支烟。一根筋儿也不客气,接过来点燃,狠狠吸了几口,然后将烟雾吐出来,再咂咂嘴,仿佛在辨别香烟是不是假冒伪劣。两个人都不说话,各自狠狠吸着烟。烟雾在屋里盘旋缭绕,有点像一根筋儿脸上的皱纹。
三叔终于吐出了一句话,生意要做死的。
一根筋说,我不怕。
谈判就破裂了。关系依然紧张起来。
开始还一起去镇上提货,一路上彼此之间装腔作势还敷衍两句客套话,谈得最多的还是生意难做,钱难挣。后来,话里话外,总归少不了冷嘲热讽阴阳怪气。一根筋说三叔存心和他过不去,让他蹲了大牢不说,还要来玩弄秦多多。三叔也说一根筋下手狠,就那么一刀子,屁股上就多了一条口子,再也合不拢来了。最后见面,就横眉冷对,到镇上提货也各走各的了。
一屋两头住,生意各做各。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这其间秦多多回过一次娘家。说来也奇怪,自从秦多多负气远嫁后,村里的姑娘好像约好一样,集体在三叔面前消失了。三叔的衣服没有人来抢着洗了,屋里的清洁也没有人来做了。三叔一会儿家里喂猪,一会儿地里抢收,一会儿去挂面厂进货,他的商店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时候半天也不见开门。家里的墙角总是堆满了来不及洗的衣服,桌子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垫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土。最不能让三叔接受的是,他猛然间发现自己已经不是二十一岁时的英雄了,他走过了自己的而立之年,不知不觉已经四十而不惑了。他的锦绣年华,被岁月这把剪刀一点一点一段一段地剪去了,剪得只剩下一张清瘦的脸,一把枯瘦的长发,一双失神的眼睛,一个干瘪的身影了。除了那个差不多只剩下空壳的商店,几头还未长肥的猪,一群满院子扑腾的鸡,一片长势不怎么良好的庄稼之外,三叔什么也没有。尤其是没有女人。在漫长的寒夜,三叔感到了孤独和冷清,一盏灯常常在他的头顶发着昏黄的光,几只飞蛾围着光不停地飞舞,岁月就这么静静地流过去,再也没有流回来。
秦多多还是和多年前一样,偷偷来到了三叔的家里。她洗完了三叔堆在墙角的脏衣服,又打扫了屋里的清洁。这间屋里的一切还是和多年前的一样,连气息都没有改变。只是少了众多女孩子的身影,多了一些沉淀的灰尘,少了一些喧嚣,多了一些孤独。秦多多的婚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美满。她的男人是个酒鬼,整天在外面喝酒,喝完酒就回家发牢骚,然后就骂孩子,打女人。没有酒钱了,他甚至想把秦多多拿去换酒喝。一根筋秦德才说,这是命,一个女人的命,老天早就安排好了的。没有办法。但不管怎么说,秦多多总算是有一个家,这就是把日子过下去的理由。犹豫再三,秦多多还是走进了三叔的小屋。她下定决心,以后再也不走进这间屋子了。这里留下了秦多多太多的记忆,一生难忘。秦多多不紧不慢,把一切收拾得井井有条,做得窗明几亮,就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
三叔回来了,拖着一身的疲惫。短暂的惊讶以后,他张开双臂抱住了秦多多,用满是胡须的嘴去扎秦多多的脸。秦多多闭着眼睛,顺从地让他扎呀扎呀。后来,三叔还想扎得更深一些,扎出一些火花来。但是被秦多多轻轻地推开了。虽然无力,但很坚决。
三叔说,我错了。这是三叔一生中唯一一次认错。秦多多说,不怪你,是我没那福气。远去的秦多多又一次转过身来,就像多年前回头那样。她对三叔说,你混蛋。不同的是,这一次秦多多掉泪了。
三叔看到了秦多多有些佝偻的背影。她的头发也没有从前那般柔软光鲜,几缕银丝在有些凌乱的黑发中偷偷摸摸,很打眼,却顽强保持着整齐。三叔明白,秦多多已不是当年的秦多多了。
有一段时间,一根筋把价格杀得有些厉害。三叔都快支撑不下去了。他狠狠抽完一包烟,坐在店里出了半天长气。最后一狠心,也把降价的牌子挂了出来。
两个商店一墙之隔,对方进了什么货,什么货脱销,什么货卖得俏,双方都一清二楚,了如指掌。冬季雨水多,三叔看准时机进了一批斗笠和蓑衣。村里的商店从来没有卖过这些东西,尽管价格叫得很响,但买的人很多。一根筋儿一看能赚钱,也跟着进了一批来降价销售,价格马上就回落下来了。一根筋儿托熟人进了一批农药,三叔也不示弱,马上通过供销社的老关系进来一批农药。再后来,三叔和一根筋儿进了很多货,可是买的人却不多了。人们都在观望着,等着三叔和一根筋儿之间的竞争,等着他们自己主动把价格降下来……不知不觉地,双方都在商品的种类上暗暗叫着劲儿。
好戏一般都是在晚上上演。
早已经夜深人静了,可是三叔和一根筋儿谁也不愿意先关门,都怕把最后一个顾客让给了对方。毕竟是年纪大了,精力有限,又是在冬天,一根筋儿坚持到十一点就有些昏昏然了。但是他还是舍不得关门,摇晃着站在门边向三叔这边张望。三叔也一个劲地打哈欠,不时偷偷往一根筋这边张望,脚边全是烟头。
三叔有时候会捉弄一下一根筋儿。他大大方方地把门关上,听到一根筋那边急匆匆地关门上后,又故意把门弄得的地一声。一根筋儿以为三叔在开门,急忙去开门,伸出头去,迷迷糊糊往黑夜里张望了一阵,寒风嘶的一声,就灌进领子里去了。像一根根针,一直钻到骨头里。两排牙齿咯的一声,相互咬了一下,才顶住了那刺骨的冷。几次以后,一根筋儿也明白三叔在戏耍自己,自己上当了。他气得站在门边指桑骂槐地又骂了一通,才哆嗦着关好门,气咻咻地睡觉,一直到深夜也瞪着明亮的眼睛盯住屋顶。你打我一拳,我还你一脚。一根筋儿也依葫芦画瓢,三叔聪明,就是不上当。
为了活跃商店的气氛,增加人气,三叔首先在自己的店里摆出了麻将桌子,喜欢打牌的年轻人都涌到了三叔店里,玩牌,喝酒,吹牛,每天差不多满满塞了一屋子的人。人都有个习惯,哪里人多往哪里扎堆。这样一来,三叔的店里就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再看一根筋这边,冷冷清清的没几个人。不时有几只麻雀掠过旁边的水塘,掠过水塘中的青山白云,停在一根筋店门口的香樟树上,歪着脑袋,好奇地看着摇头晃脑打瞌睡的一根筋,看着他长长的口水从嘴角流出来,在泛白的阳光下,亮晶晶的,怎么也不肯掉到地上。
夏天的时候,常常来了几片乌云,狂风卷起被人坐皱的废报纸漫天飞舞,悠悠扬扬地落到地上,又飞起来,然后几个空翻。雷就跟着来了。麻雀们再也没有兴致看一根筋打瞌睡,展开翅膀远远地飞开,叽的一下,声音未落,早已没有了踪影。雷一个接一个,仿佛就在头顶炸开。一根筋被这雷炸醒了,收起亮晶晶的口水,把店里堆的废旧物品一古脑儿搬开,腾出一片空隙,也摆上了几张麻将桌子。两家商店就这么针尖对麦芒地耗上了。
到了腊月尾上,正是生意兴隆的时候。镇上派出所的人围住了两个商店,亮出了手铐,带走了三叔和一根筋。
三叔和一根筋是春节过后才回来的。回家后,一根筋的商店就关门了,再也没有开过。
三叔呢,继续开他的商店。他养的鸡和鸭,他养的肥猪都很值钱。他把那些钱一律投到了商店里。而商店,又是他用来取悦女人的筹码。三叔继续喂鸡喂鸭喂猪挣钱,继续把钱投到商店里,继续用商店来取悦女人。到后来,这种情况就成了恶性循环。他变得又黑又瘦,整天咳嗽不止,性情也变得喜怒无常。直到有一天他被查出患有肺结核,才恋恋不舍把商店盘给了我父亲。在签契约的时候,三叔抓着笔,久久不落到纸上。我看见他的手只剩下了一层皮,皮下的骨头仿佛正鼓足了力气,一不小心就会冲破皮肤裸露出来。三叔说,我的病好了,就把商店还给我。一定要还给我。
父亲说,一定还给你。
事实上,三叔的病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好过。直到他去世前一个月,商店一直都是我父亲在经营。但是商店已经不在村里了,搬到了镇上。我家在镇上买了一个门面,扩大了规模,品种也更加齐全了。生意呢,也不是期待中的那样兴隆,也不是担忧的那样清淡。不咸不淡,时好时坏,吃不饱,也饿不死。没有地种了,有事情做总比没事情做好,就当是种地吧。父亲不止一次这样说。父亲还说,是三叔这个商店捆住了他的手脚,要不是这个商店,他早就出门打工挣钱了,日子肯定比现在要过得好。
真的是这样吗?
我说不清楚,相信父亲也说不清楚,三叔也说不清楚。
世事难料。
村里开发了。
开发商给每一个村民赔付了一大笔钱。从前村里的一些老光棍都相继娶到了媳妇。也有人开始给三叔张罗媳妇的事情了。那一大笔钱,三叔是一辈子也用不完的,得找一个人来和他一起用钱。可是,三叔不愿意。他担心自己的钱会白白地给人家用了。
秦多多也带着两个孩子住回了娘家。她的男人喝醉了就闹,在回家的路上掉到水田里淹死了。一根筋秦德才患了食道癌,动了手术,回到家里。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更长的时间,总之,他在等奇迹。
三叔的身体越来越差,走路摇摇晃晃的,说话嘴唇直哆嗦。他想晒太阳,从家门口走到院子里,都要喘好一阵的气。可是,三叔是个争强好胜的人,从来不服输。他咬着牙走到院子里的时候,脸色已经显得很苍白。有的人和他开玩笑,大牛,一大笔钱哟,看你那样子,怕是用不完的了。三叔就说,就怕不够我用啊。然而却从语气里能听出一种苦涩来。想必三叔也意识到钱“用不完“,而不是担心“不够用”了。
所有的人都搬出了村子,住到了镇上。三叔没有买房子,他只是在镇上租了一间不起眼的房子。凑巧的是,一根筋租的房子和三叔租的房子相隔很近。成了邻居。有一天,三叔挣扎着出门晒太阳,没有站稳,摔倒在院子里。恰好秦多多在洗衣服,跑过去扶他。三叔把脸别到一边,将手从秦多多手里抽出来。太阳也不晒了,独自回到了自己的屋里。另一个邻居想撮合三叔和秦多多。让三叔冷冷地轰出了门。三叔说,我的钱,不给女人用。
不知不觉就到了冬天,说不出的寒冷。有一天,三叔的邻居告诉大伯,三叔好几天都没有出门了,你们也不去看看?大伯叫起父亲,一起来到三叔的出租屋里。
三叔用厚厚的被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床边有一个火盆,里面早已没有了火星,透出一股凉气。旁边的凳子上泡了一杯茶,看样子也早已凉了,就像他人一样,静静地呆着,一动不动。三叔已经不能说话了,两眼瞪得大大的,目光空洞。在医院里,医生告诉大伯和父亲,三叔是全身器官功能性衰竭,没救了。
一根筋秦德才听说三叔死了,在院子里大骂三叔,说三叔是个没用的东西,还不如他一个癌症病人。骂着骂着,秦德才掉泪了。秦德才说,谁要你的臭钱?谁要你的臭钱?秦德才一把鼻涕一把泪。多多,多多,你咋办哟?
后来我才知道,三叔留下了给自己办葬礼的钱,把剩下的钱全给了秦多多。父亲把我急匆匆地叫回来,大伯也匆忙叫回了他的孩子。本来以为可以分到三叔一笔钱的,想不到三叔却给了秦多多。尽管三叔已经死了,但是父亲和大伯把三叔抱怨了好久。
旧日的荒野中多了一个新坟。一年后,新坟变成了旧坟,上面野草疯长,仿佛已经是过去了好多年。周围开了不少的野花,红的红,黄的黄,紫的紫。它们静静地开放,静静地凋谢。虽然没有什么香味儿,倒也好看。
责任编辑/文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