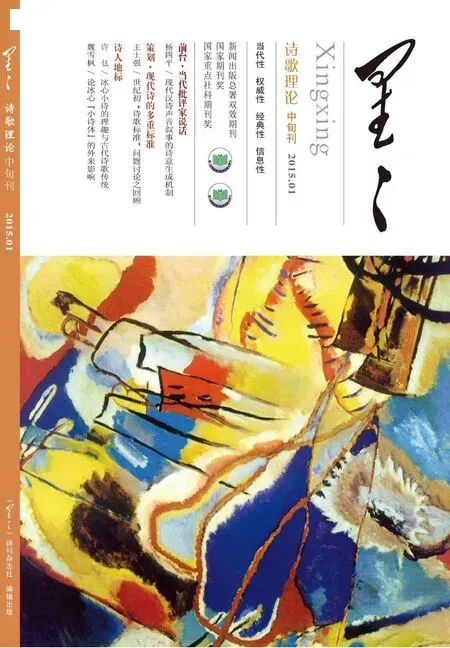寻找的意义:寻找一条路
——转角散文诗集《荆棘鸟》阅读印象
薛 梅
[文本导读1]
寻找的意义:寻找一条路
——转角散文诗集《荆棘鸟》阅读印象
薛 梅
近年来,正当中国现代诗越来越被边缘化的现实中,散文诗这种诗体却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亲睐,这看似一种偶然的接受现象,其实拥有也有其一切必然性的原因。现代诗被读者们冷落,虽然原因不可能是单一的,但近年来的大量新诗作品的诗性缺失,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中国社科院刘福春研究员指出:“在新诗无边界的审美拓展的创作的乱象中,只有散文诗还坚守的诗性的体质。”。散文诗仍然获得读者的审美支持,一定与散文诗的“诗性坚守”的审美追求有关。而体现这种坚守的是近年来崛起于诗坛,并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的“我们”散文诗群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作者以及他们的优秀作品的接连问世。在这批优秀作者中,转角是极其受到瞩目的一位新秀,她的作品,代表着“我们”的一种艺术倾向。
初识“转角”的名字当然是笔名,首先觉得这个笔名取得很好。近年有一句颇时髦的话,转角遇到爱。影视及歌曲都很红火,大抵突出两个核心,一个是奔向你,一个是下一个路口。这样的“转角”意味是奇妙的,说明她有方向感,不是被动的等待,而是积极地寻找心所向之处,也并不是一马平川,而是若一条长河,曲里转弯,但却绝不断流。
寻找是一生的事,也许心灵最终也还是漂泊,最终也还是徒劳,也还是若庄子所云的“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荼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但现代文人自鲁迅清醒并痛苦地发现了“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真相之后,寻找一条路,反而成为一种可能,成为一种必然。朦胧诗人用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确认了一条真理之路。转角以她的散文诗点亮了四野的萤火,让灵魂提着萤火虫找家,也意在确认出一条内在的永恒之途。
转角说:“2011年,我邂逅了散文诗,并为此开始了我波澜壮阔的寻找与跋涉。三年来,灵魂与生命在我的笔下交相熔接,我倾尽荒芜,诗意地流浪在这块远方的芳草地,我已分不清是散文诗接纳了我,还是我不自觉地踏上了皈依散文诗的路途。……之于写作,我感知了他们的美如同我在自我超越的旅程上割舍出另一个我,并让这个‘我’从起点最终回到了源初的位置,午夜过后,黎明醒来,我攥着我的灵魂与生命身临其境。”(《荆棘鸟·后记》)
这就是转角的寻找,寻找一条路,并能够走下去。
一
寻找一条通向潜隐体内的豹的路径。当代散文诗的美不仅在于承继了初创时期的独语方式,更创造性地进入到了半开半合的对话意味中去。一如美国大片《星际穿越》中展开的时间的虫洞,当出生这个点和成年后的点对折起来,洞穿两点后,距离就奇妙地缩短了,我们和转角一样就可能重新洞见我们自己的诞生(我多年前也曾写下过这样的诗题《我参与了我的诞生》),从而具备了一种开蒙场景与成熟叙述者的对话效应。然而转角似乎感觉更为敏锐,更为奇妙,当各种文本中“时间”已成为一种泛化意象,转角便不屑再用。她将之灵化为“太阳”,与之追慕则是一种常态,与之为敌则是一种变通。她像极了余光中笔下的夸父,她回身挥杖奔回东方,“既然是追不上了,就撞上”,她撞上了她的诞生,她放射着自信的光芒,她向世界大声地宣告:太阳,我要终生与你为敌!
这是令人胆寒的宣言,也是令人倾倒的告白。她寻找的目的不是弃绝,而恰恰是为了真正拥有。“从浑浊到浑浊。从冰冷到愈加冰冷。/从一座深山到远方的陆地,我们,缓慢驼行。/而谁最终成为火的种子。/虚指向太阳——”(《第三辑:幽冥的花朵·黑夜里的一次诵唱》),“太阳,清醒于海天一色的远方。”(第四辑:夜雨·搏杀)这是转角寻找并选择的路径。她在返还中有了新的身份和认同,她成为一只传奇的荆棘鸟。她在撞见自我的诞生中诞生了荆棘鸟的寓言。众所周知,荆棘鸟“属于自然界最执着的生命象征”(灵焚《超越死亡,抵达澄明》)。它一生只唱一次歌,它的歌声比世上所有一切生灵的歌声都更加优美动听。从离开巢穴那一刻起,它就在寻找着荆棘树,直到如愿以偿,它才歇息下来。然后,它把自己的身体扎进最长、最尖的荆棘上,在那荒蛮的枝条之间放开歌喉,曲终而命竭。世界也为之侧耳肃立,因为最美的往往是由最痛的换取。
荆棘鸟的执着成全了转角的执着,她的散文诗长旅便在开卷长诗《荆棘鸟》中壮行。全诗由36章构成,隐喻着某种时间向性或生命年轮的所指。转角便在成长与诞生这半开半合的时间维度中,使对话进入到一种寓言性的世界中去。这只“来自天堂的夜鸟”,以“热爱”衔着诞生之火照亮暗夜:
“融入浩大的历史烟尘和波澜壮阔。我用完整的黑解读黎明前更深层次的囚期。我用一把四角利刃割破,以骨血滋养豹子的太阳,迎接新一轮日出。我十月的太阳。
用尽一切光辉!”
——《第一辑:烈焰·荆棘鸟》
这样回返之后的诞生见证,已经不再单纯是灵魂的独语,而是呈现出了与这个世界,与生命历程的对抗与对话。割破以骨血养育豹子的“太阳”,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生命,新的涅槃——“豹子”意象,这“新一轮的日出。我十月的太阳”。 自此,豹子成为荆棘鸟的魂魄,一路踏上寻找“幽冥的荆棘丛”的尘世征程。幽冥即是宿命,即是命定的皈依。而“豹子”意象则成为更有意味的象征,那有着幽秘的不确定的气息的豹,那充满着滋润的水分和闪电的威力的豹,那有着滑行中最大稳定和速度的豹,正是强意志力的生命的象征。如果说转角的“荆棘鸟”意象只构成艰辛和悲壮,那么以豹为魂则凸显了生命的神力和伟大的意志,这两个意象的诞生才真正使转角的“荆棘丛”有了生存陡峭的献祭,使对话有了生命哲学思辨的闪电。于是,场景的转换碎片一样,高山、河流、大地、城池、黄昏、夜的荒凉、月下、灯前、草木虫鱼、冰霜雨雪、四季流徙,成为快速旋转的碎纸机,将浩大的地理和绵邈的时空尽数切碎,艰辛、苦痛、背叛和死别深陷其中,转角、荆棘鸟、豹子三位一体,互生互证,镶嵌着精神的迷宫,这就意味着,作为意志的主体,终能识别命定的归属:
“喧哗的声浪气势磅礴。我掏空了韬光养晦的暗,袒露最原始的真身。我张开不曾委曲求全的喙,纵情歌唱。我放出最昂贵的碧血,目送自身和豹子一程。
我的豹子啊,领走我一颗不断忏悔的初始心!
我和你最终完成一致的绝美,进入崭新的世界,崭新的空无。”
——《第一辑:烈焰·荆棘鸟》
转角在荆棘鸟的泣血歌吟中完成了宇宙裂变的新世,生命澄澈的回归和山水同盟的本相,豹子隐退,以其洁身自好还原了自我。“灵魂的施暴者终被黑暗碾为粉尘。天地澄澈,在永生中诞生新的黎明”,显然,这寓言中有荆棘鸟或者转角的自我灵魂的撕裂与张扬,超越死亡中,亦有对世界对万物的坦诚与和解,转角之上有更大的观照者,精神之豹中有神秘的启悟者,这潜隐的对话,以有词和无词的言语,构成了象外象、意外意的双重旨归,最终走向情境,走向诗性,走向境界。
“太阳”意象至此完成了它的使命,无论是真理还是谬误,无论是光明还是强权,都将以涅槃重生而化为澄明。这是通透的理性,不惧死,必得生。
二
寻找一条通向澄明空茫的重生之路。转角是一名70后女诗人,但她的文字中几乎少见70后一代的娱乐性、消费性、表演性、商业性和肉欲性,转角是深邃的、严肃的,对自我的命名有着高贵而纯正的知识分子气质。她飞沙走石般得去咀嚼沉重的生命史碎片,她是不安静的、不妥协的,她是灵魂的探险者,她是沉实的,是重的,是紧张的。她的寻找和选择的路径绝不是轻松的美学,她没有调侃、游戏、情调、好奇和对发迹向往的时尚流弊,她只是沉醉在自我灵魂的漩涡中,像一位久经沙场的将领,指挥着千军万马有序的冲突出来,并获得重生的澄澈和清明。
诚如转角在《西藏书》所获得重生意味:“路,是回旋的,是向着远方的,对此我深信不疑。在西藏,我所见到的不是在风景,而是灵魂的发现,是对自我的识别,是命运和因果轮回的反复叠加,是期许拥有美好未来的永恒愿景,这条宽阔的大路是朝向太阳屏蔽黑暗的路啊!”
“朝向太阳屏蔽黑暗的路啊”,太阳的重生,意味着转角的重生,寻找的重生,生命的重生。然而,转角的重生姿态带着禅心,带着禅性,《荆棘鸟》中的每一篇几乎都在结尾呈现出空茫的意绪。这是她对世界的姿态,清楚每一条其实都没有终结,人生终要以自身的简质和澄明走向别一维度的居处。“澄明”才是寻找一条路的本相,是万物与自我必须面对的澄明的空茫,是万物与自我泰然处之的澄明的空茫:
“一声又一声呼唤,被神孕育的喘息,在水上澄澈,使水澄澈。
路途,终被青草占领。开花的籽粒,立在风的矿脉上,打扫万物。
天与地在第三日,藏起忠贞和大雨……”
——《第二辑:大地之殇·第三日》
“站在时间之外,天地悬浮!
恍若大雨倾盆,尘世皆是随身抖落的一粒灰,即是整饬之后,也根本无法安身立命。徘徊,犹豫,辗转反侧……
被认领的过程早已蜕变,生死上升为火的高度。
盗火者需要安宁!”
——《第二辑:大地之殇·火的盛况》
“十五万片!他经受火炙、荣辱、屈尊、降位,以广阔的胸襟终究抵达了生命的近处。
他失聪之后,独自沥出虚无,用空旷接受昨日之绚烂,今日之芒刺,明日之浮沉。
他栖息在大地上,言简意赅地活着,从容,淡定,寂寞,孤独……”
——《第二辑:大地之殇·甲骨,甲骨……》
“孤独的落日见证生命这悲辛的雨水怎样脱离海与天的束缚,万物生生不息,万物突出体内荒凉的月夜。
一盏失足落水的灯正在照亮我们前行的远方……”
——《第四辑:夜雨·失足落水的灯》
“而我饱和的痛苦披衣而起,从出生日走向出生日。
日落的时刻!
我偶然缔结的虚空途径一扇门,一只死亡的手正抚摸我。时间和苍老被阻隔在门外。
火焰,守住波光粼粼。
逝者,终于见到了一处海岸——”
——《第四辑:夜雨·搏斗》
转角几乎每一首都在全心袒露着自己的灵肉之思,那些普通、卑微,和荒芜,那些火光、梦境和花朵,那些眺望、倾听,和匍匐,那些盲区、退隐,和深渊,那些地狱、落水,和搏杀,每一次灵魂的挣扎,都是一次灵魂的洗礼;每一次灵魂的安详,都是一次灵魂的涅槃。转角始终不是在写红尘滚滚,但每一处挣扎的痛和累,都写满了滚滚红尘带来的伤害及警醒;转角始终不是在写人生游戏,但每一处安详的慈与爱,都写满了游戏人生带来的选择及摒弃。
转角本身就是幽冥,是宿命,是不甘的魂魄,是清白的风。
我们恍如见到了李叔同淡然的背影,看到了贾宝玉初阳的温度,他们的智慧在转角的路口,在智慧的心的路径,在走着,并有蝴蝶重生的翩然……
这是澄明的智慧,承受沉重的,即获得轻盈。
三
寻找一条通向文字能量的语言之路。散文诗究其根本首先是诗的,然后才是其它。诗人韩东从瓦雷里那里获得了启示:“诗到语言为止”。语言构成了诗性的材质,语言的趣味决定了一首诗的风格乃至风骨。散文诗也一样,必须无条件地信任语言,就像蜜蜂信任它的毒针,牛信任它的犄角,爱信任她的吃醋一样。转角深谙其道,她信任她的语言的醋意十足,她介入语言的味道不是麻辣的,不是齁咸的,不是淡如白水的,她是发酵的,有意味的,有婉曲的,有泪水在里面温润而酸涩的,有疼痛在里面搅动而绝望的,有混沌在里面变通而清醒的,有坚执在里面呐喊而不悔的,有理想在里面活着而不弃的,转角的语言昂首走在散文诗的路上,幽僻小径也吧,通衢大道也可,它那么义无反顾地走着,暗夜来了接住,黎明来了重生,她的语言构成了大境,构成了屏障,构成了坚不可摧的防线,和带着硬度的质感:“他疼痛,隐忍,纠结,却只能高昂着头颅向内咆哮,哭泣”,“他经受火灾、荣辱、屈尊、降位,以广阔的胸襟终究抵达了生命的近处”,“他栖息在大地上,言简意赅地活着,从容,淡定,寂寞,孤独……”(《甲骨,甲骨……》)。这样的描述是对转角语言最好的诠释,她最幸运地是,她走向了语言的内里,并被融化。
转角散文诗的寓言性、象征性,当然也得益于她这种创造并运用语言的特质。她很少选择那些小的、弱不禁风的、香水气的,或者中性的词汇,她总是喜欢在语言中掌控那些有能量的,有爆破力的,有历史深度的,有纵深感的,有活跃的细胞组织的,甚至是男性的硬度和宽阔的肩膀的,她试图用这样的零件建造一座文本的时光机,在散文诗的星际之路上穿越,并寻找适合人类情感安居的所在。这是她的美梦,也是她的现实。她的理想宏大,气魄超人,但她还需要重视一个女性性灵深处更朴素、更细微、更动人的细腻和以柔克刚的情愫,否则,人性繁复,在驾驭的过程中,时光机会容易意外而变形和失控。这是转角急需的改变。
语言喜欢藏匿,只有真诚的心可以找到它。语言像珍珠一样散落在黑暗的想象之中,只有真诚的情感能把那些闪光的东西串起来,那是一条既看得见,又看不见的“藕断丝连”。我们有理由相信,转角的散文诗语言的架构只是转角的,这是她的路径,她会一直走下去,在没有出口的出口,因为情的真、爱的美、思的诚、诉的切,下一个路口,下下一个路口,都属于她。
从“烈焰”到“夜雨”,从荆棘鸟的死亡穿越到“青龙”的激荡搏杀,转角“企图完成从出生日到出生日的一次轮回或回归,她欣然在暗夜中抚平“不安之书”,她快意于《在黎明里出场》:
“每一只蝴蝶都是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几乎所有的历史都源于河流,而我与河流的相遇则在诗歌的现场里。在水之湄,在山之巅,在我魂牵梦绕的故乡,我幻化成一只盘旋在河流上方的蓝蝴蝶,只为去生命的源处寻找自己”。
转角决绝得表现了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坦然和坦荡,从来处来,到去处去,在“碎金子似的河流”里,成为“彼此的路人”,在“隐秘的城堡”里,足以给出幸福的慰藉:
“而你,是我啜饮的壶,残忍而温馨到让我甜蜜地死去。”(《日光与憧憬》)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找,寻找一条走下去的路。转角的文本意味在于,走自己的那条路,百折不挠地走下去,即便空茫也要澄明的走下去。我在转角那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前面走得太急了,我要悄悄地告诉她:慢下来走,要能够倾听到自己的心跳……
“慢下来,请再慢一点,我将更有资格黑得发亮,绿得发青,并空出整座城池供养一座江山——
神州大地!”
——《第四辑:夜雨·日光与憧憬》
(作者单位: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1. 转角《荆棘鸟》代序:“是脚印,就应该留在时光里(代序)”,燕山出版社,2014年9月,P.1.
2. “我们”全称“我们—北土城散文诗群”,创立于2019年3月14日。该诗群秉承“大诗歌”创作理念,提倡“意义化写作”,在沉寂的当下诗坛卷起了一阵诗歌审美艺术的新风,正在努力改写中国现代诗近百年的分行诗一枝独秀的审美版图,企图建构分行诗与散文诗并驾齐驱的崭新纪元。这个群体的领军人物是周庆荣、灵焚,而转角则是“我们”的主力性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