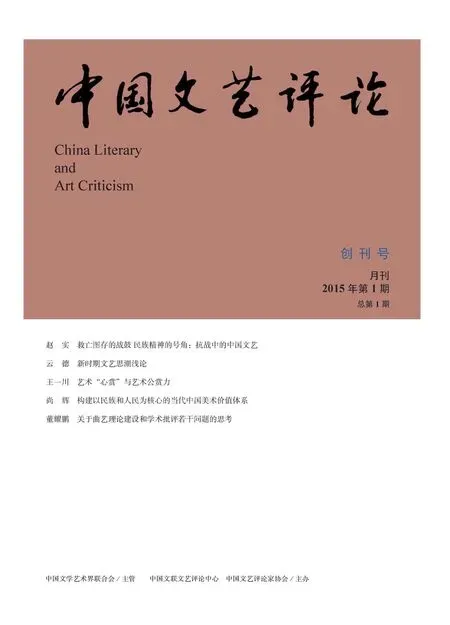经典音乐永远是人民之声、时代之声
——专访著名音乐家傅庚辰先生
娄文利
名家专访
经典音乐永远是人民之声、时代之声——专访著名音乐家傅庚辰先生
娄文利
编者按: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广大文艺工作者在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的鼓舞下,正在为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而奋斗。本刊编辑部秉持客观、理性、历史的态度,陆续刊登文艺名家系列访谈,总结他们艺术创作的实践经验,倾听他们对时代、对人民、对生活的真挚情感和深刻认识,希望激发广大文艺工作者更加深入地思考文艺与生活、与人民的关系,以及如何用当代的艺术语言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艺术精品等关乎艺术创作的根本性问题。

傅庚辰简介 1935年11月14日生于黑龙江省双城县。国家一级作曲、正军级少将。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歌舞团团长,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八、九、十届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现任第八届中国音协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荣誉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中俄友好协会顾问、联合国世界音乐理事会终身荣誉会员等。
傅庚辰的音乐创作具有极为鲜明的时代性,他的创作几乎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时期:电影音乐《闪闪的红星》《地道战》《挺进中原》《打击侵略者》等分别表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文革”后,他以一个艺术家的历史责任感创作了反映“文革”的电影音乐《枫》,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为否定文革的歌剧《星光啊星光》作曲; 1991年建党七十周年之际出版了革命家诗词歌曲专辑《大江歌》;2003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试飞成功写了大型声乐套曲《航天之歌》;2004年邓小平同志百年诞辰写了声乐套曲《小平之歌》;2005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写了交响组曲《地道战留给后世的故事》、交响诗《红星颂》,2006年为党风廉政建设写了《纪检之歌》;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后写了歌曲《你我一起走》《真爱在人间》,北京奥运会前夕写了歌曲《奥运之火》;2013年为纪念毛泽东为雷锋同志题词五十周年创作了交响组曲《雷锋之歌》;2014年7月自己作词创作了歌曲《中国梦》;2015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把1989年创作的电视剧《卢沟桥》音乐整理为《卢沟桥组歌》,还创作了歌曲《清平乐•太行古道》《黄河纤夫》等。
傅庚辰先生1948年3月入伍,参加东北音乐工作团,此后曾亲历辽沈战役、抗美援朝和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三次战争,他用自己的作品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代,他是中国红色革命文化的代表性人物,是共和国主旋律的书写者。在六十七年的艺术生涯中,他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音乐语言讴歌时代、服务人民,体现出朴素的革命浪漫主义美学精神,他用自己的作品实践、继承并发扬了聂耳、冼星海“为人民服务”的革命音乐传统。
近期,应《中国文艺评论》编辑部之约,笔者访问了傅庚辰,在此选取访谈中的几组重要问题与读者共研。
娄文利(以下简称“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您创作的《地道战》《红星照我去战斗》《红星歌》《映山红》《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雷锋,我们的战友》等作品堪称时代经典,充分体现了艺术的时代性。“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始终是您选取创作题材的自觉追求,在您看来,文艺创作的时代性是什么?当下中国文艺的时代之声是什么?作者应该怎样抓住其要义?
傅庚辰(以下简称“傅”):我认为,中国文艺创作的时代性就是反映人民的愿望,唱出人民的心声,说出人民的心里话。
文艺作品的历史价值就在于是否能真实地反映生活和时代、反映人民的呼声。那些能够经受住历史考验的、受到群众喜爱的优秀作品,不仅有重要的艺术价值,更是时代的文化标志。这样的作品之所以能产生,就是因为作者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拿群众歌曲来说,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时期都产生过这样的优秀作品。
比如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九十余年历史上产生作品最多、质量最高、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次群众歌咏运动,可以说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抗战的歌声”。为什么抗战歌曲有那么强的生命力?这是时代和生活的选择。中华民族曾长期遭受侵略,1840年鸦片战争,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1895年甲午海战,1904年日俄战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遭受了多么深重的苦难!中国共产党诞生,高举中华民族独立的大旗,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长期英勇斗争,建立了新中国。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的抗日战争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愿望,救亡歌曲是时代的呼声。身处火热时代生活中的音乐家们高唱出人民的呼唤:《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救国军歌》《在太行山上》《松花江上》《嘉陵江上》《延安颂》《五月的鲜花》《九一八小调》《歌唱二小放牛郎》《铁蹄下的歌女》《黄河大合唱》等抗战歌曲燃烧着民族的怒火,沸腾着人民的热血,唱出了时代的强音,至今还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
新中国成立之后寄托人民爱国情怀的《歌唱祖国》,表现粉碎“四人帮”举国上下欢欣鼓舞的《祝酒歌》,歌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华民族进入崭新历史时期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歌颂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等作品不仅是艺术佳作,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所以说,作品是时代的产物,时代选择了作品。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起点。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在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再唱抗战歌曲,汲取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的光荣传统和宝贵经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好的作品必将与时代碰撞出灿烂的火花,留下深刻的印记。当前,我们正身处一个伟大的时代,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鲜明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战略决策,大力提倡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中国文艺当下的时代之声就是谱写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因为这代表人民的心声,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愿望。新一代文艺工作者应当自觉以中国梦为主题,用具有鲜明时代气息的艺术语言和人民群众喜爱的艺术形式,创作出文质兼美、雅俗共赏的优秀作品。
娄:您曾经说过,“一个作曲家要想掩饰他对生活、对时代、对信仰的情感是不可能的。”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是文艺创作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请您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谈谈艺术与生活的关系。
傅:生活对艺术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这里我用亲身经历来说明。
1953年的3月至8月,我曾到朝鲜的西海地区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所到部队我们都会听取战斗英雄事迹的报告和战况介绍,一天演出两三场,要翻山越岭、过封锁线、睡坑道,这半年的战场生活对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和创作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57年我调到志愿军文工团。1958年2月中朝政府签署《联合声明》,志愿军开始撤军归国,中朝双方开展了热烈的友好活动。为了反映中朝友谊,我们创作小组下部队体验生活,首先来到上甘岭阵地。当年,在这场鏖战四十三天的著名战役中,美军调集兵力六万、大炮三百余门、坦克一百七十多辆、飞机三千架次,对这块三点七平方公里的阵地狂轰滥炸了一百九十万发炮弹,投下五千余枚炸弹,阵地的山头被削低了两米。六年后我们踏上这块战场时,破钢盔、破皮鞋、碎弹片以及废弃的坦克、大炮仍然随处可见,山坡上的石头都是碎的,踩一下,脚会陷下去,可见当年战事的惨烈!我被深深地震撼了!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亲眼见证了志愿军撤离时中朝人民的伟大友谊。平壤市民倾城出动,人山人海,夹道欢送,握不完的手,跳不完的舞,唱不完的歌,呼不完的口号,当这些都不足以表达他们的感情时,就把我们抬起来扛到肩头上……当我踏上告别列车时才发现因为无数次与平壤群众用力握手,手指缝间竟然起了水泡!火车上下,中朝两国的军民都流下惜别的热泪,火车多次鸣笛都无法开动。火热的场景引起我的强烈共鸣,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很快就写出了歌曲《告别朝鲜》,这首歌成为撤军活动中必唱的保留曲目。1985年,胡耀邦总书记访问朝鲜时,把这首歌作为礼物送给朝鲜,为此重新录音并改名为《中朝友谊之歌》。所以说,艺术家扎根生活才能激发创作的热情和灵感。
另一方面,为了艺术创作去实地体验生活,会直接影响作曲家对作品主题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定位。1963年底,我带着极大的热情接受了为电影《雷锋》写音乐的任务。我请词作家写了名为《高岩之松》的主题歌歌词:“高岩之上长青松,青松昂首望长空……”这也是当时我和人们对雷锋的普遍认识。但是,当我带着写好的歌曲到雷锋部队体验生活之后,我对雷锋的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我五次采访雷锋生前的指导员高士祥,两次采访雷锋的战友乔安山,参加雷锋班班会,听战士们介绍雷锋的情况,到雷锋生前担任过校外辅导员的抚顺市望花区希望小学访问……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训练、同劳动的过程中我对雷锋的认识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多次参观 “雷锋事迹陈列室”之后,我对雷锋和他赋予我们时代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雷锋是把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融入一点一滴的日常生活和平凡事务中,并长期坚持不懈。他在日记里写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这个深入浅出的哲学概括对一个身处和平年代的年轻战士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雷锋精神不是“高大全”,而是“伟大寓于平凡”。于是我否定了已经写好的《高岩之松》,反复斟酌、深入思考之后,自己作词写出了主题歌《雷锋,我们的战友》:“雷锋,我们的战友,我们亲爱的弟兄;雷锋,我们的榜样,我们青年的标兵。”电影上映后,这首歌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反响,一方面是旋律朗朗上口,另一方面把“战友”与“榜样”、“弟兄”与“标兵”统一起来体现“伟大寓于平凡”,使得雷锋的形象更真实更贴切。
所以说,对艺术家来说,“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创作的需要。
娄:作品是艺术家的立身之本。艺术家的历史地位取决于他作品的时代价值和历史高度。近年来专业音乐界 “有高原、缺高峰”,不是作品数量不够多,也不是写作技术不够精,而是缺乏有时代精神和历史高度的、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精神风貌的经典之作。拿交响乐来说,老百姓心目中仍然是《梁祝》《黄河》《红旗颂》,国内交响乐比赛的获奖曲目也很难走出专业圈子常驻舞台。您认为应该如何走出这个困境?
傅:关于这个问题,我主张三句话:“现代技法中国化,音乐语言民族化,音乐结构科学化。”
“现代技法中国化”是需要从创作思想上解决的问题。我们搞改革开放就是要学习、借鉴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但这种学习、借鉴绝不是生搬硬套,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1942年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新中国;马列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产生了邓小平理论,指导了改革开放,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中国国情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必将深刻地影响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音乐创作同样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在学习西方现代作曲技法的问题上发生了误解,走了弯路,留下了一些经验教训。那时,人们在课堂上讲的、在会议上说的、在作品中用的非现代技法莫属,谁不如此就不够时尚,就有保守之嫌,甚至怕被人说成“左”。曾经有一位外国专家听了某音乐学院作曲系学生的新作品音乐会后评论说:“这些作品的写作技巧很现代,一点也不比外国人的差,但听不出来是中国人写的。”这很说明问题。很多专业作曲家完全用西方现代技法创作出的交响乐不被听众接受,完成之后就束之高阁,令人痛心。2001年第一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参评的交响乐作品有一百二十一部,现在十四年过去了,又有几百部作品问世,但在一些重大的庆祝活动或对外交流演出时竟然很难选出代表新时期中国交响乐创作的“高峰”作品,不得不还是演奏《梁祝》《黄河》《红旗颂》,这不能不说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形式要为内容服务,技术要为思想服务,技术和形式不是创作的目的。我们应当辩证地看待西方的现代文艺思潮,有选择地运用西方现代作曲技法。要在中国化的前提下,用这些技法写出中国风格、中国气魄的作品,才能受到听众的欢迎,也才能诞生真正走向世界的高峰之作。
所谓“音乐语言民族化”是指必须结合中国的传统审美习惯,用中国人民熟悉和喜爱的、民族化的音乐语言进行创作。中国化的音乐语言不但是中国风格的旋律,还可以是五声性的和声语言,是强调横向线性发展的织体形态,是运用中国民歌、戏曲音调构建主题,或是借鉴中国传统音乐结构方式的发展逻辑等等。古今中外的音乐史上能真正留下来的作品,都是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和民族特色的,例如肖邦的玛祖卡、波兰舞曲,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西贝柳斯的《芬兰颂》,格里格的《培尔•金特组曲》,斯美塔娜的《沃尔塔瓦河》,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等等。中国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和钢琴协奏曲《黄河》也是因为用中国的音乐语言讲述了中国的故事才传遍全世界。最近,爱乐乐团的“2015丝绸之路巡演”,出访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几个国家的六座城市,演奏的中国作品也还是《梁祝》。专业音乐工作者必须认识到音乐语言的重要性,扑下身子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艺术中的精华,创造出既有中国个性又有21世纪风范的音乐语言。
所谓“音乐结构科学化”是指要根据音乐内容选择恰当的体裁和结构。结构的力量是无穷的,对结构的把握能力如何,也是对作曲家功力的检验。体裁结构是音乐的表现形式,对音乐作品思想内容的表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遵循音乐结构的科学规律加以运用。比如奏鸣曲式,从主题、调性的矛盾出发,经过大幅度的矛盾冲突和展开最终走向调性统一,实现调性回归,体现了对立统一的思辨过程,因而适合表现深刻、重大、复杂的题材内容,尤其是交响乐或奏鸣套曲的第一乐章基本上都要采用这种充满逻辑美的结构形式。结构不科学会削弱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在创作中要遵循音乐结构自身的规律,为作品思想内容提供恰当的形式、完美的表达和无尽的空间。
总之,技法是手段,语言是桥梁,结构是载体,三者必须有机统一。现代技法中国化、音乐语言民族化、音乐结构科学化是中国音乐作品从“高原”走上“高峰”的必经之路。
娄:但是,目前专业音乐界还普遍存在着“去旋律化”的创作倾向,从艺术院校师生作品音乐会,到一些委约作品,都很难听到完整的旋律(更不要说优美了)。作曲系的学生从避免写“能听”的旋律,到写不出“好听”的旋律,最终只写技术很好但不知所云的作品,而这些作品与社会音乐文化需求的差距是巨大的。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怎样解决当下专业音乐创作自说自话的问题?您认为中国的音乐教育和专业音乐创作到底应该向何处发展?
傅:这是个创作思想问题,是在创作思想上脱离生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这种情况在音乐院校尤为突出,存在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应当引起有关领导和部门的高度重视。当然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已经有一些好作品崭露头角,我相信找准创作视角之后必将出现优秀作品。我们必须面向人民,面向时代,面向实际。
音乐的美体现在各个方面,旋律、和声、节奏、音色、织体、结构都各美其美,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又构成复合的综合美。但对一般听众来说,音乐的美首先体现在旋律上,旋律是音乐的灵魂,是塑造艺术形象的重要手段,也是一部作品的标识性特征所在。人们说起一部作品,首先就会哼唱它的主题旋律。西方20世纪的那些音乐流派让人目不暇接,但大多数都是转瞬即逝,即使是序列音乐、十二音音乐这些曾经维持了较长时间的流派,也只有极少的作品能留存在舞台上,跟这些现代派作品没有清晰的旋律,没有能辨别、能记住的主题有很大关系。
“去旋律化”在中国尤其不合适。我们汉语语调的四声有很强的旋律感,而音乐与语言关系密切,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和戏曲都有特征鲜明的旋律,单声部的线性进行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基础。中国人注重旋律美胜过其他音乐元素,我们不能丢掉本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审美习惯,去迎合西方的趣味,何况那种摆脱调性、不要旋律的潮流在西方也已经成为历史,现在西方音乐舞台上演奏的多是古典和浪漫主义时期的经典作品。因为音乐的本质是美,它要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力量,给人以陶冶,给人以欢乐,给人以美的享受。“美”是音乐的本质,只有符合这一本质的音乐作品才能经得住历史的考验,成为经典。而这种美,首先来自旋律。
应该说,在西方现代思潮影响下出现的“85新潮”是改革开放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副产品,现在这股思潮已过去了三十年,专业音乐界和音乐教育界应该冷静下来,客观、理性地反思一下,怎样辩证地对待外来文化?中国的专业音乐创作应该怎样走出自己的道路?
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奠基人萧友梅在九十多年前就曾经深思过这个问题。他在德国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的作曲理论,但并没有因此而“唯西方”“唯技术”,而是把西方的作曲技术和中国的民族语言结合起来,创作了一些优秀的、具有中国风味的新音乐作品。在他创立的上海国立音专的教学中,也是始终贯彻这样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办学理念。同时,他在对待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上也有非常明确的态度,认为学校不应该是与社会隔绝的“象牙塔”,相反应该与时代精神和爱国思想紧密联系。所以,在举国抗战的大时代背景下,他提出音乐教育必须成为精神上的国防建设者,音乐应该有意识地为国家利益服务,向教育部申请建立合唱班和军乐班,以适应战时的文化需要。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后,国立音专的师生们创作了大量的抗日救亡歌曲,还搞了很多救亡歌曲演唱会,这些都是专业音乐教育与时代、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联系的优良传统。
西方的作曲技术理论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依照这套体系对学生进行严格的技术训练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如果不解决好“为谁写”和“写什么”的问题,必然会使我们的专业教育、音乐创作与社会需求相脱节,以至于形成了自说自话的尴尬局面。音乐作品写出来就是要给人听,要有传播的价值和文化的意义,否则,你接受了那么多年的专业教育,何以回报社会?
今年,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和“一带一路”是举国上下的主题,音乐界围绕这两个主题创作了许多作品,有很多音乐学院举行了抗战歌曲音乐会,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了《我们万众一心:抗战歌曲七十首》简谱版及钢琴伴奏版,同时与网络传媒合作,让这些红色经典歌曲在群众中广泛传唱。这些都是艺术院校主动引领社会先进文化的可喜现象。
音乐不可能脱离社会生活,我们专业音乐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不但要有过硬的基本功、一流的技术和必备的艺术知识,更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要加强在政治思想、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学习,不要满足于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要积极投身到伟大的改革开放新时代的火热生活中,去陶冶、去搏击、去放声歌唱。
娄: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优秀文艺作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水平。请您结合创作实践,谈谈如何在当今时代创作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能“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无愧于民族、无愧于时代的优秀文艺作品?
傅:首先要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以人民为导向进行创作。同时在创作中要有两个“吃透”。一是要吃透作品的主题思想,这决定作品的方向;二是要吃透作品的艺术风格,这决定作品的成败。后者尤为重要,只有找到合适的、特定的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才有可能创作出有独特风格的、有鲜明个性的作品。
电影《地道战》的分镜头剧本中有这样的描写:“清晨,一轮红日冉冉升起。潮水般的音乐涌起。画外,太行山上响起了抗日歌声”。看到这里,我在分镜头剧本上写下“此处用《在太行山上》”,但后来发现这首现成的抗战名曲和影片中唱歌时的场景在艺术分寸上不够吻合,于是否定了这个方案。第二方案是取《在太行山上》的头一句“红日照遍了东方”的立意,并把原来的小调式改为大调式,使之从深沉改为明朗,写成一首气势雄伟的合唱曲《红日出东方》,绝大多数人都反映好,只有一位老同志提出不同意见,他说:“此歌虽好,也可在音乐厅里演唱,但它不符合电影《地道战》这个农村故事的主人公高传宝的农民身份。”他的话触动了我,于是又否定了第二方案。最后几经思考修改,自己作词写成了第三方案《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还有前面提过的《雷锋,我们的战友》都经历了这样一个反复推敲找准风格的过程。
艺术创作是一项艰苦的劳动,要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精神,要选准切入点,反复推敲,锲而不舍,而不能“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七十年前,在延安成立了鲁迅文艺学院,以冼星海为主任的音乐系产生了《黄河大合唱》、歌剧《白毛女》、秧歌剧《兄妹开荒》、歌曲《八路军进行曲》(现在的《解放军军歌》)、《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游击队歌》《延安颂》《歌唱南泥湾》等伟大的作品,培养出了李焕之、安波、马可、郑律成、刘炽、王辛、时乐濛等一批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留下光辉名字的作曲家。为什么?归根结底是因为延安鲁艺的教学思想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当代的音乐工作者要继承、发扬鲁艺的光荣传统。要紧跟时代步伐,向着人民的方向,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弘扬艺术的真善美,为实现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了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创作出无愧于民族、无愧于时代的优秀音乐作品。
采访手记:
从2013年应《音乐创作》杂志之约撰写傅庚辰专题开始,两年里我多次与他接触,发现他不但头脑清晰、思维缜密、语言精炼,而且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既有作曲家的敏感多思、又有实干家的脚踏实地,既有艺术家的丰沛才情、又有坚持不懈的执着精神,感性和理性在他身上平衡、融合着。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勤奋执着,这次也不例外。初稿完成之后,我们在一周内五易其稿,每一稿他都用铅笔认真修改,连标点和脚注都不放过,严谨程度丝毫不亚于一位资深编辑,只有那微颤的笔触才让我想起他已年届八旬。交稿后他又多次打来电话,就一些细节做最后的修改、调整。我想,认真一时易,认真一世难——也许这就是傅庚辰能在中国音乐史、文化史上用作品留名的重要原因吧。
娄文利: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副教授、博士,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责任编辑:何美)
- 中国文艺评论的其它文章
- 发 刊 词
- 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专访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雪健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