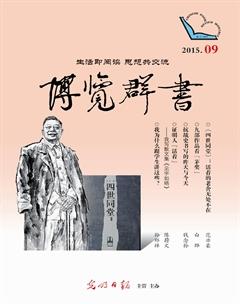抗战史书写的昨天与今天
钱念孙
20多年前的1994年,我作为国家公派高级访问学者赴英国杜伦大学(University of Dhuram)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University of Londen,SOAS)访学半年有余。在两校图书馆搜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朱光潜与中西文化》及美学、比较文学研究资料时,也经常翻阅台湾、香港地区及欧美国家出版的有关中华文化和中国近现代史的书刊。浏览这些海外出版物,尤其是有关抗战史的著作,仿佛走进一片自以为熟悉却变得面目全非的天地,思想受到很大震动。这些著述所呈现的抗战史面貌,与我从小学到大学所接受的知识,虽然描述的都是同一个对象,但从过程叙说到观点表达,多半互不相同乃至彼此抵牾。类似情况,在2000年赴美国马萨诸塞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和汉普舍尔学院(Hampshire College)任客座教授期间,在此后多次到台湾及香港访学期间,反复遇到,以至屡见不鲜、见多不怪。
初次遭际这种状况,我就意识到自己原来在学校里接受的现代史及抗战史教育,或许存在某些盲点和偏差。可是,阅读台湾及香港学者的著述,也明显感到他们对中国现代史尤其是抗战史的描述,同样存在较为严重的盲区和偏见。难道历史真的如有的人所说,是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难道我们对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的伟大的抗战史,不应该有比较冷静客观的清醒认识?不应该有自己秉笔直书的史乘吗?
步入21世纪以来,伴随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累积效应逐渐凸显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逐步上升,大国襟怀和大国气度日益彰显。在如何看待全民族共同抵御外来侵略的抗日战争的历史问题上,我们也有了比以往更加客观的视野和更加公正的心态。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中国政府给每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包括原来长期受排斥甚至受打击的国民党老兵,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2013年国家民政部发布红头文件,将原国民党抗战老兵列入优抚对象,享有与退役解放军同等的社会养老保障待遇。2015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宣布,9月3日隆重举行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将安排国民党老兵受阅;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还表示,欢迎台湾参与过抗战的老兵和他们的亲属及台湾各界人士来大陆参加纪念活动。
与这种观念转变和政策调整相呼应,学术界与出版界也先后推出一批新的抗战出版物。简略归纳,这些出版物大致可分为四类:其一,摆脱意识形态的局限,力图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抗日战争,如何理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步平著《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全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以及王树增的纪实文学作品《抗日战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等。其二,侧重探寻以往抗战史忽略的重要部分,描绘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壮阔图景,如张洪涛著《国殇——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团结出版社,2012年)、陈钦著《我的河山——抗日正面战场全纪实》(中信出版社,2013年),以及周渝编著的《为国岁月:国民革命军抗战将士寻访录》(团结出版社,2014年)等。其三,从日本及西方发掘长期埋没的史料,揭秘抗战中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史实,如萨苏著《国破山河在——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英]米特著,蒋永强、陈心心译《中国,被遗忘的西方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新世界出版社,2014)等。其四,通过抗战亲历者的讲述,再现抗战的悲壮历史和苦难细节,如梅世雄著《与鬼子玩命:抗日将士“口述历史”》(新华出版社,2009年)、崔永元等著《我的抗战——300位亲历者口述历史》(中国友谊出版社,2010年),以及各类抗战经历者的回忆录等。
综观这些著述,尽管它们透视抗战的角度不一,学术水准也颇有差异,但都表现出对以往抗战史著述中存在的狭隘历史观和意识形态局限的反思,都试图揭开被党派观点和历史迷雾遮蔽的史实真相,都摸索从更多方面挖掘抗战资料和感人故事,从而达到较为完整、较为客观地呈现抗战本来面貌的目的。此类著述的产生,既表明我们的抗战史研究在范围拓展和内容深化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和令人瞩目的突破,也昭示我们党和国家在处理涉及自身历史敏感问题时,有了较为开明的态度和更为宽广的胸怀。
抗日战争作为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全民族反侵略战争,既悲壮激烈、气吞山河,又千头万绪、纷繁复杂。毋庸讳言的是,与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和作用相比,与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世界产生的影响相比,我们目前对抗战史的认识和研究还远远不够,尚有不少有待改进、有待完善之处。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除了要隆重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也要秉持中华史学“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优秀传统,对抗战史中的诸多重大问题给予恰当的历史定位,对如何搜集、辨析、整理抗战史料采取正确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
就对重大问题的历史定位而言,无法绕开的首要话题当然是如何对抗战中两个最大的政治力量,即共产党与国民党发挥作用的认识和评价问题。八年抗战是在两个战场上展开的,主要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和主要由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形成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两个战场战略上相互配合,共同抵御日本侵略,从而取得抗战的胜利。对共产党在抗战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相对谈得较多,经常用“中流砥柱”来形容和概括。从抵制国民党一度消极抗日,到推动建立并长期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在严酷的敌后战场开辟广袤的抗日根据地,到八路军、新四军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歼灭大量敌人,共产党在抗战中确实做出了无可替代的、怎么估量也不过分的重大贡献。
对国民党在抗战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过去相对关注不够,认知态度也经历了由曲解漠视,避而少谈,到逐步直面历史,逐步客观公正对待的过程。国民党是抗战时期的执政党,它掌握当时的国家机器,能够配置全国资源和人力,调动几百万军队在正面战场抵抗日军的侵略。自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6月,国民党军队牺牲少将以上的将军共115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2人,少将65人,其抗战之惨烈程度可想而知。当然,国民党在抗战初期曾出现摇摆分化,副总裁汪精卫投降日本在南京成立伪政府;国民党在抗战中还曾同室操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但总体看,国民党及其主政的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面对强敌没有妥协、没有屈服,始终在正面战场与敌人浴血奋战。八年抗战中,因作战不力或指挥不当,被蒋介石和各大战区处决的军长不下十几个、师长不下二十多个,所以台儿庄等诸多战役中流行“不死于阵前,即死于国法”的军中语。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国民党抗战的状态。
由此可说,正如共产党开辟和领导敌后根据地和敌后战场,为抗战胜利做出艰苦卓绝的重大贡献一样,国民党领导正面战场和大后方地区与敌人顽强搏斗,也为抗战胜利做出了无法磨灭的重大贡献。从抗日战争的整体大局看,共产党提出和实施的一系列抗战方略,其所开辟和领导的敌后战场及抗日根据地在整个敌后占领区遍地开花,无疑具有全局性意义。而国民党作为执政党主持战时国民政府,其所领导的正面战场及大后方地区的抗敌斗争,具有全局性意义也是自不待言。承认国民党抗战具有全局性意义,没有削弱、更无法否定共产党抗战的全局性作用。承认共产党抗战的具有全局性意义,也无法削弱和否认国民党抗战所占居的全局性主导地位。双方在整个抗战中做出的互为补充的全局性贡献,是通过各自的领导能力和抗战实绩实现的,是在既联合又独立、既协作又斗争的矛盾统一过程中完成的,不能相互取代,也不应彼此抹杀。不承认其中任何一方所发挥的重大作用,都有违历史史实,也有违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原则。
有了这样的基本认识,我们才能避免因党派之争和意识形态偏见,干扰史实选取而片面地撰写历史;才能对抗战史中诸多重大事件、重大战役、重要人物等,做出比较客观的描述和相对公允的评价。譬如,从1939年9月到1941年12月,日军先后三次积集大批精锐部队进犯长沙,均遭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率部英勇抵抗而惨败:第一次长沙会战,歼敌死伤3.3万人,第二次长沙会战,歼敌死伤4.8万人,第三次长沙会战,毙伤敌人5.6万人,创抗战以来空前大捷。国民政府因此向他颁发青天白日勋章,后来美国总统杜鲁门还向他颁发自由勋章,以表彰其抗日功绩。可我们出版的一些民国史及抗战史对长沙会战多轻描淡写,这可能与薛岳曾率部围追堵截红军长征,解放战争中又多次与解放军对垒,后又跟随蒋介石到台湾不无联系。写好抗战史,需要明辨当时风云变幻的政治形势和复杂多重的人物关系,进而做出符合史实并恰如其分的叙述、分析和评价,这无疑饱含对我们史德、史识、史才的挑战和考验。
编写抗战史,另一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对待和处理有关抗战的多种资料。
抗日战争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算起,已过去78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三省算来,已长达84年。在这段相对漫长却消失不久并与今天紧密相连的岁月里,不同时期、不同主体以不同视角和不同方式,如报刊、书籍、日记、文稿、文件、档案、录音、影像资料等等,对抗战做了各式各样的描述、评说及研究。这些积累下来资料时间跨度较长,数量庞大,有的颇有史料价值,有的较少参考意义,还有的甚至充斥偏见,混淆视听,需要做一番认真梳理辨析,披沙拣金的工作。
自日本在祖国大地燃起战火那一天起,各种反映日寇暴行和中华儿女英勇抗敌的著述就层出不穷。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抗战结束后,尤其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陆和台湾学者及有关人士撰写的抗战文章和抗战史著作。这些多写于上世纪后半叶的著述,客观上已成为今天抗战史研究的一种背景和参照。可是,由于较长一段时间海峡两岸处于对立状态,受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两岸发表的不少抗战论著都存在明显偏弊,如台湾一些出版物说共产党在敌后战场是“游而不击”,而大陆一些出版物也说国民党抗战是“抗而不战”。如此罔顾事实的说法,都是不值一驳的。这类抗战著述的存在,与其说可让人作为某种参考,不如说提醒人从中吸取教训。我们今天研究抗战史,要认清此类著述感染了特殊时期的流行病菌,增强自身抗病毒、抗感染的免疫力。
还有一类需要审慎对待的抗战史料,就是各种各样的抗战回忆录和访谈录。抗日战火熊熊燃起,投身抗战者及经历战火磨难者就不断写出有关抗战的回忆录和亲历记等。近二三十年来,由于抗战参与者多步入耄耋之年甚至期颐之年,许多报刊设“致敬抗战老兵”或“抗战老兵口述历史”等栏目刊发大量访谈类作品,一些出版社也围绕抗战推出不少口述历史类或采访性纪实性书籍。这类著述由于具有当事人亲历、亲见和亲闻的特点,时常被当作珍贵史料予以重视。应该说,这类著述确有一部分讲述者经历独特且回忆和记叙严谨准确,很有史料价值和意义;但不少或因年代久远记忆有误、或因名誉夸耀之心作祟、或因采访记录者添枝加叶乃至杜撰编造,采纳使用时应特别小心谨慎。
最近读到一篇《老兵讲抗战》的文章,97岁高龄的解放军某部军政委刘增钰少将,1940年百团大战时在八路军129师任营长,采访者向他求证两个关于他抗敌的史实:“山西至今流传着‘刘营长赤脚进张净’的故事,我问他是否有这回事。他说:‘没有,那只是一种宣传,其实我打的是赛鱼车站。那次我们跑到张净车站的时候,别的部队已经把张净车站的日本鬼子打完了。……当时宣传人员找我问情况,我正好进城买鞋刚回来,因为下雨打仗我把鞋丢了,结果他们就用文学手法给加工一下,说我打的张净车站,后来这个故事就流传开了。’我问他是否参与消灭过日军的一个运输大队。他说:‘没有。只有一次我们在平定西边的一条小路上埋了几个地雷,结果炸死日本鬼子运输队的一匹马,马肚子炸开个窟窿,马上的人没死跑了,这事宣传得也不对。’”(见《文艺报》2015年7月27日)我很敬佩刘增钰老人谈论自己抗战不掠美、不邀功的诚挚的态度,但这两则兼有张冠李戴和捕风捉影的抗战报道流传很广,并被载入当地抗战史的事实提醒我们,书写抗战史对于一些来自采访、口述或回忆类的资料,选择和使用时应该慎之又慎。
书写任何一段已经逝去的历史,主要应依据这段历史的原始资料。所谓“原始资料”,即指这段历史当事人当时记载、当年留存或刊印的资料。这一点对于撰写抗战史尤为重要。其原因不仅在于原始资料相对可靠,相对接近史实真相,更在于中国抗日力量组成结构的特殊性,以及抗战后中国历史进程的沧桑巨变。中国抗日力量的构成,主体是共产党与国民党领导的两支部队。抗战前,共产党部队(红军和游击队)被执政的国民党视为“赤匪”而多次残酷围剿。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9月国共双方发表《国共合作宣言》,国民党转而承认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合法地位,并将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联合抗日。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发动内战,共产党针锋相对推翻其在大陆的统治,建立新中国。正由于八年抗战是国共合作时期,此前和此后是双方反目阋墙年代,因而抗战当时对战事等的记述,相对较少选择性过滤或有意无意地扭曲变形。如由苏中抗日根据地 1945年7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收有《关于抗战与团结的前途问题》一文,毛泽东在答美国合众社记者问时明确说:“我们拥护现在的中央政府,因为它坚持抗战的方针并领导抗战的行动”(P69)。而由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署名的《八年抗战经过概要》(国防部史料局1946印行)一书,对八路军新四军参与的重要战役也多肯定性记载,并在所附“作战要图”上有明确标注。
基于抗战原始资料具有这种还原历史的功能和价值,我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就较为注意搜集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战时期的出版物。这本《故纸硝烟——抗战旧书藏考录》,从抗战发生背景、日本侵略战序幕、八年抗战历程、战时中国政治、战时中国军事、战时中国外交、战时中国经济、战时中国文化、日本对中国研究、中国对日本研究、抗战善后与恢复等十余个方面,图文并茂地展示和评点抗战当事人当时写、当年印行的抗战旧书。我很庆幸自己能够与这些旧书结缘相伴,期望这些发黄发脆甚至破旧破损的文献资料,以当年白纸黑字、时代见证的身份,昭示中华民族在血腥抗战中的深重灾难和英勇伟绩,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狂妄野心和滔天罪行;同时也期盼这些旧籍能够为抗战研究者和关注抗战人士提供一点探寻真相的蛛丝马迹,早日读到更加全面更加公允的抗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