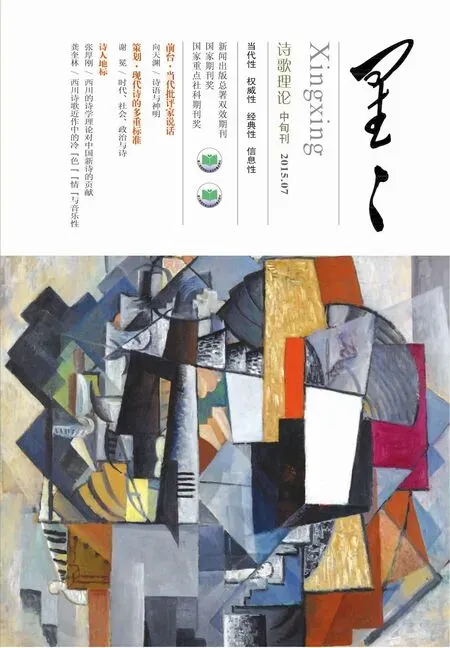追风人的行吟诗学和现代性体验——任怀强诗歌论
张元珂
追风人的行吟诗学和现代性体验——任怀强诗歌论
张元珂
我断断续续读过怀强的一些诗歌,故对其诗歌风貌也略知一二。我也曾经写过一篇不成体系的诗论。不过,那篇在济南读研期间匆匆草就的文章既没有打开其诗歌的艺术之门,也没有破解其诗歌的核心密码。当然,对其诗歌的表意体系、审美倾向和美学思想也就更无从把握。对我来说,单从对少量文本的解读,或者对某一阶段文本共性的归纳,想全面而准确地评介怀强及其诗歌是非常困难的。为了不致让这次写作又沦为片面或肤浅,我不得不将古人研习诗歌的方法引入笔者的以“文本”为中心的批评范式中来。我们知道,“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作为诗歌鉴赏的方法一向是中国古典文论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在新文学领域中作为新诗外部研究的一个基本策略也一直被广泛采用。认识怀强也有五个年头了。五年中,对其为人、为文也稍有了解,因此,我觉得这种既有文本细读体验又有外部考察经验的研读能够修补此前由于单纯地聚焦于审美形式的分析所带来的诸多弊端。
先从一个事例说起。我们知道,在美国本土,有一群以追赶台风为志趣的追风人。每当台风来临,他们成群结队向着台风的方向奔袭,逐渐靠近台风中心,甚至做出与之拥抱的举动。在一般人看来,这简直不可思议,因为它挑战了人们对大自然危险性一面的认知底线。然而,人类文明正是因为追风人们的梦想及其实践而生生不息,源远流长。追风人是一种隐喻的主体。这是一类不遵从世俗规则,不安于现定秩序,不满于此岸风景而总是对自由世界、他处生活和彼岸风景充满无尽幻想并为此而努力实践的寻梦人。天才作家也大都是这种追风人。他们要么徜徉于天马行空的想象世界里,要么陶然于自我营造的自在空间里。前者以庄子和李白为例,后者以陶渊明为证。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界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追风人的存在而使得人类在追寻精神天空的高度、深度与宽度中有了与浩瀚宇宙展开对话的资本和能量。伟大的文学家固然如此,每一位有理想有抱负有创造性的诗人也不同程度地拥有此种气质。
细细打量怀强十多年来的履历,其由新泰到济南、再由济南到北京的或长期或短期的居留经历,其从在济南的求学、打工、写诗到北京的办刊、生活与游历,其从京城到故乡之间如同候鸟一样的往返过程,其从中心到边际的如同江湖侠士一样的游走经历,其从创办民刊《诗群落》的野心到现代性诗艺的探索与实践,都使我觉得以追风人这一称谓指称其作为诗人的身份特征是较为合适的。我们从《去瓦城的路上》、《追风的人》、《走在城市的路上》、《临窗而望》等这些标志性的诗歌文本中深刻体会到这种诗人形象。不妨说,付之于生活,他在是与非之间摇摆,身体与心灵的相互分离让其永远处于一种漂泊状态;付之于理想,他在实与虚之间抉择,感性与理性的彼此排斥让其处于一种游走状态;付之于审美,他在真与幻之间思想,物性与神性的最终诀别让其处于一种忘我状态。总之,诗歌作为其精神意识的产物,其审美边界就是在是非、虚实和真幻之间移动,最终假借个性化的语言(文字)或有意味的言语(声音)表达某种意识。
如果说追风人一词是界定怀强诗人身份特征的一个,那么,由此而生成的“行吟诗学”则可看作评介其诗歌美学思想的
。“我只是一名诗歌路上的行旅者。”“瓦城的存在与否不重要,为什么要去瓦城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曾背着行囊走在路上;更为重要的是,如今我依然背着行囊走在路上。”(引自诗集《走在瓦城路上》后记)在这里,“走在路上”不仅是一种物理状态,也是一种精神状态,更是一种写作状态。前者给现实境遇中的诗人以一种生活的历练,中者给诗人以精神上的富有,后者为其探索与实践新新诗经验提供了更多可能。也就是说,经年累月的漂泊与旅行带给诗人以体验生活、反观现实和映照自我的足够的经验意识。他携诗歌上路,且行且吟,或以诗代酒,不断抵御着外在的风寒,或以梦为马,屡屡消弭粗砺生活带来的现实窘境,然而,他以修辞的方式进入生活中心,也以修辞方式进入这个世界的关于审美化的理解。这也使得他的诗歌总是深深打印着异乡抒怀的游子情怀、体恤众生的人文精神和孤独言说的生命意识。需要强调的是,他的诗歌无论指向乡土和都市的形而下的日常体验,还是有关时间和生命的形而上探索,其表达重心无一不是现代人的现代情绪和情感。这里有怜悯,有批判,有反思,也有寄托。这是从行旅生命中提炼出来的经验,一种种真切到骨子里的透彻、澄明,这份来自大地深处和灵魂内部的诗情诗意绝没有丝毫的扭捏或斧凿。
他的诗歌不但成为一种个体生活和精神的需要,也最终定格成为一种反映当代社会风景,反思现代文明的主体镜像。近年来,其在《尾随乡村身后》、《又想见我的外婆》、《去瓦城路上》等文本中对现代文明映照下的乡土情怀、精神寻根、日常人伦的表达与言说,其在《阳关三叠》、《广陵散》、《高山流水》、《梅花三弄》、《平沙落雁》等一组以古人古事为诗意生发点的文本中对历史情景、氛围和人物精神境界的现代性体验与书写,其在《凌晨三点钟的修路工》、《花灯老人》、《燃灯塔下》、《守陵人》等当下文本中对凡人俗事和日常风景中的本相及意义的聚焦与表现,其在《一个人的好天气》、《经过这条大河》、《被风吹过的青春》、《初雪》、《童年》等文本中对个体情怀、理想愿望、往昔生活的聚焦与体验……都充分显示了其诗歌所呈现的两个较为明显的审美向度——持续向内指涉和大幅度向外拓展。向内指涉是深度表达一己情感的需求,向外指涉是充分介入现实生活需要。这两种审美向度既表征了其诗歌写作视野的有效拓展,也表现了一位有追求的当代诗人因不满足于已有秩序而试图开创新诗作经验领域、探索新诗表现形式的创新精神。
忧郁和感伤是岁月赠予诗人们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永恒性地成为其灵感生发和经验表达的原乡。而对于由乡村走向城市并最终留驻大都市环境中生活和写作的诗人来说,他们写作大都趋向于一种驳杂的经验综合,呈现为一种分裂的精神幻象。从这方面来说,我非常欣赏《去瓦城路上》这首诗。首先,其意象体系是有意味的。瓦城不是一个实在的存在,而仅是一个符号。无论“我浮在瓦城的空中”,还是“去瓦城的路上”,“我”最终都不能进入它的腹地。“我”和瓦城以隔离的方式相互对视。其次,其主题是多义的。这首诗充分地诠释了诗人“在路上”的姿态和体验。它不仅表达了个体的爱和忧伤,也表达了现代人寻觅精神家园的游子心态。再次,其表现方式是富有新意的。它的节奏和意境是古典的,它的情感和意绪是现代的,它的言说和表达是含蓄的。总之,这个文本给人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和诸多阐释可能性。
现代社会高速发展,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现代观念翻天覆地,这当然是人类几千年不遇之胜景,但所谓“发展”从来就有有序和无序之分,前者给人类以福祉,后者会引发灾难。所谓“现代性”也不单纯是一个时间概念,进化论逻辑也不适用于文化(精神)领域,而中国的现代性发展也绝对不是GDP一统天下的畸形模式。中国近30多年来的发展让人眼花缭乱,事实上,文明与生活的冲突、发展与守成的矛盾、生存与生态的对立每天都在上演着。一位优秀的诗人即使出于最基本的道义也断不可无视这种矛盾与冲突。《高速公路边的庄稼》、《经十路以南》、《藏人治沙记》等诗歌都是诗人以个体之思深度介入文明与生活冲突中心的典范文本。其中,有些文本因为灌注了诗人情感的汁液而显现为一种“身与物化”、“兴象应感”的合一状态,所以,其情感表达和诗意呈现也都格外感人。比如,“高速路穿过庄稼地/活着的庄稼向死去的庄稼哀悼”(《高速公路边的庄稼》),像这样的以略带感伤的挽歌调子表达现代与传统冲突中的乡土之痛和被劫掠之无可奈何境遇的写作都是入于心、关乎情的;“草原在退化/若尔盖曾开沟排水疏干沼泽/植草种树是为过去还债/而恶性循环已渐渐癌变”(《藏人治沙记》)像这类以再现而非表现方式直面现实的文本虽不如前者感染人,但其不动声色的批判背后也寄托诗人对人类与自然生态关系的深度思考和美好期盼。
他的诗歌从来不缺乏对时间之纬、孤独之思、存在之谜等形而上主题的表达。这类偏于体验性的独语性的文本常因主体思维的大幅度跳跃、情绪节奏的不合乎逻辑性以及时间空间化的抽象处理而在诗意呈现和诗境形成方面表现为混沌状态。当然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样的写作是诗人面向自我内心、封闭言说的艺术结晶,也是现代社会中高度发达的现代人的精神思维活动的必然产物,更可以说是超脱于寻常经验世界和日常逻辑规则的诗艺术实践使然,然而,高度陌生化的意旨与形式也使得文本在可写性与可读性之间不具有和谐的通约性,实际上,那种随便的缺乏关联的对抽象经验的简单罗列阻隔了接受的正常言路。所以,我对《沙尘》、《一个人和他的影子》、《研究史前动物的生存方式》、《镜子》、《墙》、《照片》等一类诗因过于纠缠于抽象命意而忽略了诗歌在声音指向和意像指称的不及物性的诗歌写作路径心存疑虑。比如,在《一个人和他的影子》中,那些散乱、破碎、混沌,线团化、复合化、矛盾化的情感、情绪,那种有关黑暗、恐惧、爱情、光明、终极追问等一系列生命景观的深度呈现,都被置于一个文本内,显得多么凌乱而又拥挤不堪。而一旦当类似“接近一个生命又关闭一扇门”、“我来来往往中烧干了骨头和血肉”、“黑暗一手拍打着我”、“我也一手拍打着火焰”等语言单位构成了文本的形式要素之时,这就成为一种个人游戏:语言从迷宫到迷宫,主题从抽象到抽象,表达从不及物到不及物。与之相反,《一棵树能承受多少重量》、《如此我穿越了平原》、《追风的人》、《火焰》、《解读时间》等同样表达现代性生命内涵或哲理意蕴的文本则呈现了一种返璞归真之态。简易的形式、熟悉的节奏和不加雕琢的语言使得其不仅因读写规约的通约性而具有了可亲可感的面容,还因其以小见大、以此映彼、以简单烛照抽象的修辞意向而使其意蕴呈现的层次、秩序和精神指向有了较为清晰的纹理。比如,在《火焰》中,作为诗歌意象的“火焰”和作为核心句式的“一部分之外的一部分”组成了这首诗歌的形式因素,而句式的不断循环往复,两种意绪的对立呈现,不但使得形式本身就是内容,也使原本复杂的生命景观因诗人修辞的简单介入而有了感性化的呈现。这是笔者愿意看到的经验呈现的路径:简约中见出复杂;单纯中映出深邃。
节奏是诗歌的脉搏。节奏跳跃性大既是标志诗歌经验呈现驳杂景观的标志之一,也是标志诗人思维走向深邃、与现实生活或生命存在产生深度感应的外显标志之一。怀强的诗歌善于以大幅度的情绪跳跃结构文本,其诗作内部往往因为情绪单位之间缺乏必要的合乎逻辑的连接而产生读解的难度。不过,他发表在《青年文学》(2013年第12期)和民刊《诗群落》(2012年第1期)上的一组诗歌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生活啊生活》、《谁说我不在乎他》、《平沙落雁》等诗歌无不表现为具体可感的艺术形式,不但句与句之间,节与节之间极少过于抽象的、不合情感逻辑的跳跃,而且句内以断句形式表征的情绪节奏也较少出现大幅度的断裂。这使得其诗歌趋于意境的营造和情感的集中显现,而非表达的离散化、碎片化。比如《谁说我不在乎她》:“十年多少个十年/爱与恋纠缠/没有脚印的水泥路/没有泥土的呢喃/那些背影 那些天空的蓝/比记忆更久/比我的生命更完美/当我老了 是否依然想起/那牵过童年的手/和没有黄昏的小河边/有双小脚丫搅动水波/多少爱这样无声无息的滑落”。
而《一个人的好天气》和《初雪》则代表了其诗歌写作的另一面向:风格轻灵飘逸,思想简单澄澈,经验甚接地气。“一个人的风雨同舟,一个人的/天下,一个人的死去活来,/一个人破茧为蝶,一个人的/飞翔,一个人还是一个人。/一个人的好天气,是/某时某地都有一个人在心中,/有她或他的祝福想念问候和/连绵不止的关爱。一个人的/好天气,不是他或她的,也有/你和他或她的甜美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一个人的好天气》)“时而鹅毛,时而谷粒,时而碎片。/不缓不急,不躁不乱。/一如既往的雪,一如万卷翻开的书卷。/有留声机缓慢地倾诉,/有千言万语悄悄植入你胸怀。/曼舞而来,随风飘去。/栖居树枝头的,也不甘落寞。/守候,仅仅是为了华丽的展翅。/平躺下的,大地有几分安逸。/我们微小的生活,有了几分刻度。/极目望去,所有的安静而秩序。/所有的平淡而真实。而有我,/我在;让具体的生活有了一丝暖意。/这是那么微小,而我又不得不做的。/那么强悍的胸怀,一览无余。”(《初雪》)很明显,这类诗歌中的意象、节奏和气韵都是为我们所熟悉的,那种陌生化的经验和扭曲的形式完全没了踪影。诗人对于美好人性、人情的渴盼,对于吉祥生命和安静岁月的期待,借助简单的形式和音乐性的节奏得以艺术化地呈现。这类诗歌从形式到内容都是返朴归真的。《致美好》、《童年》、《礼物》、《纸飞机》、《被风吹过的青春》、《打捞时间的人》、《华尔兹的春天》等诗歌中更是多了一些对童年生活、青春岁月和美好未来的诗意抒写。这些诗歌的意境单纯明净,情感意绪温暖柔和,言说语调娓娓动听,尽显诗歌的婉约质地。也许因为步入中年的缘故,其诗歌写作似乎少了一些尖锐,多了一些温柔,少了一些直接批判,多了一些理性反思,少了一些剑拔弩张,多了一些温文尔雅。繁华落尽见真淳,这也是一种诗歌写作的至高境界。此种境界让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