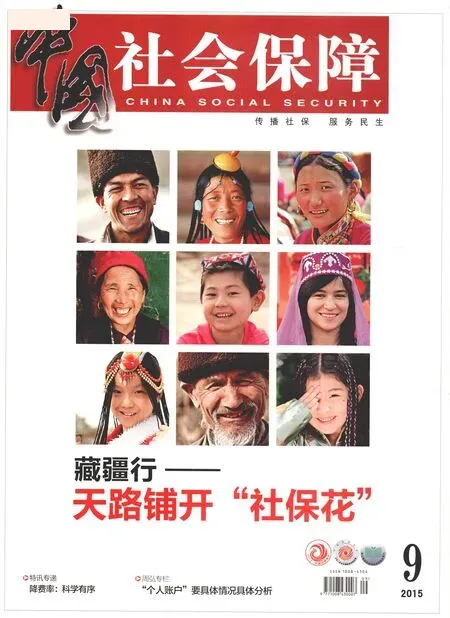受降现场:只有我能自由走动
■采访、整理/本刊记者 陈萧军
受降现场:只有我能自由走动
■采访、整理/本刊记者陈萧军
老兵档案

新六军军官俱乐部开幕纪念合影,图中后排左五为赵振英
姓名:赵振英
年龄:98岁
主要经历:
曾任国民革命军新六军14师40团第一营少校营长,1944年4月入印缅作战;1945年9月9日在南京侵华日军投降仪式现场负责警戒工作。
我1917年出生在北平通县一个普通家庭。“九一八事变”时,我刚上初一。我从小喜欢读书识字,初中毕业后上了通州师范学校,想以此改变未来的命运。
一记耳光打碎求学梦
1937年,通县师范学校搬到了西单皮库胡同,那时我师范快毕业了,准备报考北京大学,将来做一名工程师。但是卢沟桥的枪声彻底打碎了我的人生规划。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兵临城下,北平异常紧张,西单、新街口等主要路口都围上了铁丝网,修起了碉堡,中国军队准备跟日本兵巷战。一天,我走在大街上,一个日本兵无缘无故抽了我一记耳光,在耻辱和愤怒之下,我决定离开北平,走上从军报国之路。
1937年7月底,我乘坐火车离开北平,到达连云港,辗转找到曾在中学时负责军事集训的黄杰将军(注:黄杰,黄埔一期生,“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时任陆军第八军军长兼税警总团长),将军推荐我和一些同学去江西星子县的黄埔军校特训班。随后,我和同学们步行入川,在成都分校学习,正式成为黄埔十四期十总队的学生。
1939年秋毕业后,我来到驻扎在常德的54军服役。54军驻防滇南时,我担任军部参谋,军长是黄埔一期生黄维。当年黄维看中我忠厚正派和好学,让我在他身边当参谋,还替他保管财物。为了让我有更好的发展,他保送我去中央陆军大学参谋班进修,然后去一线作战部队任职。再后来我来到战斗部队,上司潘裕昆、龙天武等人,也都是黄埔四、五期生。
1939年12月,日军发动第一次粤北作战,54军奉命驰援,我参加了韶关一带的作战。1940年初,54军又调往广西,增援昆仑关。1942年后,54军调防云南,防备日军从越南北犯昆明。
1944年3月,我随部队54军14师从云南祥云机场搭乘C-47前往印度利多,成为驻印军。飞机沿驼峰航线入印,飞行途中,我望向舷窗外,那时有个说法,说驼峰航线底下的那条路,是用飞机的铝片铺成的,意思是说那里曾经掉下来过很多架飞机。
在利多,14师脱离54军建制而转入国民革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新六军建制。部队全体换上英式军装,戴上英式钢盔,装备都是美械,还配备了火箭筒,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步兵反坦克利器。伙食也比国内好得多,牛肉罐头随便吃。训练中,美军毫不吝惜弹药消耗,子弹炮弹随便打,完全没限制。
虽然配备了美式装备,但远征作战的艰苦和危险,仍然出乎我的意料。在遮天蔽日的原始丛林中,部队艰难地行进着。开路的两位士兵,一人拿一把砍刀,披荆斩棘,一人砍左边,一人砍右边;后面再一点点扩大,逐渐开成四个人的路,六个人的路……直至将路扩到可以过车。
日本人很歹毒,把机关枪架在树上,隐蔽且居高临下,杀伤力强。我们一进森林,就得先举起机关枪冲着树上扫射,扫掉隐蔽的日本兵再往前走。
1944年4月,我已是新六军14师40团1营少校营长,那年我27岁,离开北平从军进入第七个年头。
1944年底,日军突然抵达贵州独山,直逼重庆,廖耀湘(黄埔六期生)率新六军回国。1945年4月,雪峰山会战开始,新六军空降驰援芷江,正是在芷江,我迎来了抗战胜利那一天。
1945年8月,新六军奉命进驻湘西接受日军洽降,我担任受降仪式的警卫工作。8年前,我手无寸铁,乘坐挂着白旗的火车,胸怀耻辱和愤怒离开北平;如今,我全副武装,看到日本鬼子坐着挂着白旗的汽车前来投降。岁月峥嵘,无法掩盖我作为一名中国军人的荣光。

奉命保卫南京受降现场
新六军被称为“王牌中的王牌”,1945年8月底,部队被空运至南京,驻地附近在田里劳作的农民看到是中国军队,都兴奋地举起锄头致意欢呼!
1945年8月28日,我率领第一营,负责南京城外大校场机场的警戒工作。这是在历经8年抗战后,第一支重返南京城的中国军队。一天,一名喝醉酒的日军突然擅闯警戒中的机场,我下令击毙,关键时刻,不容有丝毫马虎!
9月初,我接到命令,率第一营官兵负责日本投降签字典礼会场警戒。9月8日晚,我彻夜未眠,与团长王启瑞商量第二天的会场警戒工作。
9月9日,令所有中国人无法忘却。
投降签字仪式设在南京中央军校的大礼堂。从礼堂门口一直到外面的大街上,每隔50米就竖着一根用蓝白相间布条包裹着的旗杆,旗杆上挂着中、美、英、苏等同盟国国旗。每根旗杆下都站着一名全副武装的一营士兵,他们身着绿色卡其布美式军装,戴着钢盔与白手套,背军用背包,手持美式冲锋枪。
礼堂正门上方的塔楼上嵌着一个巨大的红色“V”字,以示胜利,下面悬挂着红布横幅,上书“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会场”。礼堂正中间就是签降地所在,用淡蓝色的布包围起来。受降席桌边放着5把皮椅,桌子中间预先放置了文具盒、文件夹。投降席桌子比受降席窄,旁边有7把木椅。
8时52分,悬挂在礼堂上方的4盏水银灯突然亮了。时任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走进礼堂,全场肃立。
8时58分,由军训部次长王俊中将引导日本投降代表、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及小林浅三郎等7人,自大礼堂正门步入会场。这次,日军代表的着装,还算整洁。因为参加密苏里号上投降仪式的日军军官为了表达作为投降代表的不满,现场故意穿着又脏又旧的军装。曾经不可一世的日军军官们耷拉着脑袋、哭丧着脸,手枪被要求放在会场之外,没有武器,也不准带日本军官特有的指挥刀,徒手进入会场。
冈村宁次低垂着头,一言不发。他在投降书写上自己的名字后,从上衣口袋内取出印章盖上。中国受降代表何应钦起身接受日军的投降书,后人多对何应钦起身接过投降书大为不满,其实应该客观看待。因为当时那个桌子很大,如果不站起来,坐着是接不到投降书的。
签字仪式时,我的位置在投降席后面。身为营长,我对整个仪式的警戒任务负有检查之责。那天我穿上了特别为这一刻定制的马裤和马靴,来回在现场巡视,是当时会场内外唯一可以自由走动的人。我的任务是时刻注意现场情况,防范意外发生,这是抗战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我们必须保护和守卫它。
受降仪式结束后,南京倾城欢庆,军民上街游行,热闹极了。游行队伍中,我骑马走在第一营队列的最前面。
受到习总书记接见
新中国成立,我把军队的经历向组织做了说明,组织并没对我进行处理。退休后,我过着默默无闻的平静生活。
2005年9月9日晚,《新闻联播》播放了纪念南京受降仪式60周年的新闻,我突然开口对儿子赵精一说:“那个时候,我在现场。”儿子并不相信我的话,因为他从没听我说过这事。此后,我没有再提,他也没有再问。
2008年春节,有亲戚来访,听说我曾参加过远征军,就在网上搜索我的名字与部队番号,无意间进入了黄埔军校网,并看到了一篇寻访老兵的帖子。帖子里有一张合影和一个红色的记录本。合影上写着:“陆军新编第六军军官俱乐部开幕纪念 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六日于南京”。红色记录本的主人是新六军14师美国少校联络官约翰・葛顿南,抗日战争期间他在中国的行程都记录在这个小红本上。
眼前的一幕,将我重新拉回到60多年前。合影最上方右侧,穿着长筒马靴微笑的那个人就是我。合影后不久,约翰・葛顿南离开中国之前,拿出一个红色记录本,让在场的中国军官签名,我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的儿子赵精一一眼就认出了我的名字和笔迹,辗转找到了发帖人——抗战名将潘裕昆的外孙晏欢。晏欢知道后来北京看望我,他一直在收集远征军文史资料,在一位美国远征军老兵后代的网页上看到了一个红色日记本,上面有许多中国远征军军官的签名,也包括我的。于是便开始寻找签名者,终于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当年签名者之一的我。
2010年10月,93岁的我在朋友的帮助下注册了微博,由孙子将我的口述敲成文字,而我常拿着放大镜看网友的留言,和他们一起交流那段难忘的历史。
2014年7月7日,我作为抗战老兵代表出席在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的纪念仪式,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