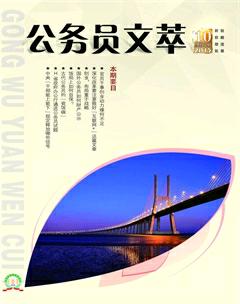三种人生态度
梁漱溟
“人生态度”是指人日常生活的倾向而言,向深里讲,即入了哲学范围;向粗浅里说,也不难明白。依中国分法,将人生态度分为“出世”与“入世”两种,但我嫌其笼统,不如三分法较为详尽适中。我们仔细分析:人生态度之深浅、曲折、偏正……各式各种都有,而各时代、各民族、各社会,亦皆有其各种不同之精神,故欲求不笼统,而究难免于笼统。我们现在所用之三分法,亦不过是比较适中的办法而已。
按三分法,第一种人生态度,可用“逐求”二字以表示之。此意即谓人于现实生活中逐求不已,如:饮食、宴安、名誉、声、色、货、利等,一面受趣味引诱,一面受问题刺激,颠倒迷离于苦乐中,与其他生物亦无所异;此第一种人生态度(逐求),能够彻底做到家,发挥至最高点者,即为近代之西洋人。他们纯为向外用力,两眼直向前看,逐求于物质享受,其征服自然之威力实甚伟大,最值得令人拍掌称赞。他们并且能将此第一种人生态度理智化,使之成为一套理论——哲学。其可为代表者,是美国杜威之实验主义,他很能细密地寻求出学理的基础来。
第二种人生态度为“厌离”的人生态度。第一种人生态度为人对于物的问题,第二种人生态度为人对于人的问题,此则为人对于自己本身的问题。人与其他动物不同,其他动物全走本能道路,而人则走理智道路,其理智作用特别发达。其最特殊之点,即在回转头来反看自己,此为一切生物之所不及于人者。当人转回头来冷静地观察其生活时,即感觉得人生太苦,一方面自己为饮食男女及一切欲望所纠缠,不能不有许多痛苦;而在另一方面,社会上又充满了无限的偏私、嫉忌、仇怨、计较,以及生离死别种种现象,更是使人感觉得人生太无意思。如是,乃产生一种厌离人世的人生态度,此态度为人人所同有。世俗之愚夫愚妇皆有此想,因愚夫愚妇亦能回头想,回头想时,便欲厌离。但此种人生态度虽为人人所同具,而所分别者即在程度上深浅之差,只看彻底不彻底,到家不到家而已。此种厌离的人生态度,为许多宗教之所由生。最能发挥到家者,厥为印度人。印度人最奇怪,其整个生活,完全为宗教生活。他们最彻底,最完全;其中最通透者为佛家。
第三种人生态度,可以用“郑重”二字以表示之。郑重态度,又可分为两层来说:其一,为不反观自己时——向外用力;其二,为回头看自家时——向内用力。在未曾回头看而自然有的郑重态度,即儿童之天真烂漫的生活。儿童对其生活,有天然之郑重,与天然之不忽略,故谓之天真。真者真切,天者天然,即顺从其生命之自然流行也。于此处我特别提出儿童来说者,因我在此所用之“郑重”一词似太严重。其实并不严重。我之所谓“郑重”,实即自觉地听其生命之自然流行,求其自然合理耳。“郑重”即是将全副精神照顾当下,如儿童之能将其生活放在当下,无前无后,一心一意,绝不知道回头反看,一味听从于生命之自然的发挥,几与向前逐求差不多少,但确有分别。此系言浅一层。
更深而言之,从反回头来看生活而郑重生活,这才是真正的发挥郑重。这条路发挥得最到家的,即为中国之儒家。此种人生态度亦甚简单,主要意义即是教人“自觉的尽力量去生活”。此话虽平常,但一切儒家之道理尽包含在内,如后来儒家之“寡欲”、“节欲”、“窒欲”等说,都是要人清楚地自觉地尽力于当下的生活。儒家最反对仰赖于外力之催逼与外边趣味之引诱往前度生活。引诱向前生活,为被动的、逐求的,而非为自觉自主的。儒家之所以排斥欲望,即以欲望为逐求的、非自觉的,不是尽力量去生活。此话可以包含一切道理,如“正心诚意”、“慎独”、“仁义”、“忠恕”等,都是以自己自觉的力量去生活。再如普通所谓“仁至义尽”、“心情俱到”等,亦皆此意。
此三种人生态度,每种态度皆有浅深。浅的厌离不能与深的逐求相比。逐求是世俗的路,郑重是道德的路,而厌离则为宗教的路。将此三者排列而为比较,当以逐求态度为较浅,以郑重与厌离二种态度相较,则郑重较难,从逐求态度进步转变到郑重态度自然也可能,但我觉得很不容易。普通都是由逐求态度折到厌离态度,从厌离态度再转入郑重态度,宋明之理学家大多如此,所谓出入儒释,都是经过厌离生活,然后重又归来尽力于当下之生活。即以我言,亦恰如此。在我十几岁时,极接近于实利主义,后转入于佛家,最后方归于儒家。厌离之情殊为深刻,由是转过来才能尽力于生活;否则便会落于逐求,落于假的尽力。故非心里极干净,无纤毫贪求之念,不能尽力生活。而真的尽力生活,又每在经过厌离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