虫草(四)
洛桑卓玛
夜半,街灯白惨惨的,风躲进狗窝里取暖,河水发出沉重的叹息,独自嘀咕消逝的容颜。偶尔有醉鬼踉踉跄跄地寻思着该往哪个方向。在公安局折腾到半夜,斜眼和帕尔楚现孤零零地走在冷冷的街头。
斜眼摸了半天才找出钥匙,哆嗦了半天打开门,拉亮灯,房里堆满箱子,有两只耗子吱吱叫着逃到暗处。箱子的深处搭着一张床,上面睡一女人,怀里的孩子被开门声惊着了,哇哇大哭。女人看了他们一眼,无声无息地起床,收拾好孩子,走进里屋,借着昏暗的灯光,帕尔楚看到这女人一只脚长,一只脚短。斜眼抱出一床崭新的被子,盖在床上,让帕尔楚睡,自己钻到里屋,关上门,熄了灯。
早上,帕尔楚被孩子的哭声吵醒,头重脚轻着起床,推開里屋,里屋有张木桌,木桌上是两口黑不溜秋的锅、一个脱了色的水壶、半把焉白菜,一根干干的香肠,两个大瓷碗,几双筷子装在半截塑料瓶里,半桶清油放在桌下,落满灰尘。一张破烂的小沙发上,孩子正哭闹着。
夜幕降临,帕尔楚走进里屋,关上门。他不想让格绒知道此事,更不想让家人担心。
连续几天,帕尔楚和斜眼一大早守候在公安局门口,看着每一辆警车开出去,燃起满腔的希望,看着每一辆警车开进来,兴奋地跑过去,听到办公室的电话一响,心也跟着扑通扑通地跳,看着办公室电话放下去,又期待下一次快点响起,可每次都像给熊熊燃烧的火,浇了一盆水,连冒缕烟的机会都没有。最后俩人走到街上,看到一个穿白衣服的,都想扑过去,也不分是个男人还是女人。
第四天清晨,天还没开亮,有人轻手轻脚地敲门,斜眼揩着眼屎去开门,突然惊呼:“老板?老板!老板……你可回来了!呜呜呜呜呜……”帕尔楚从里屋冲出来,白西装依然一身白,身后拖着密码箱,笑容像春天:“我回来了,哎!遇上了一些事,不好意思让你们担心了!”。白西装不像欠了这么多钱消失了,而像回家过年的人,因事耽误了几天而懊恼。
斜眼找来洗脸帕,赶忙擦拭木凳,白西装从兜里拿出一张纸,垫在木凳上才落座。他打开密码箱,没设密码,一碰就开了,里面是钱,还有帕尔楚的虫草,根本没动,帕尔楚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打的疙瘩。白西装拿出一叠钱,放到斜眼手里,斜眼的眼里满是泪:“我只要每天一百元的工资就行了,老板,我不要这么多,我没做什么事!”。白西装一挥手,细声细气地训:“把钱收起来,怎么像个女人婆婆妈妈的!”。斜眼的儿子瞪大了眼睛,一声不哭。
白西装又把帕尔楚叫到身边,把一捆钱放到帕尔楚手上:“数数!十万。一分不少!”帕尔楚抽出一张,拿到耳边啪啪啪地拍,大红钞票发出啪啦啪啦啪啦的声响,举到灯下一照,毛主席温和地对他笑着。帕尔楚赶忙找到褡裢,把钱塞进去,奄奄一息的褡裢一下精神焕发,像饿了十几天的狼突然吃了一头牛。白西装又拿出一沓钱,笑眯眯地放到帕尔楚手里:“这是利息,快点回家,给家人买点好东西。”。
帕尔楚背着胀鼓鼓的褡裢,像背着整个世界。他找到格绒一起回家。格绒迎着风:“怎么样?城里比牧场上好吧?——”帕尔楚大喊:“我要回家,我要去放牧,再也不做生意了!城里有钱过好日子,没钱连碗水都没人给,而且我怕城里没钱的日子比死还难受!”格绒大笑:“是啊,我刚来康定,连厕所都找不到,尿又急,到处都是人,没办法,来到河边就撒了。背后有人指指点点:“脸上长毛了!”,帕尔楚接话:“是啊,我都问了四五个人才找到,还要给钱。城里没钱别说吃不上饭,就是给尿都要憋死——”。格绒笑:“哎!在城里怎么有钱也找不到在牧场上的感觉,而且好好想想,有时在城里吃什么、用什么、往哪里走、往哪里坐,什么都搞不懂,也真跟牦牛差不多!还是回家好,过惯了,不管有钱没钱,踏——实——”。帕尔楚咧开嘴:“在草原上虽当不上格萨尔,可也算是他的一员猛将啊!我们谁也不离开草原好吗?”格绒很坚定:“好的!一言为定!”。
阿妈穿上绵羊皮袄,用鸡爪一样的手,不停擦拭眼角,左看看,右转转,直犯嘀咕:“我这把骨头,也太糟贱这身衣服了,还是给央宗穿吧!”。他看着满世界的阳光:“阿妈,给您买的您就穿上吧,等到冬天,我再给央宗做一件就是了!”央宗自顾自地穿着白布仁衬衫,脸上盈满笑,一点都没掩饰。小儿子看到拨浪鼓,叽叽咕咕地笑个不停,涎水流了一胸。
阿爸没站起来已有一些时日了,也坐不了摩托车,还是包个车吧,顺路到女儿的学校把书包送过去。
车一路颠簸着前行,阿爸卷在车里,哦呵哦呵哦呵地咳,忍不住推开车窗,吐了一口痰,气力不够,痰被风吹了回来,落在胸口,猩红猩红的,有血。帕尔楚拿出氆氇卷,擦拭了几下,让阿爸把头枕在自己腿上,阿爸乖乖地躺下,像个婴儿,卷缩在他腿边。
阿爸的头发灰白灰白的,颧骨高高隆起,眼眶落在低处,身子骨跟车吱吱嘎嘎地响着。阿爸曾经是夏龙草原上叫得响的汉子,勇猛、能干、风流,可前些年落下这咳嗽的病,天也不帮,接连遭了几场雪灾,牛也所剩无几,阿爸的病就这样拖下了。如今阿爸卷在他腿上,像个孩子一样听他的话,帕尔楚心里酸酸的,把阿爸的头紧紧抱住。
到女儿的学校把书包送上,还买了一个笔盒子,盒盖上有只猫,坐在河边的木凳上,长长的鱼竿上吊着一条鱼。那猫,撅起胡子笑着,那鱼,湿滑的身子还在跳跃。小小年岁的女儿,居然抱着书包和笔盒子哭了,那伤心劲,比她的年龄久远了很多!
阿爸的病一天天好起来,没过多久就回家了,钱还剩了不少。
早上的阳光像金子,像虫草的颜色,洒遍了草原。牛群散向草原,阿妈摇着经筒出门,阿爸跟在阿妈身后,笑得落到低处的眼眶里看不见眼睛。
突然儿子的哭声震破了草原,手里的拨浪鼓绊成了两瓣。他抱起儿子,怎么哄劝都不停,儿子就这么铺天盖地的哇哇哭。
帕尔楚的耳朵要被震破了,使劲摇头,使劲睁开眼:眼前有张木桌,木桌上是两口黑不溜秋的锅、一个脱了色的水壶、半把焉白菜……自己的身体正挤在一张破旧的小沙发上,额上冒着汗,外屋斜眼的儿子哭得撕心裂肺。
整整五天,两人天天守在公安局办公室门口,除了白西装往成都方向逃了,第二次接听斜眼的电话时都到了雅安之外,再没任何消息。警察告诉他们:“有消息会通知你们的,你们天天守在局里,妨碍我们办公,还不如快点去挣点稀饭钱。你们两人的事自己协商解决吧,解决不了就上法院,公安局管不了此事!”。
第六天清晨,云很黑,很沉,有雨,落不下来,斜眼跨着一彩色书包,包里装了个拨浪鼓,老婆手里紧紧握着一红布包,包上缠的线打了几十个疙瘩,她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斜眼身后嘀咕:“哎!吃一顿肉要想一个星期,手上生满冻疮,都舍不得买双手套,看来没命,没福气的人就是这样了。但愿这积攒一辈子的血汗钱,能躲过这个祸,不然我们真的走投无路了。”斜眼瞟着上方,脸上揪出水来:“老婆,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知道这些钱都是你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哎!今后我当牛做马也要挣回这些钱。可人家损失了那么多,我们也没办法不赔人家啊!”。
斜眼推开门,静悄悄的,老婆推开斜眼,扑向床,床上空空落落,什么也没有,老婆又扑向斜眼:“你这天杀的,还我儿子——你还我儿子——”。
警察来到斜眼家里,斜眼看到这个面色白皙的警察,把同样白皙的手指放在鼻前,像思索着什么,又像阻挡着什么。斜眼细细描述帕尔楚的模样,帕尔楚的德行,却越来越迷惑:“他根本不像个坏人!”,警察带着鼻音嘟哝:“人在沉重的打击下,所作出的决断是不能用常理去推断的!”。那白皙的手指堵着鼻子,斜眼听不清警察在说什么,斜眼感觉到压在胸口的有个东西瞬间爆炸了,像火山一样直往上喷,在喉结堵了一阵,无法呼吸,突然冲破,向天门汹涌,从眼角淌下,入到嘴角——暖暖的,咸咸的,血的味道!那白皙的手指变成了一座山,他像一只压在山下的蚂蚁,他只想即刻买包耗子药,一了百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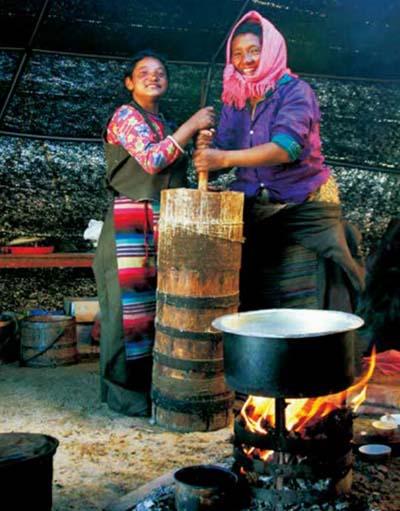
斜眼突然着了魔,嗷嗷嚎叫着扑向一箱箱水果,把它们狠狠地摔向地面,满地的苹果哗啦啦滚了一地,斜眼不甘心,用脚狠狠地踩,死死地踏,想要把整个世界都踩成泥浆。突然脚下一滑,腾空摔在苹果上,他便瘫在苹果上,双手捂着脸——这个大男人,居然哭得像个三岁的孩子失去了父母,没有一线生机。
“咚咚咚”,门被敲响,警察看着斜眼,斜眼缩了缩背,摇摇晃晃站起身,轻手轻脚走过去。帕尔楚站在门外,他的儿子装在帕尔楚藏袍怀里,只露出个头在外面,手里握着一大奶瓶,里面装满奶,正咕叽咕叽地吸吮着。
斜眼拉了一把老婆,跪在帕尔楚身边,有些哽咽:“阿哥——真不知道怎么办啊?!我们两口子风里来雨里去,苦了一辈子,就挣了这么点钱,就算是给你的补偿吧,谁叫我贪点小便宜,把你我都害了!”,说着,斜眼把红布包放到帕尔楚手里。斜眼的泪水夺眶而出:“阿哥,你在这里住多久都可以,你跟我卖水果也可以,我一定让你好好地回家!”。帕尔楚握着钱,一句话也没有。
第二天天还没亮,斜眼和妻子扛起水果默默出门。一整天,眼巴巴地等待著一个个人经过水果摊,一个个人翻来覆去地挑选。饿了,找一些快要腐烂的水果。
傍晚,天空飘起雨,明晃晃的灯泡围满飞蛾,没有一个人走过水果摊,街上偶尔飙过一辆车,旋起冷飕飕的风。
两口子收完摊疲惫地推开门,房里空空荡荡,帕尔楚不在,孩子醒着,居然没哭,手里捣鼓着奶瓶。老婆径直走向孩子,突然大叫:“老李!你快来看看!”,斜眼跑过去,睁大眼——孩子的被盖下躺着一红布包,红布包上有几十个疙瘩,一个都没解开……(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