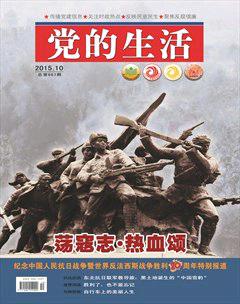父亲的“潜伏”故事
庞怀中
如今车水马龙的肇源县市场院内,在20世纪30年代只有零星的几家煎饼摊、小吃店,其余则是一些住土平房的小户人家。我家的抗战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神秘的“客屋”聚会
1936年,父亲庞振武随所在的蒙古骑兵队调入肇源,改编为警察队,他做内勤。
1937年冬,母亲领着我和妹妹来到肇源,与父亲团聚,在市场院内租住了一间土平房。
住在同一间房对面屋的邻居叫王化清。他性格豪爽,为人正直,与父亲言语投契、志同道合,两人很快成了莫逆之交。
1939年6月,中共北满省委派抗联12支队支队长兼参谋长徐泽民到三肇地区组建抗日救国会。在朋友的引荐下,父亲和王化清一起秘密加入了抗日救国会。王化清担任抗日救国会副会长。
不久,父亲被派到花尔村(今肇源县薄荷台乡)警察分驻所当所长。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为抗日联军打掩护,暗中开展抗日活动。
肇源大十字街北路西的肉食门市部,伪满时是一家前店后厂的大商号——裕昌源,由李文堂和司景荣两家合资经营。股东兼掌柜的李文堂也是抗日救国会会员,在他的商号营业室后面有个规模不大但很幽静清雅的客屋:一铺小炕,一张方桌,几把椅子,专门用来招待外地主顾以及与生意相关的嘉宾喝茶、打牌、洽谈生意。虽然各大商号都设有这样的客屋,可裕昌源的客屋却别有用途——制定抗日行动方案,交流各村屯抗日组织发展情况,汇报侦察到的敌人动态,总结经验教训,布置下步工作。
父亲每次从花尔村回到肇源,都要到裕昌源的客屋参加朋友“聚会”。有两次,我跟父亲去了,见他们几个人先是在麻将桌上码好牌,牌打到半路就停下了,连同一旁“把眼儿”的人都凑到一起,低声说着什么。一旦有外人进来,他们就继续打牌。
我长大以后听母亲说,裕昌源商号的客屋就是东北抗联和肇源抗日救国会的联络点。
抗联活动保护伞
父亲调到花尔村警察分驻所当所长以后,为抗联12支队和管境内各屯的抗日救国会开展活动提供了极大方便,使日伪警特防不胜防。
当时,肇源境内抗联最为活跃、抗日救国会组织发展最为广泛的就是花尔村。村内的后薄荷台、八家子等屯均建起抗日救国会,经常秘密聚会,为我地下党搜集敌伪情报,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发动青壮年参加东北抗联,参军人数最多。
以父亲为所长的花尔村警察分驻所对抗日救国会的活动既不追查,也不上报,还暗地里对抗联给予必要的资助,成为抗日救国会重要的保护伞和挡风墙。
据母亲在世时回忆,当年有一位头戴礼帽、身穿长衫的中年人常到家里来,时间多是凌晨或黄昏后。那人进屋后,父亲就把母亲打发到大门口去望风,发现有人来就赶快回屋报信儿。父亲和那人每次谈话的时间都很短,最多十分钟便匆匆告别。
有一年即将入冬时,那人来我家和父亲密谈几句就走了。随后,父亲马上到薄荷台街面拐角处当地最大的布幌商号福海长买了青斜纹布和棉花,又买了12双棉靰鞡,要母亲赶制了7条棉裤。然后,父亲把这些东西连同平日私藏的一些子弹,送到潜伏在八家子屯的抗联12支队。
参与策划“三肇事件”
1939年冬,我的家人随父亲迁到花尔村的前薄荷台居住,只有我留在肇源国民优级学校念书,在父亲的一位朋友家吃住。
1940年8月的一天,王化清突然找到我说:“你爸捎来信了,让你马上回家。”
我惊讶地询问原因,王化清口气坚定地回答:“不因为啥,就是让你暂时不念了。”第二天,王化清就给我买了一张去薄荷台的客车票,送我回家。
回到家,父亲也没向我说明究竟为何让我退学,只是说:“暂时在家呆着吧。”
当时我并不知道,一场对日伪军警实施重大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酝酿之中。
父亲被捕前后见闻
1940年10月的一天,王化清乘客车从肇源来到薄荷台,与父亲密谈到后半夜。第二天上午8点多,王化清和我父亲在靠窗的桌子两边继续低声交谈,我在一旁听到了只言片语。只听王化清跟我父亲说:“……到时候,队伍从二站过来,你就可以从这边儿打接应……”上午10点左右,王化清又乘客车返回肇源。
1940年11月8日夜里,抗联12支队一举攻占肇源城,这就是震动北满的“三肇事件”。抗联部队70人仅用40分钟就结束了战斗,火烧伪公署,击毙伪滨江省参事官东荣作等11名日本警政要员,打开监狱释放无辜群众100多人。
因为父亲事先知道抗日联军攻打肇州的准确时间和作战方案,所以对进展情况极为关注,一夜没合眼。由于电话线被切断,他不时到屋外看看,盼着有人赶快传来胜利的消息。
第二天,父亲仍没有得到来自肇源方面的准确消息,看到的却是日本关东军的运兵卡车从哈尔滨源源不断地往肇源方向驶去。
原来,“三肇”事件发生后,日伪当局极为震撼,伪滨江省警务厅立刻组织“特别搜查班”前往肇源。他们收买汉奸、叛徒,谋取抗日救国会的人员名单和抗联家属情况,肇源陷入阴森森的白色恐怖之中。
1940年12月4日下午3点左右,我正在警察分所门前玩,突然看到从肇源方向驶来一辆绿篷客车,在分所门前停了下来。车上下来三个人,都穿着青色便服式大皮袄,皮袄的下襟翻毛掖在皮带上,腰间露着手枪。
见这三个神秘的外来人进了屋,我也好奇地跟了进去,看到父亲正坐在办公桌前写着什么。那三个带枪的便衣围住父亲,其中一人冷冷地说:“找你办个案子,马上跟我们走!”
我当时并不知道,父亲已经被捕了,而且是有去无回。
爷爷和母亲对父亲出此意外感到万分难过,可又想不出营救的办法,还担心特务再闯进我家搜查逼供。当天夜里,爷爷对我母亲说:“快看看家里还有啥犯禁的东西没有?”
母亲低声说:“就是在大枕头里缝着一个用秸秆卷着的纸,好像是地照吧,别的没啥了。”
爷爷听了惊恐地说:“快拿出来我看看,是惹祸的就烧了!”
母亲赶紧把大枕头拆开,从中取出一个秸秆纸卷交给我爷爷——她不识字。
母亲后来跟我说,爷爷一看吓得手都哆嗦了。那是一张石印的《会员证》,会长是金策,发证时间是“大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八月”,上面贴有父亲的二寸照片,骑年盖月的宽边方形公章是用篆体字刻的“北满抗日救国总会印”九个字。爷爷明白,这个证一旦落入特务和日本人手里,我父亲是万难活命的,便马上销毁了。
父亲被押解到肇源以后,音信皆无。全家人也不敢打听,只能盼望他无罪开释。哪知道,父亲被捕后没几天即被杀害了!
事后得知,伪滨江省警务厅从哈尔滨派到肇源的特务叶永年,通过奸商刘发、李华英夫妇,采取各种卑鄙手段,获得了抗日救国会人员名单,并按照名单进行大搜捕。我父亲单上有名,自然难逃魔掌。在被捕后的第六天子夜,日本宪兵用两辆军车把包括我父亲在内的19名爱国志士载到三站李家围子前的江面上,推进了冰窟窿。
父亲牺牲时年仅39岁。而这一噩耗直到东北光复,我们家人才得知。
如今,在肇源博物馆中,父亲的照片和事迹陈列在“肇源大地革命英烈展厅”。作为英烈的后人,我们为父亲感到光荣,感到骄傲!
(中共大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肇源博物馆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