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样与正轨:《石渠宝笈》及其纂者创作
艾江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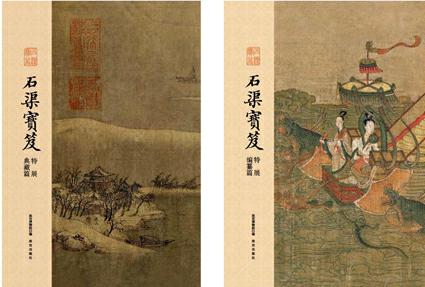
左:“《石渠宝笈》特展”图录之《典藏篇》封面右:“《石渠宝笈》特展”图录之《编纂篇》封面
“几暇怡情”
乾隆九年(1744)二月初十,乾隆的一道上谕拉开了此后绵延70余年、参与者多达31人的《石渠宝笈》初、续、三编的编纂之幕。这部以清宫收藏为基础的大型书画著录,共计收录从魏晋至清初的1.2万多件书画珍品,堪称中国书画著录史上集大成者的巨著。所谓“石渠”,典出《汉书》,本指西汉皇家藏书馆——石渠阁。
“朕于清?之余,偶一批阅,悦心研虑,左图右吏,古人岂其远哉?”上谕的最后一句话,似乎说出了《石渠宝笈》的编纂缘由,不外乎供皇帝本人欣赏。但另一方面,经历顺康雍三朝积累,乾隆内府的书画收藏已达顶峰,这一年又恰逢清朝入关100年,《石渠宝笈》的编纂便不仅是悬夸博古,实为彰显其文治武功。
在此之前,乾隆已敕令臣工编纂专载释道书画的《秘殿珠林》初编。《石渠宝笈》初编始于乾隆九年二月,成于乾隆十年十月,共有张照、董邦达等11人参与。乾隆五十六年(1791)正月到乾隆五十八年夏至,续编由王杰、董诰等10人编纂而成。嘉庆二十年(1815),嘉庆继承父亲遗志,将2000多件新增书画编入三编。这些作品,一方面来自新进宫的私人收藏,还有不少搜罗自废弃不用的行宫别苑。编纂队伍由英和、黄钺等10人组成。
《石渠宝笈》的编纂者除章嘉胡土克图外,其余均为进士出身,这些人多以词林起家,并已出任高官,兼具书画与鉴赏才华,有的本身就是有名的藏家,比如张照、张若霭、董邦达、英和、黄钺等人,有的还长于书画理论,甚至出有书画碑帖方面的专著,比如张照的《天瓶斋书画题跋》,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与《石渠随笔》,沈初的《西清笔记》,以及胡敬的《西清札记》等。他们中间有17人的作品入选《石渠宝笈》,其中如张照、励宗万、张若霭、陈邦彦、董邦达这样的书画特出者,作品遍及《石渠宝笈》初、续、三编。
能够入选初编、续编编纂者之列的书家与画家,正如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员杨丹霞所说,都是深受乾隆皇帝喜欢的一派。某种程度上,理解他们的创作,便足以了解乾隆的艺术趣味及其一朝的所谓艺术正统。而论及影响之远,受誉之隆,31人中莫过于奠立乾隆一朝官样书风、为乾隆主要代笔者的书法家张照,还有被称为“三董相承、画家正轨”的山水画大家董邦达。
官样书风
张照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的进士,参与《石渠宝笈》初编的编纂工作时,已是53岁的三朝重臣。在雍正十三年(1735)之前,他的官宦生涯非常顺利,进士高中后,从庶吉士、侍讲学士、刑部侍郎、左都御史,一路迁至刑部尚书。1735年5月,他被任命为抚定苗疆大臣后,由于平定无功,更涉挟私弹劾,被夺职下狱,乾隆元年(1736)廷议当斩。乾隆怜其才华,将他特赦出狱,随后更让他步步官复原职。
张照是个艺术全才,能诗善画,通晓音律,精通鉴赏,甚至还编过杂剧,当然,他最擅长的还是书法。康雍乾三朝都很推重晚明书法家董其昌,时风所及,张照早年在其舅舅、书法家王鸿绪的指引下,从临摹“用笔清淡、结体内敛、章法虚空”的董其昌入手。后来又学米芾、赵孟頫,逐渐成为擅长行楷、自具面目的书法大家,颇负时名。其楷书秀媚婉丽,平正圆润,是清代“馆阁体”的代表。
也正因此,张照成为乾隆的主要代笔者与艺术合作者。2015年9月,在故宫博物院的“石渠宝笈书画特展”上,在乾隆御题的许多书画后面,都有张照奉命撰写的题跋与题诗。同时展出的还有他被录入《石渠宝笈》三编的《临王献之帖卷》,看起来意兴飞扬,别有一番天真之味。据统计,张照的作品入选《石渠宝笈》著录的有167件之多。
乾隆十年正月,在编纂《石渠宝笈》初编十几个月后,张照在奔父丧途中因病去世。乾隆四十四年(1779),在张照去世34年后,乾隆念及旧日臣工,将他与梁诗正、汪由敦、钱陈群、沈德潜称为“五词臣”,并写诗纪念:“书有米之雄,而无米之略,复有董之整,而无董之弱,羲之后一个,舍照谁能若,即今观其迹,宛似成于作,精神贯注深,非人所能学。”乾隆对这位书家的喜爱超乎寻常,以至于后世一些论者颇有不满,称皇帝对张照书法的偏好,正如“欲一手掩尽天下目”。
事实上,即使在当时,尽管时名盛大,人们对张照书法的评价却并不一致。《石渠宝笈》续编的编纂者之一阮元在《石渠随笔》中便称张照尽管为本朝一大家,功力可佩,但竟不能脱俗。诟病之处,仍在其书法的过于圆熟和缺乏气韵。另一方面,不难想见,当张照的书法一纸风行,处处见于各种敕书诏令以及士子笔端时,不俗亦难。
不论怎样,张照终以奠立一朝书风名世,正如启功在《论述绝句》中所做的分析:“有清八法,康、雍时初尚董派,乃沿晚明物论也。张照崛兴,以颜米植基,泽以董赵,遂成乾隆一朝官样书风。盖其政成财阜,发于文艺,但贵四平八稳。而成法之中,又必微存变化之致,始不流为印版排算之死模样。”

《石渠宝笈》续编
画家正轨
巧合的是,同为《石渠宝笈》初编纂者的董邦达,在年轻时便受到张照的欣赏与提携,随后两人共侍内廷,分别成为最受乾隆喜爱的当朝书家与画家。
董邦达是雍正十一年(1733)的进士,在乾隆二年(1737)授编修,后来官至礼部尚书。与张照类似,董邦达的艺术造诣也很全面,长于诗歌,书画俱精,尤以墨笔山水画见长。比张照幸运的是,他宦途顺利,并未经历太多起伏。
有意思的是,董邦达的儿子董诰也是书画名家,父子俩合称“大小董”。董诰累官至东阁大学士、太子太傅,还是《石渠宝笈》续编的纂者,与父亲比起来,他的画风更趋工稳严谨。两人都是名臣与书画名家,于艺术、政治二途各有名重,一般来说,人们更愿把“大董”的身份排序为名画家、书法家、名臣,“小董”的排序则为名臣、书画家。
董邦达的山水画远取五代董源、巨然还有元人黄公望,近学明人董其昌,善用枯笔,“勾勒皴擦,多具逸致”。据杨丹霞统计,《石渠宝笈》收录董邦达的作品多达202件(不含合作),可惜多数已然散佚。他传世的画作多为水墨山水,设色山水一般也喜欢用“浅绛色”,青绿着色的山水则流传甚少。学者邱雯曾经分析,与董源山水擅绘南京一带的浑厚华滋、董其昌山水表现上海松江一带的清润宁和,浙江富阳人董邦达更喜欢描绘浙江富阳、杭州一带的秀美景致,他称得上绘画史上描摹西湖最多的画家,多数作品都与西湖一带的湖光山色有关。录入《石渠宝笈》续编的《西湖四十景》在系列作品中最有名气,该图共分4册40幅,每幅尺寸均为“纵九寸八分,横九寸五分”,全面细致地描绘了西湖诸景。
乾隆对董邦达的山水画推崇备至,称其繁简皆佳,运转自如,曾写诗将其与南宗大师董源、董其昌并驾齐驱:“吾于达也无间然,丰不觉繁俭不欠。前称北苑(董源)后香光(董其昌),艺林都被卿家占。”
乾隆十一年(1746),乾隆集齐晋代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贴》与王珣的《伯远帖》,设立“三希堂”,并令董邦达绘制《三希堂记意图》,这也是乾隆第一个书斋名号图。乾隆喜欢让自己最欣赏的臣工在一些古代巨迹的本幅或副页、尾纸上进行书画创作,“三希堂”三帖之中,除了张若霭奉令在《快雪时晴帖》后作梅花图外,其余两帖后面的山水画作都由董邦达所作。在“《石渠宝笈》书画特展”上,一进武英殿的展厅就可以看到《伯远帖》与其后尾纸上董邦达以“悠游”为意奉命创作的山水,画卷中,在巨石林立怪树旁逸的大江边上,一人邈然远望。
由于深受乾隆厚爱,董邦达在70岁时得乾隆钦赐,可以在紫禁城骑马入朝。三年之后,他以年老多病请辞引归,乾隆不舍其离开,给他放假安心调养,但并不同意他解职。不久,董邦达病逝,乾隆又为其亲撰碑文。
犹如张照所确立的一代书风,继清初王原祁之后,董邦达引领了清朝中期的山水画风,正如《清史稿·董邦达传》所称:“邦达工山水,苍逸古厚。论者谓三董相承,为画家正轨,曰源、其昌、邦达也。”

1. 唐 《明皇幸蜀图》(藏于“台北故宫”)2. 南唐 赵幹《江行初雪图》(藏于“台北故宫”)3. 北宋 崔白《双喜图》(藏于“台北故宫”)4. 宋 赵佶《听琴图轴》(局部)(藏于北京故宫)5. 东晋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局部,藏于北京故宫)6. 宋 易元吉《猴猫图》(藏于“台北故宫”)
三联生活周刊2015年4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