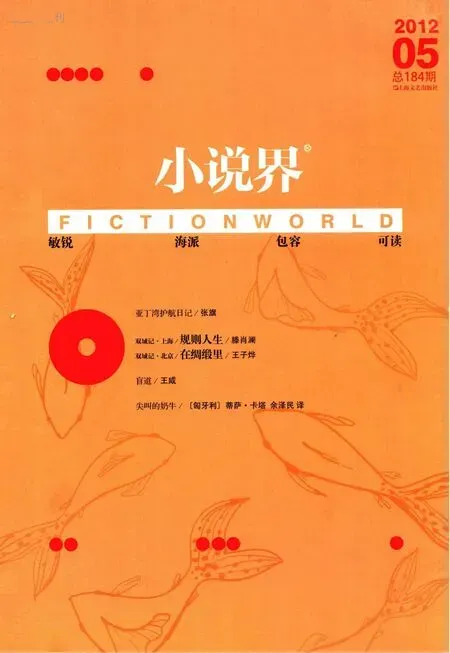黑墙
简平
我在潇潇的竹篱笆墙的长影中走回那个晚上。细碎的月光如同雨点从密致的隙缝里泻下。秋风已凉,我却追不回那永远消失的背影,路灯飘忽的微光在我心里窸窣不绝。
一九六六丙午马年。那本是一个心惊惶然的秋日,可我却将那一天当作了节日。那天是我十岁的生日。外面从初夏开始便已云水怒,风雷激,喧嚣声逐日高涨。虽说暑热未消,但我们家的窗帘从来没有卷起过,我爸我妈整日坐在帘下愁眉相对。我并不太在意这些,我甚至溜出家门,去往街上,跟着人潮奔跑,欢叫,争抢那些从飞机上撒下的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传单。这是我十岁的生日,我缠着我爸我妈送我生日礼物,并希望在切开生日蛋糕的时候,我姐会为我在钢琴上弹一曲《祝你生日快乐》。我真的不知道,其实,那一天并不是什么节日。
虽已入秋,可蝉鸣未退。屋里的台式风扇在转头的时候总是摇摇晃晃,发出吱吱的声响。每一次的摇晃,好像都让我爸我妈心惊肉跳。我在纠缠中发现他们心神不定,并且在悄悄地做着什么准备,我爸把几本线装书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定下那天晚上趁着夜色逃离这座城市,去北方一个小城的亲戚家暂避风头。我爸是研究明清史的大学教授,我不知道什么叫明清史,我以为历史就是很长很长的日子,只有一个朝代,从古至今,没有任何的变化。那时,我爸已得到风声,那些天将会有造反派前来抄家,极有可能他会被投入关押知识分子“臭老九”的“牛棚”。我妈决定陪伴我爸踏上遥远的不知未来的路程,生死与共。他们想把我和我姐留下,他们觉得如果带上我们,处境会更加危险,也更没有希望。他们还相信大我八岁的我姐会照顾好我这个小弟。这是一个窗帘后的密谋,但我爸我妈终究舍不得我这个那天刚好十岁的男孩,所以,他们差遣我姐去外面看看能否买到一个生日蛋糕。其实,这是一件根本无望的事情。
就在我姐刚要打开房门的时候,隆隆的轰鸣声铺天盖地滚滚而来,口号声、脚步声此起彼伏,又重又急。刹那间,屋门洞开,窗帘被扯到地上,黑压压的人群仿若爆发的山洪涌来。他们中有我爸的学生,不久前还在我家喝茶聊天,我爸还对我说,以后要像他们一样虚心虔诚地拜师做学问。现在,他们将一顶高高尖尖的纸帽子套在我爸头上,一群女生则围住我妈,用剪刀去剪她并不很长的头发。我躲在角落,惊恐地看着这一切。一个穿工装的大汉站在一边,露出满意的微笑。我姐突破人群向我跑来,犹如一只逆流中颠簸的小舟。她一下子蒙住了我的眼睛。
我爸我妈在震天动地的声浪中被押走了。潮水退去,只剩下一地被撕烂的线装书。我和我姐相拥着呜呜抽泣,泪珠滴落在碎纸片上,漾开了上边被践踏时留下的污浊的脚印。这一天原本是我的生日,我的节日,如今却成了我家的受难日,我爸我妈在劫难逃,而我注定了即使点燃生日蜡烛,那摇曳不安的烛火也会在风中熄灭。
那一夜,我没有看到月亮升起来。云层深厚,不断地遮掩住欲露不露的月光,黑影幢幢。我和我姐睡上下铺,我在上铺趴在床边不时地看看我姐。我姐躺在床上,目光凄迷而散淡,不时有泪珠成串地滚落。
我偷偷地爬起来,坐到窗前。窗外是另一排房子,先前每到夜晚,总有灯火从每一扇窗口泻出来,那时,橙黄色的白炽灯已经少了,流行的是石灰墙面一般煞白的日光灯。因为节电,平时很少有人家开四十瓦的,只开十二瓦,厕所里更只有三瓦,且那灯光是绿色的,如同幽幽鬼火。那夜,那些窗口几乎没有灯光,黑漆漆一片。
忽然,我看到对面的窗口前站着一个人,他看上去只比我姐稍大一些。这不是他第一次站在窗前望我们。他跟我姐一样会弹钢琴,有一次我姐弹完琴之后,我看见他站在窗口一直朝我们家张望。我没跟我爸我妈说,但悄悄地跟我姐说了,我姐顿时满脸通红,让我千万不要瞎说。我不知道我瞎说了什么。现在,我看着他站在窗前,黑暗中形单影只。突然,他打开了四十瓦的日光灯,白光晃眼,灯下的人影反显模糊绰约。我看不清他的脸廓,但可以清晰地断定他看过来的眼睛是棕黑色的,眼白干净。我默默地看着他。这是两双没有交集的眼睛,山水无逢。他似乎还在等待着什么,一动不动地站立着。许久过后,他离开了窗口,不一会儿,便像先前那样,有溪水般的钢琴声从那扇窗口淙淙流出。夏天以后,我已很久没再听过他的琴声了。
这琴声如泣如诉,像是一种召唤。我掉头看向我姐,她惊慌地瞪大了双眼。这琴声确实让人魂飞魄散,因为与当下激昂的进行曲和红色的语录歌实在格格不入,如遭人投告,必将横祸加身。我姐怔怔地听了一会儿,便害怕地将脸埋进了枕头深处。忐忑中,我重又回到窗前,这时琴声戛然而止,他又出现在了窗口,定定地站着,无声无息。这时我才想到,他这样做,是不是希望我们有所回应呢?
我沉沉地睡去,不知道他是何时离开的,也不知道我姐竟是一夜无眠。
我姐比我更像惊弓之鸟。白天,她不让我在房间里走动,而是把我关在厨房间里。的确,敞开的没有帘子的窗户,随时都可能再次涌来洪水急浪。时钟走得那么慢,一日漫长。虽然心里慌乱,但外面的敲锣打鼓声还是那样地吸引我,终于,我趁我姐不备,溜出门去。一列游街示众的大批判队伍走来,我随着人潮跑去旁观,还挥舞手臂跟着呼喊口号,一时间忘却了曾在口号声中瑟瑟打抖的我爸我妈,甚至还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感。我也想不起来此时正焦急地满街寻找我的姐姐,她不安的泪水与骤然而至的秋雨相叠相合,洇入大地。
我冒雨逃回家来。这时,夜幕已降,我姐一边数落我一边为我端上热粥。她端碗的手那么好看,十指纤纤。她梳着两条并不细长的小辫,亭亭玉立,宛如天仙。我爸我妈本来也让我跟着我姐学弹钢琴,但我坚决不肯,我的理由很充分,我姐将来是位钢琴家,我最大的理想和愿望是在我姐走上被追光灯打亮的舞台时,为她掀开沉沉的琴盖。
我坐到窗边,不曾想昨晚的一幕重又出现。那人站在对面窗口,定定地朝我们这里看着。我告诉了我姐。我姐一听,急急忙忙关掉了开着的小灯。他一定注意到了,就像是一种对话,他再次打开了日光灯。这回应该是十二瓦的,光色淡了,却多了几许柔和。我姐躲到我的背后,看向对面的窗口,我听到了我姐扑通扑通的心跳。我们一动不动,对面白光如瀑,可以看见气息的流动。
许久,对面的灯光倏然熄灭。
我姐很轻很轻地叹了一声。
那天夜里,我没有睡好,似乎看到对面的窗口灯如天光,他还是那么站着,纹丝不动,恍然间,变成了一朵灯笼中闪烁的芯火。
不知不觉,天亮了。
猛地,我姐用力摇醒我,并示意我听门外的声音。我竖起耳朵,听到了很轻很轻的敲门声,那声音虽小,但很有些急促。我姐拉过被子,整个地盖住我,然后前去开门。
我悄悄地将头探出来。
我惊讶地看到对面窗口的那个人站在我家门口。我姐没有让他进来。他急促地说道,他是来向我们通报消息的,那天带队来我家造反的身穿工装的大汉叫洪湖水,是工宣队队长,先前是他家邻居,当了造反派后抢占了资本家的一间大房,现在搬过去了。他说,那个地方他认得,有一排黑色的竹篱笆墙,因为那个资本家是他家的亲戚。他还说,洪湖水可能知道我爸我妈的下落,可以到他那里去打听一下。我姐听着,没有答话。他就那么站着,两只手一会儿放在前面,一会儿放在后面,好像不管怎样都是多余的,不知该搁在哪里才好。我姐非但不说话,还一直垂着眼睛,倒是我清楚地看见了他的眼里有些羞怯而慌张的东西,但眼白如雪。
秋雨暂歇。我姐又把我关在了厨房间里,她让我保证在她出去的那段时间里绝不偷跑到外面。我问我姐,你去哪里?我姐说,去那排有黑篱笆墙的地方。我说,我要跟你一起去。我姐坚决地摇了摇头。她转身而去,她的背影虽然单薄瘦弱,却像一枝春柳,袅袅娜娜,舒展而轻盈。
我哪里放得下我姐?她才出门一会儿,我便悄悄地跟了过去。我怕我姐看到,只远远地跟着,不如影相随。忽然,有个身影一闪而过。我屏住呼吸,那个身影忽而快走,忽而放慢脚步,一会儿躲到电线杆后,一会儿藏进树影里。我再仔细看去,原来是我家对面的那个人,他也在后面跟着我姐。
我拉大距离,跟在了他的身后。
前面就是那排黑篱笆墙了。如今,黑色的竹篱笆上白色森然,贴满了大字报,一些没有糊牢的纸角掀起来,在风中飘摇。
黑篱笆墙里是一栋西式洋房。由于那洋房周围有着很大的草坪,黑篱笆墙就显得又深又长。我看见我姐抖抖索索地站在墙外,然后大声地喊着洪师傅洪师傅。这时,从洋房里走出一个身穿工装的人来,他的手臂上套着红卫兵的袖章,跟洪湖水一样有着壮壮的身子。但他不是洪湖水,他是洪湖水的儿子洪缨枪。当然,这名字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洪缨枪跟我家对面的那个人一般大的年龄,但他们完全不一样,他嘴里叼着香烟,两手叉腰,不停地晃着腿。因我没在近处,而且我姐背对着我,我没有听到我姐说的话,但洪缨枪的声音却随阵阵秋风传入我耳。他不无得意地说,这事归他爸管,他会问他爸的,问到后就会告诉我姐,甚至可以带我姐去看我爸我妈。我姐不住地点头。这时,我看到洪缨枪盯着我姐的眼神里喷出一股烈焰……火势如此凶猛,我却直打冷战。
我四处寻找那个尾随而来的人,他躲在黑篱笆墙那些在风中翻飞的大字报中,领袖的话覆盖住了他:“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我拼命地奔跑着,耳边风声萧萧,我得赶在我姐之前回到家里。我躲回厨房间,听着门外的声响。可是,等了很久,还没听见我姐的脚步声。我忍不住回到屋里站在窗口,马上看到了对面窗口站立着的那个人。他与我对视着,有些喘息,还露出一丝羞涩的微笑。
那天晚上,我姐第一次坐到了窗前。
对面,窗前也坐着他。
秋虫唧唧,月影摇曳。
他离去了。可只一会儿,溪水般的钢琴声从那扇窗口流了过来。我姐这次没有仓皇而逃,她坐在那里静静地听着,直到曲终。
夜色在琴声中落定。
第二天,他又来敲门了,询问我姐昨天去黑篱笆墙那边的情况。他说,如果没有回音,那就再去,那个洪湖水是个很有权力的人,只要他点头,是可以见到被关押的我爸我妈的。不过,他说要当心那个洪缨枪,那可是个小流氓。
他把两只手背在身后,说完那些话后,他把手往前一伸,原来一手一个小袋。他说,一袋是炒麦粉,一袋是冰糖。我姐坚决不要。他尴尬地站在那里,连耳朵根都发红了。
我姐和他一个站在门里,一个站在门外。
突然,一个壮汉仿若从天而降,一把夺过那两个小袋,往后扔去。
他大声喊道,洪缨枪,你想干什么?
洪缨枪猛地将他推到一边,我还想问你干什么呢!
我姐吓得浑身发抖,砰地一下关上了房门。
洪缨枪拍着门,扔下一串话来:你爸你妈的事情放心好了,我已经跟我爸说过了,以后,我会罩着你的,你就跟着我,谁也别想打你的主意!
我把耳朵贴在门上,那些话渐渐地飘远,晃晃荡荡,荡荡晃晃。
我走到窗边,看到他在对面的窗口对我做着手势,好像是告诉我洪缨枪已经不在了,让我打开房门。我姐想阻止我,但我向她摆摆手,表示不用害怕。我开了门,看到那两袋被洪缨枪扔掉的东西依旧放在门前。
我回到窗口举起袋子,向着对面挥啊挥啊。我说不出来为什么,但我真的很开心。
我爸我妈计划出逃的时候,给我姐留了一张存折。这天,她想去银行取一些钱出来,不然,我们就揭不开锅了。她穿上一件很厚的衣服,将那本存折小心翼翼地放进内衣的口袋。她还是想把我关进厨房间,但我跟她说,我一定要去,就算不保护你也要保护那些钱。我姐笑了。我姐笑的时候,两靥灿若桃花,熠熠生辉,天色为之一亮。
我和我姐走到银行,这才发现银行的人都去闹革命了,门上贴有布告,说是营业停止,革命不止。我姐着急起来,来回踱着,一个趔趄竟从银行门前的台阶上摔了下去。这时刚好有一架撒传单的飞机从空中飞过,瞬间人潮涌至,人们仰着头奔跑着,欢呼着,根本没有看到摔倒在地的我姐。眼看着我姐要被汹涌的人流淹没,我拼命大叫着去拉我姐,可我的叫声如此微小,我的臂力如此孱弱。绝望之时,对面窗口的那个人冲了过来,他弓起身子使劲用后背抵住黑压压的人群,他向我姐伸出手去,奋力将她从地上拉起来,而后突破重围。
我姐脸色煞白,气喘吁吁,身体软软地歪在一边。我大哭起来,不断地叫着姐姐姐姐。他说不行,得去医院。他蹲下身来,让我把我姐的双手搭到他肩上,背起我姐飞跑起来。渐渐地,我姐呼吸有些顺畅了,她睁开眼睛,看到自己被驮在他背上,连连直叫停下来停下来。他收拢脚步,将我姐轻轻放下。他问我姐要紧不,我姐说,我们回家吧。
这时一个壮汉将一辆自行车横挡在我们面前。
洪缨枪朝他紧逼过去,嘴里叫道,黑小子,谁让你把她驮到这里来啦?洪缨枪抡起拳头朝他挥去,一下,一下,又一下,他转着圈,被打倒在地。洪缨枪一脚踏在他的背上,从口袋里掏出“红宝书”,大声说道:最高指示,要将一切反动派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洪缨枪回头对惊恐得不知所措的我姐说,你爸你妈的事情放心吧,我明天就带你去见他们!走,我送你回去!他一边说着,一边将呆若木鸡的我姐一把抱到他的自行车前档上,飞车而去。我看见他将自己整个人前倾着,紧紧地压到我姐身上。
对面窗口那人从地上爬起来,原本清秀的脸已是鼻青眼肿。我怯怯地走过去,拉住他的手。他牵着我走着,一路上没有说话,鼻血嘀嗒嘀嗒地落了一地。
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姐显得神思恍惚。她告诉我说,洪缨枪让她明天下午先去他家里,然后他带她去见我爸我妈。我问,为什么先要去他家里呢?我姐茫然地摇摇头。一会儿,我姐问我对面的那个人怎样了,我说他流了鼻血,眼睛乌青。我姐用手捂住眼睛,泪水从指缝间滑落。
晚上,我姐不让我开灯,她摸黑坐到久违的钢琴前,掀开琴盖,默默地坐了很久很久。最后,她把她的纤纤十指搁到琴键上,顿时,溪水叮咚,汩汩流淌。对面的窗口立刻亮起了灯光,那是四十瓦的日光灯,白光耀眼,照彻夜空。
第二天,一早就开始下雨了,雨丝倾斜,一如愁绪。
我姐不安地在屋里来回走动,她不断地告诫我,这次一定要听话,不能跟去,因为那个洪缨枪说了,如果发现有任何人跟着,就不带她去看我爸我妈了。我答应她不跟过去,因为我要让我姐能够见到我爸我妈。可是,我姐却像不相信似的还是不断地要我保证,我委屈地哭了起来。
下午两点多钟,我姐出门了,临走前,她把那张存折缝进了我的衣服口袋。她走出门的那一刻,不知为什么,我害怕得要命,我拉住她的手臂说,你早点回来啊,我在厨房间里等你!
那天,我乖乖地待在厨房间。一直到夜幕完全将我罩住,我姐还没有回来。我又冷又饿,我一直一直地在心里说,姐,你快回来吧快回来吧,一直到沉沉睡去。我梦见我姐去看我爸我妈了,他们在一间很小很小的黑屋子里,我姐跟我爸我妈说,今天我不回去了,就跟你们在一起。
这是我记得的第一个完整的梦,这也是我整个童年的唯一的梦,所有的梦。
天蒙蒙亮的时候,一阵敲门声将我惊醒了。
我打开房门,见是对面那个满脸青肿的人。他忽然哭出声来。一个跟我姐一样大的人在我面前痛哭,让我手足无措。他抽抽嗒嗒地告诉我,我姐被洪缨枪给玷污了,而且,我姐根本没有见到我爸我妈,洪缨枪在玷污了我姐后才跟她说,我爸我妈已经在被关押的屋子里上吊自尽。我姐从那排黑色的竹篱笆墙里走了出来,一直走到江边,走下江堤……
他猛地跪倒在地,反反复复地说,我真后悔,我怎么那么愚蠢,会让她去找那个流氓!他边说边哭着,迟迟不肯起来。
从那天晚上开始,我每天都走在我姐走过的那段漫长的路上,从黑篱笆墙到江边再到江堤。那是一条每每让我窒息的长路。我跟着我姐,踏着篱笆墙的长影,踏着细碎的月光,踏着已凉的秋风。我总想着我姐走在路上的时候会想些什么。她一定会想到我爸我妈,一定会想到我。我相信,她也一定会想到对面窗口那个跟她一样会弹钢琴的人。但她一定不会去想那个洪缨枪,当然,我也不会去想,我和我姐都喜欢像琴键一般的黑白分明,而魔鬼的脸是模糊不清的。
飘忽的路灯窸窸窣窣,那排黑色的竹篱笆墙透出星星点点的微光,投射于我姐永远消失的背影。
我一次又一次地泪流满面,掉下的泪珠打在琴键上,敲出叮咚的音乐。
溪水流淌,汇入浩淼无界的江河。柳树在每个寒冬过后的春日兀自爆出嫩黄嫩绿。我姐的纤纤十指在钢琴上曼妙起舞。
——洪湖凤舟